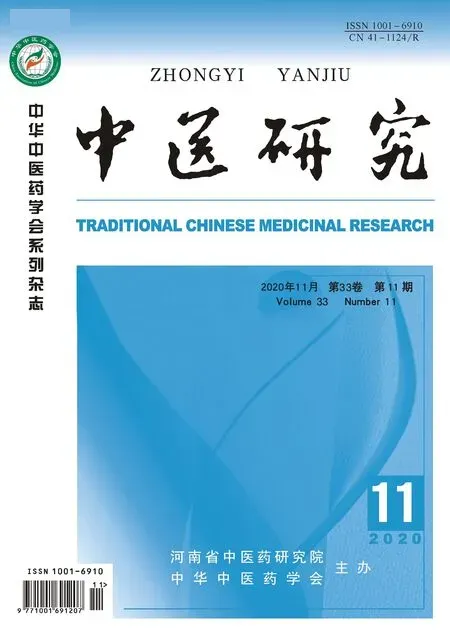李東垣學術思想及其用藥規律探析*
袁利梅,李榮立,張曉娜,孫玉信
(1.河南中醫藥大學針灸推拿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 2.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 河南 鄭州 450008; 3.鄭東新區白沙鎮衛生院,河南 鄭州 451464)
李東垣,字明之,晚號東垣老人,宋金時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為金代著名的醫學家, 有《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蘭室秘藏》《醫學發明》《活法機要》及《東垣先生試效方》等多部著作。現就其主要學術思想及用藥規律做如下探討。
1 脾胃為元氣之本
李東垣認為脾胃為元氣之本,與疾病發生與否關系密切,如《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曰:“真氣又名元氣,乃先身生之精氣也,非胃氣不能滋之。”他認為人之所以發病,是因為脾胃衰弱,不能滋生元氣,元氣失充,虧損所致。《脾胃虛實傳變論》[1]提出:“元氣之充足,皆有脾胃之氣無所傷,而后能滋養元氣;若胃氣之本弱,飲食自倍,則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由所生也。”其因此提出重視脾胃學說,著有代表作《脾胃論》。他在此書中提出脾胃病的五證五法,即胃病其脈緩,怠惰嗜臥,四肢不收,或大便泄瀉,治從平胃散;脾胃五行屬土,肺五行屬金,土生金,脾胃虧虛,無以生金,現肺脾氣虛,癥見自汗、四肢發熱,或大便泄瀉,或皮毛枯槁、發脫落,治從黃芪建中湯。《黃帝內經》云:“脾胃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若脾胃虧虛,氣血生化乏源,癥見脈虛而血弱,于四物湯中摘一味或二味,以本顯證中加之;或脾胃真氣虛弱,氣短脈弱,治從四君子湯;若脾虛無以化濕,濕邪下注致下焦氣化失司,癥見或渴,或小便閉澀、赤黃而少,從五苓散去桂,摘一二味加正藥中以健脾化濕。其在《蘭室秘藏·婦人門·經漏不止有三論》[2]云:“脾胃為氣血陰陽之根蒂也。”若“脾胃一傷,五亂互作……元氣不能運用,故四肢困怠”,可見元氣與脾胃關系密切。因此,李東垣提出了“病從脾胃所生,養生當實元氣”論。
2 脾胃內傷,百病由生
李東垣在其師張元素“運氣不濟,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學術思想及《黃帝內經》理論的影響下,結合其所生活的社會背景,提出了“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觀點,并不斷總結完善,形成了其獨特的學術理論——內傷脾胃論。如《脾胃盛衰論》曰:“飲食不節則胃病,胃病則氣短精神少而生大熱……胃病則脾無所稟受,故亦從而病焉。”“脾胃虛弱,陽氣不能生長,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臟之氣不生。”在此理論指導下,李東垣創立了一系列治療脾胃病的方劑,如黃芪人參湯、調中益氣湯、升陽湯等。其中以補中益氣湯為代表,此方中黃芪用量最多,為君藥,發揮健脾補肺、益氣固表、肥腠理不令自汗以損其元氣之功。人參、黃芪、炙甘草、白術補氣健脾燥濕,共奏培土生金之功。“諸陽氣根于陰血中”,《醫學真傳·氣血》[3]云:“人之一身,皆氣血之所循行,氣非血不和,血非氣不運,故曰:‘氣主煦之,血主濡之。’”這種關系概況為“氣為血帥,血為氣母”,方中當歸養營陰和血脈以斂陽氣。佐以陳皮導滯氣、益元氣,預防參、芪壅滯之弊。同時以少量升麻、柴胡行春升之令、行少陽之氣上升,協助君藥以升提下陷之中氣。諸藥合用,共奏健脾補氣、升陽舉陷之功,使氣虛者得補、氣陷者得升、氣虛發熱者得此甘溫益氣而除之,同時發揮令脾氣充足、中焦升降有序、氣機暢達之效。此方被后世醫家奉為“甘溫除大熱法”的代表方劑,體現了李東垣“補脾胃升清陽”的治療思想[4]。
3 脾胃為升降之樞紐
李東垣認為自然界是不斷運動變化的,如《天地陰陽生殺之理在升降沉浮之間論》曰:“履端于始,序則不衍。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如環無端,運化萬物,其實一氣也。”而人體精氣的運行賴于居于中焦的脾胃所主宰,即“脾胃為人體氣機升降之樞紐”脾以升為健,胃以降為和[5]。如其曰:“蓋胃為水谷之海,飲食入胃,而精氣先輸脾歸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養周身,而清氣天者也;升已而下輸膀胱,行秋冬之令,為傳化為糟粕,轉味而出,乃濁音為地者也。”由此可見脾主升清,胃主降濁。此與《素問·經脈別論篇》所言:“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合于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為常也”同為一理。《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曰:“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云,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云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臟;清陽實四肢,濁陰歸六府。”意以陰陽升降之道展示氣候變化、人體機能營運治理。李東垣在此理論指導之下,提出了“夫脾者,陰土也,至陰之氣,主靜而不動;胃者,陽土也,主動而不息。陽氣在于地下,乃能生化萬物。故五運在上,六氣在下。其脾長一尺,掩太倉,太倉者,胃之上口也。脾受胃稟,乃能熏蒸腐熟五谷者也”“若胃氣一虛,脾無所稟受,則四臟及經絡皆病”等理論。可見脾胃為臟腑氣機升降的軸心,它臟皆賴之以行其用,正如其在《內外傷辨惑論》[6]所言:“胃虛不能上行,則肺氣無所養,故少氣;衛氣既虛,不能寒也。下行乘腎肝助火為毒,則陰分氣衰血虧,故寒熱少氣。胃氣既病,元氣不充,則不能上升水谷之氣于肺,故肺虛氣少;脾胃氣陷,水濕內停下溜于肝腎之間,陰火內郁而見寒熱;陰火為毒,又可內灼耗傷津血。更有甚者,胃氣下溜,陰火升騰,清濁相干可見“五臟氣皆亂”。倘若胃氣升而不降,“若天火在上,地水在下,則是天地不交,陰陽不相輔也,是萬物之道,大易之理絕滅矣”,即是胃氣升而不降所致病的體現[7]。
4 用藥規律
4.1 善用甘溫補益,注重升陽益氣
李東垣生活在戰火不斷、民不聊生的南宋北金戰亂年代,人民居無定所,饑飽無常,加之精神緊張致使脾胃多損。故其立法以補益虧損為義,潛方用藥多用甘溫補益之品,如黃芪、人參、炙甘草等。高氏等統計其用藥規律發現:行氣藥所占比例為13.15%,而補虛類藥物比例則達25.32%,補氣藥占到補虛藥使用頻數的73.08%之多。這種藥物之間的比例關系與李東垣代表方劑補中益氣湯、升陽益胃湯等藥物組成相似。以藥測證可見:李東垣論治脾胃病以虛損為主,氣機不暢和濕濁阻滯為次[8]。同時李東垣亦認為“脾胃虛弱、元氣不足是四臟病脾胃病之根本”,在此基礎有“至而不至……所勝妄行,所生受病,所不勝乘之”等的病機變化[9]。如:“至而不至者,謂從后來者為虛邪,心與小腸來乘脾胃也”而成“心之脾胃病”,以柴胡為君,臣以升麻、黃芪、人參、炙甘草的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即為“心之脾胃病”而設。“肺之脾胃病”則為“脾胃之虛,倦惰嗜臥,四肢不收……兼見肺病,灑淅惡寒,慘慘不樂,面色惡而不和,乃陽氣不伸故也”,創立升陽益胃之法之升陽益胃湯,方中用人參、白術、白芍補肺氣,為母氣不足損及子病之范疇。“肝之脾胃病”則為“右關脈緩而弱,兼見弦脈,或見四肢滿閉,淋溲便難,轉筋一二證”,乃所勝乘之所為,主要病機為肝木克脾土,治以補氣升陽、理氣調中之調中益氣湯,方中黃芪量大為君,臣以人參、甘草、蒼術等本經藥,以助春夏之氣生長;因中虛下溜,故用升麻、柴胡升提清氣,以起到“從陰引陽”之意;陳皮、木香理氣醒脾,以起“補而不滯”之用。諸藥合用,共奏益氣升陽、調中醒脾之效。可見李東垣治療“肝之脾胃病”是以補氣升陽為要,兼疏肝理氣[10]。“腎之脾胃病”為所不勝乘之者,即水乘木之妄行反來侮土。李東垣用方神圣復氣湯治水來侮土之“腎之脾胃病”,方用辛熱之附子、干姜溫補脾腎陽氣,助水氣化;配以黃芪、人參、炙甘草等健脾補氣之品溫振中州;用陳皮、肉豆蔻芳香理氣;配合升發陽氣、助長脾陽之用的風類藥,如羌活、柴胡、升麻、防風、藁本等,體現了“風能壯氣”之思想[9]。由上可見,李東垣治療疾病尤重補益脾胃、升舉陽氣。
4.2 屢用風藥
李東垣在《黃帝內經》及張仲景少陽證的啟發下,創立了少陽春升論。其在《脾胃論·胃虛臟腑經絡皆無所受而俱病論》中言:“甲膽風也,溫也,主化生周身之氣血。”又云:“感天地之風氣而生甲膽……此實父氣無形也。”從而確立了“春氣升則萬化安,故膽氣春升,則余臟從之”的理論(《脾胃論·脾胃虛實傳變論》)。其在潛方用藥中善用羌活、升麻、防風、柴胡等風藥。他認為風藥有助脾胃氣機生發之用;風藥生升則脾氣健運,即有助脾清陽提陷之力;風性輕清,有發散郁火之功;風藥芳香溫燥,辛散走竄,有醒脾祛濕、辛散祛瘀之用;風藥辛散能行,有疏肝解郁之效。如:治療肺脾虛損補中益氣湯、升陽益胃湯等,一般用小劑量的風藥以起助脾氣升清之用;而在升陽散火湯方中,風藥的用量則略大于甘溫補氣藥,以取其升提陽氣之意。
4.3 祛濕化濁散陰火
陰火理論是李東垣學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其在《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蘭室秘藏》《醫學發明》4 部著作中,提及“陰火”達40處之多。《脾胃論·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曰:“既脾胃氣衰,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者,陰火也……脾胃氣虛,則下流于腎,陰火得以乘其土位。”王昀認為李東垣的陰火內涵即指建立在脾胃氣衰基礎上的內傷之火。因此其提出陰火的治療意在解決氣不足(氣虛)與氣有余(火)之間的矛盾[11]。《脾胃論》首方即是為治陰火而創立的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其中以黃芪、人參、炙甘草等甘溫之品補脾胃以絕陰火的產生;升麻、柴胡、羌活等風藥升發清陽以潛降陰火;而瀉陰火最為直接的方法則是祛濕化濁,因濕濁下趨、閉塞肝腎氣機是陰火產生的直接因素[12],故李東垣在此方中處以了苦寒燥濕的黃連、黃芩,謂“如見腎火旺及督、任、沖三脈盛,則用黃柏、知母……不可久服,恐助陰氣而為害也”(《脾胃論·脾胃盛衰論》)。
5 小 結
李東垣作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所創作的《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等著作在當世中醫學界依然流行,其所提出的補脾胃生元氣、甘溫除大熱、脾胃升降樞紐和陰火論等觀點依然指導著當今臨床。總之,東垣學說對后世醫家學術思想發展與形成起到了顯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