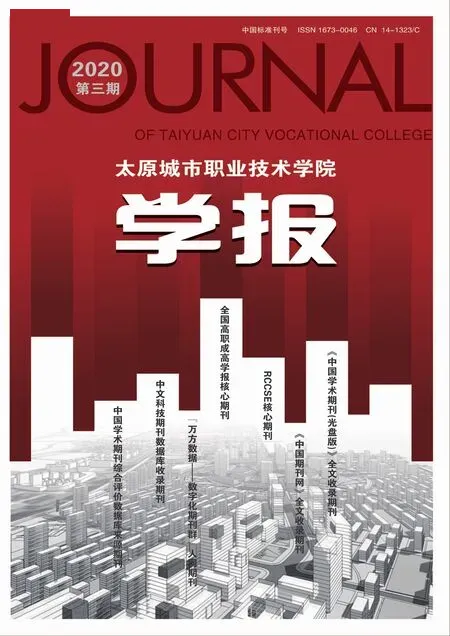譯者主體性研究的后現代主義視角
■孫 毓
(聊城大學外國語學院,山東 聊城 252000)
在西方,翻譯研究大約在20世紀70、80年代開始注重文化轉向。受其影響,翻譯理論也開始努力突破原中心語的框架范圍,進行譯入語取向的探索。后現代主義翻譯理論隨之被納入了當代西方翻譯學研究的范疇。后現代主義是一種理論體系,更是一種方法論。它既注重政治批判,也強調文化的介入。文化轉向在后現代主義翻譯理論發展方面的主要表現就是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等的興盛。后現代主義翻譯理論這幾個流派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對譯者主體性的闡述。
一、后現代主義與翻譯理論
(一)后現代主義的源起與發展
關于后現代究竟何時出現這個問題說法不一,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起初用于表達要有必要意識到思想和行動需超越啟蒙時代范疇,它是一個由一系列觀念組成的復雜術語,19世紀70年代后,后現代主義一詞被社會學家和神學家開始經常使用。學術研究領域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關注后現代主義。后現代的主要理論家們都反對用任何固定的形式來對他們所堅持的主義進行界定或者規范,因而后現代主義從理論上很難用精準的定論來概括。后現代涉及到的學術研究領域十分寬泛,包括工藝、藝術、建筑、時尚、音樂、影視、文學、哲學、社會學、傳播學等。這些不同的領域都反對以特有的方式來繼承原有的或者既定的理念,因此就當下的后現代境況,他們都提出了各自領域內成體系的論述。由此可見,后現代主義是一個由具有不同特點的多項藝術主義融合而成的派別,這種融合性決定了后現代主義涵蓋內容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絕非幾句話就能對它進行公式化的界定。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哲學和建筑學是最早出現后現代主義的領域。哲學史上的不同學者都對相似的后現代主義的人文境況進行過各自的解說,但都沒有形成一個相對全面的概括性的文本。大致說來,法國的解構主義算是其中能夠將后現代主義在總體上做大致性表述的一個哲學文本了,它解構文本、意義、表征和符號。解構主義認為對既定的一個文本、表征和符號存在無限多層次解釋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任何一個文本、表征或者符號都存在著多方面的意義,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下,用哪種意義對其進行解讀就要看作者的意圖和讀者的反映了。
(二)后現代主義翻譯理論的興盛
在翻譯理論方面,后現代主義在方法論上已經影響到諸如解構主義翻譯觀、文化學派翻譯觀、后殖民主義翻譯觀以及女性主義翻譯觀等的理論建構。認識論上是對本質主義哲學觀當中語言意義單一性與固定性的否定[1]。我們說后現代主義翻譯理論,并不是把翻譯理論歸屬于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翻譯理論只是借助于或者說結合后現代主義的思想或者理論框架而興起。當前后現代主義翻譯理論研究在當代西方翻譯學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對翻譯理論和研究整體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是由于后現代主義是多種藝術主義的融合,它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的趨向性、解構而非建構的破壞性,因此國內的一些翻譯理論學家遇之繞道而行。先不說后現代主義翻譯理論如何,單從哲學的角度來說,這是不符合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我們應該認識到后現代主義理論也許會對建構中的翻譯學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后現代主義由解構主義方法論為基石,涵蓋了政治、社會意識形態等領域,這就會對受縛于本體性研究、遵循語言的線性邏輯規約的傳統翻譯理論帶來巨大的質疑和沖擊,它同時也能促使人們從一個全然不同的視角對翻譯理論進行思考。也正是受此影響,西方翻譯理論研究展現出高度的協作性和跨學科性的特點,將研究拓展到翻譯的外部,出現了現代翻譯研究的第一次轉向——文化轉向。而20世紀80年代后期,文化轉向的表現主要就是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等后現代主義翻譯理論的發展[2]。
1.解構主義
20世紀60年代中期解構主義興起于法國,創始人雅克·德里達。德里達出版了《文字語言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三部書,確立解構主義。解構主義的主要特征為消解,具體來說,它應該看作是西方文藝批評理論界對結構主義進行的否定,之所以稱“解構主義”,是因為它否定了結構主義關于結構和意義等幾個重要的概念。同時,對語言提出了挑戰,代表人物主要有德里達、本雅明和韋努蒂。解構主義自產生后被應用于學術界諸多領域,其中包括翻譯領域。
解構主義對語言、意義的本質進行了論述,拓寬了翻譯研究的思路。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將意義視為中心,認為意義先于語言而存在,將語言和意義分離,強調所謂的“超驗所指”(transcendental signified)。德里達提出的“延異”這一說法粉碎了這一幻想。德里達認為,意義并非產生于語言之前,而是“延異”嬉戲(the play of différance)之后產生,“延異”是意義產生的條件。由此而言,符號的意義、文本的意義都不是確定的,我們所捕捉到的意義只是在某個語境下的、暫時的意義。如此,意義不能同語言分離,更不是先于語言而存在,這種解構下的意義就不可能毫無損壞地從一種語言中提取出來轉移到另一種語言中,也就是說某一語言狀態下的意義不可能原封不動地用另一種語言方式表達出來。所以,任何一個文本都包含多重意義,對其進行的任何一種解讀都不能窮盡文本的意義。推而廣之,德里達突破傳統的思維,主張用“有調節的轉換”(regulated transformation)來代替翻譯,也就是把翻譯看作是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一個文本向另一個文本的轉換[3]。德里達的意義不確定論顛覆了意義確定論,同時對翻譯的新詮釋中翻譯不再是意義的“等值”轉換,開拓了翻譯研究的視野。詮釋解構主義過程中,翻譯理論家們將傳統翻譯研究領域擴展到哲學、歷史等層面,同時也拓展了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的研究領域。
2.后殖民主義
后殖民主義是一種激進的理論批評話語,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薩伊德、斯皮瓦克和霍米米巴巴。后殖民主義理論首次將西方對殖民地進行文化殖民的事實及后果納入了研究范圍,將研究中心由文本形式轉移到了文化政治上,顯示了西方當代批評理論在“后現代主義之后”的一種新傾向[4]。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者定位于殖民文化和相關聯的前國或者附屬國文化,旨在殖民文化的獨立復興,其中也包含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平等文化交流與對話。在后殖民主義理論的研究范圍之內,我們確實意識到了世界范圍內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存在的比例失衡狀況,弱勢文化受到強勢文化的侵略和殖民化。以東方為代表的弱勢文化和以西方為代表的強勢文化受到廣泛關注。由此觀點而言,翻譯活動實際是殖民文化的產物,是殖民化的過程。為了消除西方對東方文化的扭曲理解,展現東方殖民地語言與文化,抵制西方霸權主義的侵略,后殖民主義翻譯家提出了相應的“抵抗式”翻譯策略。如霍米米巴巴提出“雜合”翻譯策略,即翻譯時將兩種語言與文化的特征融和在一起,優勢互補,呈獻給讀者原有文化基礎上的優化文化。再比如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提出“異化”的翻譯策略,即翻譯時譯者要將語言和文化差異傳遞給讀者,為了消除文化霸權現象,在必要時甚至可以特意使用不透明、非地道的翻譯表達方式。
3.女性主義
起源于西方的女性主義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質疑西方傳統中將男女割裂、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話語體系。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形成于上個世紀末,產生于加拿大,是將女性主義與翻譯研究結合的翻譯理論。一直以來,關于翻譯的女性氣質話題經久不衰,它包括不同文化間的性別角色的差異及其不同的表達方式等。其代表人物有弗洛托、西蒙、張伯倫、斯皮瓦克、哈伍德等。縱觀歷史,不分種族地域,女性歷來地位低下,相應的女性在翻譯時以及翻譯中女性的地位也很低下。女性主義翻譯觀旨在消除翻譯中對女性的歧視,進而重新認定原有文本和已有譯本的地位。成功的翻譯不僅是語言使用的過程,還必須考慮包括文化在內的諸多因素。基于此,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突出強調使用女性特有的語言展現獨特的女性心理和在社會中的整體建構,轉變女性的一直以來卑微的形象。同時將文化等因素考慮在內,從整體大背景下突出女性的地位。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進行解讀。
二、傳統翻譯理論框架下的譯者主體性
譯者主體性,就是譯者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主觀能動性,當然這一主觀能動性首先是以尊重翻譯對象為前提的,在此基礎上展現其能動性,也就是在文化、審美等方面的創造性。翻譯活動的整個過程都貫穿著譯者主體性。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主體性包括譯前主體性和譯中主體性。譯前主體性是指譯者翻譯之前對翻譯文本、翻譯目的、翻譯策略等的考量;譯中主體性是指在翻譯過程中對作品的理解、闡釋以及語言層面上的藝術再創造等。
眾所周知,傳統的翻譯理論強調翻譯的“忠實”,認為翻譯是忠實基礎之上的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信息傳遞。“忠實”的標準顯然就是突出了原作的中心地位,任何翻譯都要以原作為基準進行語言轉換和信息的傳遞。原作及原作者被賦予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權威。這樣譯者翻譯時就要嚴格忠實于原作者,處于翻譯活動的從屬地位。譯者就是原作者的傳聲筒,自己基本陷于失聲狀態,主體性受到了嚴重的限制甚至壓制。同時,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受原作者、原作、譯者本身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約,嚴重影響主體性的發揮。基于這種狀況,韋努蒂提出術語——譯者的隱形,呼吁翻譯界讓譯者“現身”,發揮譯者的主體性。
三、后現代主義翻譯理論中譯者主體意識的強化
傳統翻譯理論中的主體意識對應的是笛卡兒與康德式倡導的理性的主體性原理,以及強調主體性實踐的帶有中心性的現代主義文化,而后現代文化,比如詹姆森指出的那樣,是一種遠離中心化或者說是一種主體零散化的實踐過程[5]。看似矛盾的過程,譯者的主體意識確實在以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翻譯理論中得到了強化。
(一)解構主義是在文本之間、文本與譯者之間的互文關系中去構建意義
對于文本的意義,解構主義認為文本的意義具有開放性、互文性和非原始性的特點。意義具有開放性,是因為意義本身具有不斷擴散的特性,這樣任一文本的意義就會同其他的文本形成互設的關系,存在于文本之間的互文關系中。從意義的互文性我們可以看出,不存在最初的或者恒定不變的意義。這也是意義非原始性的特點。也就是說,不會有任何一個譯文文本的意義與原文的意義完全相符,由于文本的意義的開放性、互文性和非原始性的特點,翻譯一個文本,就必須追根溯源,聯系它之前的各種相關文本,并加以引用。這種情況下,就無從談起忠實或對等。解構主義構建下,譯者無法挖掘到已有的意義,譯者的翻譯實際是一種基于原文本的建構行為,在翻譯過程中需要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不斷修改完善。后現代主義思潮下形成的解構主義理論用于翻譯實踐中,使譯者從從屬和被遮蔽中解放出來,肯定了譯者的作用,提高了譯者的地位,凸顯了譯者積極的主體性作用。
(二)后殖民主義譯論認為譯者不是消極被動的模仿者,而應是積極主動的創造者,應該主動地把握和占有原文
后殖民主義體系下的譯者在對受殖民地的“統識性”(hegemonic)翻譯中,譯文文本就是對殖民統治者強勢文化的重新塑造、對受殖民統治的踐民形象的重新刻畫。基于此,后殖民主義者主張以另一種方式釋放譯者的主體性,既能夠糾正“他者”文化被貶抑的形象,又可以借助于抵抗式的“混雜”策略反對殖民主義的“統識性控制”[6]。在后殖民主義翻譯中,殖民主體充當了譯者這一主體,他們是話語權力者,在翻譯過程中,將其話語權力推廣擴大,對被殖民者實施權力布控,使被殖民者臣服于他們的殖民統治,而翻譯就充當了他們的殖民工具。這樣后殖民主義翻譯的譯者就可以發揮主體性,為所說的“他者”文化正言。
(三)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與后殖民主義翻譯理論對于譯者主體性的論述基本一致
它是將性別因素納入譯者主體性的研究,認為譯者主體性“是以爭取女性的平等和尊嚴為起點,并不將譯者、譯本打入次一等級的觀念,力求戒除翻譯研究和社會觀念中帶有嚴重的性別歧視的那部分陳舊意識”[7]。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從女性特有的角度出發,對原作和譯作的關系進行論述,突出強調譯者主體性,并對其加以補充闡釋,同樣拓展了翻譯的研究領域。女性主義翻譯理論者認同翻譯不是單純的語言轉換或文化交流,還認為翻譯是實現女性譯者主張的手段。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從另一個角度突破傳統譯論,為譯者主體性研究開辟了新的視角,促使人們開始關注譯者的性別,從不同的角度彰顯譯者的主體性。
綜合以上三點,解構主義翻譯理論認為意義都存在文本之間的互文關系中,文本和語言具有同質關系,無形之中提高了譯者和譯文的地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在對意義的解讀過程中,倡導突出譯者尤其是女性譯者的主體性,強調翻譯中的女性意識;而后殖民主義譯論認為譯者不是消極被動的模仿者,而應是積極主動的創造者,應該主動地把握和占有原文。由此可見,后現代主義框架下的這幾種翻譯理論從不同的思考角度對翻譯中譯者的主體性進行了相同方向的詮釋,即強化譯者的主體性意識。
四、結束語
后現代主義翻譯理論突出強調譯者的主體性,相應地解決了翻譯與意識形態、性別、文本闡釋等問題,使我們進一步理解翻譯絕不是簡單的語言轉換,而是譯者主體意識之下的包含各種因素、力量的語言操作過程。后現代主義框架下的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在翻譯理論的研究問題上彼此滲透、相互影響,共同倡導強化譯者的主體意識。后現代主義翻譯理論視角下解讀譯者主體性,既有助于還原殖民主義在其文化交流中的真實境況,突出女性的主體地位,了解譯者活動的積極作用,深化譯者主體性的研究,還有助于拓寬翻譯研究的視野,推動翻譯理論的建設。總之,后現代主義這一全新的研究視角應用于翻譯研究,正在不斷促進中國乃至西方以及整體翻譯理論的完善,推動著翻譯學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