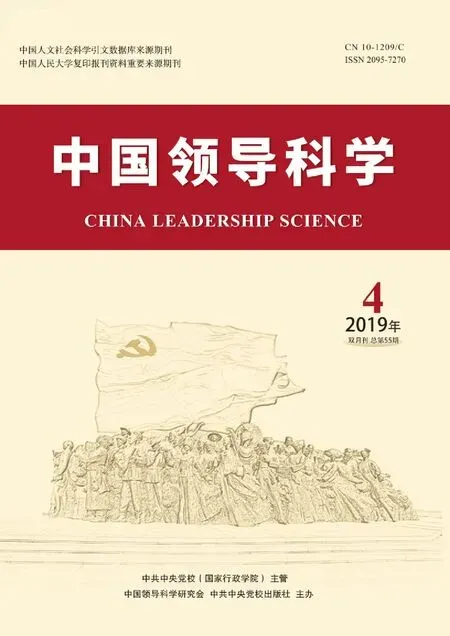以黨的領導力鑄就國家能力
◎祝靈君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的建設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各個領域實現了全方位的發展與進步。中國的成功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解釋版本,同時還有不少預測中國未來走向的論說。客觀地講,盡管今天的中國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離建成現代化強國的奮斗目標仍有較大距離,但無疑是成功治理的國家。
一、國家能力的理論研究
國家能力問題,從國家誕生就開始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在論述國家起源時指出:“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之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國家產生的基本前提——國家必須擁有超越并整合不同社會利益、構建社會秩序的能力,同時也指出了國家能力發展的永恒性、利益矛盾的永恒性決定了國家能力的永恒性。
在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尤其是法家對國家能力問題進行過深入思考。在西方,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研究過城邦能力問題。他指出:“國勢強弱與其以人數來衡量毋寧以他們的能力為憑。有如人們的各從其業,城邦也得各盡其用;凡顯然具有最高能力足以完成其作用的城邦才可算是最偉大的城邦。” 亞里士多德之后,對國家能力的思考逐漸式微,尤其是當歐洲進入神學政治時期后。公元1500年后,隨著民族國家逐步誕生,越來越多的歐洲學者開始研究國家的起源、本質、職能。二戰以后,隨著發展理論的興起,在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的研究中,國家能力成為影響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因素。
西方學者關于國家能力研究大致形成以下派別:
政治體系論。20世紀50年代,一大批行為主義政治學者用政治體系能力取代對國家能力的研究。如美國學者阿爾蒙德等,認為政治體系的能力取決于國家活動的環境。
“回歸國家論”。20世紀60年代,一批西方學者強調回歸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強調國家在政策制定和社會變遷中的重要作用。如美國學者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等。
“國家悖論”。20世紀8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派以國家本質的“經濟人”假設,提出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國家又是經濟衰退的根源等結論。如美國學者道格拉斯·諾斯等。
國家建構學派。本世紀以來,一些西方學者提出失敗國家成為當今世界諸多問題的根源。對眾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強化國家能力是當務之急。如美籍學者福山等。
國家終結論。全球化使民族國家走向大統合,民族國家必將走向終結,如德國學者哈貝馬斯等。
國家衰落論。全球化時代,國家不再壟斷權威,國家權威必然有所衰落。如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等。
國家包容論。美國學者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 在《國家為什么失敗》一書中分析國家貧富差距的原因。其結論是制度差異導致發展與治理水平差異。包容型國家鼓勵創新和促進經濟增長。壓榨型國家阻礙創新,經濟增長缺乏動力,除非一些國家在制度上做重大改革,更加容納“創造性破壞”。
二、成功的國家治理離不開強大的國家能力
歷史和現實證明,成功的國家治理離不開強大的國家能力。從國家能力的角度看,大部分西方學者承認國家能力是國家發展和治理的基礎,但也指出國家權威和能力必將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而日漸走向衰落。
首先,拿美國來說。
1932年是美國經濟危機最嚴重的年份,大量工人失業,銀行倒閉,公務員得不到工資,許多人無家可歸,人民怨聲載道,全社會彌漫著頹廢、低迷氣氛。1933年3月6日,民主黨候選人富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美國的第32任總統,取代共和黨總統胡佛。接手這樣一個爛攤子,羅斯福總統在其就職典禮上宣誓:“我會讓國會拿出僅有的一件應對危機的武器,那就是廣泛的行政授權。這一授權要強大得如同我們正面對外敵入侵。美國人民并未氣餒,危急時刻,他們的要求是,希望政府采取直截了當、迅猛有力的行動。他們愿意接受領導并遵守紀律、聽從調配。他們讓我領受了這一使命,為他們實現愿望。” 事實證明,羅斯福總統正是借助于國會授權建立“行政國家”,增強國家能力,通過實施“羅斯福新政”讓美國走出了困境。美國號稱是世界上最具有自由精神的國家,當面臨無法渡過難關的風險時,依然會毫不猶豫走向“大政府”,增強并使用國家能力。事實證明,這個選擇符合國家發展與治理的基本規律——即任何國家都必須有能力,當國家處于競爭追趕狀態或應對重大困難風險、完成急難險重目標時,必須強化中央政府權威。
其次,我們來看其他國家。
二戰以后,一大批民族民主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大多缺乏國家能力。這些國家多保留執政黨與反對黨體制,執政黨往東,反對黨往西,形不成合力,很難形成政黨領導力,最終導致國家能力弱。在處理國內細小矛盾和問題時,國家能力弱的弊端還不太容易看出來,但在應對國際壓力和處理重大事件時,國家能力弱的問題就會充分表現出來。比如,在面臨外部力量壓制時,內部的不團結往往給人以可乘之機。在國際資本主義秩序中,政治競爭與市場競爭是一體的。競爭喚醒了沉睡的生產力并最終改變生產關系,競爭實現資本對經濟基礎的控制并最終影響上層建筑。英國劍橋大學韓裔經濟學教授張夏準認為,發達國家倡導發展中國家遵循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上了樓就踢掉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防止發展中國家趕上發達國家。
冷戰后,經濟全球化大潮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都從中受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也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方。 然而,一國在全球化進程中忽視國家能力建設必然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悲劇。全球化主要是生產要素的全球化,其中又以資本的全球化為主,資本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資本流向哪里,哪里就出現生產與發展的活力;資本離開哪里,哪里就死氣沉沉。然而,資本的本質是追逐利潤,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作為生產要素帶來的收益率遠遠高于勞動力、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的收益率,也高于經濟增長率。因此,在資本快速流動的地方,一方面經濟迅速發展,一方面貧富懸殊拉大,而貧富懸殊產生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必然留給主權國家和地方政府。于是,資本流動必然與主權國家發生這樣那樣的矛盾。為了消除這些矛盾,一方面,擁有資本、技術優勢和金融霸權的國家必然以自由主義作為思想武器,倡導各國推行自由市場,政府較少干預,使資本自由流動;另一方面,則以跨國公司為代表影響或控制主權國家,通過資助反對派成功實現政府更替,或者通過資助非政府組織(NGO)實現“社會反對國家”,導致政局不穩,給主權國家制造難題。在發展中國家,市場競爭與政黨競爭的“雙標配”成為當仁不讓的“普世價值”,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制衡,制衡,制衡;為制衡而制衡”,最終傷害的是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穩定、經濟和文化繁榮。如此看來,在全球化時代,經濟風險與政治風險交織,推進經濟社會發展進步,解決國際國內風險與矛盾,實現社會和諧治理,世界各國家都需要強大的國家能力。
在這里,我們特別要說的是一些非洲國家。現在許多非洲國家還在經歷“底層治理之痛”。盡管不少非洲上層精英大都在歐美或南非求學,大都顯得彬彬有禮,有寬闊視野、遠大抱負和政治頭腦,有些甚至是很優秀的政治家。但是,非洲治理的真正問題并不全在于上層人士,而在于一個數量龐大卻不能有效組織的底層民眾。這個底層在傳統社會里曾被部族有效控制,而今天則由于被過去的內戰、種族屠殺、移民潮破壞,演變為“一盤散沙”,上層治理結構與底層治理結構之間缺乏有機聯系,形成上下“兩張皮”,類似于中國晚清至新中國成立前的狀態。由于底層社會不能有效組織,其豐富的資源難以開發而導致國家貧窮,加劇了上層統治者對外部援助的依賴。作為聯結上層統治者與底層民眾的行政管理人員(政府官員),在得不到政府足夠的財源支持和底層民眾有效認同的前提下,執行能力低下、腐敗成風、裙帶主義蔓延并喪失公務員理想與精神。這就是一些非洲國家的“治理之痛”。一言以蔽之,這些國家缺乏國家發展與治理的基本要件——國家能力。
比較世界各國,成功的國家發展與治理都需要有強大的國家整合與認同能力、高效執行國家法律和有權威地進行統治的能力。在國家應對危難和風險挑戰或擬定國家發展方向的關鍵時刻,尤其需要有優秀的政治領袖確定航向,看得遠、把得準,大膽超越一般民眾的短期利益和既得利益。國家能力,對于每一個國家都不可或缺,只不過在有些國家是顯性的,在有些國家處于“隱性”狀態罷了。
三、中國的國家能力來自中國共產黨的成功領導
中國的國家能力從哪里來?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嚴肅思考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在眾多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學術文獻中,黨和國家的關系曾被貼上諸如以黨領政、以黨統政、黨在政上、政黨國家、以黨治國、以黨代政、黨政不分、黨治國家、黨政體制、黨的一元化領導等諸多標簽。其中,“黨國體制”一詞長期誤用,以致許多觀察人員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關系的深刻變化熟視無睹。
“黨國體制”在西方學術話語中是一個很負面的詞匯,即使當今德國學者也不愿意承認納粹時期是黨國體制。 蘇聯學者阿·阿夫托爾漢諾夫就指出,蘇聯的根本體制是“黨國體制”“黨國制”“黨治制”,其主要特征是一黨執政,黨凌駕于國家之上,具有立法和行政機關的職能。通過這種體制,黨成為國家中的國家,或者說,它本身就是國家,對政府和社會實行全面的控制。 其實,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既不等于蘇共與蘇聯的關系,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黨和國家關系,而是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國情相結合而形成的“黨領導國家”體制。
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與近代歐洲誕生的政黨和國家的關系完全不一樣。公元1500年,歐洲國家的近代史開始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歐洲進入民族國家時代。有了民族國家,就逐步發展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有了國家治理體系,才有政黨。國在前,黨在后。所以,歐洲國家長期以來是以國家為中心,政黨并不重要。中國數千年就是一個天下國家,直到1840年還是如此,但很快就變成了現代國家。“中國是個天下國家,所以沒什么認同問題,只有等到另一種文化來時,才會產生認同觀念。”從“天下”到“萬國”,從“天命”到“人民”,近代以來中國人一步一步深化對現代國家的認識,最終建立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創舉。黨在前,國在后,黨興國興、黨強國強。只有建設強大的政黨,才能建成強大的國家。正所謂,強黨為強國,強黨建強國。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利益最大公約數的代表者,必然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領導核心。一般情況下,政黨(party)就是一個“部分”(part)。世界上許多政黨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不同的“部分”通過競爭獲得執政權。選舉結束后,一個較強的“眾意”戰勝了一個較弱的“眾意”,但難以找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自1840年以來,中國陷入了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國人民經歷了戰亂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難。從此,實現國家統一、推進現代化建設、建立民主政治、實現中華文化繁榮興盛等,客觀上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必然成為中國政治舞臺上一切有抱負有正義感的政治力量的崇高使命。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承載了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必須把自己的命運與人民、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起來。而實現初心使命,單靠中國共產黨人是不可能的,必須匯聚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力量共同奮斗。
第二,中國共產黨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成功實現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大都是在封建社會中誕生并逐步壯大的,并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對這些制度成果予以“追認”,資產階級政黨盡管參與了資產階級革命,但他們并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唯一締造者。那么,中國共產黨則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中誕生,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締造了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由此,黨的命運與社會主義的命運關聯在一起,黨興則社會主義興,黨強則社會主義強。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第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融進了單一制治理結構之中,成為國家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世界上超過一億人口的國家,絕大部分都實行聯邦制。中國超過13億人口,卻用單一制作為國家權力的組織原則,而且還很成功,許多人想不明白。其實,在一個超大型國家,通過競爭實現多元利益代表往往會損害人們的長遠利益或一部分人的現實利益,甚至像美國那樣弘揚多元主義價值觀的國家,其代表權往往落在少數精英手中。一旦精英與資本聯手,就會出現資本集團影響并掌握國家的結局。而在當代中國,中國共產黨繼承了幾千年 “一盤棋” 的國家治理思路,協調、綜合、代表各方利益,使各方面的利益訴求沿著同一個方向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前進。因此,黨的領導已經變成國家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抽離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央和地方就會“打架”,這個單一制結構就會坍塌。顯然,黨的領導已成為國家權威和國家治理的基礎。
第四,中國共產黨堅持以自我革命推進社會革命,有效領導社會治理。中國共產黨歷經磨難、曲折,依舊能煥發出新的生命力,這要歸功于黨高度重視政治建設和思想建設這兩個傳家寶。中國共產黨把政治建設的成果變成了正義的力量,把思想建設的成果變成了真理的武器,再把正義的力量和真理的武器交給了人民群眾,最終匯聚為推動社會革命的不竭源泉。中國共產黨在“一大”綱領中就鄭重提出:“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現社會革命。”每一次社會革命的結果,都必然把真理的武器成功轉化為中國共產黨人自我革命的武器,必然把正義的力量成功轉化為中國共產黨人自我革命的動力。如此循環往復,生生不息,螺旋上升。在黨領導社會治理的過程中,黨的政治功能為社會治理指引了方向,黨的服務功能讓社會治理充滿活力。由此,中國共產黨強大的組織力為社會治理提供了秩序,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大格局。
四、中國共產黨領導力形成的理論邏輯和經驗啟示
中國共產黨要實現國家富起來的目標,一定是與過去比,必然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就必須抓住國際環境為我提供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中國共產黨要實現國家強起來的目標,別人一定要與我們比,必然會面臨國際博弈格局,這就必須具備維護國際秩序和創造戰略機遇期的能力。大黨治理大國,其難度與復雜性超乎想象。總結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管黨治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黨的領導力形成既有深刻的理論邏輯,又有客觀的經驗啟示:
一個有理想的執政黨,必須把自己的命運與人民、民族的命運關聯在一起。必須站得更高,看得更遠,自覺承載人民和民族賦予的神圣使命,把歷史使命與理想信念統一起來。每個國家的政黨制度都是在本國土壤當中“長”出來,不能簡單從國外“抄”過來。“長”出來的有生命力,“抄”過來的沒有生命力。一個國家無論選擇什么樣的政黨制度,都必須以維護社會穩定為前提,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根基,把實現“眾意”與實現“公意”統一起來,代表并實現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積極回應民眾的訴求,形成黨與人民群眾的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行動共同體,建立黨群關系同心圓。任何執政黨不能不把發展經濟作為現代化建設的中心任務,但是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執政黨認同。世界上有許多執政黨在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時刻戛然停步,黯然退出歷史舞臺。因此,一個有作為的執政黨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既重視“做大蛋糕”,也重視“分好蛋糕”,審時度勢地推進從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才能最終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帶來的物質福利與精神愉悅。
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要善于用先進思想治理國家。在一個貧窮落后的大國,要迅速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不但要善于執政,匯聚各方面資源,勇于突破體制機制桎梏,善于打破既得利益藩籬,形成各方面比較成熟的制度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要善于植入核心價值觀,增強黨的政治功能和思想引領力,提升黨在基層社會的組織力和凝聚力。同時發揮家庭、社會組織、企業、宗教、媒體等各方力量的作用,在一個迅速變化的基層社會,實現多方參與、協同共治,提高執政效率。
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要善于發現優秀政治人才,并把這些政治人才輸送到各種崗位上磨打滾爬,積淀豐富的執政經驗,應對各種風險與挑戰。國家越大,治理的難度就越大。大國治理需要一大批忠誠實干并有真才實學的優秀政治人才。因此,中國共產黨努力把好干部挑選出來、使用起來、管理起來,以便更好地實現治國理政目標。
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要勇于自我革命。黨在自身建設上不可避免會沾染各種細菌病菌,甚至會讓人民產生執政疲勞、審美疲倦。因此持之以恒管黨治黨,全面從嚴治黨,不斷增強先進性、純潔性,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才能得到人民衷心擁護,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永葆旺盛生命力,用“自身硬”去打“硬的鐵”。
大家好才是真正好。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還必須時刻觀國際大勢、謀國內大事,努力構建與各國平等、開放、合作、共贏的伙伴關系,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讓世界上每一個國家得到更好發展的同時,推進本國的繁榮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