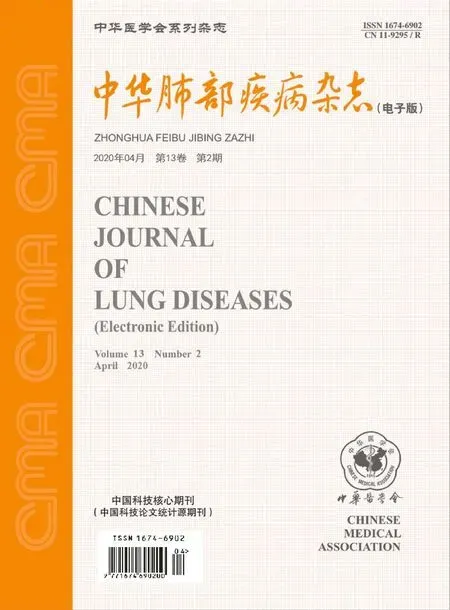中西醫結合辯證論治惡性胸腔積液再認識
周紅梅 馬想明 史亞鵬 金發光
惡性胸腔積液(malignant pleural effusion, MPE)又稱腫瘤性胸腔積液,分為原發性(胸膜本身的病變)和繼發性(繼發于胸膜以外的器官組織), 一般見于各種惡性腫瘤的中晚期,最常見的肺癌,乳腺癌和淋巴瘤, MPE是胸膜原發腫瘤或諸多腫瘤繼發轉移至胸膜的表現形式,是中晚期腫瘤的常見并發癥,MPE有時與原發病同時出現,臨床診治困難,中位生存時間短,預后差。臨床上主要以胸痛、呼吸困難,胸悶、內環境代謝紊亂及惡液質等為表現。目前報道的治療MPE方法繁多,主要以姑息性的經驗治療為主,MPE隨著腫瘤發病率的升高而增加,尤其是男性肺癌和女性乳腺癌的增加,MPE患者反復入院治療與病死率均較高,給臨床帶來很大的困惑與挑戰。其發病與治療特殊性是否與其胸膜腔的隔離環境相關,認識其發病機制的特殊性迫在眉睫,在具有挑戰性的治療中,如何發揮中西醫結合優勢,在辯證論治中探索MPE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法,旨在進一步規范、精準及個體化治療,以提高療效,改善該類患者的生存質量,延長生存時間,為臨床提供中西醫辯證論治的理論基礎和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法。
對MPE相關研究推動了診斷和治療的新范式,激發了許多正在進行的研究中評估的新概念。主要體現在應用細胞病理學和影像學技術、留置胸膜導管作為MPE一線治療提供堅實證據基礎,包括最佳胸腔引流管和手術在MPE中的作用,以及目前研究的重點所在的關鍵知識差距[1]。由于MPE無法治愈,臨床上主要是對癥治療,長期困擾臨床,隧道式留置胸腔導管和動態胸腔引流的發展改變了MPE的治療,改變了醫療實踐中如何看待姑息性疾病治療促進了個性化醫療在MPE中應用[2]。國內目前治療是以中西醫結合治療,既往以通訊作者的身份發表了中西醫結合治療MPE綜述[3],對這一時期國內外治療MPE進行總結,隨著臨床治療MPE的方法及思維路徑的不斷更新,有必要對MPE治療進行再認識,以提高臨床治療水平。
一、中醫治療MPE方法
胸腔積液在中醫臨床中屬于“懸飲”范疇,《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并治》指出“飲后水流脅下,咳唾引痛,謂之懸飲”,即懸飲是飲邪潴留于脅下,循經上逆射肺,致肝氣不升,肺氣不降,氣機逆亂而產生咳嗽并牽引脅下作痛。MPE患者一般多伴有惡性腫瘤,惡性腫瘤患者水液代謝失常的病機是肝主疏泄,脾主運化,腎主一身之水,《傷寒來蘇集·傷寒附翼》日:“人身之水有二:一為真水,一為客水。真水者,即天之所生;客水者,即食飲之所溢。故真水惟欲其升,客水惟欲其降。若真水不升,則水火不交而為消渴;客水不降,則水土相混而為腫滿。”腫瘤患者肝、脾、腎三臟受損,肝失條達,脾失健運,腎失溫煦,氣機不暢,水液代謝失常,水濕內停,泛濫于肌膚、經脈、胸腹,形成懸飲、臌脹、關格、水腫、肢腫等并發癥,嚴重影響了腫瘤患者的生存質量[4],病機特點是本虛標實,本虛為臟腑虛弱、氣化失調,標實為痰濁瘀毒聚結,水飲停蓄, 臨床可又分為水飲壅塞,痰瘀交結,氣虛等證型,對于懸飲中醫治療以十棗湯為代表,根據辨證論治結果用藥治療,當急則救標, 緩則治本, 內外并治。中醫理論指導下中成藥制劑在MPE中應用主要是靜脈注射劑艾迪注射液、參芪扶正注射液、復方苦參注射液、康艾注射液、康萊特注射液、香菇多糖以及病變局部使用華蟾素、鴉膽子油(Brucea javanica ail emulsion,BJOE)局部治療,這些治療方法均在臨床取得了一定臨床效果。Dai等[5]通過對14項研究共包括1 085例患者,納入研究的樣本總數從60例患者增加到123例患者不等,患者人群25~86歲,所有患者胸腔積液量均大于1 000 ml,在BJOE乳劑聯合組和對照組中,男性569例的數量分別多于女性546例。研究表明,BJOE可以通過上調腫瘤抑制因子或基因直接殺死癌細胞,還發現可以逆轉腫瘤細胞對化療的耐藥性,提高機體免疫力,而無明顯不良反應。實驗表明,BJOE是一種細胞周期非特異性抗癌藥物,對腫瘤細胞G0、G1、S、G2、M期具有殺傷和抑制作用,能顯著抑制腫瘤細胞DNA合成。此外,以往的研究也提示BJOE的抗腫瘤活性可能與腫瘤細胞凋亡機制有關,影響細胞周期進程,擾亂細胞能量代謝,抑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的表達。到目前為止,已有大量的研究報道BJOE可以通過改善腫瘤反應和生活質量,從而發揮協同作用來控制MPE。同時BJOE聯合治療可通過調節可溶性Fas/可溶性Fas配體的表達促進肝癌細胞凋亡,BJOE還可誘導結腸癌細胞凋亡。BJOE脂質體可抑制肝癌HepG2細胞的增殖,這種增殖呈劑量依賴性,可能通過誘導癌細胞凋亡來實現。與單用化療藥物相比,BJOE的存在顯著提高了MPE患者的生活質量(OR=1.56,95%CI1.21至2.0),其生活質量絕對提高了28.2%。也就是說,與單純化療相比,含BJOE治療可使MPE患者的生活質量提高約1.56倍。BJOE通過抑制C6膠質瘤細胞的磷酸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和核轉錄因子-κB(NF-κB)蛋白表達,抑制C6膠質瘤細胞的增殖,從而抑制膠質瘤細胞的侵襲性,提示BJOE的抗腫瘤作用與抑制PI3K/AKT信號通路有關BJOE誘導T24膀胱癌細胞凋亡的分子機制可能是通過上調Caspase-3和Caspase-9蛋白的表達,抑制NF-κB和cyclo-oxyge-nase-2(COX-2)蛋白的表達,激活caspase凋亡途徑。Meta分析顯示,靜脈注射BJOE加放化療與單純放化療相比,在緩解率、改善生活質量、降低部分AEs發生率等方面對肺癌患者有積極作用。然而,由于納入研究的質量較低,因此需要謹慎看待研究結果。傳統化療藥物加BJOE胸腔內注射與單純化療藥物相比, BJOE可以減少化療藥物的毒性。
另外,受藥代動力學與藥效動力學影響,田愛平等探索低頻超聲促進中藥(CM)透皮給藥能否提高白細胞介素-2(IL-2)胸腔內給藥治療MPE的療效。將110例符合條件的受試者隨機分為CM(LSF/CM)組(55例)和對照組(55例),對照組給予腹腔注射IL-2;LFS/CM組給予CM凝膠劑LFS,聯合與對照組相同的IL-2注射液。中藥配方由麻風子、芥子、桂枝、茯苓、枸杞、赤芍組成。治療2周后,通過B超和/或胸部X線檢查評估MPE量表的變化和東方腫瘤合作組(ECOG)的表現狀態評估生活質量(QOL)評分的變化來判斷治療效果。結果發現胸腔內IL-2加LFS/CM治療獲得的客觀緩解率(ORR)顯著升高(P=0.049),LFS/CM組患者的生活質量評分提高了(P=0.048),LFS/CM組患者的生活質量沒有降低。中藥復方LFS能有效緩解MPE,提高癌癥患者的生活質量[6]。
二、西醫治療MPE的方法
隨著分子醫學的發展,腫瘤-宿主細胞相互作用的影響越來越明顯。研究認為高滲透性血管產生的胸膜液是MPE形成的重要機制。一系列不同的細胞和分子參與了這一過程。這些作用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分子刺激胸膜炎癥, 如白細胞介素2(IL-2)、腫瘤壞死因子(TNF)和干擾素(IFN);第二類分子刺激腫瘤血管生成, 如血管生成素1(ANG-1)、血管生成素2(AGN-2);第三類分子影響血管高滲, 如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基質金屬蛋白酶(MMP)、趨化因子(c-c基序)配體(2-CCL)、骨橋蛋白(OPN)等,肥大細胞對MPE的形成有顯著影響。胰蛋白酶α/β1和白細胞介素-1β的釋放增加了肺血管的通透性,并誘導NF-κB轉錄因子的激活,從而促進液體的積累和腫瘤的生長。研究人員利用腫瘤細胞的基因組分析發現,具有激活突變EGFR、KRAS、PIK3CA、BRAF、MET、EML4/ALK和RET的腫瘤與MPE形成增加有關。KRAS突變常見于遠處轉移,EGFR突變常見于直接浸潤轉移的腫瘤。原發性腫瘤的突變不同于MPE的轉移,這項研究與靶向治療領域密切相關。肺癌通過DNA改變、DNA甲基化、mRNA表達、microRNA表達和蛋白質表達機制,最常見的生物學標記是EGFR突變和Alk易位。肺鱗狀細胞癌(SCC)腫瘤細胞直接侵入胸膜,治療選擇基于EGFR狀態。已經證明在轉移中發現的腫瘤細胞,包括MPE,與原發組織具有不同的分子特征。小細胞肺癌中MPE是淋巴管間接浸潤所致。乳腺癌(BC)發生MPE概率為2%~11%,最常見的是單側,同側,乳腺癌通過淋巴管擴散到胸膜腔,MPE在三陰性乳腺癌(TNBC)中最常見。激素和靶向治療都不是標準的治療方案。轉移最常發生在初次診斷后的第二年至第三年,轉移瘤常發生隨后的突變和分子變化。卵巢癌(OC)腫瘤細胞直接通過膈肌、胸膜腹膜或血細胞浸潤胸膜腔,77%的病例出現同側MPE,23%的病例出現雙側MPE。淋巴瘤發生MPE為16%~20%,積液常在左側形成。其病理生理機制為:①胸膜腔直接浸潤;②淋巴管阻塞伴肺和縱隔淋巴結浸潤;③胸導管阻塞,導致乳糜胸形成,主要機制是胸膜腔浸潤和腫瘤-宿主細胞相互作用。淋巴瘤引起的MPE的診斷非常困難,主要是因為滲出液中細胞的缺乏,也有觀察到1/3的MPE和淋巴瘤患者對化療耐藥。胸膜惡性間皮瘤常見于腹膜腔和肺漿膜,有時位于睪丸的心包和鞘膜上。惡性間皮瘤MPE發生在54%~90%的惡性胸膜間皮瘤病例中,并在早期形成。滲出液具有生物活性,保護腫瘤細胞免受化療的影響,并誘導腫瘤生長。
近年來,MPE中的多種核酸已被鑒定為間皮素、CEA、CA15-3、CA125、CYFRA 21-1、免疫細胞表面受體(巨噬細胞表面CD163+)、細胞外基質蛋白(OPN、fibulin-3)、RNA/DNA水平和序列等,但由于目前的驗證不足,這些生物標記物的臨床應用受到限制。然而,必須強調的是,胸膜液中間皮素的升高是惡性腫瘤的一個有用指標,包括在最初的細胞學陰性積液中。隨著有希望的生物標記物不斷涌現,還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內科胸腔鏡(MT)和電視胸腔鏡手術(VATS),MT和VATS可以直接顯示和活檢胸膜的異常,如結節、腫塊和增厚。在MT前使用US(尿激酶)有助于更好地顯示胸膜腔,并且已經成為常規手術的一部分,因為它減少了手術時間和并發癥的數量。盡管手術本身具有侵襲性,但局部麻醉的MT并發癥和死亡率較低。
特殊情況下MPE的治療建議,對于懷疑或診斷為MPE的患者,建議使用超聲對胸膜干預進行管理。對于懷疑或已知無癥狀的MPE患者,存在的問題是否應該進行胸膜引流。早期介入治療的主要優點是降低晚期發展為不可復張肺的風險,然而,根據最新的指南,建議這些患者不進行治療性胸膜干預。大容量胸腔穿刺術是一種在手術過程中清除1 L以上胸腔積液的方法。胸膜壓力計是用于測量胸膜內的壓力或肺的彈性。用這種方法,我們可以確定引流后肺是否會復張。大容量胸腔穿刺的優點是證實呼吸困難是由積液引起的。這在小容量胸腔穿刺術中并不總是明顯的。當胸腔穿刺術后患者的病情沒有改善時,醫生必須找出根本原因(如心包積液、肺栓塞等),最新數據顯示,60%的患者在初次引流后9 d內需要再次進行治療。對于有癥狀的MPE患者,建議進行大容量胸腔穿刺,特別是如果不清楚癥狀是否與積液和/或肺部可膨脹有關。以TPC或化學性胸膜固定術作為首次收集的無需預先治療的有癥狀MPE患者,在TPCs之前,首選的治療方法是滑石粉胸膜炎。然而,TPCs已成為已知肺不復張患者的首選。根據最新的指南,建議在呼吸困難的治療中同時使用化學胸膜固定術和TPC作為首選治療方法。經胸腔鏡或胸腔管(滑石漿)行滑石粉胸膜固定術治療癥狀性MPE在這些患者中,建議通過胸腔鏡或胸導管使用滑石粉,因為沒有證據表明他們之間的療效有差異。TPC或化學性胸膜固定術在有癥狀的MPE患者中的應用至少30%的MPE患者有不可復張的肺。這些患者的胸膜固定術失敗率為30%。因此,在這些患者中,TPC插入法是首選方法。與滑石粉胸膜炎相比,TPC的住院時間更短。TCP感染的治療TPC置入已成為許多患者的首選方法。插入TPC時感染的發生率較低。與TPC相關的感染通常在不拔除導管的情況下進行治療。當感染沒有改善時,建議拔掉導管。胸膜切除術,在化學性胸膜固定術不成功的MPE患者中,偶爾會采用根治性全胸膜或次全胸膜切除術(壁胸膜和內臟胸膜切除術)。在惡性間皮瘤患者中,由于缺乏與微創手術相比干預有效性的數據,很少使用。患者應適合手術,并有較長的預期壽命。胸膜次全切除術可以通過胸腔鏡進行,手術本身對胸膜腔的閉鎖幾乎總是有效的。分流器,胸膜腹膜分流術很少用于肺部受困、惡性乳糜胸或胸膜固定術失敗的患者,很少使用分流術的原因是已經建立的交通(阻塞、感染等)的特點以及與TPC相比干預的相對攻擊性。胸膜腹膜分流術的優點可能是在惡性乳糜胸的情況下。手術在胸腔鏡下進行,插入可由放射科醫生完成。目前療效的證據不一,而且有大量的并發癥報告。該技術的使用目前還不是標準臨床路徑和建議的一部分。纖溶藥物在胸腔內的應用,與安慰劑相比,在MPE患者中使用尿激酶并沒有在隨機試驗中顯示出更有效的效果。目前,該技術的使用不屬于標準臨床路徑和建議的一部分。抗腫瘤治療包括化療、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在大多數患者中,抗腫瘤治療并不被認為比標準治療更適合于MPE引起的癥狀的治療;然而,由于癌癥免疫治療在過去十年的進展,研究努力設計新的方法來治療而不是減輕MPE。目前,國際上還沒有對使用抗腫瘤療法對抗標準姑息性MPE治療程序的基本原理提出建議。在大多數惡性腫瘤的全身抗腫瘤治療中,MPE的療效較差。由于原發性腫瘤(如淋巴瘤、BC、SCLC、生殖細胞腫瘤、前列腺癌和OC)的有效治療,也有例外。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是MPE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細胞因子。NSCLC中EGFR突變的患者對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劑有反應。不幸的是,大多數NSCLC患者最初在沒有胸腔積液的情況下有突變的表皮生長因子受體,在一年內對治療產生耐藥性,導致MPE反復加重。故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證實貝伐單抗和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劑的療效。
目前,預測MPE患者預后最成熟的方法是LENT評分。LENT評分(L-LDH水平、E-ECOG、N-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T-腫瘤類型)是一種有臨床意義的預后方法,有助于預測患者的生存率和指導治療。這是第一個證實的預測MPE患者生存率的風險分層系統, LENT評分根據胸水乳酸脫氫酶、東方腫瘤合作組績效評分(ECOG)、血清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LR)和腫瘤類型計算。每個預后指標都有一定的數值。根據計算的分數,患者被分為低(0~1分)、中(2~4分)或高風險組(5~7分)。低風險組的中位生存期為319 d,而中風險組的中位生存期為130 d,高風險組的中位生存期為44 d。另一個評分系統是Brims決策樹,它被證明是預測惡性胸膜間皮瘤患者預后的有效方法(敏感性94.5%,陽性預測值76%)。
近年來在MPE的病理生理機制領域的發現強調了分子因素和突變在疾病動力學及其預后中的作用。更新后的指南有望幫助醫生診斷和治療MPE患者。但是,仍然需要單獨的患者方法。在不久的將來,提高對腫瘤疾病的治療水平和對MPE病理生理機制的認識,將有助于改善MPE患者的預后[7]。
1. 藥物治療: MPE是晚期肺癌患者生活質量降低的主要原因。最常見的治療方法是化學胸膜固定術,使用化學藥物通過纖維蛋白誘導胸膜炎癥和粘連從而防止胸腔積液復發,改善呼吸困難。化學制劑可以用胸腔鏡或胸腔內導管注射,其效率因制劑而異。迄今為止,滑石粉,強力霉素和抗腫瘤藥物,如多西他賽,紫杉醇和博萊霉素等在臨床應用較廣,單一應用某種藥物均有其不良反應,因此藥物治療優先考慮個體化治療方案。
2. 免疫治療: 免疫系統激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NSCLC患者對胸腔內IL-2具有良好的耐受性,胸腔內注射的IL-2水平比血漿中的IL-2水平高出6 000倍,表明局部注射的IL-2(公式重量=15.5 kDa)被隔離在胸膜腔中。盡管在31例患者中有28例患者胸腔內IL-2清除了積液,并且在其他細胞因子模式下看到了部分反應,但進展的中位時間不等,因此,高劑量Th1相關細胞因子的滴注本身不足以克服胸膜腔的免疫抑制環境。最近的一項臨床試驗描述了來源于MPE和惡性腹水的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IL)與順鉑聯合應用的情況。滲出性TIL比單純順鉑具有更長的無進展生存期和更好的生活質量,這是適應性免疫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調節性T細胞(Treg)比傳統的CD4+T細胞更易受鉑類聯合化療的影響,有可能從Treg介導的抗腫瘤免疫抑制中釋放出來。滲出性TIL與原發性腫瘤或實體轉移活檢TIL相比有幾個重要優勢:①MPE或腹水的T細胞產量比活檢高出一個數量級,所需傳代次數少,培養時間短;②MPE中T細胞(PIT)是TIL的一個橫切面,而來源于實體瘤的TIL具有空間異質性,其功能和特異性因活檢部位而異。由于它們的豐富性,可以通過短期體外暴露于激活信號來啟動PIT,并在不膨脹的情況下恢復它們。由此產生的細胞不會像常規TIL一樣對細胞因子上癮,也不需要大劑量IL-2來維持其存活。
PD-L1在惡性間皮瘤和其他惡性腫瘤上表達,因此可能被抗PD-L1抗體所靶向。與非惡性對照組相比,NSCLC伴MPE的T細胞顯示PD-1、TIM-3和CTLA-4的表達增加,這可能是由于PD-L1+腫瘤相關M2巨噬細胞分泌的大量TGF-β所致。MPE常規治療和免疫治療失敗原因在于胸膜腔是一個隔離的環境,腫瘤細胞和免疫細胞相互作用,而腫瘤進一步增生,這種環境中T細胞效應器被抑制或殺死,巨噬細胞被引導到M2程序,協助血管生成和轉移,所有這些都最終促進了侵襲性和侵襲性EMT腫瘤表型。
MPE中大多數分泌的細胞因子是Th2樣的,包括IL-10、VEGF和TGFβ,進一步促進傷口愈合環境,損害抗腫瘤效應器反應。多效性細胞因子IL-6及其可溶性受體成分sIL-6Rα是MPE中最豐富的細胞因子之一。IL-6由腫瘤和胸膜間皮細胞和基質細胞產生。IL-6和IL-10上調腫瘤細胞PD-L1的表達。IL-6信號轉導是通過IL-6Rα(CD126)和IL-6Rβ(CD130)組成的受體復合物介導的。IL-6Rβ廣泛表達,但IL-6Rα的表達主要局限于白細胞和肝細胞。在正常生理學中,IL-6通過反式信號傳導介導強大的系統效應,這種效應發生在IL-6與可溶性IL-6Rα結合以及與膜結合的IL-6Rβ復合物時。在卵巢癌的惡性腹水[28]和乳腺癌的胸腔積液中,IL-6反式信號轉導已被證明可促進腫瘤的侵襲性行為和進展,并在NSCLC中促進EMT,使其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治療靶點。Tocilizumab,一種針對IL-6Rα的單克隆抗體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已用于治療癌癥相關惡病質和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胸腔內給藥可能對胸膜免疫環境的極化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全身效應最小。胸膜腔近距離、高濃度的T細胞、巨噬細胞、間皮細胞和腫瘤有利于細胞間的接觸和信號傳導。例如,通過將腫瘤上的CD90和EphA4分別與巨噬細胞上的CD11b和Ephrin結合來促進EMT。同樣,腫瘤和胸膜巨噬細胞表達的PD-L1和PD-L2與T細胞上的PD-1結合,促進無能,誘導調節性T細胞(iTregs)的發育和凋亡。在胸膜腫瘤上表達的其他配體,如與TIM-3結合的CEACAM1,可能與PIT上表達的免疫檢查點受體相互作用[8]。
MPE治療性胸腔穿刺和胸腔造口術是一種姑息性治療。胸膜腔內的免疫抑制環境包括髓源性抑制細胞、T調節細胞和功能失調的T細胞。針對肺癌和其他惡性腫瘤的檢查點抑制劑和過繼細胞療法的有效免疫療法的出現,意味著對這種疾病的局部和系統療法的重新檢查。細胞因子IL-2的滴注,在臨床治療效果需進一步評估[9]。MPE患者常發生免疫功能障礙,主要來源于巨噬細胞TGF-β在抑制MPE的T細胞毒性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研究發現MPE中CCL22水平明顯高于非MPE,CCL22的高水平與MPE肺癌患者的低生存率密切相關。CCL22主要由MPE中的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AMs)產生[10]。同時,TAM衍生的TGF-β通過c-Fos介導TAMs中CCL22的表達。CCL22促進MPE中調節性T細胞(Tregs)的募集。Treg分泌高水平的IL-8進一步誘導TAMs產生TGF-β,促進MPE中腫瘤免疫抑制微環境的形成,巨噬細胞來源的CCL22通過IL-8在MPE的免疫抑制腫瘤微環境中起重要作用。
3. 腔鏡治療: 多西紫杉醇是紫杉烷衍生物,通過阻止蛋白質降解抑制有絲分裂,并通過與微管(微管蛋白的一種蛋白質成分)結合而穩定,通過胸腔鏡下胸腔積液引流并清除胸膜粘連帶后胸腔內注入多西紫杉醇,治療MPE的療效及預后。是一種有效且相對安全的NSCLC伴MPE的姑息治療方法。MPE的控制率為100%。在安全性方面,大多數情況下,不良反應輕微且控制良好。此外,所有患者的生活質量均有改善,尤其是呼吸困難癥狀明顯減輕。這是首次在臨床實踐中分析醫學胸腔鏡引導下多西紫杉醇胸腔內治療的療效,并確定多西紫杉醇胸腔內治療對改善生活質量的姑息作用。多西紫杉醇胸腔內不良反應與以往研究相似,主要表現為皮下氣腫、胸壁疼痛、氣胸、貧血和過敏反應均報告為不良反應,但均為1~2級,無嚴重不良反應報告。基于以上結果,我們認為胸腔內注射多西紫杉醇是一種相對安全的治療方法。在NSCLC相關的MPE患者中,胸腔鏡下多西紫杉醇治療顯示出良好的臨床療效、緩解呼吸困難癥狀和提供可耐受的安全性。胸腔鏡引導下多西紫杉醇胸腔內注射治療MPE是一種安全有效的姑息治療方法。未來,需要與對照組進行大規模前瞻性臨床研究,通過與其他治療方式的比較來確認多西紫杉醇胸腔內的治療效果[11]。也是MPE是腔鏡治療MPE另一種方法。
4. 局部治療: MPE局部治療主要包括治療性胸腔穿刺術、滑石漿胸膜固定術、留置胸膜導管(IPC)和胸腔鏡滑石灌注(TTP)胸膜固定術。研究發現TTP、TS和IPC在4~12周內似乎能改善MPE患者的健康相關生活質量(HRQOL),但由于高消耗率,長期數據不足[12]。去毛刺手術和熱療胸腔內化療(HITHOC)已成功應用于治療胸部腫瘤。21例患者中,10例患者在各自發表文章時仍然活著,全身毒性和治療相關死亡率為零。雖然關于N0-N1 NSCLC伴MPE患者的去毛刺手術和HITHOC治療的現有證據略顯不足。隨機對照試驗結果具有一定選擇偏倚[13]。
MPE 局部治療目的是將肺實質外表面(臟層胸膜)與胸腔內表面(壁層胸膜)融合,有效消除胸膜腔和胸膜液再積聚。熱療胸腔內化療(HITHOC)也稱為胸膜內灌注熱血療法(IPTC),在細胞減少手術后,在不能實現完全(R0)腫瘤切除的情況下,作為多模式癌癥治療的一部分,多于術中使用。在轉移性多發性肺氣腫的肺癌患者中,HITHOC被應用于電視胸腔鏡手術(VATS),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且無嚴重并發癥。因此HITHOC-VATS(IPTC-VATS)是治療肺癌患者胸膜粘連的一種安全、微創、有效的新方法。深入分析表明,胸腔內化療、熱療化療和滑石化學胸膜固定術是治療NSCLC伴MPE的安全有效的方法,兩種方法沒有明顯的優勢[14]。
留置胸腔導管(IPCs)可以有效地治療胸腔積液,使胸腔空間的動態引流,減少與胸腔積液相關的癥狀,降低整體住院時間。IPCs作為管理MPEs的一線選擇,其作用正在不斷擴大,認為IPCs應被視為MPEs的一線管理,與標準滑石粉胸膜固定術同樣重要。使用IPCs會引起胸膜粘連,導致導管脫落。對于那些以迅速拔出導管為首要任務的患者,更積極的引流方式或通過IPC注入滑石粉是一個合理的選擇[15]。MPE確定性胸膜干預的常見選擇包括插入留置胸膜導管(IPC)或滑石胸膜固定術。研究發現,與單純IPC引流相比,通過IPC給藥分級滑石粉可增加胸膜粘連的機會,且與不良事件的風險無關[16]。在首選非臥床治療路徑的患者中,通過IPC給藥滑石粉增加胸膜粘連的機會可導致更快的器械取出時間,并可能與更好的生活質量和癥狀評分相關。
5. 靶向治療: 隨著靶向藥物的出現,NSCLC患者的治療方式也發生了變化。EGFR-TKI單一治療對MPE的控制作用與胸腔內化療加TKI沒有差異,應進一步研究探討胸腔內藥物的作用。靶向下一代測序確定了51個基因中的56個非女性化的改變,包括TP53和APC,這些在胃食管交界處(GEJ)癌癥中是常見的改變。老年MPE患者癥狀性房顫可使IPC在高達14%的IPC治療患者中的應用復雜化。癥狀性房顫的微創治療包括胸腔內溶栓治療,如組織纖溶酶原激活劑(tPA),以溶解粘連,但這有胸膜出血的風險。首次成功和安全地使用極低劑量tPA胸腔內治療IPC相關癥狀性房顫的報告。有癥狀的房性滲出物在IPC插入后可使14%的患者復雜化。恢復IPC的引流功能是理想的結果,作為替代策略,例如,反復胸膜抽吸、插入輔助導管或手術,只能提供一個暫時的解決方案,而且具有侵襲性。目前還沒有針對不同纖溶藥物的I期劑量遞增研究或頭對頭比較,以確定最有效的藥物和劑量,用于房水胸腔內治療。因此異質性在臨床上很常見。有趣的是,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使用低劑量的tPA(脫氧核糖核酸酶)作為胸膜感染的胸腔內治療。在不同的患者中,胸腔內纖溶治療的最小有效劑量可能不同。在有一個可靠的預測系統之前,從非常低的劑量開始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特別是在出血風險高的患者。治療癥狀性室性胸腔積液的tPA的最低報告劑量。這表明,低劑量可能會被成功地使用,從而降低副作用和成本,因此值得進一步探索[17]。 胸腔內或靜脈注射貝伐單抗治療NSCLC伴MPE的療效和毒副反應。貝伐單抗胸腔內輸注治療NSCLC伴MPE療效和安全性均高于靜脈輸注。貝伐單抗治療后72 h血清VEGF水平的下降與胸腔積液的緩解率和持續時間密切相關[18]。對于GEJ癌誘發MPE,需要更好地了解該病的發病機制和惡性進展。鑒定了一個新的GEJ癌細胞系,GEAMP,來源于先前治療過的GEJ癌患者的MPE。綜合遺傳學分析證實GEAMP細胞與原發性腫瘤之間存在克隆關系。此外,還發現多個拷貝數改變,包括EGFR和K-RAS基因擴增以及CDKN2A和CDKN2B的丟失。裸鼠和NOD-SCID小鼠皮下側翼異種移植瘤的組織學檢查顯示,癌細胞具有鱗狀和腺狀混合分化,提示GEAMP細胞含有一個具有多能潛能的亞群。最后,藥物對EGFR信號通路的抑制導致關鍵下游激酶的下調和細胞增殖的抑制。因此,GEAMP是對有限數量的真正GEJ癌細胞系的有益補充[19]。
6. 終末期關懷: MPE是腫瘤的晚期表現,治療困難,預后差,在不同的地區和醫生的處理,不同的癌癥護理中也存在性別差異。回顧研究分析胸外科手術MPE患者,轉診組和非轉診組或接受或不接受胸膜固定術的患者均無生存差異。405例(59.0%)為女性。研究認為性別差異存在于MIPE最終管理的轉診模式中;女性比男性更不易被提及。盡管轉診率較低,但女性存活時間更長,接受胸腔穿刺的次數也更多。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了解男性和女性在轉診率和轉診結果方面的差異[20]。
三、目前臨床治療MPE中存在的問題
MPE是NSCLC患者常見的嚴重并發癥。分子檢測發現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基因突變已被證明是亞洲NSCLC患者的主要驅動基因。我國尚未批準用滑石胸膜固定術來控制MPE。化學治療胸膜粘連有惡心、嘔吐、胸痛、發熱、血液學毒性等副作用。無胸膜內化療的EGFR-TKI治療可控制MPEs,其療效與聯合治療相似。我們的發現是第一個證明EGFR-TKI單獨治療在控制EGFR突變患者MPE復發方面可能等同于胸腔內化療。MPEs常見于肺癌患者,尤其是長腺癌和EGFR突變患者。胸腔內注射化療藥物或生物制劑通常用于控制MPE。雖然胸膜內治療能預防胸腔積液,但所有化療藥物都有副作用,如發燒、惡心、胸痛或血液毒性。滑石粉胸膜固定術的安全性與胸腔鏡下灌注法相同,但滑石粉在中國還沒有商業化。對于EGFR突變的MPEs肺癌患者,胸腔內化療并不能提高MPEs的控制效果。此外,化療引起的不良事件的發生率可能會增加[21]。MPE患者再次住院的風險很高,再入院期間的死亡率為17.3%, 25%MPEs患者在出院后30 d內再次入院,再入院期間有五分之一死亡。胸腔穿刺術的非確定性治療導致再次入院。對導致可預防的再次入院的因素的進一步理解可以顯著提高該人群的護理質量[22]。MPE作為測定EGFR突變的一個來源,用于指導EGFR TKI治療肺結核晚期腺癌。研究了EGFR突變狀態在MPE、組織和等離子體中的一致性,以及EGFR突變在MPE中的價值,同時評價EGFR-TKI的有效性。發現MPE是一種可信的腫瘤組織突變外源物,MPE可以提供EGFR基因突變對EGFR-TKIS治療由肺腺癌患者的決定,即使在組織和等離子體都可以獲得[23]。
四、臨床治療發展趨勢與思維方法討論
原發性未知轉移癌(CUP)是指一組在轉移部位被組織學檢測到但原發部位未知的異質性腫瘤,盡管經過了徹底和廣泛的醫學評估。它們占所有侵襲性癌癥的4%~5%。超過一半的患者將被確診為有多處轉移的腺癌。大約11%的MPE是由CUP引起,第一步應該是通過規范的診斷測試完成廣泛的醫學評估。胸腔穿刺是區分腫瘤性和副腫瘤性積液的必要條件。如果最初的病理沒有顯示或者組織產量低,則應考慮額外的組織取樣方法。液體細胞學和胸膜活檢標本的免疫組化檢測可避開原發性惡性腫瘤并指導治療,因為這些病例大多被認為是肺癌。隨著基因導向療法和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出現,有新的療法正在考慮這些患者[24]。
惡性胸膜間皮瘤(MPM)是一種侵襲性腫瘤,胸腔積液(PE)可以細胞學檢查診斷MPM。作為MPM的新生物標記物,MicroRNAs已經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靶點。MPM研究報告稱,分析的可變結果主要集中在從小患者隊列收集的組織上。最近,研究了微小Micro-RNA在PE細胞學標本中的診斷潛力。作為細胞學分析的補充,miR-21和miR-126被鑒定用于區分MPM和反應性間皮細胞,miR-130a用于區分MPM和肺腺癌。然而,miR-130a的表現并不比免疫組化診斷好,而且由于只分析了一定數量的microRNAs,更有效的生物標記物可能被忽略了。miR-143、miR-210和miR-200c先前被證明在MPM組織中異常表達。這些microRNAs在MPM中可能具有重要的生物學意義,因為它們被預測調節信號通路(ERK5、EGFR、Bcl-2和Wnt),已知它們在該疾病中起作用。因此,miR-143、miR-210和miR-200c也可能是MPM的新治療靶點。PE液與MPM細胞直接接觸,是MPM細胞釋放microRNA的來源。microRNA特征需要在更大的患者隊列中進行檢測,并且考慮到MPM是一種相對罕見的腫瘤,這可能需要多中心協作。開發一種更簡單、更快速的MPM診斷測試可能有助于早期治療和改善患者預后[25]。
MPM與轉移性胸膜腺癌的鑒別診斷對惡性胸腔積液患者是一個挑戰。隨著MPM發病率的不斷增加,MPM已成為近年來外科病理學家面臨的主要問題。免疫組化為鑒別MPM與肺腺癌提供了重要指標。免疫細胞化學標記物(CEA、E-cadherin、Ber-EP4、calretinin、HBME-1、P53和TTF1)被用來區分間皮瘤和腺癌。研究發現HBME1在所有腺癌患者中均為陰性(100%),但在所有間皮瘤患者中均為陽性(100%)。腺癌患者(100%)的calretinin結果均為陰性,而間皮瘤患者(100%)的calretinin結果均為陽性。TTF1在8例腺癌患者中呈陽性(61.5%),而在所有間皮瘤患者中呈陰性(100%)。癌胚抗原在7例腺癌患者中呈陽性(53.8%),而在所有間皮瘤患者中呈陰性(100%)。CEA、CK7、TTF1、calretinin和HBME1是肺腺癌和間皮瘤鑒別診斷的標志物,與間皮瘤和肺腺癌的高精度鑒別診斷有關[26]。
結核性胸腔積液(TPE)是結核病流行地區胸腔積液的最常見因素, MPE由于其相似的臨床特征,包括淋巴細胞性胸腔滲出物,常被誤診為TPE,新的胸腔積液生物標志物將有助于TPE和MPE的鑒別,目前的證據表明,Mtb感染可引起感染部位IFN-γ反應升高,而胸膜IGRA可作為TPE診斷的有用佐劑,特別是與ADA和CEA檢測相結合,為TPE和MPE的鑒別提供一種快速、無創的方法,與常規檢查(包括微生物檢查和胸膜活檢)相平行[27]。
在晚期NSCLC患者中,在50%以上的腫瘤細胞中P-L1陽性表達,pRimuliMub已成為一線治療的標準。研究表明,接受包括貝伐單抗在內的藥物聯合治療的患者骨髓間充質干細胞較少,治療后1型輔助性T細胞和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的數量與未接受藥物組合的患者相比更大。認為這些療效是由貝伐單抗治療引起的MSCs減少的結果,可能導致有效的抗腫瘤免疫的恢復,包括PD-1/PD-L1檢查點抑制劑和針對VEGF/VEGFR的藥物在內的藥物聯合治療包括NSCLC在內的多種癌癥的臨床試驗正在進行中。這些未來的研究可能有助于闡明這種現象背后的機制。總之, MPE的存在是晚期NSCLC患者抗PD-1抗體療效的負性預測因子。因此,需要對接受抗PD-1抗體的患者進行MPE新治療策略的評估[28]。
與單獨使用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劑相比,聯合使用表皮生長因子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和貝伐單抗有望延長NSCLC胸腔積液或心包積液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已報告奧西米替尼加貝伐單抗聯合治療的Ⅰ期臨床試驗數據,并證明其安全性,但療效仍不清楚,特別是在胸腔積液或心包積液患者中[29]。這是一項正在進行的單臂、前瞻性、開放性、多中心、Ⅱ期試驗,旨在評估奧西米替尼聯合貝伐單抗治療未經治療或復發的NSCLC、胸腔和/或心包積液的表皮生長因子受體突變陽性患者的療效和安全性。每天口服1次奧西米替尼,劑量為80 mg, 21 d為一個周期。貝伐單抗15 mg/kg將在每個周期的第1天滴注。治療將繼續進行,直到進展性疾病或任何中止標準得到滿足。主要終點是1年的PFS率;次要終點是有效率、PFS、總生存率、不需要胸膜/心包引流的生存率和安全性。奧西米替尼加貝伐單抗聯合治療有望延長PFS,減少不良反應。
盡管目前能夠提供有效的全身和局部的細胞毒性和免疫療法,但仍然缺乏有效治療MPE的方法。我們認為胸膜腔,由于間皮提供的物理屏障,就像一個生物反應器,癌細胞、TAM、PIT和基質相互作用。傷口愈合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濃度以及由這些多途徑反饋相互作用引起的環境極化促進了EMT和侵襲性腫瘤行為,并通過多種不同且可能協同的機制阻礙了抗腫瘤免疫效應器的反應。胸腔內給藥的好處是,高分子量的生物制劑被隔離在胸膜腔中,其機制與允許高濃度局部分泌的細胞因子積聚相同。因此,當系統性給予時,具有不可接受的劑量限制毒性的再極化處理組合,當在系統劑量的一小部分直接給予胸膜空間時,可能具有更可接受的毒性譜。近十年來腫瘤免疫治療的顯著進展要求我們設計新的方法來治療而不是減輕MPE。認識到胸膜腔是一個隔離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有效的抗腫瘤反應所需的所有成分都存在,但被要求進入傷口愈合模式,局部治療結合免疫檢查點阻斷和治療效應細胞可能足以使嚴峻的臨床形勢轉變為治療優勢[8]。
在臨床MPE的治療中,無論是中醫治療,還是西醫治療MPE的都有一定的優勢與不足,對于臨床診療MPE無明確的臨床路徑可循,如何辨證論治提高療效,探索安全、有效、經濟的中西醫結合治療MPE治療方法,獲益于MPE患者將具有深遠的臨床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