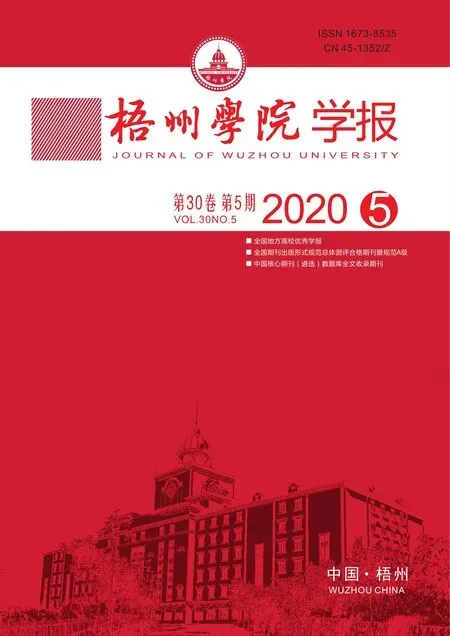苗族“拉鼓”儀式的文化功能與社會功能闡釋
石子健
(南寧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1)
“拉鼓”在苗語里叫“希牛”。“拉鼓”儀式是苗族人民祭祖求吉驅邪的活動,以血緣為紐帶的祭奠活動。主要流行于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和三江侗族自治縣,而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桿洞鄉堯告村的三百堯告苗族“拉鼓節”最具代表性。“拉鼓節”一經確定舉辦,舉辦方幾乎“傾巢出動”而牽連周圍所有苗寨的苗族民眾,并且吸引很多的游客及觀光者,參加活動上萬人以上,堪稱“苗族民間大狂歡節”。由于苗族沒有文字,拉鼓始于何時,我們尚未知曉,但在筆者的調查中,從村民口述中可以推斷,“拉鼓”至少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由于特殊歷史原因,拉鼓這一節日于新中國成立后暫時停歇了很長的時間,幾乎處在休眠的狀態。20世紀80年代后又開始復蘇,國家開始重視傳統文化,與當時被全盤規劃為封建迷信打入深淵的“廟會熱”同步復興、發展,“拉鼓”文化至此也光明正大地活躍于苗族社會中,成為了苗族正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苗族“拉鼓”習俗已經被自治區列為非遺項目名錄。
從筆者檢索的文獻看,對于融水苗族拉鼓的研究甚少,而且主要是對拉鼓作用的一些研究,且都是整體描述“拉鼓”儀式及其文化的。如,錢應華等認為“拉鼓”儀式活動“是以拉鼓、蘆笙踩堂、斗馬等傳統競技為核心內容,融傳統體育、宗教、服飾、歌舞、文學、飲食、經濟等文化為一體,通過競技、儀式、表演、交流等符號活動模式達到一種綜合效應的民俗喜慶集會。它歷史悠久,產生于廣大苗族人民的生產與生活之中,承載著苗族人民數百年的歷史記憶與聰明才智”[1]。而且“以體育人類學的視角,在文獻資料調研和深度訪談的基礎上,對拉鼓儀式活動內容、組織形式以及功能的現代性變遷進行了探討,認為拉鼓儀式完成了從祭祖到世俗的轉化過程,并已深深融入到當今人們的生活之中”[2]。已有的研究雖然對拉鼓有了一些成果且開始從體育人類學視角來分析,但總的是基于整體的概述,主要是對整體文化、功能等進行論述,缺少系統分析調查。為此,筆者以在堯告村大寨屯2018年10月17~20日融水縣桿洞鄉舉辦“2018年融水縣第四屆三百堯告苗族拉鼓節”的田野調查所獲得的一手資料為基礎,以“拉鼓”儀式為突破口,再次對苗族“拉鼓”儀式以宗教人類學及民俗學理論為理論支撐進行更為深入的剖析。在對苗族“拉鼓”儀式的文化功能與社會功能闡釋中,發現儀式背后實質是苗族文化的踐行,且儀式最終的目的是實現對苗族社會的控制。從儀式文化展演中不僅可以窺探出苗族對超自然世界想象及其能“自圓其說”那一套詮釋,從中了解苗族的文化屬性及其苗族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心態,還能總結出“拉鼓”儀式得以傳承至今的文化因子,對傳承和發揚“拉鼓”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堯告苗族“拉鼓”儀式概述
“拉鼓”節作為苗族的傳統節日,“拉鼓”在苗語里叫“希牛”,是以祭祖為中心的活動,只要有一村作為東道主舉辦拉鼓節時,附近村的各族民眾及其親友都來“吃鼓”。如,2018年10月17~20日在三百堯告主辦的“拉鼓節”,附近各村寨早早就集結于堯告大寨蘆笙球場。清晨,鼓主和鼓師頭帶白寒蛋殼,手持拐杖,身穿長袍,莊嚴肅穆地將苗族民眾引到山上,并通過相應的祭祀取回楠木,制成“拉鼓”,期間他們邊走邊唱歌,由有秩序而又有“等級”似的隊伍完成整個過程,歌唱的歌詞內容主要為懷念祖先的公德及敘述民族來源和遷徙過程,其中也包括了稻作文化、生產勞動及倫理道德,等等。在踐行完所有儀式祭祀后,在鼓頭師傅的指引和指揮下,鼓師們齊聲祈禱,緩緩從祭祀籃中拿出盛滿燒酒的杯子在地上澆灑幾下,然后燒香燒紙,開始向天地祭拜,祈禱風調雨順、幸福安康。
(一)儀式前準備
在開始進行拉鼓儀式前,需要準備的集體工作和個體工作。集體工作主要有:第一,村委工作人員和寨上有權威的族長進行活動商討并寫好策劃案,定良辰吉日、定鼓師和鼓頭。鼓師,也稱陰陽師,是能和祖先和神靈溝通交流的人,他能幫助人們向自己的祖先以及各路神靈奉上酒肉和禮品,也能幫人們向祖先和神靈對話。鼓頭,是拉鼓節的帶頭人。鼓頭的選拔條件是非常嚴格的,首先,道德品質優良,在寨子上受人尊重;其次,家庭條件比較優越,經濟條件在寨子上處于中上水平;再次,必須是已婚人士,夫妻雙方身體健康,有兒有女,并且雙親健在。按照這幾個條件來評選,寨上有多名男子符合條件,因此還要群眾投票來決定最終人選。第二,定制蘆笙。蘆笙是苗族人特有的傳統樂器,有小、中、大等不同的樣式,每個參加活動的寨子都要準備自己的一堂套蘆笙,一堂蘆笙一般都是由單數組成。第三,準備集體物資,包括宴會上要用到的肉類、菜類、米飯、酒水和餐具等。
個體工作就是各家各戶自己要準備一些物資。各家各戶的物資準備主要是祭祀用到的和給親朋好友吃的酒肉。在活動期間,有些外來游客或者周邊親戚需要住宿,因此還要準備住宿物資。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婦女們要準備好在節日期間要穿戴的服裝和飾品。服裝分為男裝和女裝,男女裝的布料都是婦女們通過傳統手藝用藍靛染成的苗布,男裝比較單一,沒有花邊;女裝有花邊,女裝的花邊是根據個人的喜好而縫制上去的,有些花邊比較簡樸,有些花邊比較艷麗,但總體看上去大多女裝都是做得比較簡樸而端莊,具有復古感。飾品有戴在頭上的,有掛在脖子上的,還有戴在手上的,它們都是由銀做成。另外,男女也都會背上自家準備好的斜跨包,斜挎包也是由布做成的,包的表面繡上一些鳥和花草的圖案。
(二)儀式過程描圖
堯告拉鼓節流程主要有“醒鼓”“接鼓”“葬鼓”。主要程序為醒鼓、砍鼓木、斷木鑿鼓、拉鼓、大型蘆笙比賽、蘆笙踩堂、葬鼓。
醒鼓,它是揭開拉鼓節的序幕,標志著拉鼓節儀式正式開始。農歷九月九日,“三百堯告”人民即堯告村和小河村的村民帶上自家釀的酸魚酸肉、現殺的雞鴨魚肉、糯米飯和自釀的甜米酒等飯菜帶到指定的地點舉行醒鼓儀式。醒鼓儀式由鼓師和鼓頭共同主持,首先把酒肉和米飯擺放在固定位置,然后鼓師一邊燒香和燒冥紙,一邊念著祭祀鼓的詞,醒鼓儀式做完后,鼓民們紛紛拿出自家帶的酒肉擺好,大家一起就地就餐,吃飽喝足,接著吹蘆笙比響和蘆笙踩堂。
接鼓,醒鼓的第二天就到接鼓儀式,接鼓儀式包括砍鼓木、鑿鼓、拉鼓、祭鼓、制鼓等內容。第一,砍鼓木。砍鼓木前也要擺些許酒肉和米飯在鼓樹旁邊,由鼓師祭拜古樹完畢并向古樹砍三刀后,再由鼓頭和其他年輕有力的男子用斧頭砍倒古樹。把古樹砍倒后,取約43厘米長的根部來制鼓,接著把鼓木從山林里拉到巴天山鼓場。拉鼓木也是有講究的,先由拉鼓寨主一方的青年男女在鼓木的前面往前拉,由外地的親朋好友在鼓木的后面往后拉,雙方假裝拼命搶鼓,而鼓師和鼓頭唱著拉鼓歌,眾人也跟著唱起來,場面震撼,熱鬧非凡。第二,鑿鼓。鑿鼓是由鼓師對鼓木的兩頭進行簡單的制作,以便能用樹藤綁實。鑿鼓完后,鼓頭把用竹子制成的酒杯擺在鼓樹上并把酒倒滿,鼓師念上幾句祭鼓詞,鑿鼓儀式才算完成。第三,拉鼓。這是把鼓木從巴天山鼓場拉回寨上,還是由拉鼓寨主的青年男女和外來親朋好友以拔河式的形式進行拉鼓木。在快到寨子上的時候,親朋好友一方的人故意用力拉,并把繩子掛到樹上,不讓對方把鼓木拉進寨子,除非寨里的青年男女有意讓外來的親朋好友留在本寨子做客才會松繩子。這是一個增進感情和增加娛樂氣氛的儀式,最終雙方達成協議一起把鼓拉到寨子的蘆笙廣場。
葬鼓,也稱丟鼓,送鼓。葬鼓并不是把鼓埋葬起來,而是把鼓帶到指定的地方安置,永不動它,任它腐朽,回歸自然。葬鼓儀式由寨上年輕有力的三男四女扛在肩膀上并走在隊伍最前面,后面跟著的是鼓師、鼓頭和寨上的鼓民,鼓師一路上吹著小號的蘆笙,笙歌悠揚。一直走到指定的地方把鼓安置好,鼓師再次起頭吹蘆笙,寨上的男子也拿著小中大號蘆笙跟著吹起來,以祈禱祖先保佑、祈求風調雨順,以及慶祝節日的喜慶和感恩大自然給予的一切。
在葬鼓儀式期間,會舉行拉鼓蘆笙踩堂,它是拉鼓節最重要的一項活動。這一屆的拉鼓節由大寨片、田邊片、小河片共三堂蘆笙,每堂蘆笙有100~120支。拉鼓蘆笙踩堂的活動順序為開傘儀式、“務夏”看鼓、“丟嘎鈴”儀式、“大灼”儀式和“巴比”儀式。
開傘儀式。大寨片的蘆笙隊、田邊片的蘆笙隊、小河片的蘆笙隊集合在本寨指定地點,然后各自出發到大寨屯附近的山坳上等待開傘儀式。開傘儀式由已安排好的蘆笙隊吹完三曲蘆笙后即開傘。鼓師穿著傳統制作的鼓服,撐著半開的黑色傘,用傘遮住頭部,7位鼓頭身持大刀跟在鼓師的身后保護鼓師,接著是吹蘆笙男子和踩堂女子。有些人手撐著樹枝,還時不時跟著鼓師和鼓頭大聲叫喊,其叫喊聲是歡快的,伴隨著蘆笙曲的節奏感走向山坳跟眾人集合。到達山坳后,鼓師進行合傘儀式。開傘意旨驅趕一切妖魔鬼怪,瘟疫疾病;合傘意為收攏“三百堯告”人民的靈魂帶回家。合傘儀式結束后,眾人就地簡單就餐,接著三隊蘆笙隊進行蘆笙比響,旁邊圍著踩堂姑娘偏偏起舞,曲聲動聽,舞姿優美。
“務夏”看鼓。“務夏”是白苗語音譯,意為古代人的模樣。“務夏”是由15~23位青年男子和1位婦女扮演的,他們都穿著破破爛爛的舊衣服,帶上丑陋的面具,把手腳抹黑,不能說話,隱姓埋名,原來認識他的人也不會認出來,婦女扮演的“務夏”身上背著一個“孩子”。“務夏”雖然外表裝扮很丑陋,但是他們內心是善良的,按古老的說法,“務夏”是堯告人民的守護神,它能驅趕病魔,帶來吉祥,老人遇上“務夏”會長命百歲,小孩遇上“務夏”會健康快樂。“務夏”是跟著開傘儀式的隊伍走過來的,他們走進人群向人們討要紅包,方便的客人會給一些零錢;遇上漂亮的姑娘,“務夏”會主動和姑娘握手并討要姑娘腿上穿戴的彩帶,一些有心的姑娘則會主動取下彩帶送給“務夏”。
“丟嘎鈴”儀式,“丟嘎鈴”是白苗語音譯,直譯為踩鬼蘆笙堂,這個儀式是鼓師和鼓頭在鼓屋里舉行的。到傍晚的時候,“三百堯告”所有村寨每家每戶不能生火和點燈,必須保持一片漆黑。鼓師和鼓頭在鼓屋的火堂上架著一個鍋頭,鍋里盛有一些蝦魚,放著一對用麻樹做成的筷條,7個鼓頭在火堂邊圍著鍋頭像青蛙似的跳著,當誰跳到筷條方位時就用筷子挾一口魚蝦放在嘴里,一連跳7圈。跳完就分兩個地方吃鬼飯,每個鼓頭分得7袋糯米飯(每袋飯是2.5kg米)和7條酸魚及一些雞鴨肉。4袋飯拿到蘆笙坪西面大樹下吃,3袋飯留在鼓屋吃。鬼飯一定要吃完,不能剩也不能丟掉,所以每個鼓頭都會叫上寨里的兄弟姐妹一起來把飯吃完才回家。
“大灼”儀式和“巴比”儀式。當天拉鼓蘆笙踩堂結束后,“三百堯告”即現在的堯告、小河2個村的25個苗寨都是主人,他們把外地的客人當為尊貴的來兵,家家戶戶熱情款待,外來的客人則隨意走進一家屋里作客。當天,19:00~20:00期間,家家戶戶的大人小孩手持燃燒著的柴火望屋外舉著,過幾分鐘柴燒完則結束。待晚餐做好后,主家按照傳統的祭祖儀式,在地上擺上美味佳肴敬祖公,同時主家原來備有一壇好酒等著“巴比”儀式,主人將酒壇拿到飯桌旁邊,然后請1位親戚或者客人來揭開酒壇蓋,把酒篩滿3個碗,每個酒碗上面架著1雙筷子,在筷子上放1條酸魚。主家的意愿是要這位客人喝干3碗酒,如果客人確實不勝酒力,起碼也要干1碗酒。主人將那3條酸魚打包給揭酒壇蓋的客人,客人會回敬一些酒錢,儀式就此結束。
二、“拉鼓”儀式的文化功能:儀式背后實質是苗族文化的踐行
涂爾干認為“宗教儀式是行儀式者賴以與神圣發生聯系的一組實踐”[3]39-40。格爾茲說“通過儀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來,變為同一個世界,而它們構成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儀式”[4]。苗族的“拉鼓”儀式過程都是與神圣發生聯系的,儀式通常是伴有神圣發生。“拉鼓”儀式通過對祖先傳承下來的傳統的遵從,不知不覺中恪守自己民族信仰,也是苗族對祖先的懷念、不忘本源的族性特征的產物。在儀式過程中,“不僅體現了普通民眾對于超自然世界的想象與詮釋,也可以從中透視一個族群的文化屬性,反映一個族群性格和文化心態”[5]。
(一)具備“巫”特征的文化
“儀式,通常是與宗教或巫術有關的按傳統所規定的順序而進行的一整套或一系列的活動”[6]。巫從產生、形成、發展到演變,都在人與神之間發生。在堯告苗族社會“拉鼓”儀式是巫文化的一種獨特存在方式。當地苗族(鼓師)用有形的以儀式、道具、歌唱的表演形式去與無形的神靈世界打交道,而這種媒介主要集中在一種人的身上,這便是巫。“拉鼓”作為一種祭祖儀式,將祖先當作自己最大的神,祖先作為“神”的化身,具有驅邪避災的功能意義,人們相信,只要舉辦一定的儀式祭祀“神”,通過巫師來溝通了“神”,借來“神”的力量,為人們消災降福,從而使苗族各村寨獲得神的呵護。“拉鼓”儀式在展演的過程中,鼓師操持著與神溝通的各個過程,借助鼓書、經書、傘及其祭祀食品的媒介溝通方式,各鼓手手持大刀配合鼓師完成相應的儀式,在鼓師的指引下,進行人神溝通,祈求神的呵護,使家族興旺,苗族社會穩定安康。
(二)具有“儺”性質的文化
儺是以鬼神信仰和驅邪祈福為核心的文化,民間有“戴上面具為神,脫下面具為人”的說法。“拉鼓”儀式過程中的“務夏”看鼓環節,其實就是對苗族“儺”性質的文化展演。“務夏”身穿破爛的舊衣服,配上丑陋的面具,意為古老之意,“務夏”作為堯告人民的守護神,它能驅趕病魔,帶來吉祥,老人遇上“務夏”會長命百歲,小孩遇上“務夏”會健康快樂。“務夏”是跟著開傘儀式的隊伍走過來的,苗族民眾對它極其敬重并“唯命是從”。歷代形象的面具,具備以“肖神”為基本特征,以大自然的神格化與神靈的人格化,兩者相互融合交織在一起,造就了苗族特有特征的自然與人結合神韻的儺面具,戴上面具者成為了人神角色轉換的邊界而被奉為神物。
(三)傳承和發揚地祖文化
苗族以“萬物有靈觀”為核心,但祖先神卻是苗族最大的神。“拉鼓”儀式是祭祖儀式,主要祭拜祖先神。也就是說,苗族對自己祖先的懷念、感激及敬重之情,情感凝聚升華將祖先奉為神。祭祖其本質是教人返本報始,知恩圖報,孝為祭祖的文化精神,具有教育的功能。《論語》云:“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民俗主要表現為民眾心理精神的一方,具備對民族風俗習慣、民間儀禮、民間信仰等民族文化現象。民間各種活動的形成原因主要由于民族的社會結構、經濟生活以及風格習慣等的互動。堯告苗族以“拉鼓”儀式為對象,通過祭神娛神的形式來祈求神靈祛災降福、人寨安康的一種民間信仰的民俗事象,主要表現為苗族的對超自然世界的聯想,以儀禮活動的方式來表達對區域諸神靈的信仰,“拉鼓”儀式作為一種祖先祭祀活動,儀式過程中各種儀式活動表演,實質上是對祖籍地文化的傳承,特別是在梁、韋兩姓在儀式中的地位,可以窺探出兩姓為主要姓氏祖先的代表,周圍村寨苗族一同參加,有對祖先的追憶,對敬重祖先的群體心理,將祖先視為民族最大的神,對祖籍地的傳統文化具有世代相傳的推動作用。
(四)重構道德文化社會體系
儀式作為民族群體在生產生活中形成的具有“規定性”的行為方式,在展演中,能夠激發這個民族某些心理狀態,從而自覺地維持現有的或者重塑符合該群體道德文化體系。按照涂爾干的說法,“儀式首先是社會群體定期重新鞏固自身的手段”[7]。儀式作為信仰展演的主體,必須存在于族群記憶中,使集體意識在儀式中獲得認同。儀式可以在周期性內反復進行文化展演,使群體族群在思想和身體踐行上保持一致,并傳承下去,個體在社會本性中得到進一步加強。之后,個體在儀式中群體信仰和意識得到統一,使苗族族群在道德上的回歸或升華。堯告苗族“拉鼓”儀式中的“鼓歌”“經書”,其內容即是教育苗族民眾認同的道德倫理,并以神諭規定個人修養,重溫祖先傳承下來的被日益淡化的人生做人道理和人生價值取向。在該神圣化的場所中修煉自己的心性,極力教育苗族熱愛自己的家鄉,同時自覺以俗規道德的標準嚴格規范自己的行為,向苗族所謂的“天理”目標邁進。
三、“拉鼓”儀式的社會功能:儀式最終目的是對苗族社會的控制
“拉鼓”儀式屬于一種民間宗教信仰的儀式。作為宗教儀式活動,不僅可以透視一種文化屬性,還具有許多實際的社會功能。儀式所具有的多重功能,在個人層面上或群體還是社會層面上,成為情感溝通的渠道,并在儀式活動的互動中表達情感,引導和強化行為模式,或恢復和諧與平衡,從而達到對社會控制的最終目的。
(一)強化了苗族民間宗教信仰
涂爾干認為“宗教現象很自然的分為兩個基本范疇:信仰和儀式。信仰是信念的狀態,主要由表象組成;禮儀則是一定的行動方式。這兩類現象之間,有把行動與思想分開的根本區別”[3]31。這說明了信仰與儀式既相互區別又密不可分的關系。在儀式中文化得到展演,普通民眾獲得了信仰,正如格爾茲所說的“文化展演”(cultural performance)中對儀式性質及其所蘊含的象征意義所詮釋的那樣,并認為“對宗教觀點的展示,形象化與現實,就是說,它不僅是他們信仰內容的模型,而且是為對信仰內容的信仰建立的模型。在這些模型的戲劇中,人們在塑造他們信仰的同時,也獲得了他們的信仰”[8]。“拉鼓”儀式雖隔5年左右才展演1次,但每次展演苗族全民眾都參與其中,在儀式過程的互動中便再次強化他們的信仰,更加恪守他們的信仰。功能主義認為“儀式有助于個體想到圣潔領域,復興和加強對于這個領域的信仰”[9]。儀式作為信仰的外圍表現象征,體現為人神互動關系的場所。主要在鼓師全程操持下,鼓頭、普通民眾穿戴著自己民族的服飾參與其中,此時儀式已被無形之中將人們帶到一個自覺規范模式及統一認同的信仰生活之中。民間信仰與關于教義知識在儀式中被往返重復展演,對苗族民眾產生一種宣揚自然是肯定的,但主要還是增強了苗族各村寨的聯系和內聚力,并從本質上起到了強化與鞏固信仰的作用。
(二)儀式中祖先神對當地苗族的威懾力和權威的確立
“拉鼓”儀式中,祖先神在此特定場域里,成為苗族最高的統領神。對祖先神如此敬重,是基于祖先神在苗族遷徙歷史中形成的一種威懾力,并且在當地成為苗族心中烙印下來的神格功能,祖先神在苗族民眾心中確立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并規定著苗族必須身體力行認真實踐。對祖先神在信仰與精神上的高度依賴,苗族社會各個階層都有求于祖先神,而與苗族生活生產有直接關系,所以倍受信崇。“儀式一經形成,往往與社會機構相輔相成,構成了社會機制的一部分。一方面,它成為社會控制的有效力量;另一方面,儀式的形式本身也轉化成為一種權力”[10]。苗族社會就是依賴于“拉鼓”儀式祭祀祖先神為主,從而確立了祖先神為苗族最大的神,由此在苗族民眾中起到威懾作用來規范苗族民眾的行為。“拉鼓”儀式,主要是通過鼓師操持全局,帶領苗族民眾進行莊嚴而肅穆祭祖儀式活動。在以祖先神為主的神圣場域內,基于這一全民信仰,苗族民眾作為身體力行者,積極參與到儀式活動中,在堅定維護這一傳統信仰的同時,成為了恪守這一信仰者,在此神圣場域中,權威得以更穩固的確立。
(三)實現“等級”差異,有利于對苗族社會的管理
在“拉鼓”儀式文化展演中,無形之間確立了一種“等級關系”,從在場或家庭中都有所體現。儀式過程中,以師公為操持“大局者”、鼓頭及其長子成為領頭人,帶領并引導苗族進行“拉鼓”儀式。在此場域,鼓師權力很大,是神的“代表者”,并按照神的“圣旨”,帶領并按照傳統進行祭神、娛神等儀式活動。此時的儀式不僅僅體現苗族族群對自己所創文明的認可,而且關聯著苗族社會秩序的重構,及其在儀式中彰顯的個人等級身份的強化。“拉鼓”儀式作為苗族族群的一種社會性或會眾性的儀式活動,儀式中的苗族族群傳統文化得到展演,并通過鼓師作為媒介以及敬神、拜神、供神等方式,與神溝通,儀式中更多的是追憶祖先,使群體自身在儀式中得到了強化,促進其價值觀念重組,使價值觀念得到再次肯定。通過儀式,將苗族社會群體中的不同個體暫時或者永久“捆綁”在一起。鼓師、鼓頭、長子、老者以及追隨者先后順序及其在儀式中的作用,似乎在肯定這個團體關系的同時,也在確定一種等級觀念,儀式中各個組成部分都得到體現、堅持和加強。但凡屬該族群的人都有義務去遵守該象征稱號及其族群社會中所規定的各種“等級”身份。通過人神溝通并按照神的旨意,在“拉鼓”儀式中規定有著“老者為先、長子為先”的傳統并確立自己“字輩、輩分”等,確立自己在儀式中的身份,按照“字輩”來履行儀式中的職責,而且這種“字輩、輩分”等排行實質是一種等級身份的識別體系,有利于對苗族社會的管理。
(四)實現族群文化認同,實質是對社會的控制
文化表演往往是指“在這樣的一些場合,我們作為一種或作為一個社會對自我進行反思并進行概定,將我們共同的神話或歷史戲劇化,以不同的方式表現自我,最終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變而在其他方面卻依然故我”[11]。而“儀式是一個民族觀察和組織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是按計劃進行的或即興創作的一種表演,通過這種表演,形成了一種轉換,即將日常生活轉變到另一種關聯中,而在這種關聯中,日常的生活被改變了”[12]。“拉鼓”儀式的舉行,實現了三百堯告苗族及其附近村寨得以統一大交流,以祭神、拜神、供神、娛神、神人共歡等形式,實現了從“日常生活到與祖先、靈魂、自然神發生的儀式場域的轉換。這一轉換體現的靈魂觀念與祖先崇拜是文化表演所要表現的文化內涵,而基于此這一文化表演所形成的是一個世界與現實世界溝通交流的歡鬧的場域”[13]。“拉鼓”文化作為一種苗族民間特有信仰文化,等同于苗族民間信仰的符號,和其他民族的信仰一樣,對區域范圍內生活的族群的社會秩序起著重組和整合的作用,對延續與鞏固苗族傳統文化發揮著至關重要作用。在儀式中,不但成為凝聚苗族團結的“黏合劑”,而且強化苗族族群文化內心深處意識中文化的象征。“拉鼓”儀式過程中的“鼓歌”及經書,也似乎在反復地警醒苗族,勿忘本,要恪守祖姓及其敬重自己的祖先。因此,在“拉鼓”儀式中所展現出來的苗族特有文化色彩及其表征,聚集祖先固有的民族文化,促進建構苗族族群文化及其認同,最終實現對苗族社會的控制。
四、結語
綜上所述,從堯告苗族的“拉鼓”儀式來看,既有其文化功能,也有多重的社會功能。“人們的獻祭是行為,但其文化的動力是象征和精神上的,祭祀是在信仰的世界里運轉的。在這種氛圍里,人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對神圣和神圣生活中的一種隱喻,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14]。在“拉鼓”儀式文化展演過程中,我們看到堯告苗族普通民眾對自己民間信仰如此恪守,他們對于超自然世界的想象和詮釋在儀式展演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體現出苗族族群專屬的文化屬性。在此神圣的場域內,族群內部互動中更多的是體現出苗族族群的性格和文化心態。“拉鼓”儀式中所體現的多重社會功能,無論是從個人還是族群層面上,甚至社會層面上看,儀式活動中的互動交流是苗族情感真切表達,通過這樣的情感表達方式來引導并強化苗族民眾行為,使其社會恢復至平衡狀態,從而達到對苗族社會的控制。
儀式中各個文化展演的部分構成了一個社會組織的有機統一體,目的是為了共同維護現有的社會體系。隨著城鎮化的推進,似乎沒有使這一傳統文化衰落,而是在通過與異文化的搏擊中刺激該傳統文化,凸顯其極強的生命力,同時促進了該傳統文化復興、傳承,即使地處偏遠的東南少數民族的村落也不例外,在新舊文化碰撞中,尋求自己的生存道路。“拉鼓”儀式作為苗族一種專屬的民俗文化現像,在異文化的入侵下,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苗族“拉鼓”文化不斷地探尋自己的生存之路,也成為了“拉鼓”文化的外驅力。“拉鼓”作為苗族特有的文化,傳承道路艱辛,是苗族生產生活中的產物,成為苗族創造、享用并傳承下來的文化的精華。苗族“拉鼓”文化能光明正大地在日常生活中活影活現,是苗族恪守自己民間信仰的表現,更是體現出“拉鼓”文化在苗族社會里蘊藏著深厚的文化價值底蘊。基于此,筆者認為一種文化能得以傳承,必定有其外驅力和內驅力的結合,想要對一種文化進行探討,不要只注重人的主體作用,而是要統籌兼顧。苗族“拉鼓”文化,其儀式作為主體,俗與民的行為貫穿儀式始終,構成了完整的“拉鼓”儀式。正如烏丙安所言,“民俗學的研究理應以研究這個民俗的‘主體’為中心,即以研究習俗化了的俗民個體與俗民群體為對象。對一切民俗事項的調查研究,都應當服從于研究這個‘主體’,而不是只見‘俗’而不見‘民’。民俗學的‘主體’研究,應當是21世紀民俗學充分展現人文精神的重大課題”[15]。“拉鼓”文化能成為一項非遺項目,足以說明其價值。而地處偏遠且交通不便的堯告苗族“拉鼓”文化卻很少被受外界所關注,好在“拉鼓”以其自身超強的生命力及苗族的“愛戴”,還保存著。但是,在城鎮化急速推進的今天,苗山想要留住“拉鼓”,保存好這種文明并將其延存下去,需要更多專家學者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