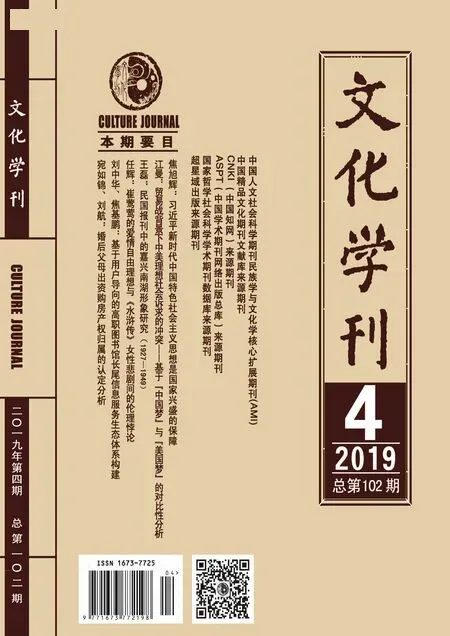托尼·莫里森《所羅門之歌》的生態女性主義解讀
吳 蕾
《所羅門之歌》是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在該著作中,作者對于非裔美國人的生存情況進行了獨特的思考,主題宏大。《所羅門之歌》中更是體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揭示了自然同女性之間的聯系。
一、《所羅門之歌》中生態女性主義的體現
(一)黑人女性與自然
在《所羅門之歌》中,黑人男性奶娃是小說的主人公,但在小說中,女性人物卻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品當中重點描繪的幾名女性,在深受種族歧視以及男權制戕害的同時,也為主人公奶娃的成長提供了重要的幫助,也正是她們給予的愛,使奶娃獲得了真正的成長。同時,該作品中也充分展現了黑人女性對于種族歧視以及男權制的隱忍和憤懣,表達了她們對打破種族間、男女間隔閡,對和諧自然家園進行建立的追尋及美好愿景。生態女性主義的首要內容是女性與自然的認同[1]。可經濟學家認為,女性是維持人類社會的“生命給予者”“養育者”和“主要力量”。她們來自自然,與自然關系密切。奶娃的姑姑彼拉多就是象征自然的人,出生之前,她的母親便去世了,她是摸索著自己出來的,她沒有肚臍眼,這在隱喻層面表征她是由自然孕育而來,具有神性。因此,她自由地親近自然,不受父權話語和種族歧視的限制。她將崇拜自然和母系社會的價值觀當作生活的一部分,將自我道德觀建立在關心、愛護和信任上。她認為男女平等,也將人類與自然視為平等的伙伴。與自然一樣,她承載著對個人和人類的愛與責任,幫助奶娃尋根,幫助英雄化解仇恨。
(二)融入自然
人同自然的和諧相處是生態女性主義積極倡導的精神。人類只有關注與其他所有形式生命的相互關聯,才能有效凈化心靈,與自然共存。大自然不僅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豐富的物質資源,也是人精神的歸屬。正因為西方現代科學打破了人類對自然的依賴,使得人類為世間萬物劃分等級,因此,在小說里受到西方現代科學體系影響的奶娃的父親,無論是在文化價值還是思想道德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心理扭曲。他拋棄在現代科學體系下處于劣勢的黑人民族文化,割斷與自然的聯系,最終在權力和種族歧視下自我身份、文化身份混亂,內心空虛。父親被科學從自然中剝離,導致奶娃遠離黑人民族的文化傳統,從小受到白人文化的影響。彼拉多以無私的愛引導奶娃走出狹隘的個人世界,給予他力量。奶娃南下尋找金子,意外得知家族史和黑人傳統文化,并在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中,開始反思自己,開始意識到之前的行為傷害了周圍的女性。此后,奶娃不但積極融入自然,成為自然的一部分,更開始反思自己。他不再自私和不負責任,而是懂得了感恩和如何愛人。雖然主人公沒有找到黃金,但卻在該過程中得到了黑人文明的洗禮,受到了來自文化的啟發,真正獲得了新生。在黑人文化中,自然即是神同人之間交流的媒介。在這次南方之旅中,奶娃了解了他們祖先的奮斗歷程,增進了對民族、家庭的歸屬感,重新回歸到黑人民族當中,凈化了自己的心靈。
主人公在成長的經歷中,女性在其人生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生態女性主義中,女性同自然間具有一定的聯系,其本質是能夠引導男性,使其也回歸到自然中,從而獲得新的生活[2]。在奶娃的成長過程中,正是其周邊女性將無私的愛給予了他,他才能夠下定決心走出原本的環境,去到遠方,積極尋找家族的歷史和傳統文化,并同自然有了親密的接觸。在這個過程中,他逐漸認識到了自己原本所具有的男權思想,經過不斷地回顧和反思后,他終于認識到之前自身的一些做法對周邊的女性造成了較大的傷害,而在經過自然的洗禮、考驗后,他也重新認清了目前自己所承擔的責任,學會了愛別人,從而獲得了內心的和諧。
(三)遠離自然
生態女性主義對西方現代科學觀提出了疑問和挑戰,顛覆了普遍認可的基本價值觀念[3]。就西方現代科學而言,它打破了人類對自然的依賴,并將世界上所有東西劃分成了不同的層次。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順序,對于男性來說,他們同文明、文化以及理性具有密切的聯系;而女性則同原始、自然以及被動具有密切的聯系。正是生態女性主義徹底暴露了西方的科學主義,指出人同自然間應建立密切的聯系與強烈的情感。在小說中,麥肯正是這樣的一個人,為了達到目標而瘋狂地賺錢,通過多種手段積累財富,為了獲得露絲的家產而在沒有愛上她的情況下結婚,不僅沒有愛情,而且也沒有親情,對女兒也沒有給予應有的父愛,使她們每一天都在沒有愛的日子里生活。麥肯從未平等地對待過女性,更多是將其作為自己占有的對象,這也正是其遠離自然后所具有的表現。
二、結語
通過對托尼·莫里森《所羅門之歌》的生態女性主義進行解讀,我們發現這部著作充滿了生態女性主義意識,充分體現了女性對自身與自然聯系的認同,對人類命運的深切關切,同時歌頌了人與自然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