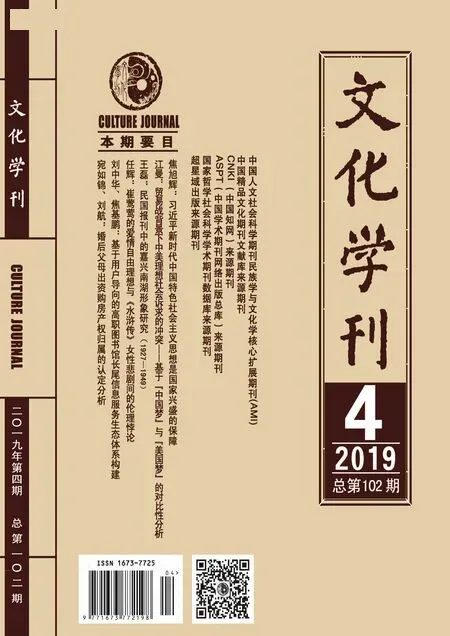《海的女兒》的生態女性主義解讀
廖曉梅
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是世界文學童話的代表人物之一。安徒生童話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兒童可以從他的童話故事情節中體味到快樂,而成年人可以品嘗到其中的深意。《海的女兒》是安徒生童話中最膾炙人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講述了一個悲劇故事:美人魚離開美麗的人魚世界去人類世界追尋王子的愛情,最終化作了七彩泡沫。這是一篇內涵非常豐富的童話。這篇童話譯介到中國已有百年之久,對這篇經典童話,國內學者不斷地從多角度、多側面、多層次進行解讀,主要聚焦于生命意識、形象原型、審美追求、宗教信仰和女性主義傾向等方面。然而,卻少有研究者從生態女性主義角度觀照。本文嘗試從女性和自然的雙重視角來解讀《海的女兒》,通過剖析作品中蘊含的女性和自然、女性和男性之間的關系,展現安徒生隱含的深層復雜的女性關懷和生態意識,發現作者意在重構一個男性與女性、人與自然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社會。
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學批評范式,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是生態學與女性主義的有機結合。1974年,法國奧尼波在其《女性主義·毀滅》一文中首創這個概念,提出構建平等兩性關系和保護生態環境雙重訴求。20世紀90年代中期,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支批評流派呈迅速發展的態勢并衍生出多種流派。盡管流派紛呈,既有一些主張相互補充,也有一些主張相互對立,但是它們觀點都建立在“非二元論”的基礎上,“考慮性別歧視,對自然的控制,種族歧視、物種至上主義。與其他各種社會不平等之間的相互關聯性”[1]。生態女性主義特別尋求普遍存在于社會中壓迫女性與掠奪自然之間的關聯,它反對人類中心論和男性中心論,堅持去中心化,否定人統治自然的思想;并且,它將女性的解放,與不存在破壞的、權力自由的自然-社會建立密切聯系,提出要構建一個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平衡和諧的生態體系的終極目標。
《海的女兒》創作于1837年,它是產生于生態女性主義思潮興起一百多年前的作品,從總體上看不算是經典的生態女性主義作品,但作品中卻以大膽而超前的意識表達了工業革命后人類對自然環境貪得無厭的掠奪破壞的擔憂,和對強權男性意識下女性生存困境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揭示與批判,蘊含著深刻的生態意識和深切的女性關懷。
一、女性與自然:一種獨特的親近關系
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的構建是基于女性與自然本源同構的觀念。由于女性和自然都有創造和養育生命的能力,因此女性與非人類的自然有一種獨特的親近關系。
女性與自然這種獨特的親近關系在《海的女兒》中得到生動的詮釋。女性是“水”和“生命”的同義詞。而大海是自然萬物的孕育者,像搖籃一樣孕育生命。《海的女兒》一開始描繪了一個寧靜、美好的海底世界:“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上,海水藍藍的,就像最美麗的矢車菊花瓣一樣;海水清清的,就像最明亮的玻璃一樣。”[注]文中《海的女兒》引文均引自《安徒生童話》[M].葉君健譯,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這深邃蔚藍的大海深處就是人魚世界。作者用人魚這個非人類物種隱喻女性。老祖母、六個人魚公主、女巫這些女性角色是這個海洋世界的主導。老祖母是那樣的古老,她“是大大值得稱贊的,特別是她非常疼愛她的孫女們”。老祖母充滿慈愛地打扮著女孩們,給她們講故事,開舞會讓大家盡情玩樂。老祖母充分展現了她的母性、人性,在老祖母這樣溫和統治下的海底世界是一個有序的、理想的社會。安徒生在描寫這個海底世界時用的詞匯是蚌殼、水蛇、玫瑰這些富有女性色彩的意象,海底世界是女性的天地,這里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宮殿是由珊瑚礁、琥珀、蚌殼等構成,老祖母和人魚公主們用牡蠣、鮮花等裝點自己。人魚世界里舉行盛大的舞會上發出的絢爛的光芒都是大貝殼、魚鱗發出的自然之光。她們唱著最美麗動聽的歌,在鮮花樹林里盡情玩耍。
大自然是那樣的美好,而生活在其中的女性與大自然是那樣和諧。在安徒生筆下,自然之美和女性之美已經合二為一。海底世界有一種近乎永恒的寧靜的田園美,這里的時間只是單純地流淌著,生活在海底世界的女性的活動就猶如四季更替一樣循環反復,這是一種生態的、和諧的生活節奏。
19世紀是西方海上航運迅速發展的時期,在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觀察和思考的基礎上,安徒生敏銳注意到人類在大肆破壞自然。在他筆下,大海不再平靜了,人類的巨輪在大海上頻繁活動,“海洋的深處響起了嗡嗡聲和隆隆聲”,海底遺留越來越多人類制造的工業產品。大海正遭受著日益嚴峻的破壞。生活在海底世界的人魚也因大海遭受污染而受到傷害。人魚經常被嚇得逃回海底,或者盡量停留在尚沒有人煙的海上,人魚不得不注意避開漂浮在水上的船梁和船的碎片。在童話中,海底世界和人魚在以水手們為代表的人類眼中是沒有靈性的,被動的角色,是死亡的象征。
“自然在西方文明發展史中被視為沒有發言權的他者和被征服與統治的對象,它被迫成為被人類開發的自然資源,用以服務于人的需要和目的。”[2]大多數環境主義者認為,導致當代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是人類中心主義,但生態女性主義者關注到女性和自然的命運是如此相似,因此,她們認為導致當代生態危機的確切根源應當是男性中心主義或者父權制。男性才是征服自然的倡導者、行動者和受益者,而女性被看成是自然資源的一部分,成為征服自然的受害者。“女性與自然被納入統治的框架,被物化,被客體化,成為男性中心主義的‘他者’。”[3]在男權體制下破壞自然的生態平衡與剝奪壓迫女性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著名的生態女性主義者麥西特(Merchant)在《自然之死》中指出:“自然的概念和婦女的概念都是歷史和社會的建構。”[4]
女性自從人類社會進入父系氏族社會之后,遭到嚴重的貶抑并受到無情的控制,淪為被排除在男權中心之外的他者,充當著證明男性存在和男性價值的工具與符號,因此,在父權制的羅格斯中心主義的觀照下,男性與女性,人類與自然,成為對立的范疇與概念,自然與女性同被排斥于主流文化之外,女性被男性貶為自然物,自然則被視作女性。
二、叛離自然:成為男權中心價值觀之下的犧牲品
許多批評者聚焦于美人魚典范性的愛情悲劇,贊揚美人魚對愛的執著與勇氣,認為塑造了一個人類的“不滅的靈魂”。但從生態女性主義角度細讀這篇童話,就會發現美人魚是男權中心價值觀下一個可悲的犧牲品。
童話中展示一個以王子、水手們等為代表的男性主導的人類世界,巨輪、無數盞五顏六色的燈、一百多發焰火、喧鬧的城市象征著人類的文明。王子的宮殿那貴重的絲窗簾和織錦都預示著王子是這個世界的主宰。這個陸地上的人類世界和海底的人魚世界是相互對立的。人魚世界的公主們唱出最美妙動聽的歌聲,可是“水手們聽不懂這歌聲,以為這是暴風雨的吼聲,他們也看不到海底的美景”;他們彼此對美丑的認識也是截然不同的,海底認為很美的魚尾,人類卻認為很丑。人類只有死亡才能進入人魚世界,而人魚也無法在人類世界存活。以女性為主導的人魚世界是被人類世界俯視的海底生物,除了最小的美人魚,其他美人魚都能感受到人類社會的恐怖,她們或者被狗嚇壞了,或者受不了太陽的灼熱,或者驚恐那血紅的雷電,她們渴望待在自己的海里。這些美人魚象征著女性的本來狀態,她們符合自然標準中一切對美好的定義。當然,這個自然的世界也存在異類,海底的巫婆就深諳男性主導的人類社會的規則,將男權社會的邏輯滲透到小美人魚的精神深處,一步一步引導小美人魚叛離自然,最終成為男權中心價值觀下的犧牲品。
小美人魚極度渴望融入這個以男性為主導的人類社會。她的自我逐漸失落在這樣的向往中。作品一開始就營造了一種小美人魚和自然之間令人不安的緊張關系。在她的花園里,除了只栽種像太陽一樣鮮紅的花朵以外,就是擺放著一個從人類的沉船里獲得的英俊的大理石男子雕像。這個與她其他五個姐姐完全不同的花園布置蘊含了她對男權社會的無限向往,她常凝望著“海岸上聳立的大城市,城市里那星星般的萬家燈火;靜聽著音樂聲、馬車聲和人的嘈雜聲;觀看教堂的尖塔,傾聽教堂的鐘聲”。小美人魚想要進入這個男權社會,必須經歷難以忍受的痛苦,“一把尖利的雙面劍劈開了她那細小的身體”,要將人魚眼里最美的魚尾巴,變成站立行走的雙腿。小美人魚還必須失去她的舌頭,變成啞巴。失語后的美人魚只剩下美麗的身材、幽雅的步姿和迷人的雙眼,她就這樣步入男權社會。作者一再強調了美人魚的身體,青春美貌、動人的舞姿是她進入男權社會的唯一資本。她按照男權價值觀完成了自我重構。她壓抑自己的內心世界,順從、隱忍、寬容。她等待著王子評價、占有、享樂。小美人魚被置于奴隸群體中,不停地取悅王子,盡管她的每一步就像在尖針和刀刃上行走一樣。為了得到王子的認可,她忍受著劇痛跳了一次又一次。面對她的付出,王子作為回報,允許美人魚睡在他房間門外的一塊天鵝絨墊子上,并給了一套男人的衣服讓她陪著自己騎馬。王子從未平等對待過她,作品中處處展現了王子的男權態度。王子常吻著美人魚鮮紅的嘴唇,摸著她的長發,而當王子面對一個比美人魚更美而又學習了王室的一切美德的公主,便立即把美人魚拋諸腦后。美人魚內心承受了沉重的情感創傷,悲傷地對著自己的魚尾。小美人魚淪為男權社會一個美麗而空洞的符號,徹底喪失了自己的主體精神。盡管如此,現實中并沒有小美人魚的生存空間,在社會階級、道德輿論、物質主義等因素的影響下,她不可能獲得幸福。最后,小美人魚只能化作泡沫永遠地毀滅了。她的失語和毀滅,正是對男權社會中女性生存困境的一種客觀描摹。
這種女性身體上的創傷和心靈上壓抑,就像人類對自然無情的征服和掠奪一樣,女性和自然的價值被肆意降低,這就是男權對自然和女性的一種異化。
三、自我與他者:從對立到和諧
生態女性主義除了關注日益突出的生態危機,探討建立平衡的自然循環,更主要探究如何解決男性與女性對立這一根本的社會問題的方法與策略。
安徒生把女性的自我建構看成是克服和幸存于男權世界的一個重要策略。所以,他探尋女性自我建構的另一種可能性。
面對小美人魚的即將毀滅,她的姐姐們用自己的頭發換了巫婆的一把刀子,因為只要小美人魚刺死王子,她就能獲救。顯然,殺死王子的思維來自男性與女性的對立思維,而拯救女性的還是女性。可是,小美人魚放棄了殺死王子,選擇化作泡沫飛到那炎熱的國度去,把清爽和花香帶給正在遭受帶病菌空氣侵害的人們。化作泡沫的小美人魚確認并樹立了自我,所以她沒有回到大海,而是選擇廣闊的社會空間,把愛帶給每個需要的人。她的生命獲得了全新的意義。安徒生充分肯定了小美人魚的社會價值,勾畫了未來美好的圖景。安徒生在結尾寫道:“她看到光明的太陽,同時在她上面飛舞著無數透明的、美麗的生物。透過它們,她可以看到船上的白帆和天空的彩云。它們的聲音是和諧的音樂。”小美人魚的心靈達到一種驚人的純真狀態。她已經實現自我解放與救贖。
生態女性主義理論主張將充滿感性與溫情的女性思維等作為建立生態社會的途徑之一,但不是要確立另一種二元對立模式。中國學者王寧先生在2000年出版的《西方當代文學批評在中國》中指出,生態女性主義把“建構女性文化作為解決生態危機的根本途徑,尊重差異,倡導多樣性,強調人與自然的聯系和同一,解構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精神/肉體、理智/情感等傳統文化中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確立非二元思維方式和等級觀念”[5]。
小美人魚并不是追求地位和權力,不管命運多么殘酷,她都常常幻想,常常期待。海底的女性世界是那樣一個有序、理想的社會。安徒生并無意于建構一種新的二元對立模式:女性優越于男性。生態女性主義不是旨在取代男性社會而建立一個女權社會,而是嘗試建立一個人與自然、男性與女性、人與人三個維度的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社會。在作品中,小美人魚所隱喻的女性不再迷失在追求身份認同的困惑中,而是在廣闊的社會空間中確認了自我,完成了自我建構。這個社會空間是不存在破壞的、權力自由的自然-社會關系的寫照。小美人魚與美麗的生物為伴,在光明的陽光下既可以看到船上的白帆,也可以欣賞天上的彩云,而身體也不會再被物化。這些都表明,作者并非簡單主張“重返自然”,而是認為重構和諧關系必須建立在個人、社會以及意識形態的轉變上。
重構一個和諧理想的生態社會,也離不開男性對女性與自然的認同。王子對小美人魚的付出從不知情,但最后王子熱切地尋找小美人魚,傷心地望著大海。王子和小美人魚存在彼此認同的基礎和可能性。這一描寫表達了作者向往一個男性和女性、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好境界。
四、結語
《海的女兒》中詩意化、理想化的結局,突顯了作者深刻的生態意識和女性關懷,表達了作者對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的向往。雖然安徒生建構和諧關系的意旨讓小美人魚化作了泡沫,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的身體,但他對壓迫女性和自然的二元主義給予否定,呼喚個人的、社會的以及意識形態的轉變卻頗富超前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