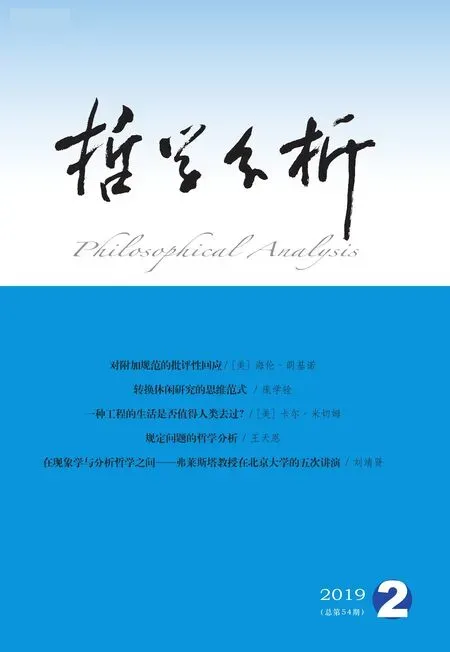權利與啟蒙
——康德對革命的雙重拒斥
方 博
雖然在理論哲學領域發動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其理論還被馬克思稱為“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a《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頁。,但是在實踐領域,康德對政治革命的拒斥卻是極為堅定明確的。在《道德形而上學》的第一部分“權利學說的形而上學基礎”(以下簡稱為《權利學說》)中,康德明確聲稱,“針對國家的立法者并不存在人民的任何合乎正義的反抗”,因此“人民有義務忍受最高權力的即使令人無法忍受的濫用”b本文對康德文本的引用依據的是普魯士皇家科學院版的《康德全集》: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von K?niglich Preu?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Berlin: De Gruyter, 1902—,VI 320。后引只在文中注明頁碼。。同樣的觀點在此前的《論通常的說法:這在理論上可能是正確的,但不適合于實踐》 (以下簡稱為《論通常的說法》)中也已經清楚地表達過并在一系列反思中被重申。康德對人民反抗暴政的權利的這樣一種斷然否定的態度毫無意外地遭致了諸多尖銳的批評,比如赫費(Otfried H?ffe)就將其視為康德法哲學中的錯誤觀點之一aOtfried H?ffe, ?K?nigliche V?lker “: Zu Kants cosmopolitischer Rechts-und Friedenstheorie, Fankfurt/M: Suhrkamp Verlag, 2001, S. 24.,而拜瑟爾(Frederick Beiser)則更為激烈地指責康德背叛了自己的激進的權利原則并將此歸結為康德對普魯士王權的愚忠bFrederick Beiser,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and Romanticism: 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1790—1800, Massachusse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6.,在康德研究中,類似的觀點并不鮮 見。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暫且拋開關于這一觀點自身在自由主義的敘事傳統中是否政治正確的爭論,僅僅從學理上去考量的話,那可以說,康德的這一主張在其法哲學和政治哲學中是邏輯自洽的。本文的目的在于證明:康德對革命的拒斥是建立在充分的論證之上的,在他的學說中實際上包含著對革命的雙重拒斥,即基于權利概念的拒斥和基于政治實踐的拒斥。在法哲學的層面,康德從權利論證的角度指明了所謂的積極抵抗權不可能在理論上得到辯護,因為其將會從根本上消解作為一切權利的現實性的基礎的政治共同體的存在,并因此與權利的概念直接相矛盾。而在政治哲學的層面,康德則進一步論證了通過暴力革命并不能如革命者所期待的那樣建立起全新的理想秩序,因為其并不能帶來人的快速的啟蒙,而后者恰恰是制度的持續革新與良序運行所必需的條件。就此而言,只有基于人的啟蒙之上的改良才是實現人的權利的唯一合乎理性的現實路徑。
一、抵抗權的可能論證進路
對革命權或積極抵抗權的拒斥當然不是什么新的觀念,相反,這是從主權概念產生伊始便一直與之相糾纏的老命題。當博丹在《共和六書》中將主權明確地定義為“國家所特有的絕對的和永恒的權力”之時,就明確強調了它是“針對公民和臣民的不受法律約束的最高權力”。cJean Bodin, On Sovereignty, edited by Julian H. Frankl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從這一定義出發,一種可以暴力反抗主權者的權利在邏輯上就不可能與主權概念相容。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博丹在其著作中也留下了一些口子,即強調主權者對權力的行使不應違反神法、自然法甚至是其與臣民之間的契約,但他既未為這一觀念上的約束提供任何可以實踐的措施,亦未承認臣民有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免除政治服從義務的權利。從博丹自己的理論立場來看,他在《共和六書》中事實上已經偏離了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自然法傳統,而更多地采納了一種實證主義的立場,即將立法的主權視為權利的普遍來源而非相反。aDan Engster, “Jean Bodin, Scepticism and Absolute Sovereignty”,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Vol. 17, No. 4 1996, p. 491.當然在這里真正重要的并不在于博丹自己對此問題持有什么樣的立場,而是他在這一態度上的保留實際上全面地反映了中世紀和近代早期對抵抗權的各種論證范式:神法論證、自然法論證和契約論論證。
與之相比,霍布斯則更為決絕地摒棄了殘留在博丹思想中的這些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關于抵抗權的思想。在《利維坦》的一開頭,霍布斯就否認了國家的任何神圣的起源,而明確宣稱其“是用技藝造成的,它只是一個‘人造的人’”b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頁。。因此雖然在他的著作中仍然存在著諸多神學的術語和隱喻,甚至我們還可以承認他的國家理論與基督教神學之間可能存在某些敘事結構上的相似性,但他所理解的國家已經完全是世俗的和理性的,并沒有為所謂的神法論證保留任何余地:關于國家的論證無需引入或預設任何具體的神學命題作為某個必備的論證環節。而霍布斯雖然仍然承認自然法的存在,但也僅僅將它們視為指引愿意尋求和平的人們擺脫自然狀態的一些理性規則,它們并不構成可以指導或者約束主權者行使權力的超實證規范,自然也就不可能證成一種反抗最高權力的權利。霍布斯同樣反駁了基于主權者與臣民之間的服從契約之上論證臣民的有限服從義務的思路。在他看來,在社會契約論的模式中,主權者雖然是通過社會契約獲得權力的,但他不可能作為契約當事人與臣民締結契約,“否則他就必須將全體群眾作為一方與之定約,要不然就必須和每一個人分別定約。將全體群眾作為一方與之定約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在那時還不能成為一個人格。要是有多少人他就訂立多少單獨的信約,那么在他有了統治權之后,那些契約就無效了”c同上書,第134頁。。在國家狀態之中,主權者本身就是判定契約效力的最終的依據和裁決者,契約只能存在于平等主體之間,因此一種能夠約束主權者的契約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中世紀的臣服契約與近代國家理論中的主權概念互不相容。康德后來在一則反思中精確地將這一反駁概括為“在主權者與社會的成員之間不存在契約”(XIX R 7759)。
可以說,霍布斯全面反駁了在博丹那里所殘留的論證暴力反抗主權者的權利的可能進路,從而確立了擁有不受限制的至高權力的主權者的地位,但他以自然權利為起點論證國家的必要性的理論進路卻同時為抵抗權的論證開啟了另外一條進路,即基于自然權利的論證。在霍布斯看來,每個人在先于國家的自然狀態之中都擁有自我保全的自由,這是唯一的自然權利和個人的行動決策的最高原則,其普遍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性和情感傾向之中,人們正是為了自我保全的目的才建立國家并無條件地服從于主權者。在霍布斯看來,自然狀態之下以自我保全為目的的自由必然是恣意的、無規定的,雖然從自然狀態進入公民狀態意味著這一自由通過被公共權力所抑制轉化為法律下的自由,但既然自我保全始終是人的行動的最高原則,這就在邏輯上留下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如果國家權力的行使危及了個人的生命,那個人就可以免除對國家的服從義務甚至反抗國家,因為自我保全是每個人不可放棄的自然權利。“如果有一大群人已經不義地反抗了主權者或犯了死罪、人人自知將因此而喪生,那么這時他們是不是有自由聯合起來互相協助、互相防衛呢?當然有,因為他們只是保衛自己的生命,這一點不論有罪沒罪的人都同樣可以做。他們當初破壞義務時誠然是不義的,往后拿起武器時雖然是支持他們已經做出的行為,但卻不是一種新的不義行為了。如果他們只是為了保衛人身,便根本不是不義的行為。”a霍布斯:《利維坦》,第 170 —171 頁。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在關于自然狀態和國家的理解上與霍布斯有極大的不同,但洛克在《政府論》下篇中對革命的權利的論證正是基于同樣的進路:以自然權利來論證革命的權利。在洛克看來,自然狀態下的每個人生而擁有的自然權利(生命、自由和財產)以及由此派生的自然權力,即對侵害這些自然權利的行為自主進行裁判和處罰的權力。自然狀態中的人們通過社會契約建立國家就是讓渡自然權力給政府以保護其自然權利的過程,這一目的本身就設定了政府權力的邊界:從目的上它不能超出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的限度,從手段上它不能超出人民所能轉讓給它的自然權力的范圍。社會契約所表達的同意構成了人民的政治服從義務的基礎,因此政府權力的行使一旦超越了必要的限度就構成了違約,人民就有權免除自身的服從義務,甚至反抗政府。正如洛克在《政府論》中所明確表達的:“當立法者們圖謀奪取和破壞人民的財產或貶低他們的地位使其處于專斷權力的奴役狀態時,立法者們就使自己與人民處于戰爭狀態,人民因此就無需再予服從,而只有尋求上帝給予人們抵抗強暴的共同庇護。”b洛克:《政府論》 (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39頁。由霍布斯和洛克所開啟的這一進路構成了自然權利學說論證抵抗權的基本范式,因此康德在自然權利學說的語境之中若想堅持自己拒斥革命的立場,首先就必須令人信服地反駁這一論證。
二、第一重拒斥:權利的邏輯
康德并沒有像其他保守主義的思想家比如伯克那樣訴諸歷史進程中超越人的理性的智慧為現存的秩序辯護。c伯克:《法國革命論》,何兆武、許振州、彭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44頁。相反,他首先為自己的主張提供了一個基于理性權利的進路之上的論證:我們在邏輯和理論上無法證成一種暴力反抗現存的最高立法權力的權利,因為后者的存在恰恰構成了一切權利得以成為可能的現實基礎,因此暴力推翻現存的最高立法權力,無異于消解了權利的一切現實性基礎并最終否定了權利的概念。這構成了康德反對政治革命的最為基本的理論理由。
康德的反駁的出發點是:自然狀態之中并不存在任何確切的權利。與霍布斯和洛克不同,康德并不認為自然權利就是每個孤立的個體在自然狀態之中就能夠擁有的確鑿無疑的權利。正如黑格爾后來在《論自然法的科學探討方式》中所批評的,以霍布斯和洛克為代表的經驗主義的自然權利學說對自然狀態下的人的規定僅僅基于某種經驗的任意性,而未能為偶然的東西與必然的東西之間的界限提供一個先天的判定標準。aG. W. F. Hegel, Hauptwerke in sechs B?nden,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99, Bd. 1, S. 425.在康德看來,我們只能從理性的先天立法的角度去理解所謂的自然權利,它們相對于實證權利所指的只是“基于純粹的先天的原則之上”(VI 237)的權利,換言之,它們是與理性的先天原則相符合的、處于普遍的外在立法之下的每一個人作為理性存在者都應當擁有的權利。在康德的法哲學之中,構成論證的規范性起點的是一種天賦的權利,它所指的是這樣一種“自由(對他人的強迫的意愿的獨立性),只要其與每個人的自由依據一條普遍的法則能夠共存,就是這一唯一的、原初的、每個人憑借其人性即被賦予的權利”(VI 237)。康德也將其稱為內在的“我的”和“你的”,但在嚴格的意義上,這并不是一種權利而僅僅是一種消極的自由。更為關鍵的是,即使我們承認每個人憑借其人性都應該先于國家而擁有這樣一種自由,它也并非自足的。人生而應當擁有的并非恣意的、無規定的自由,而是能夠與他人的同等自由共存的外在行為的自由,但自然狀態中的每一個個體首先就無法確定自己的自由的邊界,因為這一邊界是理性所無法先天地認識到的。人與人之間的自由的共存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始終需要一系列的條件,其中的那些主觀的條件,就是康德所理解的權利:“權利是這樣一些條件的總和,在其之下每個人的意愿與其他人的意愿根據一條自由的普遍法則可以被聯合起來。”(VI 230)權利是人與人之間的自由的共存成為可能的條件,而每個人作為與他人生活于共同的時空之中的經驗存在者,他自身的實存和持存都意味著,他在他的行動之中必然要排他性地占有某些外在于自身的東西,并因此與他人處于潛在的沖突之中。人與人之間的自由的共存因此并不能像幾何學那樣通過劃定人的行動空間就得到實現,而是首先要確定人對外在的東西的權屬,這就是所有權,而在康德看來,這在自然狀態之中恰恰是不可能的。
康德的這一分析首先揭示了權利的本質,它所涉及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意愿的關系,是為了界定“我的”和“你的”而產生的。對于盧梭意義上的孤立無依的自然人而言,權利的概念毫無意義。而霍布斯所賦予自然狀態中的人的那種恣意的、無規定的自由,從根本上就不符合權利的定義,這種自由的實現非但不能在共同生活的人與人之間建立起行動的邊界,反而使得人與人必然地陷入權利的爭端之中。這也就意味著,對于霍布斯而言,從自然狀態進入公民狀態并非自然權利得到更好的保障或實現的過程,反而是自然權利在一定程度上被公共權力所抑制的過程,這就埋下了公民狀態之中的個人權利與公共權力之間無法得到裁決的沖突的根源。與之相比,洛克從一開始就沒有將自然權利所包含的自由理解為恣意的自由,并且通過自然權利與自然權力的區分避免了霍布斯所遭遇的困境。但洛克從一開始就將自然狀態視為“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a洛克:《政府論》 (下篇),第5頁。,這固然部分源自他對人性的樂觀假定,但更為根本的是出于他對權利的本質的錯誤認識。洛克認為自然狀態中的每個人都可以獨立于所有其他人的意志而僅僅通過自己的勞動就可以獲得對外在物的權利,這意味著他將財產權視為人與物的關系。洛克在這里實際上混淆了純粹物理意義上的占有和具有權利意義的占有,即康德所說的經驗占有和理智占有之間的區別。自然狀態中的人誠然可以通過勞動在物理上占有某一外在物并排除他人的染指,但這一物體一旦脫離他的直接控制,他便沒有任何依據再去排除他人的占有和使用了。具有權利意義的占有必然是一種即使并不在物理上控制某物也能約束他人的意愿和行為的排他性的權利,正如康德所指出的:“當我(在語言上或通過行為)宣稱我希望某個外在的東西是我的的時候,我實際上是在宣稱,所有其他人都必須避免染指我的意愿的對象”(VI 255)。所有權的實質就是通過單方的意思表示去約束所有其他人的行為,而這在自然狀態之中恰恰是不可能的。只有存在共同的外在立法的地方,個人的單方意愿才能以共同的立法權力為中介獲得這樣一種約束性。這就意味著,只有在國家之中,所有權才是可能的,人與人之間的自由的共存也才是可能的,脫離自然狀態而進入國家狀態就此成為實踐理性的一個無條件的定言命 令。
自然狀態的這一缺陷并非出于人的認知的欠缺,也與對人性的善惡假定無關,而純粹是在缺乏共同的外在立法的情況下在人的共同生活的實踐中必然存在的問題,因此也就不能期待當人們的認識進步到幾乎窮盡了理性法的所有先天規定之后,這一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到時候人們就不再需要國家了,相反,在康德看來,國家必須“永久存續”(VI 326)。對于洛克來說,通過暴力反抗政府從而重返自然狀態并不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事情,因為自然狀態雖有諸多不便,但已然是一個自由的完備狀態,但對自然狀態的這一理解事實上建立在他對所有權的實質的錯誤認識之上。對康德來說,重返自然狀態是理性所絕對禁止的,因為這消解了權利的一切現實性基礎,而墮入了一個“權利的真空狀態(status iustitia vacuus)”(VI 312)。自然狀態僅僅是人基于其作為理性存在者的人格應當擁有卻無法真正擁有自由的狀態,因此理性為了實現其所賦予每個人的自由,必然要向所有人頒布一條無條件的法則:“脫離自然狀態!”(exeundum e statu naturali) (XIX 243)任何試圖賦予個體以積極抵抗權的規則都必然與這一條法則相矛盾,因此都不可能在理性面前得到辯護,所謂的積極抵抗權無法通過自然法或自然權利得到論證。
在一個統一的法律秩序之內保留一種暴力反抗最高權力的權利本身就是一個矛盾,也不可能以合乎權利的方式被執行,正如康德所指出的:“為了使人民有權反抗,就必須存在一條允許人民的反抗的公共法律,這意味著,最高的立法在自身之內包含著一個規定,自己并不作為最高的立法而存在,并使得作為臣民的人民在同一個判斷中成為人民所臣服的主權者,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而這一矛盾通過這一問題將會立即凸顯:誰應當在這一人民與主權者的爭端中擔當法官呢?(因為從權利的角度來看,他們畢竟總是兩個不同的道德人格)這表明,人民希望在自己的事務上擔當自己的法官。”(VI 320)康德在此實際上是重申了霍布斯的主權概念和一個關鍵的問題:誰來判斷(Quis judicabit)?而霍布斯雖然并不認可國家權力需要受自然權利的約束,但他將自我保全視為人的不可讓渡的自然權利卻會在邏輯上造成政治秩序的懸置甚至解體:在一個死刑判決中,國家有權力以暴力保證判決的執行,而被告也有自由為了自我保全以暴力反抗這一判決。在康德看來,這實際上意味著人們仍然停留在自然狀態之中,“當每一個人都僅僅依據他自己的判斷和運用他自己的力量去追求他所認為的權利的時候,他所處的就是戰爭狀態”(XIX R 7945)。洛克當然也不認同將判斷的資格因此是反抗的權利授予每一個單獨的個體,因為這將意味著政治秩序從一開始就是不存在的,因此這一權利的主體只能是作為集體的人民。“如果在法律沒有規定或有疑義而又關系重大的事情上,君主和一部分人民之間發生了糾紛,我以為在這種場合的適當仲裁者應該是人民的集體。”a洛克:《政府論》 (下篇),第156頁。但洛克在此很顯然預設了一個實體性的人民概念,而并沒有為此提供任何進一步的論證:超越現行的法律制度所設定的程序,人民如何能夠作為一個集體表達和貫徹它的意志?正如康德所指出的,恰恰是通過服從于一個共同的立法權力,一群人才能聚合為人民。如果人民自身就是主權者,它當然有權去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但在這一情境中不存在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反抗最高權力的權利。
對抵抗權問題的進一步追索必然會觸及政治理論中所通常存在的依據理論建構的理想國家與現實存在的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霍布斯和洛克都將個體對國家的服從義務歸于社會契約所表達的同意,因此社會契約構成了政治權力的正當性的來源。而霍布斯通過將主權者置于契約當事人之外而捍衛了主權的絕對性,使得對政治權力的正當行使的約束成為不可能,但既然將同意視為統治的正當性基礎,他就得面對依約建立的政治性國家與通過暴力建立的自然國家之間的對立問題。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論事實上摒棄了絕對主權的概念,并提供了關于理想的政治秩序的一個范本,但他仍然需要面對同樣的問題:如果統治的正當性需要建立在社會契約之上,那我們該如何面對現實中那些并非建立在社會契約之上或者其制度并不完全符合這一契約的國家?在一個依據理論建構的理想國家之中,討論人民的反抗權是毫無意義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該如何面對經驗和歷史之中的那些必然存在缺陷的國家。
洛克實際上為國家的開端設置了一個基于特定的自然權利之上的最低限度的門檻,并將那些沒有達到這一門檻的國家統統剝奪了正當性。但這一視野中的國家只能是現代國家,國家的產生似乎僅僅是一個現代歷史的事件。與之相比,康德則更傾向于將國家的發展或人的權利的實現視為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并因此對那些即使在當下的正義視野之下仍然不夠正義的國家也給予了一定的認可。但康德并沒有就此放棄理想政治的信念,他并不接受霍布斯的君主不會對臣民行不義的命題,在《論通常的說法》中他就明確指出:這樣的命題是“極其可怕的”(VIII 304)。在其法哲學中,康德致力于為人類的共同生活提供一個基于理性的先天立法的規范性基礎,并借助一個假定在理性上會得到所有人共識的原初契約的理念,推導出完全合乎理性的共和國的理念以及一個世界公民主義的全球法治秩序。康德承認存在一些我們能夠據以評價現行的國家權力的運行是否合乎正義的超實證規范,但并不能就此否定經驗和現實中那些不符合原初契約的理念的國家的統治的正當性,因為這兩者在論證上并沒有必然的相關性。在康德看來,社會契約并非一個經驗事實,也不能構成公民的政治服從義務的依據。通過服從于共同的立法權力從而擺脫自然狀態是實踐理性基于人的權利的實現的理由而頒布的定言命令,因此政治服從義務的基礎并非個體的同意,而是理性自身的要求。但理性要求個人所服從的并非像赫費所認為的那樣僅僅是完全符合原初契約的本體國家(respublica noumenon)aOtfried H?ffe, ? K?nigliche V?lker “: Zu Kants cosmopolitischer Rechts-und Friedenstheorie, S. 24.,因為這樣的國家不可能存在于經驗世界之中,它的意義僅僅在于作為“一切公民制度的永恒規范”(VII 92)為存在于經驗中的現象國家(respublica phaenomenon)提供借以觀照自身的不完善性并由此持續改善自身的范 本。
借用康德的范疇表,如果說在國家狀態與自然狀態之間是模態的差別:權利的有與無,那在不同的統治形式之間則僅僅是量的差別:權利的多與少。任何經驗和歷史中的國家,不管其最初是如何產生的,只要能夠通過普遍生效的立法界定了人與人之間的“我的”和“你的”,就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人的權利,因此即使尚未具備充分的合義性(Rechtmigkeit),也已經具備了可以要求公民的政治服從的合權性(Rechtlichkeit)。aRobert Spaemann, “Kants Kritik des Widerstandsrechts”, in Materialien zu Kants Rechtsphilosphie, hrsg. von Zwi Batscha, Frankfurt/M: Suhrkamp Verlag, 1976, S. 348.正如康德在《論永久和平》的一個腳注中所說的:“這就是理性的許可法則,它們允許一個帶有非正義的公共權利狀態得以延續,直至它要么自己成熟起來,要么通過和平的手段被引向成熟而足以變革一切:因為任何一個合乎權利的(rechtliche)的制度,即使僅僅在細微的程度上是合乎正義的(rechtm??ige),也要好于沒有制度,后一種命運(無政府主義)是過于急促的改革所將遭遇的。”(VIII 373)人的權利的實現并非始于現代國家,雖然現代國家的確是人們在那個階段所能夠獲知的實現人的權利的最佳模式,但在現代國家出現或被普遍建立之前,個人的權利在前現代的政治秩序之中也已經獲得了一定的實現。康德很清楚,政治秩序的歷史開端并不建立在人為建構的社會契約之上,相反,在歷史中其往往是由暴力行動所促成的,但這樣的秩序一旦被建立了,就其是每一個具體的人或民族已然身處其中并由此實現了某種程度的權利的現實秩序而言,也就構成了他們唯一能夠以合乎權利的方式進一步實現其理性權利的出發點。從人的權利的現實化的角度來看,自然狀態而非暴政才是人所應當無條件避免的政治的“首要惡”bWolfgang Kersting, Wohlgeordnete Freiheit: Immanuel Kants Rechts-und Staatsphilosophie, Paderborn: WBG,2007, S. 374—375.,因為它是權利的真空狀態,意味著權利的徹底喪失。正是在此意義上康德才會主張:“服從于現存的國家權力,不論其源出何處!”(VI 319)但這里對抵抗權的拒斥并非出于秩序的理由,而歸根結底是基于權利自身的邏輯。
但康德所禁止的僅僅是暴力的反抗,因此也為某些非暴力和非強制的反抗保留了空間。雖然在他看來臣民只有通過言論進行反對的權利,但行動上的服從也并非絕對,政治服從義務仍然有其界限。首先,并非在所有秩序,而是只有在某種權利秩序中,個體才負有政治服從的義務。比如在奴隸制中,因為被徹底剝奪了權利主體的地位而被當作純粹的物看待,奴隸也就不應當承擔包括政治服從在內的任何義務。在《權利學說》中,康德明確否認了“人與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的存在者之間的權利關系”(VI 241),所以在奴隸制下奴隸暴力反抗奴隸主的可辯護理由并非奴隸擁有暴力反抗奴隸主的權利,而是奴隸并未負有服從奴隸主的義務。其次,即使是在某種權利秩序之中,個體的政治服從義務仍然有可能受到內在道德的限制。在理性的立法中,法律義務與倫理義務當然是不存在沖突的,但是實證法義務與倫理義務的沖突卻是完全可能的。在《權利學說》的附錄中,康德就對設定服從義務的定言命令給出了一個更為完整的表述:“服從于對你們擁有權力的最高當局(在一切不違背內在的道德的事情上)。”(VI 371)但在這種義務的沖突之中,尤其是當實證法義務的履行會侵犯到第三者的時候,個人應該如何行為?內在的道德規范并不能取消人的外在的服從義務,暴力的反抗當然是不被允許的,因此個人在這種情境中只能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擇:要么以違背道德的方式履行實證法義務,要么以違反實證法義務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的方式去遵守倫理義務。康德當然會贊賞后一種選擇,但在這里反抗仍然不是一種權利,因為對倫理義務的遵守并不能在法律上構成要求責任豁免的抗辯理由,但從道德的角度來看,通過個人犧牲去克服遵守倫理義務的外部障礙卻會賦予這一行為以更高的道德價值。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康德對積極抵抗權的拒斥實際上與當代政治哲學所主張的公民不服從是可以兼容的,因為公民不服從恰恰要求通過“一種公開的、非暴力的、良知的然而是政治的行動去違抗法律”a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itce, Massachusse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364.。
三、第二重拒斥:政治的進路
康德對政治革命的拒斥當然首先是因為革命作為一種徹底消解政治共同體的存在的極端行動在邏輯上與權利概念無法兼容,這一點在他的法哲學中已經得到了很明確的表達。而在康德研究中往往會被忽視的是,在這一拒斥背后實際上還隱藏著康德的更進一步的與經驗和歷史相關的考慮:以革命的方式往往很難超越既有的歷史條件飛躍式地建立起革命者所期待的與現存的秩序迥然有別的理想政治秩序。康德在他的法哲學中的確致力于為人類的共同生活和現實的政治秩序提供一個由先天的—形式的權利原則所構成的規范性基礎,但他并非一個無視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的和歷史的經驗,而退居孤寂的書齋單純在頭腦中編造人類社會的理想圖景的哲學家,因此在他對政治革命的反對中實際上同時包含著出于政治的—實踐的原因的考慮。但并非如人們通常所可能誤解的那樣,康德是被法國大革命的暴力和恐怖所驚嚇,從而在革命的問題上倒退回了保守的立場。事實上,康德對政治革命的反對態度在大革命前后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政治的—實踐的層面,這一主張與他的政治改良主義的啟蒙方案緊密相關,這構成了康德反對政治革命的第二重理由。而這一方案的雛形在康德于大革命之前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業已被勾勒了出來,比如同發表于1784年的《世界公民意圖中的普遍歷史理念》 (以下簡稱為《普遍歷史理念》)、《回答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 (以下簡稱為《什么是啟蒙》)以及發表于1786年的《何謂在思維中確定方向?》等。
我們為什么不可能通過革命一勞永逸地建立一個完善的政治秩序?其原因首先在于,我們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對正義以及理想的政治秩序有一個整全的認識。絕對完善的政治秩序作為一個理念既不構成我們的理論認識的對象,也不可能通過實踐在經驗層面上被徹底實現,這與康德對理性理念作為調節性原則的規定相一致。雖然在法哲學中他試圖基于理性的先天立法為人的自由的共存推導出一整套先天的權利原則的體系,但這一體系就其是先天的而言也只能是形式的,其中并不包含能夠直接規范我們的行為和政治行動的完整的規則,而只有將這些形式的原則與具體的經驗條件相結合,我們才有可能獲知具體行動的規則。正如亨利希所指出的:“權利概念并沒有為自身提供任何對行為的指引。它必須與對世界狀況的解釋結合起來,唯有如此,它才能變成一個政治行動的方案。”aDieter Henrich, “über den Sinn vernünftigen Handelns im Staat”, in über Theorie und Praxis hrsg. von Dieter Henrich, Frankfurt/M: Suhrkamp Verlag, 1967, S. 35.這樣的一個具體行動的方案(通過權利概念與具體的經驗條件的結合而獲得)要成為可能,至少要同時具備兩方面的條件:作為對象條件的具體的經驗情況和作為主體條件的將規則的形式與質料相結合的能力。而恰恰是因為對這兩方面條件的要求,使得完善的政治秩序只能在歷史進程之中被逐漸揭示出更為全面的面貌,而絕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被認識到。
從對象方面來看,由于現象世界的經驗的雜多性,先天的權利原則需要應用于其上的經驗情況永遠也不可能被窮盡,這也就意味著我們不僅無法構建一個可以將所有的經驗情況都歸攝于其下的規則體系,甚至也無法去估測我們離一個現實可能的最完善體系還有多遠。正如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里針對理念國家在現象世界的實現所說的:“人性必須停留于其上的那個最高的程度將是什么,因而在理念及其實施之間必然留下的那道鴻溝會有多大,這是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應當加以規定的,這也正因為它就是自由,而自由是可以超出任何被給定的界限的。”(III B 374)在《權利學說》中,他在談及必然要將其在經驗中的應用同時考慮在內的完整的權利體系之時,也坦誠我們“所能期待的僅僅是接近于體系,而不可能達到體系自身”(VI 205)。而這種接近只能是循序漸進的,因為我們不可能先于經驗或脫離經驗就能獲知在經驗情況之中能夠進一步實現人的權利的具體條件,而只能在變動的世界之中通過與新的經驗情況的結合持續地拓展我們對合乎理性的政治秩序的認識,在此意義上,現存的經驗世界本身就構成了我們的進一步認識所無法一步跨越的出發點。
與作為認識對象的經驗的雜多性相對應的是認識主體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這一有限性不僅體現在理性不能超越經驗的可能性界限去認識絕對的無條件者,還體現在人的包括理性和判斷力在內的各種稟賦的發展都必須經歷一個漸進的歷史過程。康德雖然強調理性作為“我們的思辨的一切權利和主張的最高的法庭”(III B 697),但對于每一個現實的個體或群體而言,能夠主張其運用的普遍有效性的成熟的理性并非一種現成的能力,其毋寧說是“一個仍然需要去獲得的和人為的能力的理念”(V 240)。在《普遍歷史理念》中,康德就很明確地指出:“理性并不依從本能而自行起作用,而是需要嘗試、訓練和教導,以逐漸地從一個見識的階段進步到另一個階段。”(VIII 19)這一過程就是人的啟蒙,康德在這里已經明確地指出了人在歷史中的持續啟蒙與政治制度的持續革新的相關性,即理性的持續進步需要體現在外在的客觀的政治秩序之上并在一個個世代之間傳承。因此正如維蘭特(Wolfgang Wieland)所指出:“不僅僅因為現實世界的生活條件的持續變遷,即使僅僅考慮到每一條普遍規范的應用所需要的條件,所有的實證法都已經指向了這一點,它們只能持續地被形成。”aWolfgang Wieland, “Kants Rechtsphilosophie der Urteilskraft”,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Bd. 52,H.1, Jan.-Mar., 1998, S. 20.形式的權利原則所要應用于其上的經驗的雜多性和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決定了我們首先在認知的意義上就不可能獲知一個完全合乎理性的政治共同體的現實形態,因此只能在經驗的歷史中通過對現存的政治制度的持續改良去不斷逼近,卻永遠不可能徹底實現這樣的一個理想。在他的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中,康德對人的自由在經驗中的實現已經持有了一種歷史的和生成的理解,而這種立場通常被歸為費希特后期和之后的黑格爾所特有b貝克:《費希特和康德論自由、權利和法律》,黃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227頁。,甚至是黑格爾在批評康德的形式主義的時候都沒有意識到這一 點。
但僅僅出于認知的理由仍然不足以反駁革命作為一種改進業已落后于時代的政治秩序的手段的有效性。我們無法超出既存的經驗而獲得對一個完善的政治秩序的現實形態的整全認識,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無法認識到比現行制度更為合理的政治秩序的現實形態,而意在克服現行制度業已暴露出來的巨大缺陷的政治行動并不需要以我們的前一種認識為前提。即使是在黑格爾的語境內,密涅瓦的貓頭鷹要到夜幕降臨才會展開它的雙翼,但依據他對現存的事物與現實的事物的區分,理性仍然可以通過現存的事物在思想中把握到政治秩序的更具現實性的形態。一個直觀的例子就是,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所為之辯護的君主立憲制很顯然并非當時的普魯士體制。正如馬克思后來所指出的,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的法與國家哲學要高于德國當時的政治狀況。c《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頁。而這種錯位的另一個原因是:即使德國仍然停留在舊制度的經驗和迷夢之中,在國家間的交往日益緊密的世界歷史時代,英法兩國的政治實踐也已經提供了新的經驗,并揭示了現代政治的原則和可供參考的具體規則。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不考慮權利的問題而僅僅著眼于有效性的話,革命是否可以成為建立更為合理的政治秩序的一個可考慮的選項?如果我們可以站在康德的立場之上替他回答的話,答案應該仍然是否定的。問題并不在于德國是否應該實現現代政治的原則以將自身在政治上提升到與時代同步的水平,關鍵在于:(1)在與舊制度相伴隨的各種歷史條件的約束之下,如何能夠一如革命者所預期的那樣建立起新的制度?(2)即使新的制度在形式上通過革命被確立了,其如何能夠良序運作?
雖然在康德所設想的理想國家中,進行統治的將是法律自身,但這始終是一個理念,在經驗世界之中,任何法律體系都是不完善的,也始終是不自足的,因此任何時候都需要人的政治實踐作為補充和驅動,政治的規范性目的正在于實現權利的概念。這同時也就意味著,不管是制度的可預期的革新還是制度的良序運轉,都需要政治實踐的主體具備某些特定的品質。在《普遍歷史理念》中,康德自己提出了這樣一個難題:人作為動物都需要一個主人,否則其將不可避免地濫用自己的自由,但主人本身也是動物,也需要一個主人,“不管他是求之于一個個別的人也好,還是求之于為此而選出來的由若干人所組成的集體也好”,問題都依然存在。(VIII 23)不可暴力反抗的主權是政治共同體的構成性要件,但這樣一個至高的權力只能掌握在人手里,因此始終存在著被濫用的危險。統治者也是人,這是所有的政治理論都要面對的一個難題。在康德看來,解決問題的關鍵并不在統治者身上,而在于人民自身。他在此明確訴諸人民的普遍的啟蒙,并堅信“它必定會把人從其統治者們的自私自利的擴張計劃下拯救出來,只要他們能懂得自己本身的利益。而這種啟蒙以及隨之而來的啟蒙了的人們對于自己已經充分理解到了的好處所不可避免地要采取的一種衷心的同情,就必定會一步步上升到王座上來,并且甚至于會對他們的政體原則發生影響”(VIII 28)。在《論永久和平》中,康德進一步闡明了人民的啟蒙何以能夠遏制主權者濫用權力的沖動并自下而上地推動制度的持續改進。在該文的附錄中,康德提出了公共性原則作為調和道德與政治的分歧的手段,他所訴諸的正是這樣的實踐的檢驗,即當我的一條不正當的準則被公之于眾,“必然會不可避免地激起所有人對我的意圖的反對”(VIII 381)。他在《系科之爭》中也有類似的表述:“為什么從來沒有一個統治者敢公然宣稱,他根本不承認人民有任何反對他的權利,人民只能把自己的幸福歸功于將之恩賜于他們的政府的仁慈,而且臣民對這一反對政府的權利(因為這一權利自身中包含著允許反抗的概念)的一切妄言都是荒謬的,甚至是可罰的?——其原因就在于:這樣一個公開的宣告會激起所有臣民對他的反對。”(VII 86)訴諸人民的公開的反對,實際上已經對人民的啟蒙提出了要求。人民不僅要有能力認識到特定的規則和決策的不正義性,而且要有足夠的動力和勇氣進行公開的反對,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權力的濫用并推動秩序的持續改進。人民必須有覺悟和能力積極參與共同體的塑造,才能實現自己的自由,這正是《判斷力批判》的那個著名的腳注所表達的:“人們在新近發生的一個偉大的民族徹底成為一個國家的事情上通常用有機體這個詞來恰如其分地指稱市政制度等等及整個國家體的建立。因為每個成員在這樣一個整體中當然應該不僅僅作為手段,而是同時也是目的,并且就其共同促成了整體的可能性而言,每個成員借助于整體的理念反過來又依據他的地位和功能得到了規定。”(V 375)
當康德將調和政治與道德的分歧的希望寄于所有人的反對之時,并不意味著他容忍任何積極抵抗的方式。他在《論永久和平》的附錄中借以說明公共性原則的應用的第一個例子正是對積極抵抗權的駁斥,人民對主權者的反對的方式因此只能是非強制和非暴力的。在《論通常的說法》中,在反駁了人民有暴力反抗國家元首的權利之后,康德隨即指出人民還有一種不可離棄的反對權利,即對公共法律和政治決策進行公開的討論和批評的自由,這是“人民權利的唯一守護神”(VIII 304)。而在此前的《何謂在思維中確定方向?》一文中,他同樣將表達自由視為“在一切公民的負擔之下仍然留存給我們的唯一珍寶,只有憑借它才能抵御這一狀態的災禍”(VIII 144)。在更為根本的意義上康德會將表達自由以及建立在這一自由之上的公共領域視為理性的實存之所在,而他在政治的意義上對這一自由的論述所關注的始終是政治服從的界限,以及在服從之時如何始終保有更進一步實現人的權利的可能性的問題。《什么是啟蒙》里對理性的公開運用和私下運用的區分正是對此給出的一個解答:理性的私下運用意味著在權威領域的服從,而理性的公開運用則意味著在公共領域的自由批評。康德主張公民應該有“在一切事情上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VIII 37),因為正是在這一無損于政治服從義務的自由之中,他看到了人的持續啟蒙以及由此推動制度的持續改進的可能性。通過理性的公開運用,一方面是公眾在公共領域之中持續地自我啟蒙,另一方面是公共領域獲得了政治批判的力量,促使最高權力不得不進行政治改良以維持他的“立法的威望”,即韋伯意義上的民眾的正當性信念。aMax Weber,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Tübingen: Mohr, 1972, S. 122.在《權利學說》中,康德明確指出在代議制中人民有一種消極的抵抗權,可以通過他們的代表去反對不正當的法律和政治決策。而如果人民的代表一直怠于行使這一反對的權利,這將表明“人民已經腐化了”(VI 322),他們已經失去了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并監督代表們盡責履職的能力。以啟蒙不足或再度腐化的人民為基礎的共同體,即使出于某種偶然的機緣在形式上建立了好的制度,也會不可避免地重新滑向專制主義。因此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英法兩國的政治實踐是否揭示了現代政治的原則,而在于德國人是否有能力去促成這些原則的持續實現。啟蒙并不簡單等同于知識的占有,知道某些原則并不等于有能力通過自我思考和公共參與去實現這些原則。作為現代政治的基本組織形式的民主制度的良序運行尤其需要有能力和意愿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并監督權力的運行的公民,這只有通過啟蒙才能達到——啟蒙所要造就的正是有能力和勇氣在公共事務上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的人。
而在康德看來,人的啟蒙恰恰不可能通過政治革命來實現。雖然啟蒙要求個體的思維方式的根本轉變,要求“人的內在之中的革命”(VII 229),但內在的革命并不能通過外在的革命來促成,尤其是這里所要求的并非單一個體的啟蒙,而是更廣泛意義上的人的普遍啟蒙。康德充分意識到了在現實世界中人的啟蒙所將遭遇的困難。對于個體而言,在習慣了他人的照料之后,要從近乎本性的懶惰和懦弱之中擺脫出來并學會自主思考是極其困難甚至是充滿了危險的,而只有依托于公共領域,啟蒙才是可能的。只有在公共領域之中,個人才能被激發出主動運用自己的理性的積極性,也只有在與他人的溝通之中,個人才能學會如何進行普遍有效的思考。這也就意味著每個人都被深深地嵌于自己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之中,只能與同時代人一起在交互影響和自我反思的關系之中逐漸地自我啟蒙。啟蒙并非某個單一個體的事情,而是一項公共的事業,這也就注定了它是“一件困難的而且只能緩慢完成的事情”(V 294)。而革命雖然在權利的意義上會造成一種斷裂的狀態,但并不會像后來的阿倫特所認為的那樣可以造就一個新的開端a阿倫特:《論革命》,陳周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頁。,根本原因就在于被特定的傳統和偏見所束縛的人們不可能通過革命就能一下子建立起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正如托克維爾后來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所表明的,人們誤以為是大革命的產物的許多思想、情感和制度,恰恰是舊社會的殘余。b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1頁。在《什么是啟蒙》里,康德事實上就已經很明確地表達了這一觀點:“公眾只能緩慢地通往啟蒙。通過一場革命或許可以推翻個人的專制和貪婪心或權勢欲的壓迫,卻不可能帶來思維方式的真正改良,相反,新的偏見將會和舊的偏見一起成為毫無思想的大眾的桎梏。”(VIII 36)激進的暴力革命不僅無法把控自身的走向,即使它取得了成功,也無法塑造新社會所需要的主體,正是這一點決定了我們很難通過一場暴力革命建立起全新的秩序,而這直接與盧梭的革命觀相對立。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明確地表達了革命對人性和習俗的改造所可能具有的積極作用,這幾乎是一個已經被腐化的民族能夠獲得新生以配享自由的唯一希望,雖然這一作用也是建立在諸多的偶然性之上的。“正如某些疾病能震蕩人們的神經并使他們失去對于過去的記憶那樣,在國家的經歷上,有時候也并不是不能出現某些激蕩的時期;這時,革命給人民造成了某些重癥給個人所造成的某些情形,這時對過去的恐懼癥代替了遺忘癥;這時,被內戰所燃燒著的國家——可以這樣說——又從死灰中復活,并且脫離了死亡的懷抱而重新獲得青春的活力。”c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56頁。盧梭在這里表達了一種浪漫主義的革命觀,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實際上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即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塑造全新的社會主體:“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a《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頁。而康德很顯然并不認同這樣的革命觀,在他看來,暴力革命非但不能讓人擺脫舊的偏見而形成新的思維方式,反而會將人們拋入更深的偏見和對立之中,并因此不可能成為建立并維持全新的制度的主體,這構成了他反對革命的第二重理由。
四、結論
由此可見,康德對革命的拒斥并不能簡單地被歸結為對現實政治的妥協,而是包含著深思熟慮的理由。而這些理由合起來也就指向了一個以啟蒙為核心的政治改良主義的方案,這一方案以在經驗層面上實現一個合乎理性的權利秩序為目標,但其方式只能是漸進式的,正如康德在《權利學說》中所總結的:“如果它不是革命地,通過一個跳躍,即通過暴力地推翻迄今所存在的有缺陷的憲法——(因為這將會瞬間導致所有權利狀態的解體),而是通過逐漸地依據固定的基本原則的改良而被嘗試和被實施的話,那這一理念能夠引導我們持續地接近最高的政治的善,接近永久和平。”(VI 355)人們當然可以進一步質疑康德關于持續改良的可能性的設想是否太過于樂觀,尤其是在某些統治形式下持續的政治改良最終必然會要求政體原則的根本變更,改良這時就會觸及無法逾越的限度。但是從權利論證的角度來看,所謂的積極抵抗權的確很難獲得辯護。唯一可能的辯護方式或許是像馬克思那樣,徹底摒棄權利的話語,轉而從社會歷史運動的角度去理解革命的必要性。但這對于西方近代以來以權利概念為核心的政治哲學而言,將會是更為致命的,因為這將意味著它的規范性基礎的徹底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