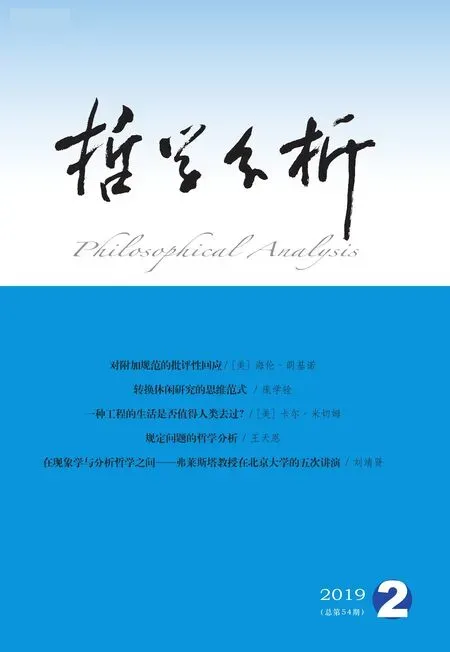規定問題的哲學分析
王天恩
現代科學和哲學中描述(description)問題的全面凸顯和深入研究,使作為描述前提的規定(stipulation)成為亟待進一步探索的重要課題。a王天思:《描述和規定》,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而在當代信息文明的實踐層面,大數據基礎上的創構,特別是人工智能研究,則使規定浮出水面,使在先規定的研究成為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
從語言學中的規定主義(prescriptivism,stipulationism)和描述主義(descriptivism)到哲學中的規定主義(stipulationism)和描述主義,從規范人類行為的外在法規到與事物“本質”相聯系的內在規定性,規定問題的研究既涉及認識論、價值論、倫理學、邏輯學和美學,又涉及語言學、心理學、法學,甚至政治學。這一特點決定了規定問題的研究具有多學科交叉的綜合性質,涉及對于真、善、美共同哲學基礎的探索。
作為人類(目前為止只有人類)為認識對象所作的關于量和質、方式、方法和模式等的規范性設定,規定注定具有異乎尋常的復雜性。關于規定的研究,人們可以在語言學和哲學中感受到一種共有的張力。語言學和哲學研究中由“規定主義”和“描述主義”構成的張力機制,使規定問題得以從思想深處凸 顯。
一、語言學中的規定主義致思
在語言學中,規定主義不僅有“prescriptivism”,還有“stipulationism”意義上的,只是“stipulationism”的使用頻率遠不如“prescriptivism”高。語言學中的stipulationism受到越來越多挑戰,以至于早在20世紀80年代,聯結主義(connectionism)的興起就被認為“為規定主義提供了一個替代選擇”aBrian MacWhinney, Language Emergence in An Integrated View of Language Development—Papers in Honor of Henning Wode, edited by P. Burmeister, T. Piske, and A. Rohde, Trier: Wissenshaftliche Verlag, 2002, p.17.。之后“形式語言理論也開始遠離規定主義”bN. Chomsky,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而“從歷史發展看,突生論(emergentism)是作為對規定主義的反叛開始的”cBrian MacWhinney, Language Emergence, p.18.。與“stipulationism”不同,辭典編纂的規范主義和規范語法則在語言學研究中始終具有重要地位。
在語言學研究中,辭典編纂的規范主義和規范語法雖然分別有被辭典編纂的描述主義和描述語法淹沒的現象,但這不僅不意味著語言學中關于規定問題研究的式微,而且相反,語言學中關于規定問題的研究,事實上正是在與規定主義和描述主義、規定語法和描述語法所構成的張力中得以更深入系統。
一些辭典編纂的規范主義代表人物被看作語言上的保守派,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語言是活的;與語言的使用性相比,語言的規范性不僅在關系上位居次要,而且二者的權重完全不同。從根本上說,語言的規范從屬于語言的使用,因為語言的規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語言的使用服務的。在規范語法和描述語法中,這一點有更具生命特征的展開。
語言是活生生的,是在人們使用中的生命體。因此語言規范不是依據某個一成不變、具有本質特質的既定標準而存在,而與人們使用語言的需要和使用的具體情景密切相關。因而,語言的規則和使用規范本身不是一個枯死的標本,而是活生生的具有生命的過程。規定主義辭典編纂原則似乎完全是一個僵死的原則,但這一原則反映了兩個重要方面的內在關聯。
一方面,語言是最講究規范的,沒有規范的語言不能成其為語言,因為它不能使用,達不到使用語言的目的。另一方面,對于語言來說,最根本的是使用。正如不會投入使用或沒有使用價值的工具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工具,不會進入使用的語言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語言。因此,語言的規范性是為語言的使用服務的,從屬于語言使用者使用語言的需要。由于人們使用語言的需要始終處于變化發展之中,語言本身也在隨之不斷變化發展。語言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其規范也在不斷變化。作為語言的關鍵要素,語言規范與語言的使用密切相關,而不是某種與具體使用無關的標準,也不存在一種關于語言規范的無條件客觀標準。要把握語言這個不斷發展的有機體,就必須把握語言不斷演變的規范,這就必須客觀地描述不斷變化的語言,其中就包括對語言使用規范本身的描述。在這個意義上說,正是描述主義更好地體現了語言規范,體現了語言的規定性,即語言——包括其規范——的約定俗成性質。
英語詞典編纂雖然經歷了一個從以規定主義為原則到以描述主義為主流的過程,其發展趨勢是從規定性轉向描述性,但規定主義始終具有自己不可取代的位置,只是規范從強制性轉向指導性。發展到當代,作為兩種在理論上曾經完全對立的觀點,規定主義和描述主義呈現出兩相結合的總趨勢。這種結合趨勢,在語法理論研究中如出一轍。
規定語法明確規定什么正確、什么不正確,以固定不變的標準把語言當木乃伊了;而語言是活的,語言的生命就是語言的使用。英語的規定語法最早根據拉丁語法建立,但隨著英語的發展,日漸與實際使用中的英語拉開距離。特別突出的是,一方面是實際使用中的英語,另一方面則是規定語法為口語的習慣用法。后者所規定的條條框框,與前者越來越不相符合。描述語法則著眼于描述語言實際使用的方式,更注重語言的約定俗成本性,注重語言應當如何使用,而不是把約定俗成的語言規定看作不可移易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個外在的固定標準可以脫離語言本身活生生的使用。
由于把語法看作語言使用者廣泛默認的結果,描述語法更關注語言的變化及其文化語境的時代性。但也正是由于語境及其時代性,脫離習得語言環境的外語學習曉示了描述語法的局限性。當人們的語言習得脫離語言使用的文化語境時,最好的辦法就是抽取該語言的截面,把它制作成一個干枯的標本,供外語學習之用;不這樣做,人們就沒有辦法或難以脫離語言環境學習一門外語。在這樣的情況下,純粹的描述主義弊大于利,甚至不可行。
作為人們在語言使用過程中供大家共同遵守的規則,語法具有很強的“規定性”,但語法沒有一個客觀的、本質性的標準。正是語言重在使用,從而使語言或語法的“本質”概念失去了意義。這也正是在感性實踐中,“本質”概念失去原本意義的根本原因。語法就是語言的實際用法,一切取決于語言實際使用中使用者的需要及其語境。正是語法,以一種最為平常的方式標示著本質主義的癥結所在;正是實踐使用,使“本質”概念從本體意義回歸到描述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語法也許是標明本質主義臆造性的最好例證。這也是維特根斯坦那么熱衷于語言游戲研究的內在原因。
語法必須具有相對規范因而是相對穩定的,但語法本身不是語言的標準。語言的標準是生活實踐,是語言的實際使用需要。因為,正是人的生活需要語言,而語言的使用需要語法,而不是相反。語法如同交通規則,也像交通規則一樣決定于交通的實際需要——當然歸根結底是人的需要。人的語言是供人使用的,而不是相反。
與規定語法一樣,辭典編纂的規定主義把語言規范絕對化,堅持說法和寫法非“對”即“錯”的固化標準,將語言因時代變化而突破既定規范的現象看作語言的退化。這種主張甚至推動成立專門組織“照看語言”,以遏制語言的變化,從而日漸走向保守。
描述語法立足于語言的約定俗成,因而反映了時代性,關注語言的變化發展。這種語法理論的一個主要根據,就是歷史上是錯誤的語法,可以由于語言的現實發展變成新的語法現象。在語言的使用中,語法變異就像某些生物變異,它正是語言發展的契機,不能等同于語法錯誤,比如“很中國”和“百分百”等。社會發展速度越快,語法變異發生的頻度就越高。在信息文明時代,語法的變異甚至成了網絡語言的標志性特征。一些網絡語言雖然明顯具有不受傳統語法制約的隨意性,但由于得到網民的普遍認同,就融入了網絡語法規則。在語言環境中,由于文字作為即時交流的工具,中文語言的變化就受文字拼音的極大影響。“神馬是浮云”,如果脫離網絡時代,只能往文學性描述理解;而從網絡語言活生生的使用中,我們卻可以看到它與時代相契合的奇妙使用效果。而規定語法則闡明了一種語言具有相對穩定的共同規則的根據,這是有效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基礎。所以,人們強調教師在語言教學中應當以規定語法為基礎。但是,規定也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發展的。如果句子“被和諧了”很常用,從描述語法看,其存在就是自然的,而從規定語法看則會被認為語法蹩腳,應當改為“出于和諧考慮被……”了。這里之所以有這種區別,主要在于語言必須有規范(約定)的一面和俗成的一面。也就是說,語言歸根結底是用來使用的,只有使用中的語言才是活的語言,因而語言是與其使用分不開的。這是語言學研究的一大進展,同時也是推進哲學研究的重要契機。
語言既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產物,又隱含著人類認識形成及其性質的密碼。描述和規范的語言學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其形式方面。事實上,不僅在語言形式中,在經驗科學中——即使在人們心目中最具客觀性的自然科學中——也是如此。
二、科學研究中的規定問題
在社會生活中,我們常常必須作出某些規定;所有的法律和規范都是建立在這種規定基礎之上的規則的典型形式。但規定并不僅限于社會生活領域,即使在對于自然的描述中,規定也都無所不在。如果這一點在經典科學中表現得還不是很明顯,那么在相對論和量子理論中則再清楚不過了。
在牛頓力學中,不僅有一個一個似乎與外部客觀存在一一對應的概念及其所構成的體系,而且有一些特殊的規定,比如“伽利略坐標”和“萬有引力”等。現代科學的發展表明,“伽利略坐標”沒有一個對應的客觀存在,只是我們根據建立經典物理學理論需要設立的一個規定。而一些看上去并不那么特殊,甚至與我們的日常經驗高度契合、似乎完全是客觀存在的基本概念,實質上也是規定,典型的如“波動”和“粒子”等。而在量子領域,則完全不像我們的經典想象,一些基本概念的主觀規定性質暴露無遺。正是量子力學,使規定問題在現代科學中得以集中凸顯。深入考察量子理論基本概念的規定性質,是規定問題研究的重要基礎工作。
在量子力學的建立過程中,相對于經典物理學,物理學家們遇到了空前的理解困難。早在1926年,量子力學的數學表達形式就已經基本完成。量子力學的數學形式十分成功地表達了微觀領域的復雜關系,可是與以往的科學體系完全不同,它對于我們理解現實過程幾乎沒有任何幫助。正如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在談到當時的感覺時所說的,量子力學“顯得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對它的正確性確實不能有進一步的懷疑。但我們仍然不知道對這種量子力學應該如何進行解釋,我們應該如何談論其內容”aWerner Heisenberg, Encounters With Einste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12.。英國理論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的創始人之一狄拉克(Paul Adrie Maurice Dirac)也曾回憶道:“我們雖然有了涉及這些非對易量的方程,但在當初,我們沒有對于這些方程的一般解釋,對于一個物理理論來說,那確實是一種奇異的情勢。”bP. A. M. Dirac, Directions in Physics, John Wiley, 1978, p.7.面對這種不能有直觀理解的理論體系,物理學家們不能不感到不安。即使一些現代物理學家也仍然有同樣的感覺,巴瑟爾·希勒(Basil Hiley)就曾寫道:“我已經被作為一個物理學家培養成才,我覺得直觀總是具有極大幫助。但當我考察量子力學時,我發現它完全是非直觀的。我們只有一種規定——一組規則:我們有一個波函數,它被假定描述了系統的狀態;我們有一個算符,它可以運用于這個波函數及我們從中得到一定具有預示性的實驗數據。但這對于我理解——譬如說雙縫實驗并無幫助。當穿過狹縫時,電子到底在干什么?它是穿過一道縫,還是穿過兩道?這些問題對于力圖獲得一種什么正在實際發生著的感覺,是極為重要的。”aP.C.W. Davies, Julian Brown, The Ghost in the Atom: A Discussion of the Mysteries of Quantum Phys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36.這里所涉及的,就是規定和規定問題。
現代科學越來越不容置疑地表明,在自然科學領域,科學家們所建立的關于自然的科學理論,并不是客觀實在的鏡式反映,而只是對它的描述。那些沉湎于描述的科學家,始終把對自然的描述當作自然本身的性質或對自然的純客觀認識。人們談論著、描述著世界,而沒有注意到描述者,更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作著一種與以往不盡相同的努力。
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學者們似乎與此不同,他們所面對的是宏觀事物,好像不存在描述與解釋分離的問題。在這些領域,描述似乎是不重要的,正像在經典物理學中那樣,人們所要關注的似乎只是理解或解釋(interpretation)問題。其實,那只不過是多了一層“建筑”,或者說更隱蔽些而已。一些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的文本就是描述的結果,就是一種描述。在那里同樣存在著描述問題。而且,人類認識越是深入,描述問題越是明顯和突出。只是在人文世界和宏觀領域,由于更深地卷入人類學特性,描述問題進一步滲透進規定的問題。在這些領域,描述問題的研究主要側重規定問題,這是關于規定研究的內容。關于規定的哲學研究更深地涉入人類學特性,它是在人文世界和宏觀領域描述研究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描述問題研究的重要內容是對語言表達式的分析,但其根本任務則是對我們描述的探究。而描述的規定基礎問題,則典型地表現在當代自然科學前沿。
在當代基礎科學發展的前沿,我們可以最為典型地看到描述和實在這兩種不同致思的微妙而富有深意的交織。其中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之一,就是當代英國著名科學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虛時間”概念的提出和在宇宙描述中的運用。
虛時間聽起來的確有點像科學幻想,但作為一個很好定義的數學概念,它就是用虛數度量的時間。虛數是數學上和實數對應的數,它對應于一根垂直線上的位置:零在中點,正虛數畫在上頭,而負虛數畫在下面。這樣虛數可被認為是與通常的實數夾直角的新型的數。事實上,在對宇宙的描述中,虛數的引入本身更意味深遠。
由于虛數“是一種數學的構造物,不需要本體的實現;人們不能有虛數個橘子或者虛數的信用卡賬單”。從實在論角度看,“人們也許會認為,這意味著虛數只不過是一種數學游戲,與現實世界毫不相干”。然而從霍金的哲學立場看,“人們不能確定何為真實。人們所能做的只不過是去找哪種數學模型描述我們生活于其中的宇宙”。由于人們發現牽涉到虛時間的一種數學模型不僅預言了我們已經觀測到的效應,而且預言了我們尚未能觀測到但因為其他原因仍然堅信的效應,霍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哲學問題:“那么何為實何為虛呢?這個差異是否僅存在于我們的頭腦之中?”a史蒂芬·霍金:《果殼中的宇宙》,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57—59頁。這一問題不僅涉及對宇宙的描述本身,而且涉及規定的基本問題。虛時間概念本身,再好不過地表明描述和實在的關系。正因為其“虛”,虛時間使我們看到描述和描述對象本身的不同。由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到,霍金通過自己的工作所得出的一些觀念意義重 大。
霍金自稱實證主義者,他同意英國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Karl Popper)的基本觀點,認為科學理論只不過是一個數學模型,它描述和整理我們所進行的觀測。一個好的理論可以在一些簡單假設的基礎上描述大范圍內的現象。并且作出能被檢驗的確定的預言。如果預言和觀測相一致,則該理論成立,盡管它永遠不可能被證明是正確的。如果觀測和預言相抵觸,人們就必須將該理論拋棄或加以修正。從實證主義立場出發,我們不能說時間究竟為何物,人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將所發現的現象描述成時間的一種非常好的數學模型并且說明它能預言什么。b同上書,第31—32頁。然而,霍金不是一個簡單的實證主義者,他在建構自己的宇宙理論時具有豐富而深刻的關于描述和規定的思 想。
霍金認為,我們不能詢問一個理論是否反映實在,因為我們沒有獨立于理論的方法來確定什么是實在的。甚至在我們周圍被看作顯然是實在的物體,也不過是在我們頭腦中建立的一個模型。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能有幾種對于宇宙的不同描述,所有這些理論都預言同樣的觀察。我們不能說一種描述比另外一種更實在,只是對一種特定情形來說,某種描述更方便。所以一個科學理論網絡中的所有理論都處于類似地位。沒有一種理論可以聲稱比其余的更實在。即使時空及其維度,也不是絕對獨立于理論的量,而只是依賴特殊的數學模型導出的概念。這樣一來,什么是實在的呢?根據實證主義哲學,這是沒有意義的問題。因為不存在獨立于模型的實在性的檢驗,或者說什么是宇宙的真正維數是沒有意義的,在宇宙理論中,四維和五維的描述是等效的。我們生活在三維空間和一維時間的世界中,我們對這些自以為一清二楚,但是我們所看到的自己,也許只不過是柏拉圖“洞穴”中,閃爍篝火對面我們在墻上的投影而已。面對那個“膜的新奇世界”,“我們不能問什么才是實體,是膜還是泡泡?兩者都是描述觀測的數學模型。我們可以隨便使用這兩個模型,哪個方便就使用哪個”a史蒂芬·霍金:《果殼中的宇宙》,第198頁。。在這里,我們所看到的不應當是對真理的否定,而是關于真理問題的更真實闡述。這種闡述之所以更真實,就因為它是建立在對量子力學規定性質認識的基礎上。無論語言學還是科學中的規定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哲學意蘊,都與哲學研究中的規定問題聯系在一起。
三、哲學研究中的規定問題
在哲學中,規定主義(stipulationism)與約定主義(conventionalism)密切相關。約定主義盡管受到諸多批評,但以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為代表的“約定論”研究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始終給我們以不能擺脫的影響。
彭加勒認為,幾何學中的基本命題,包括歐幾里得公設,都不過是些公約。因此問它們的真假是不合理的,問它們是真的還是假的,就像問米達制是真的還是假的。彭加勒的這一觀點,并不像有些理解那么簡單,他在兩方面作了重要解釋。一方面,“這些公約是便利的,而這是若干實驗告訴我們的”;另一方面,“這種公約并非絕對任意的;它不是由我們的私意而出;我們采用它,因為有些實驗向我們指出它是便利的”。正因為如此,他甚至批評有些哲學家把全部科學看作原理,從而把全部科學看作公約。彭加勒認為這種觀點是唯名主義的,“這種荒謬的學說”“不值一談”。b彭加勒:《科學和假設》,葉蘊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97—98頁。因此,對于約定主義觀點,我們絕不能想當然地簡單對 待。
即使我們忽視甚至反對約定主義,但無論如何不能對后現代主義思潮的約定論特征視而不見。約定論觀點中很多重要約定的假設性質及其試圖在經驗論與先驗論之間作出新的探索,都表明約定論與預設理論的內在關聯。正是從規定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由吸取約定論的合理因素到深化規定問題研究的重要方向。
約定主義是這樣一種觀點,“認為某些事實是能動者(agent)建構的,而敘述它們的句子也是這種行為使其為真”cJohn Woods and Alirio Rosales, “Virtuous Distortion Abstraction and Idealization in Model-Based Science”, in Lorenzo Magnani,Walter Carnielli, and Claudio Pizzi (eds.), Model-Based Reason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Springer-Verlag Berlin and Heidelberg GmbH & Co. K, 2010, p. 24.。而且,科學理論中的很多內容都具有約定的性質。
哲學中的“規定主義”具有與約定主義相似的一面,認為“某些對象和某些事態與其說是被發現的,不如說是被創設的,而涉及其創設的是它們被想出來(being thought up)。同樣,規定設定了對象和事態在這樣的方式中被想出來——使表達它們的句子為真。”更簡要地說,規定主義“認為某些事實是被建構的,而且一些關于它們的陳述是能動者的語言行為使其為真”aJohn Woods and Alirio Rosales, “Virtuous Distortion Abstraction and Idealization in Model-Based Science”.。 這既與真理問題密切相關,又在一個不同角度涉及實在論。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教授伍茲(John Woods)的“真理的規定性 (stipulationist)理論”就試圖“在抽象領域發展一種反實在論,在這種抽象領域的核心保留反實在論傾向”bA. D. Irvine, John Woods,“Paradox and Paraconsistency: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Abstract Sciences (book review)”, Studia Logica, Vol. 85, Issue 3, 2007, pp. 425—428.。規定主義認為一些事實是被建構的,而關于它們的一些陳述的真則是能動者的語言行為使然,這就無疑脫離了規定所必不可少的客觀根據。這是規定主義既具有重要思辨張力,同時又面臨諸多挑戰性問題的根本原因。
規定的客觀根據問題在給規定主義帶來嚴重挑戰的同時,又使規定本身的研究蘊含著重要契機。一方面,在哲學中,人們認為規定主義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而且是富有成果的,但是規定主義未必能對這一現象作出自己的解釋。“規定主義者必須解釋,這種關于對象的方法論迷戀為什么會產生這種成果”,由于規定主義“以對象為中心的思想只是解釋學的”,讓人們擔憂規定主義者“不能作出解釋”cJody Azzouni, “Proof and Ontology in Euclidean Mathematics”, in New Trend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edited by Tinne Hoff Kjeldsen, Stig Andur Pedersen, and Lise Mariane Sonne-Hansen, Denmark:University Press of Southern Denmark, 2004, p. 120.。這種擔憂肯定不無根據,而規定主義在客觀根據方面的不足則是最為根本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規定本身的地位越來越凸顯,在哲學特別是數學和邏輯學的哲學基礎中,規定主義仍然是強大的張力來源;甚至在經驗科學中,規定問題亦日漸凸顯。
隨著哲學的發展,規定的特殊地位早在近代就已露端倪,“對于康德來說,規定是綜合,就是新概念的創設”。這里可以看到規定問題在哲學中的基礎地位,規定與綜合密切相關。“分析和規定的區別大致相當于康德的分析與綜合對比。康德認為,分析的任務是使概念清晰,綜合的任務是創設明確的概念,那就是構造概念。”dJohn Woods, Semantic Penumbra: Concept Similarity in Logic, Topoi( 2012) 31:121,C134.這已經是對規定的直白說明了,只是在西方近代哲學中,由于自然科學的發展還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規定性質,從而還沒有更強有力的支撐,關于規定問題的研究條件還不成熟,以致數學和邏輯早已天然表露出來的規定性質,也被掩映在“先驗”或“先天”的迷霧之 中。
事實上,數學的規定性質最為明顯,而且最易于為人們所理解。“規定在近代哲學中歷史悠久,而且很久以來在數學中發揮著主導作用。”aJohn Woods and Alirio Rosales, “Virtuous Distortion Abstraction and Idealization in Model-Based Science”.而“對于羅素而言,規定是數學定義,這使事物為真而沒有產生由以說明如何為真的概念”bBertrand Russell,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37, p. 27.。由于規定的約定性質,人們很難想象,規定怎么能支撐起精確的數學。因而“規定主義”就時而被當作存在問題的標志。喬納森·卡斯汀(Jonathan Kastin)就被貼上“數學規定主義”的標簽。cJody Azzouni,“Proof and Ontology in Euclidean Mathematics”.直到現代人們才認識到,雖然規定隨約而變,卻并不影響它們作為理論的基礎。“正像康德所說,規定是數學的股票和貿易(stock and trade)。但它也在所有基于模型的科學中穩定地工作。”dJohn Woods, Semantic Penumbra: Concept Similarity in Logic.而變動不居的規定成了基礎,這正是規定在人類認識中起作用的方式。也正因為如此,數學和邏輯都具有規定的性質。
與數學相似,邏輯也具有明顯的規定性質。“一個虛無主義的早期預示是卡爾納普的寬容原則,按照它的觀點,邏輯既是規定性的(stipulationist),又是與人的意識無關的事物的先在事實(unattended by antecedent facts of the matter)。對于卡爾納普來說,邏輯是你所做成的東西。”eIbid.事實上,不僅數學和邏輯,也不僅在語言學和科學中,在哲學中,規定問題的研究早就開始了。在約定論(conventionalism)和預設理論(theory of presupposition)中,在當代哲學前沿,這種研究由于涉及對象的內容而事實上轉向規定問題的哲學研究。因而,規定問題的研究將涉及規則和規律的共同哲學基礎。在我們的認識中,規則和規律似乎是涇渭分明的。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游戲都必須有規則,規則賦予游戲以意義。“要獲得一種意義也必須用公約”,而公約就是典型的規定。所有的游戲規則都必須建立在一定的規定基礎之上。事實上,所有理論基石都具有規定的性質。“蒯因(Quine)說理論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概念化;愛丁頓(Edington)說它們‘是預先商定的工作’。”fIbid.而哲學更是如此。人們之所以認為“分析是哲學的范圍,綜合則是數學的領域”,只是因為從分析哲學的傳統把哲學看作只是分析。只要承認“解釋和理性重建是二者的結合,只是解釋更多的在于分析而理性重建則更傾向于規定”gIbid.,哲學基石的規定性質就是理所當然的。而所有理論基石都具有規定的性質,正是規定對于科學和哲學研究的重要性所在。
所有理論都是規定及其相互關系構成的體系,我們必須在規定的基礎上作出解釋;而在解釋的基礎上,我們又可以作出更新的規定。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正如奎因的著名妙語:一個人的解釋,是另一個人的規定”aJohn Woods, Semantic Penumbra: Concept Similarity in Logic.。解釋和規定建立起一個無限的思想空間,在這個空間中進行著“人類的偉大創造” (愛因斯坦語)。只是我們必須在基于規定建構起來的空間中,將真理問題落到一個更真實的基礎之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規定回答這一問題:‘那么,怎樣使它們為真的?’答案是,他們被理論家規定為真”,也就是說,“由此引起的關鍵問題是:理論家的規定——他的如是說——何以可能產生真理?”bJohn Woods and Alirio Rosales, “Virtuous Distortion Abstraction and Idealization in Model-Based Science”.在這里,問題本身就是深化研究的“端口”。而這一問題的解答,卻正是在規定問題的研究過程中,真理問題本身探索的深入,無論在科學還是哲學中都是如此。哲學基石的規定性質自不待言,科學基石的規定性質也正是哲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因而規定問題就成了哲學研究至關重要的內容。
霍金關于前沿科學問題的哲學探索,表明他不僅是一個科學巨人,而且像愛因斯坦和波爾他們一樣,也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至少就其所涉及的描述和規定問題而言是如此。從規定的角度,我們可以把“實在”作為一個規定來考察,把關于實在的規定提到一個比“關于實在是什么”的問題更具前提性的地位。甚至“實在是什么”的問題本身,也可以改寫成更有效的“我們關于‘實在’的規定意味著什么”的問 題。
在關于規定研究的哲學前沿,當塞爾孟(Nathan Salmon)說我們的規定和形而上學的規定是兩種不同的規定(decides)cNathan Salmon, “Trans-World Identification and Stipulation”,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84, 1996, pp. 203—223.時,其實就把形而上學看作與我們的認識無關的外在于我們認識的東西。事實上,我們的規定和形而上學的規定是同樣的一個規定,因為即使形而上學本身也建立在我們規定的基礎之上。因而,與我們相關的法規(legislation)和形而上學的法則(law)事實上是同一個東西。在計算機科學中,我們則可以看到一種與規定更為密切相關的情形。規定語法有一套語法規則規范語言,而描述語法則詳盡、完整地描述語法結構的規律。在數學、邏輯學和計算機科學等學科中,所使用的形式語言的語法是描述語法,而自然語言的語法則往往既具有描述性又具有規定性。在這些領域,規律和規則相互交織,甚至可以通用。之所以如此,就因為對象的存在方式與我們作為特定宏觀主體的人類學特性密不可分,與我們的思維規定密切相關。所有這些都在提示著一個重要研究領域:關于規定問題的哲學研究。
關于規定問題的當代哲學研究,弗雷格的探索是深層啟動,維特根斯坦的奇特命題是規定問題研究的重要啟示,之后才有了克里普克的邏輯展開和規定問題研究的當前進展。規定問題的當前研究,首先是在規定的使用中研究規定問題。在使用中探究規定,正是規定問題研究本身能具有的基本特點,也是不同于傳統哲學范式的重要特色;其次是在專名研究中涉及規定的形成機制,弗雷格和克里普克關于專名和通名的研究,蘊含著關于規定形成機制的重要思想萌芽;再次是在悖論消解中研究規定;最后是在邏輯和經驗間探索規定與真以及先驗性問題。
四、結 語
關于規定問題的哲學分析表明,隨著人類認識的發展,特別是大數據開啟的信息文明的到來,關于規定的反思日益凸顯,規定論研究呼之欲出。
規定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有規定的形成、規定的性質、規定的發展和層次、規定的合理性和合理化等。規定形成不僅具有特定的客觀根據,而且與主觀需要密切相關;規定具有實踐性、相對性、主體間性、規約性、抽象性和人類學特性。規定的類型主要包括有限規定和無限規定、相對規定和絕對規定、具體規定和抽象規定、知性規定和理性規定、經驗規定和邏輯規定、定性規定和定量規定等。既存規定的突破把描述帶入一個更高的層次,意味著規定的發展。規定的層次呈現出一個以理性為中心的系列:涉及否定概念的規定、涉及思維邊界的規定以及涉及活動前提的規定和涉及理性本身的規定。規定的合理性包括形式的合理性和實質的合理性。規定的合理化不僅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而且具有以人類實踐需要為轉移的性質。在規定的合理性發展和合理化過程中,規定批判居有重要地位,涉及規定的反思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