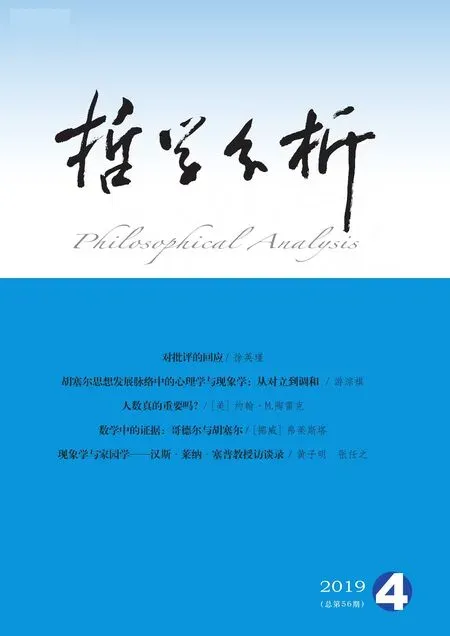從“興于詩,立于禮”看詩性智慧
——試論《詩》禮合一的成德之學①
黃子洵
子曰:“興于詩,立于禮。”②《論語·泰伯》。在注釋中,朱子把“詩”和“禮”分別與“學者之初”“學者之中”相對應,認為初學者首先應該學《詩》,在此基礎上再來習禮。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指出:“學《詩》之后即學禮,繼乃學樂。”③劉寶楠:《論語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98頁。相比起劉寶楠的解釋,朱子側重于強調為學階段的不同,并根據時間的先后順序區分出為學境界的高下。盡管如此,兩位學者都把學詩、學禮視為求學的先后階段,主張學《詩》之后,繼而學禮,并引《禮記·內則》為證,“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④孔穎達:《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3頁。。
《詩》與禮被視作求學之人在不同年齡階段學習的不同內容。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詩》與禮的關聯:兩者都從屬于禮樂造士的傳統,都是育人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教學內容。那么,這一解釋是否道盡了孔子將《詩》與禮并稱的用意?
雖謙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對六經精神的體究不可謂不深。夫子屢次將《詩》、禮并提,如“不能詩,于禮謬”①孔穎達:《禮記正義》,第1619頁。,“詩之所至,禮亦至焉”②同上書,第1627頁。,這只是對當時教育方式的客觀陳述,還是另有深義?這一問題也可以表述為,《詩》與禮是否存在著內在關聯?本文立足于孔子的詩學理論,以“興于《詩》,立于禮”作為切入點來探究以上問題。“興于《詩》,立于禮”③這句文本原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限于筆者有限的學養,同時也考慮到論文的篇幅要求,該論文只探討了《詩》與“禮”的關系。至于《詩》、禮、樂三者的關系,則留待以后。雖寥寥數語,卻內涵豐富,包含了多個層面的問題。孔子首先談論了《詩》,而后由《詩》過渡到禮。針對“興于《詩》”,我們不妨進行以下幾方面的追問。其一,興于《詩》何以可能?《詩》④在此,筆者有必要對“詩”的概念做一番梳理。自古至今,“詩”的概念一直處于歷史演變之中。在比較詩學崛起之后,“詩”這一概念的基本蘊含大大豐富了。在西方文化的語境中,“詩”(poiētikē)是從動詞“poiein”(制作)派生而來的,因此詩人是制作者,詩則是制成品。“詩學”一詞,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指的是文藝理論,中世紀主要指的詩歌的創作技藝和技巧;21世紀以后,詩學用于泛指廣義的文藝理論。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詩”除了用來指《詩經》之外,還可以指一般意義上的詩,即文人所創作的五七言詩體。本文所探討的“詩”嚴格限定于《詩經》。文本中的“詩學”所指的是對《詩經》的研究。具備什么特質,使得《詩》可以興?其二,這里的“興”該如何理解?“興”反映出《詩》的哪些獨特之處?以上思考有助于我們理解《詩》的本質及其哲學意涵。在探究“興于《詩》”之后,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詩》與禮相互貫通之處,并思考《詩》與禮的內在關系。
一、詩言志
子曰:“興于《詩》。”⑤《論語·泰伯》。朱熹注曰:“興,起也。詩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04—105頁。。首先要追問的是,興于《詩》何以可能?《詩》具備什么特質,使其能興起好善惡惡之心?
《舜典》雖然提出“詩言志”⑦孔穎達:《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頁。這一觀點,但尚未對“志”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給后人留下了豐富的闡釋空間。《荀子》指出《詩》與圣人之道存在著緊密關聯。“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⑧《荀子·儒效》。楊倞將“《詩》言是,其志也”解釋為“是儒之志”。
荀子論《詩》的落腳點在于圣人,楊倞論《詩》的落腳點在于儒。雖然圣人與儒的境界不同,但不可否認的是,以圣人和儒來論說《詩》之志,意味著“志” 已具有了一定的價值規定性,而非某個有待規定的中立的意向或意愿(intention)。《詩》之所以具備“興”的功效,與具有價值規定的志存在著緊密關聯。
此后,學界關于“志”的解釋逐漸拋去了圣人、儒者的光環。陳桐生指出,先秦兩漢時期的學者傾向于把“志”解釋為“志意”①盡管我們可以在字義學上為“志意說”找到文本依據,《說文解字》以“志”訓“詩”,以“意”來訓“志”,但這不足以說明“詩言志”之“志”可以直接等同于“志意”。。晉人摯虞和唐代孔穎達牽合“志”與“情”兩個概念,提出詩以情志為本。近人試圖證明志中包含著情感因素,“詩言志”即“詩言情”。②陳桐生:《禮化詩學——詩教理論的生成軌跡》,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
那么,我們如何看待以上關于“志”的種種解釋?相比起西方文藝學區分出的作者導向、作品導向與讀者導向理論,《詩》的情況更為復雜。倘若我們脫離《詩三百》的文本內容及歷史語境,僅僅是在語義學的層面抽象地探討“志”的內涵,“志”的含義難免失于空疏。
從《詩三百》文本的形成,再到整理匯編,再至最終的流傳與諷誦,《詩》之志存在著多重性。正如清代學者龔橙指出的:“《詩》有作詩之誼,有讀詩之誼,有大師采詩,瞽蒙諷誦之誼,有周公用為樂章之誼,有孔子定詩建始之誼,有賦詩,引詩節取章句之誼,有賦詩寄托之誼。”③龔橙:《詩本誼》,載《續修四庫全書·經部·詩類(7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頁。不少現當代學者同樣看到“詩言志”這一命題內涵的豐富性。俞志慧先生曾指出:“這里的‘志’理解為作者之志亦可,理解為讀者之意亦可,理解為修齊治平之抱負亦可。”④詳見俞志慧:《君子儒與詩教——先秦儒家文學思想考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08頁。
這樣一來,我們也許要問,在上述提及的“志”的多重維度中,哪一個維度最能代表《詩》之志?如果我們以維特根斯坦將概念比作家族的觀念來作為追問的起點,也許我們能發現以上發問的不妥之處。“每一個家庭都是許多個家庭的集合(包括男系與女系),概念也是一樣。在古老的時代,一個被任命為騎士的候選人,總免不了‘通報其家族的家族’的老套。當哲學家試圖去界定一個用意廣泛的概念之時,他似乎也該盡到相同的義務。”⑤瓦迪斯瓦夫·塔塔爾凱維奇:《西方六大美學觀念史》,劉文潭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頁。“志”不應被簡化為以上多重維度中的任何一種。因此,如果我們從這多重維度中單獨拈出某一個維度,將其視作“志”這一概念的全部,我們將忽略掉其他維度對于“志”的重要意義。
盡管“志”不應被簡化為某個單一的維度,我們仍能根據這眾多維度的重要性的不同,區分出本末先后之序。
《詩三百》篇之所以能成形,位列六經之一,采詩、獻詩、編詩的行動極為關鍵。洪湛侯先生曾強調匯編、整理過程對《詩三百》的最終形成起到的重要作用。“《詩三百》篇的來源有民間采集、士大夫獻詩、作詩配樂等形式和途徑,這些采來或獻來的詩歌,往往形式、字句、聲韻都不一樣。若不經過一番認真的整理,很難設想能夠有今天的面貌。”①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6—17頁。
作詩是個人層面的行為。而一經采編,再附樂歌奏,《詩三百》就不同于散落在民間、人們自發吟誦的詩作。“瞽矇和公卿列士獻詩的目的是長君之善,正君之過,太師教詩的目的是培養行人,使之能專對、達政,二者多屬家國之志而牽涉倫理、政治。”②陳桐生:《禮化詩學——詩教理論的生成軌跡》,第108頁。從作詩到采詩、獻詩再到編詩,《詩》完成了由個人領域到倫理政治的公共領域的轉向。采詩、獻詩、編詩之志作為重要紐帶,使《詩》成為一個有著內在關聯的生命體。眾詩以自身為中心的獨立性被削弱了,置身于一個整體之中,指向更崇高的目標——詩教。這樣一來,《詩三百》的布局謀篇是我們探究《詩》之志的重要進路。③然而,以往學者多注意到《風》 《雅》 《頌》三者的差異,未能將其視為統一的生命體。“《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劉安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來區分《國風》與《小雅》,并試圖用《離騷》這一他者來統攝《風》 《雅》這兩種不同的藝術風格。鐘嶸將《國風》 《小雅》當作兩種作詩風格的代表,并以此作為自漢至齊梁時代眾詩藝術風格的源頭。如古詩,“其體源出于《國風》,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鐘嶸:《詩品注》,陳延杰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頁)又如,阮籍“其體出于《小雅》。無雕蟲之功。可以陶性情,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 (鐘嶸:《詩品注》,第23頁)誠然,《風》 《雅》的確存在區別,否則編詩者為何冠以異名,為何《風》先《雅》后?關鍵在于,明知《風》 《雅》不同,還要將二者編次于同一部著作中,其用意何在?《風》在先,《雅》在后,《頌》處于末尾。這一順序究竟有何深義?在筆者看來,探究《風》 《雅》 《頌》的異中之同比放大三者的差別更有意義。欲觀《詩》之志,我們不妨把風格各異的《風》 《雅》 《頌》視作一個整體。
《毛詩大序》將《風》 《小雅》 《大雅》 《頌》列為詩之四始,通過政教范圍大小、政績王化的程度來闡釋四者的區分。四者形成了一個首尾渾然的意義系統,折射出圣賢的政治理想。平天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由身及家,由家及國,由國及天下,其立足點不離個人的成德。
一人之本,一國之事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的前提。國中人人皆正,一國之風化才能興起。一國之風化興起,四方之風才能興起,天下之化才能成就。在天下太平,王業成就之后,君王才能作樂,歌美先祖,因此,在《風》 《雅》之后,《詩》以三《頌》為終。《國風》以室家離合、宗族命運為出發點,諸詩的哀和樂多源于個人際遇和源于民生疾苦。《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視野亦由夫婦、室家等人倫切近處推及到君臣、朝野乃至夷夏。《國風》以《關雎》為首,由正夫婦至正室家,正室家及正邦國。二《雅》由室家推及朝政,意在正君臣,并進一步由正邦國至正天下。《頌》是四始之終,王化大成,澤及四海。功成作樂,通乎神明。
《詩三百》的布局謀篇啟示我們,《詩》所言說之“志”是由正夫婦到正室家、由正室家到正邦國、由正邦國及正天下,最終德合天地,功告先祖的愿景。
那么,《詩》是如何言志的?《詩》之志是如何呈現與展開的?
單從字面義看,《詩三百》記錄的無非是古人生活的各個面向,如個人的家庭生活、邦國的典禮場合以及宗廟祭祀活動等,展現了西周至春秋中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這一過程中,眾多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得以被塑造,如帝王、公卿諸侯、政府官吏、軍事統帥、勞動人民、各階層的婦女。①在《論〈詩三百〉形象類型及其審美意義》一文中,陳戍國先生對于《詩三百》中涉及的人物形象作了詳盡的分類與說明。詳見陳戍國:《詩經芻議》,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版,第212—236頁。初看上去,《詩三百》與志毫無關聯。在上古史料缺乏的情況下,《詩經》更容易被視為研究上古風俗民情的材料。
這一困惑不僅存在于近現代學界,明代學者楊慎在《升庵詩話》也曾有過一番追問:“觀《詩三百》,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周南》和《召南》所言多為琴瑟鐘鼓、荇菜芣苢、夭桃秾李,何嘗有修身、齊家字耶?”②楊慎:《升庵詩話新鑒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12頁。
在楊慎看來,直接論及“道德”“性情”“修身”“齊家”的著作才有可能被視為言志、載道的經典。相比之下,《詩三百》是對個人遭遇的敘述以及對典禮場合的記錄,更類似于記錄古人生活的文獻,充其量只能用作研究的史料。這樣一來,我們更傾向于從《詩三百》中辨識各種各樣的器物之學,而不是將其視為載道之言,從義理的角度去闡釋《詩三百》之志。
實際上,《詩三百》為我們展現的是一個鮮活的生存世界。這是日常語言所無法提供給讀者的重要維度。③王德峰老師曾對比過詩與日常語言的差別。“對同一件事的語言記錄,因其方式不同,可以產生完全不同的東西。一種是敘事,一種是由事入情。面對單純的敘事,讀者將無動于衷,他只是對某一個事件有了知識上的了解。面對‘詩的敘事’,讀者卻不可能無動于衷,因為他在了解到那個事件的同時,即被卷入了一個使事件之意義得以呈現出來的生存情感的世界。”詳見王德峰:《藝術哲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5頁。這一生存世界呈現的是在特定歷史—文化維度中,人類生存的各個可能性維度以及人在現實中的可能性遭遇。通過觀見前人紛繁復雜的生存面向與實踐維度,讀者有可能去探尋蘊藏在每一首詩中的幽深隱曲之志。
《詩》將一些角色和人物展現在我們面前。這些角色與人物有著不同的遭遇,大多數時候,他們作為無辜者,承受了種種不幸。大多數人物面對著某些共同的困境,如長年在外服役、被讒言所害,同時也對這個世界懷有共同的盼望,如與親人團聚、國泰民安。
每個人都試圖面對并解決這些問題:在某個獨特的歷史社會背景中,他們身陷何種困境,有什么難言之隱?在面對這些困境時,他們有怎樣的復雜的心理過程?最為關鍵的是,在這些復雜的倫理處境中,他們如何抉擇?凡此諸種并不是通過一系列理論來直接闡明,而是通過古人的生命樣態與生存實踐得以呈 現。
《詩》展示了處于復雜的倫理關系與政治境況中的各類人的遭遇,啟示我們思考人在世需要處理的多重關系,如自我與自我、家人、宗族、社會以及國家的關系等。在這眾多的關系中,倫理關系與政治關系是重中之重。倫理與政治是道落實于人文的必要途徑。人能弘道并不是說人直接地與道相關,而是通過人文化成來體認道。
綜上所述,《詩》的編次順序由《風》及《雅》,再由《雅》及《頌》,這一布局謀篇意味著《詩》所言說之“志”是由正夫婦到正室家、由正室家到正邦國、由正邦國及正天下,最終德合天地,功告先祖的政治愿 景。
這一具有價值規定性的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詩》可以“興”,但不意味著《詩》必然具備“興”的功能。畢竟與《詩三百》處于同時期的其他文獻或多或少也論及相似的愿景,曉諭讀者善惡之理,但此類文獻的興發作用遠不及《詩三百》。這樣一來,為了進一步探究《詩》為何可以“興”,我們應該進一步追問,《詩》言志的獨特性何在?
二、釋“情”:一時之性情與萬古之性情
《毛詩大序》指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①孔穎達:《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除了“志”之外,《毛詩大序》還關注到了另一個重要因素,即情。從心中有志到發言為詩,情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形于言的前提是情動于 中。
詩之志不是以刻板生硬的形式得以呈現,而是與情相偕,活潑潑地從內心中流淌出來。《詩》貴在以情動人,而非直接說教,以理凌人,故感人而易入。
“情”貫穿于從未言到已言的整個過程。但對于“情”的確切含義,《毛詩大序》沒有給出進一步的解釋。黃宗羲曾區分出“一時之性情”與“萬古之性情”,對我們厘清“情”的多重含義有所裨益。黃宗羲指出:“蓋有一時之性情,有萬古之性情。夫吳歈越唱,怨女逐臣,觸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時之性情也。孔子刪之,以合乎‘興觀群怨’、‘思無邪’之旨,此萬古之性情也。吾人誦法孔子,茍其言詩,亦必當以孔子之性情為性情,如徒逐逐于怨女逐臣,逮其天機之自露,則一偏一曲,其為性情亦末矣,故言詩者不可以不知性。”①黃宗羲著、陳乃乾編:《黃梨洲文集·序類》,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63—364頁。
吳歈越唱、怨女逐臣源于“觸景感物”,心中有所觸動而形于言。但在黃宗羲看來,這種情只是“一時之性情”。“一時”說明了這種情感體驗是暫時的,物現而生,物逝而散,變動不居,恒無定準。同時,“一時之性情”帶有極強的個體性。這一情感體驗往往囿于自身,缺乏普遍性,很可能只是當事人強烈的當下體驗,未必能夠持久,也未必能讓他人有所感動。而且即便是同一個人,在不同情境下因同一事物激發的體驗也很可能存在不同。出于以上原因,黃宗羲認為“一時之性情”只是“一偏一曲”,位列性情之末。
“萬古之性情”同樣源于感物而動。“萬古之性情”之所以可以稱為“萬古”,在于以下兩方面特質。一方面,這一情感體驗超越了個體性,為人類所共通。人同此心,心同此情。另一方面,“萬古之性情”穩定而持久。這一情感體驗雖由具體的事物觸發,但不會隨物的逝去而消隕。即使時過境遷,“萬古之性情”也不會減損半 分。
更重要之處在于,“一時之性情”本身的暫時性和不穩定性使其缺乏價值上的導向性,不足以成為涵養道德品質的基礎。與此相比,“萬古之性情”具有價值規定性和導向性,“合乎‘興觀群怨’、‘思無邪’之旨”。這一價值導向性將萬古之性情與其他情感區分開來。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區分,本文將“萬古之性情”稱作道德情感。道德情感一旦萌生并細加護持,會以此為基點擴充開來,最終形成堅韌不移的道德品 質。
基于以上的區分,我們可以對“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之“情”做一番辨析。此處所指之“情”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情感,并非“一時之性情”,而是“萬古之性情”,是具有價值導向性的道德情感。
孟子曾指出道德情感與道德品質的重要關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②《孟子·公孫丑》。朱子對“惻”和“隱”的解釋分別是“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③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39頁。。
旁觀者看到小孩即將掉入井中,自然而然產生怵惕惻隱的心理體驗。旁觀者的怵惕惻隱并不來自他對自己處境的擔憂,而在于他擔心那個快要掉入到井中的孩子。這種恐懼和擔憂并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①《孟子·公孫丑》。。從這一角度而言,旁觀者的怵惕惻隱具備了一種道德意義。
孟子對“惻隱”予以了相當積極正面的評價,將“惻隱之心”視為“仁之端”。仁這一道德品質不是抽象的,必定存在于具體場景之中,反映于對具體人事的應對之中。仁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必會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判斷一個人是否具有仁心仁德的一個重要標準。
與此相反,“不仁”的一個明顯表征便是麻木與無感。程子認為,醫書用“手足痿痹”來形容“不仁”,最為生動形象。不仁之人往往對周遭一切喪失了感受力。他人的一切處境無法激發任何的道德情感。 “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②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92頁。倘若對他人的困境缺乏最基本的惻隱之心,仁德根本無從談起。
同時,孟子也認識到,道德情感與道德品質畢竟還有差距。惻隱僅僅是人在具體場景中對于具體事件的情感表現,并不足以稱為道德品質。“惻隱”畢竟不能等同于“仁”。道德情感需要禮義來加以導養。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禮運》中的譬喻頗為可取,“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③孔穎達:《禮記正義》,第814頁。。鄭玄注曰:“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④同上書,第816頁。以禮義導養人情,前提是因順人情,而非革除人情,道德品質之于道德情感,正如稻禾扎根于沃土。因此,孟子對惻隱等道德情感予以充分肯定,認為四端經過擴充,能成長為道德品質。
那么,為什么《詩三百》將對道德情感的導養擺在如此首要的位置?
古人認識到,情感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實現自知的必要進路。正如納斯鮑姆所指出的,“研究情感形式是我們尋找自我認識的重要部分。情感的作用不僅僅是實踐知識的手段,而且也是我們對自己的實際處境最好的認識或知識之重要組成部分”⑤瑪莎·納斯鮑姆:《善的脆弱性》,徐向東、陸萌譯,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頁。。
同時,道德情感是維系人倫關系的紐帶。小至室家中的父子之恩、夫婦之別,大至宗族中的長幼之序、朝廷中的君臣之義,情感是維系這些遠近、親疏關系的重要載體。可見,無論是對于個人,還是對于群體,道德情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問題在于,道德情感的積極性與穩定性雖高于一般意義上的情感,但也難免失于一偏。“正直者失于太嚴,寬宏者失于緩,剛強之失于苛虐,簡易之失于傲慢。”⑥孔穎達:《尚書正義》,第96頁。道德情感的萌生固然是件好事,但倘若不對其進行積極地導養,道德情感的偏頗之處很可能會放大,以至于遮蔽本身的積極性。因此,對道德情感的導養不可斯須離身。
在古人看來,一個完善的人應能較全面、通透地理解自身的情感,洞察到道德情感的萌生與表現,并能對其收放自如。隨著自己身處的情境不同,面對的對象不同,道德情感的表達方式也需要有差異。甚至在面對相同的對象時,情感的表達方式也須與時偕 行。
恰如其分、合乎時宜地表達道德情感須經歷艱苦漫長的后天修為。若喪失對道德情感的調適,以致陷逆于某一極端狀態難以自拔,那么“發乎情”將變為“役于情”。如何涵養道德情感,使道德情感的抒發中正平和,成為詩教關注的重要問題。
三、溫柔敦厚,詩教也
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①與此類似的說法也多見于其他文獻中,如《禮解》曰:“溫柔寬厚,《詩》教也。”(《白虎通德論·五經》)對于“溫柔敦厚”的解釋,以往學界存在諸多爭論。
孔穎達疏曰:“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②孔穎達:《禮記正義》,第1598頁。孔穎達從儀態、性情兩方面分別解釋了“溫”與“柔”,并將“溫柔敦厚”歸結為“依違諷諫”,即在下位者給上位者提建議時,往往采用委婉、迂回的方式。這一立場與《毛詩大序》“主文而譎諫”的觀點一脈相承。
徐復觀先生認為,孔穎達的解釋源于“長期專制淫威下形成的茍全心理”③徐復觀:《中國文學精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頁。,他主張從《詩三百》中的感情特質來理解“溫柔敦厚”。“溫柔敦厚是就詩人流注于詩中的感情來說的。溫是適當時間距離的感情,是不太熱不太冷的溫的感情,是創作詩的感情基礎。‘溫’直接導向的是‘柔’。溫柔同時又導向了‘敦厚’。‘敦厚’與‘淺薄’相對,指的是富有深度與遠意的感情,同時也是多層次,乃至是有無限層次的感情。”④同上書,第46頁。徐復觀將“溫柔敦厚”解釋作感情。這比較符合自“五四”以來以文學解《詩》的主流。這一派的學者多將“發乎情”的“情”解釋為“感情”,從而主張《詩》生于人的情 感。
林業連先生同樣認為孔疏值得商榷。“《孔疏》只有解釋溫、柔兩字,并且只持‘依違諷諫’一個比較狹隘的觀點來作為答案,不見得可以通解古人‘溫柔敦厚,《詩》教也’泛指的大道理。”①林業連:《“溫柔敦厚,〈詩〉教也”意涵探析》,載《詩經研究叢刊》 (第二十九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頁。接下來,林業連先生對“敦”的字義做了一番語義學的訓詁,將“溫柔敦厚”解釋為“顏色溫潤、性情柔和、為人厚道”。“只有溫柔敦厚,才能有健全的人格;也唯有人人溫柔敦厚,而后有和諧安樂的社會和國家。”②同上書,第99頁。林先生的解釋質實平順,從神色、性情、性格特征等方面揭示了“溫柔敦厚”的意思。
孔穎達將“溫柔”解釋為“顏色溫潤,性情柔和”,并從言說方式上來解釋“敦厚”,將其理解為“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林業連先生將“溫柔敦厚”解釋為“顏色溫潤、性情柔和、為人厚道”。焦循指出:“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③“自理道之說起,人各挾其是非以逞其血氣,激濁揚清。本非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則聽者厭倦。至于傾軋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尋,以同為黨,以比為爭。”詳見焦循:《毛詩補疏序》,轉引自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517頁。焦循側重于從言說方式上來闡釋“溫柔敦厚”。綜上,學者們多從顏色、性情、言說和處世方式來解釋“溫柔敦厚”。而這些方面都可歸屬于一個人呈現出來的、可以為外人觀見的生命樣態和氣象。
那么,為什么“溫柔敦厚”可以作為詩教的重要標 志?
如前所述,詩教的要義之一在于涵養道德情感,并使道德情感的抒發中正平和。“詩,持也。持人情性”④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65頁。。“持”字有“持存”“持守”等含義。“詩者,持人情性”強調的是詩對于道德情感的涵養和護持,使其以恰到好處的方式呈現出來。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⑤《論語·八佾》。朱子注曰:“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于和者也。”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66頁。《關雎》之情不失其中正之道。不獨《關雎》如此,《變風》諸詩之情無不發而中節,故《毛詩大序》云“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⑦孔穎達:《毛詩正義》,第18頁。。
道德情感存主于身心之中,實現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理想狀態。這屬于未發的層面。一個人的神色、儀態、語氣、言辭等方面屬于已發的層面。未發與已發并非毫無關聯。道德情感上的涵養工夫和生命境界直接決定了此人所呈現出來的氣象。反過來說,一個人的神色、儀態、言辭等外在表征同樣能夠反映出此人道德情感的涵養狀態。道德情感有所涵養的人,自然會在神色、儀態、言語方面與常人有所不同,會呈現出“溫柔敦厚”的生命氣象。“溫柔敦厚”是效驗,其內在基礎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道德情感。而詩的作用正在于涵養道德情感。基于這一原因,溫柔敦厚可以作為詩教的重要表征。
《詩三百》的言辭“不以理勝,不以氣矜,情深而氣平”①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517頁。,以中正平和、委婉迂回見長。詩人不以理凌人,而是以情動人、感人。我們可以通過欣賞《詩三百》的言辭觀見詩人“溫柔敦厚”的生命氣象,進而體會其道德情感,領略《詩三百》的化育之 效。
從《變風》 《變雅》的詩篇可以發現,對于事理的過錯,詩人固然不會姑息縱容,但詩人不會偏執于一事的是非,自鳴理直,逞口舌之快、血氣之強,而是在體貼對方的立場和用心的前提下盡委婉隱譎之能事,唯恐觸傷對方尊嚴及彼此情誼。
今觀《變風》諸詩,不見絲毫謾罵、揭短之辭,唯務動之以情。《北門》刺君不恤臣,其詩不過哀嘆己之顛沛窘迫;《兔罝》刺王室無威,諸侯不臣,其詩不過悼己生不逢時而已;《葛藟》刺平王不念宗族之恩,其詩不過傷己惸獨,無人親厚;《子衿》刺學校廢壞,學人荒怠,其詩不過形容老師思念學生的情 懷。
即便是在直接陳述君王過失的《變雅》,詩人之情也并未偏于一端。“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明期望至重;“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傷國運維艱,積重難返;“日月告兇,不用其行”,恐天命之兇兆;“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念先王德澤,哀后嗣難續。《變雅》的目的不在于發泄自己的憤恨和怨懟,而在于使君王改過自新,因此《變雅》言語雖直切,卻沒有謾罵、侮辱之辭,自始至終都是以情理動人。
四、詩禮合一的成德之學
重視對道德情感的導養,使之中正平和,合乎禮義,不單是詩教所倡導的,禮教亦然。
“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②班固:《漢書》,顏師古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028頁。可見,圣人依人情而制禮。禮由內鑠,而非由外力強加得來,正如男女之情是婚姻之禮的基礎,長幼之序是鄉飲之禮的基礎。其中,禮與情并不是涇渭分明的兩者。禮并不是作為外在的力量生硬地附加到道德情感上,而是通過恰當的引導,道德情感能夠以合乎禮義的方式表達出來。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③孔穎達:《禮記正義》,第1260頁。“平好惡”并非是要根除人們的好惡情感,而是指情感的抒發應講究時宜,止乎禮義。禮應是道德情感的存在方式。
人有視聽食息,耳目口鼻難免成為外邪入侵的通道。“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入之矣。”①孔穎達:《禮記正義》,第1329頁。因此,教化必定要落實于目之所視、口之所言、四體之動作周旋。誦雅言于口,躬行禮儀于日用踐履之間,凡此諸種,皆在于營造涵養情性的雅正氛圍,防微杜漸,扼惡于將萌之先,使民日漸遷善而不自知。
“溫柔敦厚,《詩》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②同上書,第1597頁。“溫柔敦厚”“恭儉莊敬”都是為學之人變化氣質、調和情性之后所達到的理想境界。古人未曾將《詩》與禮當作一門客觀知識,吟詩與習禮的目的也不在于顯示自己博聞強識或是謀求具體的技能,而是尊其為安身立命之本。
詩教之于口,禮教之于行。乍一看,二者針對的官能各異。其實,口與行莫不統于心,蘊之為道德情感。“先王以六經垂教,惟詩、禮、樂之用最切。《詩》、禮、樂雖分三者,其用則一。”③錢澄之:《田間詩學》,安徽:黃山書社2005年版,第11頁。詩教與禮教是陶冶道德情感、涵養道德品質的成德之 學。
在先秦社會,禮無處不在。小至個人與自我的關系,大至宗族、國家、邦國之間的關系乃至天人關系等都需要禮來規范。冠禮、婚禮等貫穿了人的一生。意義深遠的儀式營造出莊重肅穆的氛圍,齊敬其身,宣導其情,去惡遷善。由此,人對自我的責任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能夠明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別、兄弟之情、朋友之 誼。
以禮制為綱紀的西周至春秋中期社會是孕育《詩》的溫床。“禮樂文化的特殊背景使得中國政治、倫理、道德、宗教和藝術實踐始終不能脫離禮的規范,并相互融為一體,統一于具體的禮典演習。”④王秀臣:《“三禮”的文學價值及其文學史意義》,載《文學評論》2006年第6期。作為周代禮樂文明的累累果實,《詩》必然嵌入了禮樂文化的烙印。⑤在現當代詩經學界,《詩》多被視作一部表達主觀感情的文學作品,應以西方文論作為范式來研究《詩》,將詩從禮制的牢籠中解放出來。錢鐘書是以西方文藝學來治《詩》的集大成者。在《管錐編》中,他大量引用西方詩學理論來解讀《毛詩》,認為《國風》言語切近,更近似后世的抒情詩,而《雅》 《頌》作為禮樂文明的集中反映,非但缺少個人情感的抒發,還有對典禮場景的大量描述。禮器、儀則之名不勝枚舉,沒有禮學基礎之人根本摸不著頭腦。顧頡剛幼時讀《詩經》的經歷可為其證。《國風》“句子清妙,態度溫柔”,尚且能入心坎。至《小雅》便覺困難,“堆砌和嚴重的字句多了,文學的情感少了,便很有些怕念。讀到《大雅》和《頌》時,句子更難念,意義愈不能懂得”。(顧頡剛:《古史辨自序》,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頁。) 《管錐編》論《毛詩正義》的條目共60則。撇開論鄭玄《詩譜序》的一則,其余59則中,論及《國風》的多達47則,而論及《雅》的僅有12則,竟沒有提到《頌》。數量懸殊的布局恰恰說明,如果西方文論能勉強湊合解讀《國風》,那么它對于禮文繁復的《雅》、《樂》根本無措其手足。問題的關鍵在于,《風》 《雅》 《頌》是一個整體,對《雅》 《頌》束手無策的理論方法又能對《國風》的精神領略幾分?可見,不通禮,無以治詩。《詩》是禮的精神在言說。《詩》與禮相結合,共同締造了禮樂造士的傳統。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對“興于詩,立于禮”作一番新的詮釋。“興于詩,立于禮”不僅是孔子對當時教育方式的客觀陳述,而是他對《詩》與禮內在關系的闡釋。在禮崩樂壞的末世,禮文轉繁。人們的關注點由禮之本轉向禮之器。行禮徒有虛文而無實質,甚至借禮器的齊備來炫耀財力。同時,吟詩逐漸淪為無關己心的記誦之學。《詩》與禮的內在關聯日益隱晦。
夫子與弟子討論“素以為絢兮”一詩,用“繪事后素”啟發學生思考禮之本,更進一步地借“興于詩,立于禮”來匯通《詩》與禮的內在精神。《詩》與禮,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在探討《詩》、禮關系時,我們不應執著于名稱、形式等表象,將《詩》與禮視作全無關聯的兩者,而要援表入里,體悟《詩》與禮精神的統一①降及后世,詩與禮的內在關系隱晦不彰。后世對鄭玄《毛詩箋》中“以禮箋詩”的做法貶多于褒。章如愚認為,“鄭氏之學長于《禮》而深于經制,至于訓《詩》,乃以經制言之。夫詩,性情也。禮,制跡也。彼以禮訓《詩》,是按跡以求性情也。此其所以繁塞而多失者歟。”陳善之認為:“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尺度所能束縛,蓋自古如此。予觀鄭康成注《毛詩》,乃一要合《周禮》,束縛太過。不知詩人本一時之言,不可以一一牽合也。康成蓋長于《禮》學,而以《禮》言《詩》,過矣。”轉引自向熹:《〈詩經〉語文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頁。兩位學者之所以對鄭玄“以禮箋詩”全無正面評價,是因為他們并未追溯到先秦詩禮合一的傳統中去理解詩本身。而詩禮合一的傳統正是鄭玄心之所系。在鄭玄看來,“三禮”并不是生硬地附加到《詩經》上的他者。《詩》中本來就包含著禮教傳統及精神。禮是詩的內在規定。“以禮箋詩”的目的在于激活《詩》中日益隱晦的禮的精神。。
詩教與禮教都著眼于對道德情感的導養,目的在于為學之人的成德。這可以解釋《詩》與禮的同,但不足以解釋二者之異。《詩》與禮有內在關聯并不意味著“興于詩”與“立于禮”是一種橫向的并列關系,而是先“興于詩”,繼而“立于禮”。這樣一來,值得追問的是,《詩》與禮的差異何在?孔子為何用“興”來言《詩》?
五、引類連譬的詩性言說
“詩言志,歌詠言,非志即為詩,言即為歌也。或可以興,或不可以興,其樞機在此。”②王夫之:《唐詩評選》,載《船山全書》 (第十四冊),長沙:岳麓書社1981年版,第897頁。可見,王夫之把《詩》的獨特歸結到了“興”上。詩性言說的樞機在于“興”。“興”是中國詩學傳統中的一個獨特的范疇。這是很多學者的共識。
朱子把“興于詩”的“興”訓作“起”。“興,起也。”③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04頁。什么是哲學意義上的“起”?“起”只是提供了一個端點,并未預設最終結果。“起”這一動作的結果會根據具體情境的不同、讀者稟賦的不同而有所變化。這種留白藝術開啟了廣闊的意義空間,不是限定,不是閉合,而是一種敞開,包含著無限豐富的可能。
眾所周知,射線與線段的區別在于,線段兩端都有端點,向內閉合,不可延長,而射線只有一個端點,具有向一方無限延伸的可能性。興于詩的過程正如立足于一個端點無限延伸的過程,起點在于《詩》,落腳點卻超越了《詩》,正如以手指物,目的在于所指之物,而非手指。
“起”的結果并未被限定,但這一動作并不是毫無原則、毫無方向的。《釋名》:“起,啟也。啟一舉體也。”①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頁。這一訓釋包含著局部與整體的關系。“起”這一動作是有所本的,目的在于“舉體”,即由一隅興起全體。只有著眼于“舉體”,“起”這一活動才有意義 。
《詩》所言之物、詩人在某一歷史情境中的經驗正是這“舉體”之“一”。“啟一舉體”之“體”指的不是某一個具體的技能、知識或道理,而是作為萬物關系總和的整體,即道。道周流無滯,變動不拘,其小無內,其大無外。在道之外,不復有另一個整體與其構成并列關系。道作為萬物存在的根據,雖超越于萬物,卻并非與萬物相隔。萬物作為“一”,與道之整體存在緊密的內在關聯。唯有在與道的相互關系中,萬物才能是其所是。吾國古哲未嘗離物以觀道,離事以求道。讀《詩》“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識”不是把草木鳥獸當作客觀知識來積累,而是從天地大化中來體認道。
可見,“興,起也”并不是一個普通的動作,而是有著深刻的哲學基礎——《詩》對于道物關系的理解。道物不相隔,是“一”能“舉體”的前提。更進一步的,“啟一舉體”是對“起”這一行為的基本規定。“起”并不是任意隨性、毫無原則的,而是要以“舉體”為目的。這樣一來,“興”就不僅僅意味著《詩》的藝術功能或是讀《詩》后的審美體驗②葉朗先生區分了“興于詩”的“興”與賦比興的“興”。前者是就詩的欣賞而言,后者是就詩的創作而言。陳桐生先生認為,無論是詩歌創作還是欣賞都是藝術活動的前后階段,二者都離不開藝術感性。詳見陳桐生:《禮化詩學——詩教理論的生成軌跡》,第155頁。,而是在更高的意義上與“舉體”相關聯。
《詩》之興,在于《詩》通乎道。與邏輯嚴密的論說文相比,《詩》言近旨遠,由此及彼,能夠在最大程度上實現意義世界的敞開——由有限的言說引到無限的道。
興于詩,并不是把一個具體的教義灌輸給讀者,而是為讀者開啟了一個更廣闊的意義空間,供其優游涵泳,自得于身。“興”實現的并不是對某個具體知識或義理的知,并不是從一個端點到另一個端點,從有限到另一個有限,而是使讀者能夠融入道之中,從一種潛在的無限的道的高度來反觀自己。孔子與子夏談詩的例子向我們展示了真正意義上的“興于《詩》”。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①《論語·八佾》。“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本用來形容莊姜的美貌。面對子夏的追問,孔子并未直接回答《詩》的字面義,而是通過思考“繪”與“素”的關系(繪事后素)上升到文質之辨的高度——文質相參,質為文本。基于文質關系,子夏進一步來反思禮這一概念,“禮后乎?”很顯然,文質關系、禮與仁的關系等義理并不包含在“巧笑倩兮”的字面義中。但“巧笑倩兮”卻開啟了廣闊的意義空間。
孔子稱贊子夏“始可與言詩”。在孔子看來,“言詩”并不在于疏通《詩》的字面義,或是把詩背得滾瓜爛熟,在對答時能引經據典,而是能引類連譬,“聞一以知十”,由有限的言辭上達到無限之 道。
以詩為教,基于對人靈性中的自覺能力有著充分的信任。為學之人不是教義的灌輸者,而是有待啟發的靈動的生命。子曰:“起予者商也!”②同上。“起”是詩教的神髓。詩教重在對為學之人進行提點與啟發,而非義理的灌 輸。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③《論語·述而》。朱子注:“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95頁。“開其意”與“達其辭”都充分調動了人的想象力與覺悟力。這一過程還需要恰當的時機,即“憤”與“悱”。“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子夏思考“巧笑倩兮”而未得其解,正是“心求通而未得”之時。孔子并不是把禮之本末的道理直接灌輸給學生,而是借子夏思考“巧笑倩兮”的契機巧妙地讓學生自己領悟出這一道理。
“素以為絢兮”引發了孔子對“繪事后素”的思考。但這遠未窮盡詩句的啟發義。個人的生存境況不同,文化積淀不同,同一句詩對他們開啟的意義空間也各不相同。“繪事后素”并非詩之達詁,只是對“素以為絢兮”的一種詮釋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漢人“《詩》無達詁”的提法并不是對一個經驗現象的描述,即讀者為了滿足某個具體目的而斷章取義,牽合詩意以就己意,而是對《詩》的本質規定。《詩》言說的是至高的道。《詩》的意象、場景雖有限,但《詩》相對自由的形式開啟了無限豐富的闡釋空間,能夠最大程度地彰顯道靈動周轉的特性。這必然決定了《詩》之詮釋不能限于一端。
結 語
《詩》所言之志包含著深刻的價值規定。采詩、獻詩與編詩之志使《詩》完成了從個人領域到倫理政治領域的轉向。從這個意義上說,《詩》的成書與流傳從根本上不同于后世的文學創作與文學活動。《詩》浸潤在先秦禮樂文明的時代背景之中。詩教是導養性情、成德成人的生命之學,與禮教共同締造了禮樂造士的傳統。
《詩》與禮既有同一,又有差異。《詩》與禮都非外爍,而是源于人情,立足點在于導養道德情感,使其止乎禮義。但兩者的表現形式不同,作用方式也不同。《詩》的獨特性在于“興”,在于“起”,由有限的言辭與意象通達無限的道,興起好善惡惡之心。禮的獨特性在于“立”,通過一系列節文度數使人心念純正、行為周旋中禮,“卓然自立,不為外物所搖奪”①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05頁。。盡管如此,《詩》與禮莫不以成德、達道為終極歸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