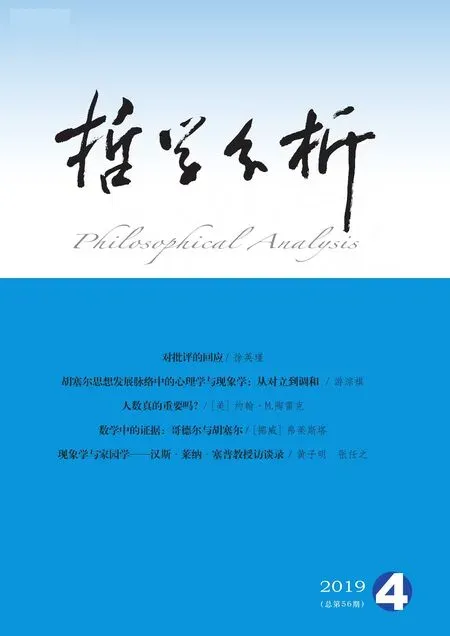阿威羅伊論質料理智
石永澤
阿威羅伊(1126—1198)是亞里士多德作品的著名評注家,他幾乎注釋了亞里士多德的所有作品,在這些評注中有長評注、中評注和短評注三種形式。阿威羅伊對亞里士多德的《論靈魂》完全使用了三種評注形式。①對亞里士多德作品進行評注完全采用三種形式的僅有五部,除了《論靈魂》,還有《形而上學》 《物理學》《論天》和《后分析篇》等。文中涉及的質料理智(al-‘aql al-hayulani)這一概念,基本等同于人的理智、潛在理智等概念的含義。《論靈魂》三篇評注的時間順序研究可參照:恩斯特·勒南與赫伯特A. 戴維森的相關研究成果(E.Renan. Averroes et L'Averroisme,Paris: Augste Durand, Libraire, 1852;Herbert A. Davidson.Alfarabi, Avicenna, and Averroes, on Intellect: Their Cosmolo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從《論靈魂》的三種評注以及其他相關作品來看,可知他有關質料理智的觀點前后不一,不斷轉換。在不同的時期,阿威羅伊在人的質料理智方面至少持四種立場。《論靈魂》短評注和《關于結合的可能性的書信》贊同伊本·巴哲的立場,即質料理智是靈魂的一種傾向,這種傾向與人的靈魂的想象能力相關聯;有關與積極理智結合可能性的一個簡短的片段和《論靈魂》中評注的原初版本,均贊同亞歷山大的觀點,即人的理智只是靈魂的一種傾向,與身體無關,也與身體或靈魂的任何特定部分無關;《論靈魂》中評注的附錄,聲言“在對亞歷山大和泰米斯丟斯的立場表示應有的懷疑之后”,決定將兩者“結合”起來。他認為,當超驗的積極理智與人天生的思維傾向結合在一起時,就為每個人產生了一種質料理智;因此,以某種偶然的方式思考的人,其思想能力是由積極理智產生的。
在其思想的早期,阿威羅伊追隨伊本·巴哲,將質料理智解釋為靈魂想象力的一種傾向。稍晚一些,我們依賴于他在短評注之后所寫中評注的一般性觀點,與亞歷山大一樣將質料理智解釋為靈魂的一種傾向,而沒有具體地將其定位于想象能力。①阿威羅伊在《論靈魂》中評注的原初版本中接受了亞歷山大的立場,人們普遍認為他是在《論靈魂》短評注之后寫中評注的。后來,他又提出了一種中間理論,即當積極理智與人的靈魂中等待著它的與生俱來的傾向結合起來時,就產生了個體的質料理智。其思想的巔峰時期,他把人的質料理智理解為所有人共有的一種永恒的實體,包含在準質料中,通過分析可以在其他非物質存在中發現,并直接居于存在等級中的積極理智之下。
一、對亞歷山大質料理智是靈魂傾向性觀點的否定
在接受亞歷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s, 活躍期在200年左右)觀點的背景下,阿威羅伊認為,亞歷山大把質料理智解釋為純粹的傾向,存在但不混合于人的有機體,強調將質料理智解釋為人的一種傾向與亞里士多德將人的理智定義為獨立于質料的描述并不沖突。阿威羅伊《論靈魂》中評注的附錄,脫離了亞歷山大的觀點但沒有進行完全否定。因為附錄主張,亞歷山大所說的純粹傾向,必然存在于質料的基底(substratum),作為一種“伴隨的特性”,從而成為“物質對象的一部分”。阿威羅伊《論靈魂》長評注,不僅認為亞歷山大的純粹傾向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來理解,而只能是本質上屬于一種質料的基底。這種觀點更進一步,為否認亞歷山大的觀點奠定了基礎,通過亞歷山大本人明確地將質料理智解釋為“產生的能力”,“就像靈魂的其他官能一樣”,這些官能是“通過[身體各部分的]混合……在身體中產生的”。②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by Richard C. Tayl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94.
阿威羅伊的《論靈魂》長評注,在亞歷山大的作品中發現了一個自然主義和物質主義的關于質料理智的概念。在亞歷山大的《論靈魂》的開頭發現了這樣的概念。③Ibid., p.394.亞歷山大將亞里士多德對靈魂的定義“擁有器官的自然身體的第一現實(the first entelechy)”應用于一般意義上的靈魂,包括具有“推理”能力的靈魂; 亞歷山大的結論是,靈魂一般是與“身體不可分離的”①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by Richard C. Tayl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96—397.,把質料理智看作是人的身體的附屬物。
阿威羅伊推想,亞歷山大由此引入其質料理智概念,是因為他注意到了亞里士多德對靈魂的定義,即“擁有器官的自然身體的第一現實”,并假設這個定義涵蓋了理性的靈魂,也因為他看到了將人的理智解釋為非物質實體的某些“問題”。在早些時候,將人的理智解釋為一種非物質實體的困難也使阿威羅伊相信,人的理智實際上必定具有不同的性質。《論靈魂》長評注將致力于解決這些困難。至于亞里士多德的靈魂定義,亞里士多德自己加了一個限制,那就是定義并不適用于靈魂的所有能力。②Ibid., p.397. 參見Aristotle, De Anima, 2.1.413a, 1—7.“靈魂是現實……身體是潛在的存在……靈魂和身體是不能分離的……如果靈魂具有部分,那么靈魂的部分也是不能與身體分離的。因為它們中有某些部分的現實不過是它們身體部分的現實而已。有某些部分也許是可分離的存在,因為它們根本就不是身體的現實”。因此,阿威羅伊現在認為,導致亞歷山大將質料理智視為身體產生的能力的考慮是可以克服的。
通過保持“鑒別力、洞察力”,人的理智可以自發地從“元素的實體”中產生出來,并且“不需要外部的推動者”去實現它,亞歷山大接近非—亞里士多德學派的、落后者的行列,“他們否認動力因的運作”,并僅通過“質料因”來解釋物理宇宙中的事件。③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by Richard C. Tayl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398.此外,亞歷山大的觀點與“亞里士多德所述”背道而馳。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質料理智是“與質料分離,不受作用者(affection)支配,也不與身體混雜”④lbid.,p.395. 參見 Aristotle, De Anima, 3.4.429a, 15—25.,然而,亞歷山大設想,質料理智是從人的質料方面生長出來的,它必然會受到作用者的影響,就像質料的其他變化一樣。最具決定性的是,亞歷山大的立場被亞里士多德對質料理智性質的“證明”所排除。⑤Ibid.阿威羅伊心中所想的證明,以展示質料理智不受任何形式束縛而開始。在阿威羅伊早期的一部作品中,該證明的結論是發現質料理智是一種傾向而非他物,但是,對《論靈魂》短評注的插語卻把這個論點帶入了相反的結論。在長評注中,這個論證現在得出了一個結論,它是在短評注的插語中得出的。阿威羅伊的理由是:由于質料理智是“所有質料形式”的“接受性”,因此它不會包含“那些質料形式自身的性質”。所以,它不可能是一個“身體”、一個“身體中的形式”或“完全與質料混合在一起”。⑥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 pp.385—386, p.396.
阿威羅伊認為,亞歷山大試圖將他的質料理智的觀點與亞里士多德的決定相協調,即質料理智“既不受作用者支配,又不受個體對象支配,也不受身體或身體能力支配”。他這樣做是為了區分思想的“傾向”和“傾向的基底”。①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 p.395.而作為人的有機體的基底,卻是物質的(corporeal),是受作用者支配的,亞歷山大——在早期的作品中,阿威羅伊同樣也是——解釋說,思維的傾向,從思維本身和其基底中分離出來,不是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為了加強人的思想傾向與其基底之間的區別,亞歷山大——阿威羅伊也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修正了亞里士多德的“書寫板”的比喻。人的“質料理智”,連同亞歷山大的修正,“類似于尚未書寫的書寫板,而不是用來書寫的書寫板”②Ibid.。亞歷山大爭辯說,不同于接受書寫的傾向,只有書寫板才會受制于作用者;同樣,思想傾向的基底受制于作用者,但思想傾向本身卻不受作用者的支配。阿威羅伊《論靈魂》長評注摒棄了傾向和基底之間的區別,并且對書寫板類比進行修正。如果亞里士多德的意思是,思想的傾向不是質料的,而且也不受制于作用者,由于在質料根基中的傾向,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質料,那么,他可以對“任何傾向”提出同樣的觀點。物理世界中的任何傾向和靈魂中的任何傾向都可以被描述為“既不是身體,也不是存于身體中的個體形式”,據此,嚴格地說,只有傾向的基底,而非傾向本身,是物質的。因為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完全是關于思想的傾向,他肯定有更重要的想法。亞里士多德肯定是在說“傾向的主體”而非“傾向本身”是孤立的。他的意思是主體,即包含思想傾向的實體,既不是身體,也不與質料混合。事實上,憑此論證,亞里士多德確實也揭示了思想的傾向不與質料混合。亞里士多德認為,“任何接受到的東西實際上都不可能包含接受到的東西的本質”,并且這個命題很明顯考慮的是基底本身,而非其內在的傾向性。如果思想的接受者必須擺脫質料的形式,那么是思維能力的基底而不是基底中固有的傾向性,必須擺脫形式且不與質料混合。因此,亞歷山大的書寫板類比同樣是“錯誤的”。亞里士多德的意圖是將質料理智比作“就其接受書寫而言的書寫板”而非“書寫板中的傾向”。③lbid., pp.430—431.
總之,根據阿威羅伊《論靈魂》長評注,亞歷山大把質料理智解釋為人體的附帶現象。阿威羅伊曾經接受過這種結構,盡管這種結構伴隨軟的物質主義。長評注拒絕把質料理智的結構當作人的有機體的傾向,因為阿威羅伊發現,它既與亞里士多德關于質料理智的論述相沖突,又與亞里士多德對質料理智純粹性的證明相沖突。作為對亞歷山大在質料理智上的立場的駁斥的推論,阿威羅伊在長評注中也否定了亞歷山大對思想傾向和思想傾向的主體的區別,以及亞歷山大對書寫板比喻的修正。
二、對伊本·巴哲先天傾向與想象力結合觀點的反駁
關于伊本·巴哲(Ibn Bajjah, 拉丁名 Avempace, d. 1139年),《論靈魂》長評注寫道:“從其樸實無華的言語來看,他似乎相信質料理智[只不過是]想象的能力,只要它所包含的概念能夠成為實際的可理解的思想;……沒有其他能力……是人的理智思想的基礎。”①Herbert A. Davidson, Alfarabi, Avicenna, and Averroes, on Intelle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61.阿威羅伊明白,通過將思想的傾向置于靈魂的能力(即想象能力)之中,伊本·巴哲希望“避開依附于亞歷山大的荒謬之處”。用長評注現有的段落來說,亞歷山大把接受可理解形式的基底,解釋為要么是“由元素構成的身體,要么是身體的一種能力”②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 p.397.;也就是說,他把質料理智解釋為人的身體的一部分,或者是身體所固有的能力。阿威羅伊推測,在將質料理智定位于靈魂而非身體的能力時,伊本·巴哲有意識地避開了亞歷山大的物質主義。盡管有了微小的改進,伊本·巴哲在長評注中的表現并不比亞歷山大好多少,他的立場被阿威羅伊斥為“明顯荒謬”,原因如下。
在不同的時期,阿威羅伊在這個問題的正反兩面都展開了論述。正如長評注再次提出的那樣,“質料理智不可能有任何現實形式,因為它的……性質就是接受所有的形式”。既然想象能力是靈魂的一種形式,如果質料理智存在于想象力之中或與之同一,那么質料理智在開始思考之前就具有一種質料的形式,并在不歪曲的情況下就無法發揮其功能。長評注拒絕伊本·巴哲立場的第二個原因出現在阿威羅伊的《論靈魂》短評注的一個插語中。長評注認為,正如短評注所述,由于理智能力是通過想象能力所呈現的圖像來運作的,如果理智能力只是想象能力的外觀,那么一種能力就會對自己呈現給自己的圖像進行操作,一個東西接受其自身,這樣作用者和被作用者是同一的,而這是不可能的。拒絕伊本·巴哲觀點的第三個原因是,想象能力所呈現的圖像,被堅持理性能力的亞里士多德解釋為“與感覺的主體相對的感覺的客體(對象)”③Aristotle, De Anima 3.7.431a, 14—15.。在伊本·巴哲的構建中,想象能力和它所包含的圖像不是與客體相對應,而是與感覺的主體相對應。因此,伊本·巴哲將質料理智與想象能力等同起來是站不住腳的。④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 p.398.
由于亞歷山大和伊本·巴哲的立場包含著這種荒謬,阿威羅伊在早期的作品中是怎么理解它們的呢? 他承認自己“在很長一段時間”被誤導了,而伊本·巴哲也同樣被誤導了,誤導的原因是他們那個時代追求哲學的方式。“現代的”哲學家們無視亞里士多德的作品……尤其是他關于靈魂的書,認為這本書晦澀難懂,于是轉而“研究評注家的作品”①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 p.470.。因為他一開始就仿效當時的哲學家,放棄了科學的源泉,研究的不是亞里士多德的《論靈魂》而是有關靈魂和理智的二手作品,阿威羅伊被誘導去接受的觀點,要么是亞歷山大把質料理智的構造僅僅看作是內在于人的一種傾向,要么是伊本·巴哲把它看作是人的想象能力的一種傾向。經過數十年的反思,阿威羅伊才意識到這兩種觀點都站不住腳。
三、對泰米斯丟斯質料理智觀的反思和超越
剩下是泰米斯丟斯(Themistius, 317—390)。“泰奧弗拉斯托斯、泰米斯丟斯和許多評論家”,阿威羅伊寫道,“表面上接受了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即質料理智與質料分離,且不與身體混合”。他們把質料理智解釋為“既不產生也不毀滅”的“實體”,換句話說,就是一種永恒的、非物質的實體。然而,他們的立場“問題也不少”②Ibid., p.389,p.391.。
首先,對泰米斯丟斯的一個反對意見如下:引導人的理智從潛能到現實的因素,即積極理智,是一個永恒的存在。如果質料理智也是永恒的,那么積極理智對質料理智的作用必然也是永恒的。“因為行為者是永恒的,行為是永恒的,結果就必定是永恒的。”現在質料理智——由哲學分析揭示并由亞里士多德確立——思考想象能力所呈現的圖像,而且通過積極理智的活動,它將呈現的圖像提升到可理解的思維層次。這些圖像,就其本身而言,是由想象的能力通過從感官知覺開始的抽象過程產生的。如果永恒的積極理智永恒地作用于永恒的質料理智,那么質料理智必須把它所思考的圖像永恒地轉化為可理解的思想。因此,由想象能力所呈現的并由質料理智所思考的圖像,自古以來就被轉化為思想。這樣,圖像所基于的感官知覺也必定是永恒的。感官對外部世界中的物理對象,所感知的鏡像也是如此。如此一來,泰米斯丟斯的立場會有一個完全矛盾的結果,那就是在感官知覺基礎上的物理對象不是可生滅的,而是永恒的。③Ibid., pp.391—392.
對泰米斯丟斯的另一個反對意見,已在阿威羅伊《論靈魂》的中評注有所體現,但與前述的觀點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質料理智是一個非物質的存在,而不存在于質料中,并且按照質料是相同特性的事物相互區別的原則,那么整個人類物種只能有一種質料理智。根據定義,質料理智是“人的第一現實”,而“理論理智”,即人在獲得了一系列可理解的思想后的理智,“是最后的現實”。每個人顯然都有自己的理論理智,該理論理智形成并可毀滅,因此,在“其最后的現實”,每個人都是“個體的”和“可生滅的”。如果一個人的最后的現實是個體的,可生滅的,那么他的第一現實應該是一樣的。因此,人的最初的現實,即人的質料理智,似乎不可能是單一的、永恒的非物質實體。①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 pp.392—393.
阿威羅伊提出了另一個異議: 如果質料理智是非物質的,那么就像剛才所看到的那樣,整個人類物種只能有一種質料理智。但是人的理智必須是個體的,否則,任何一個既定的人思考任何可理解的思想,所有的人都會思考;一個人忘記無論什么思想,所有的人都會忘記。顯然事實并非如此。既然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個體理智,那么質料理智似乎就不可能是單一的非物質實體。②Ibid., p.393.
亞歷山大和伊本·巴哲的立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泰米斯丟斯及其同儕的立場同樣具有如此不適當的含義,那么,真相在哪里?盡管在他的哲學生涯中,阿威羅伊一直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但他的長評注仍在嘗試性地、謙虛地提出自己的結論:“如果我的論文不是完整的真理,它將是一個開端。因此,我吁請看到這里所寫內容的同行們放下疑慮。”③Ibid., p.399.
四、質料理智是非物質的永恒實體
阿威羅伊堅持以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為指導,“因為除了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以外,所有關于質料理智本質的東西都顯得荒謬”④Ibid.。回到亞里士多德,阿威羅伊認為,既然人的思維的潛能“接受所有的質料的形式”,以及“每個接受者……必須免于它所接受的東西的性質”,那么以可理解的思想為外觀接受質料形式的基底就無法“具有任何質料的形式本身的性質”。從長評注的觀點來看,這一論點的結論是,接受可理解思想的人的方面既不能是身體或身體的形式,也不能在任何方面與質料混合。⑤Ibid., pp.385—386.因為它不是身體,沒有生成,也不可摧毀,就是說是永恒的。⑥Ibid.,p.389, p.406.質料的原則具有將相同特征的物體個性化,并受制于“列舉”,由于質料理智不與質料相混合,所以質料理智就不能——與阿威羅伊《論靈魂》最初的短評注完全相反——“通過個人的數目被列舉出來”⑦Ibid., p.402.。換句話說,個人不擁有個體的質料理智。更確切地說,“唯一的”質料理智在某種程度上為全人類所共有。①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 p.399.
在這里,阿威羅伊斯所接受的對亞里士多德的解釋——除了現在要討論的一個次要問題——與阿威羅伊所理解的泰米斯丟斯關于人類質料理智的本質的觀點是一致的。因此,阿威羅伊在泰米斯丟斯的立場中所注意到的困難也影響了正如阿威羅伊現在所解釋的亞里士多德的立場。②阿威羅伊重復了前兩種可能的反對意見,這兩種反對意見都是對泰米斯丟斯的“問題立場”的反對,這也影響了亞里士多德的立場。這就需要一個解決方案。阿威羅伊的解決方案是區分人類思維的兩個“主體”。他解釋說,想象能力中的圖像構成了一個主體,它們是思想過程中的“作用者”③但它們不能與積極理智相混淆,積極理智也推動著人的理智。圖像在視覺過程中就像顏色一樣起著推動作用,而積極理智在視覺過程中就像光一樣起著推動作用。參見Aristotle, De Anima, 3.5.430a, 16—17。,也是那些可理解思想的指示對象,由于與想象能力中的圖像相對應,可理解的思想是“真實的”。④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p.400, p.406. 阿威羅伊說這個功能不僅僅是由一個,而是由三個官能來完成,也就是“想象、思考和記憶”,他把被動理智和這些能力聯系起來; 在阿維森納,思考能力是思維過程的中心。永恒的質料理智是另一個主體。它是思維過程中的“接受者”,是允許可理解的思想進入現實存在的領域并成為“存在事物”的因素。⑤Ibid., p.400.對于質料理智,阿威羅伊斷言——這與他在《論靈魂》短評注的原稿中提出的觀點截然相反——從未在“本質上和根本上”依附于人,而是“僅通過其同伴”,“僅通過……想象能力中的形式與人結合” 。⑥Ibid., p.486.要解決他擺出的這一難題,阿威羅伊將人的思想潛能的表面上不相容的特征分配給了永恒的質料理智和非永恒的人的想象能 力。
抽象的時間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問題,鑒于產生思想的超驗原因和接受思想的質料理智是永恒的,那么對問題回答如下:在某種意義上,人的思想的確是永恒的,但在另一方面,卻是可生滅的。質料理智是永恒的,因為質料理智總是擁有人的真實的思想。盡管如此,它仍然是有生滅的,“憑借所涉及的主體”,它才是“真實的”,換言之,就是涉及想象能力中的圖像,從這一事實可以看出,每當一個人及其想象力喪失時,他的理智的思想意識就會停止。⑦Ibid., p.401. 參見 De Anima, 3.5.430a, 23—25。因此,永恒的積極理智對永恒的質料理智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產生了永恒的結果,同時也產生了一種真正的、非永恒的抽象過程。
當每個人的最終的現實和他的理論理智都是個體的、可生滅的,單一永恒的質料理智如何為整個物種服務就是個問題,而且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如何在不需要所有人擁有相同思想的前提下,為所有人類設想一個單一的質料理智,是要用同樣的方式來處理的。在回答后一個問題時,阿威羅伊寫道,將實際的思想與個人聯系起來并使之成為易于列舉的東西,顯然不是“在(思維過程中)扮演質料角色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說,不在質料理智之中”;服務于整個人類物種的共同質料理智并不能使個人的思想成為可能。然而,實際的思想確實與個人聯系在一起,并成為可列舉的主體,通過“某種程度上扮演著,可以說是某種形式角色”,也就是說憑借想象能力中的“圖像”。①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 pp.404—405.通過想象能力中的圖像,靈魂意識到可理解的思想。因此,盡管人們擁有共同的質料理智,但每個人仍然擁有自己個性的實際思想,而思想是不共享的。
如果人的最初的現實是全人類共有的且是永恒的,至于人的最終的現實如何會是個人的和可毀滅的,阿威羅伊解釋說,人的思想的“產生和毀滅”②這里阿威羅伊特別提到了思想的第一個命題,但后來,他把這個命題擴展到所有的科學—哲學知識。發生在“對它們的多元影響”——只要每一種思想都屬于擁有個人的想象能力的人的“個體”。盡管如此,人的思想并不是無條件地生滅,因為它們避免了“從它們統一的那一邊”的產生和毀滅;只要它們存在于質料理智中,就不會有產生和毀滅。每個人的最終的現實,即他的理論理智,因此是個體性的,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是可消亡的,而在另一種意義上,在全人類共有的質料理智接受了人類思想的整體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理論理智是所有人共有的”和“永恒的”。③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translated by Richard C. Tayl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07.
阿威羅伊還沒有告訴我們人的質料理智是什么樣的實體,他這樣做是為了解決他目前對亞里士多德的解釋所帶來的另一個哲學問題。這個問題是反對意見的一個版本,即他早期作品中反對泰米斯丟斯把人的質料理智構建為非物質實體。人的質料理智的特點在于具有或存在著思考的潛能,阿威羅伊早期的作品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如何才能像泰米斯丟斯讓我們相信的那樣,認為非物質性實體以一種潛在的狀態存在。因此,《論靈魂》長評注實際上提出了本質上同樣的問題: 質料理智“必須被假定為擁有思考能力的某種東西”。它本身不包含形式,因為如果它包含了形式,形式就會干擾或扭曲它所接受的新形式,即新思想。現在,任何不具有形式而存在的事物都具有“原始質料的性質”。然而,對于質料理智來說,擁有原始質料的性質是“不可想象的”,因為原始質料顯然沒有思考的能力。“而且,具有這樣特性的東西怎么能被描述為非物質性的呢?”④Ibid., p.399.
阿威羅伊通過揭示他在早期作品中忽略的一類存在來解決最后一個問題。他寫道,哲學家一般承認有三種存在:物理對象的質料、物理對象的形式和非物質性實體。但是,對于“第四種”存在許多現代哲人沒有注意,因為“就像感性存在被劃分為形式和質料一樣,可理解的非物質的存在也必須被劃分為形式和質料的類似物”。非質料領域中的準質料的存在可以從“非物質形式”或“推動天體”的智能物(intelligences)獲悉。亞里士多德關于“第一哲學”的書,即他的《形而上學》,確立了球體的非物質運動者必須與球體“數目相同”;①參見 Aristotle, Metaphysics,12.8。阿威羅伊的理由是,只有當非物質智能被個體化,并由于存在于其中而被列舉出來時,它們才站得住腳——或者,更準確地說,除了第一推動者,準質料組成的最外層球體的運動者之外的所有運動者都是如此。天體智能是可理解的形式和這種準質料的化合物,而永恒的人的質料理智只包含在同樣的準質料中。②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 pp.409—410.在非物質存在的等級體系中,它由第一因加冕,并通過球體的非物質運動者逐級下降到被稱為積極理智的實體,質料理智是最低的層次,較少“高貴”,直接位于“積極理智”之下,“質料理智……是最后一種非物質智能”。③Ibid., p.442.
因此,人的質料理智是一種永恒的實體,是非物質層次結構中的最低層次。它通過與人想象力的結合,以一種非本質的方式依附于人的有機體,并在理智過程中扮演接受者的角色。相比之下,想象力豐富的圖像在這一過程中起著推動作用——正如顏色是視覺過程中的推動者一樣。④參見 Aristotle, De Anima,3.5.430a,16—17。這些圖像就是理智思維所涉及的,一種被認為是“真實”的理智思維,因為理智思維是從圖像中抽象出來的,并且與之相應。表明人的思想是永恒的論證,所考慮的是屬于質料理智的人的思想,而表明人的思想是有生滅的、個人的論證,則考慮人的思想是屬于個人的想象能力。
當阿威羅伊指出人們暫時思考的實際思想永遠存在于質料理智之中時,他并不是說質料理智本身就擁有人類的思想。與物理領域有關的思想——與非物質實體的思想不同⑤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p.486.——只有借助個人想象力才能達到質料理智。質料理智的永恒思想表明,既然人類是永恒的,因為每時每刻都有個人存在,他們擁有人的思想的基本命題,而且,因為人們大概也總是存在著具有哲學思想的人,質料理智每時每刻都包含著人的真實思想的全部范圍。因此,質料理智對物質世界思想的永恒性,不是一根連續的纖維,也不是從質料理智中產生的,它完全依賴個人的推理和意識,在任何既定的時刻,物質世界的所有可能的思想都是由生活在那個時刻的個人提供的,而質料理智的思想在無限時間里的連續性,是從活在不同時刻的個體的思想中產生出來的。⑥Ibid., pp.407—408, p.448.
阿威羅伊從未解釋過質料理智何時以及如何與人的個體有機體相關聯;既然質料理智是一種永恒的實體,只與人有微弱的聯系,那么人的努力如何能使質料理智服從它的命令呢?也不知道質料理智,即人的實際思想的接受者,是如何回報并賦予個人以理智意識的。①最后一點由托馬斯·阿奎那提出(Summa contra gentiles 2.59),阿威羅伊自己似乎也認識到了這一點。
阿威羅伊在《論靈魂》長評注中的質料理智的觀點,正如他所理解的那樣,是通過修正和補充的泰米斯丟斯的觀點而獲得的。阿威羅伊在長評注中寫道,泰米斯丟斯正確地詮釋了質料理智,但忽略了一個關鍵細節;他沒有意識到人的真正的思想,或者說人的“理論理智”,雖然在一個方面是永恒的,但在另一個方面是可生滅的。②Averroes, Long Commentary on the De Anima of Aristotle,p.406.阿威羅伊還做了一件泰米斯丟斯沒有做的事,將質料理智解釋為一種準質料的非物質實體,并將其在非物質的等級體系中指定了一個精確的位置。他認為質料理智是非物質的理智的最后一種,直接處于存在層次中積極理智之下。
結 語
阿威羅伊在《論靈魂》長評注中所持的立場,正是他在短評注插補段落中所描繪的立場。在那里,他也把質料理智解釋為一種潛能狀態下的永恒實體;他把其描述為思考過程中的兩個主體之一,扮演接受者的角色,而圖像在想象力中扮演著推動者的角色。阿威羅伊還在他對亞歷山大的《論理智》的評論中提出了似乎是同樣的理論。他寫道,經過“長期的研究和嚴格的應用”,得出了一個他從未在“別人那里見過……”的質料理智的概念。在新概念中,質料理智是(所有)個體……人的靈魂共有的一種“單一力量”。為了澄清他的意思,阿威羅伊將質料理智與自然物種(natural species)進行了比照。他寫道,自然物種由“現實中存在的個體”構成,但在亞里士多德的事物體系中,確實沒有獨立存在。由于自然物種只能通過諸個體而存在,所以其自身只是“潛在地”存在。阿威羅伊認為,質料理智的情況正好相反,因為質料理智是“現實上的物種,潛在中的個體”。阿威羅伊分兩部分的概念來描述質料理智的特征——現實是物種,潛在是個體——是奇怪的。阿威羅伊解釋說,前半句話的意思是“單一的”、共同的質料理智服務于全人類,而依附于“個體”的過程中,它不會變得個體化; 它還是以前的樣子,也就是“現實中的物種”。后半部分可能等于說,正如阿威羅伊在他的長評注中所寫的,質料理智并不是在本質和根本意義上與人相結合的。①Herbert A. Davidson, Alfarabi, Avicenna, and Averroes, on Intellect: Their Cosmolo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89.
當一個人出生時,質料理智是“與人相關的(內容)產生了,但自身并沒產生”,當一個人死亡時,質料理智“與人相關的(內容)被毀了,但其自身并未毀滅”。因此,質料理智是某種東西,對所有人來說是“共同的”,“不與身體混合,與身體分離(即是非物質的)”,“不受數目約束”,“自身也不生滅”。②Commentary on De intellectu, 211—212.轉引: Herbert A. Davidson, Alfarabi, Avicenna, and Averroes, on Intellect:Their Cosmolo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94, n.160.
沿著同一立場阿威羅伊在《矛盾的矛盾》一書中也有所暗示。《矛盾的矛盾》指出根據大多數哲學家的觀點,人的“潛在的理智……”是永恒的。此外,亞里士多德從潛在理智的“把一切都當作思考的對象”,論證了“消極的”或潛在的理智是“非產生的,不可毀滅的”。③Averroes, Tahafut al Tahafut(The Incoherence of the Incoherence), Volumes I and II, translated by Simon Van Den Bergh, Glasgow: Gibb Memorial Trust, 1987, p.570.
亞里士多德所提到的證明無疑是一個人們熟悉的論點,因為潛在的理智可以思考物質世界中每一個物體的形式,所以它本身不包含任何物質形式;由于本身不包含這樣的形式,所以獨立于質料或是非物質的,因此不受生滅的影響。《矛盾的矛盾》中另一個可能與之相關的段落肯定了“證明人的理智的統一性是強有力的”。④Ibid., p.574.從這個背景來看,阿威羅伊可以說,一個完全相同的積極理智為全人類服務。然而,如果他說的是為人類服務的單一的潛在的或質料的理智,那么他在《矛盾的矛盾》中提到了他在對《論靈魂》長評注中主張的要點。他指出,質料的或潛在的理智是整個人類物種共有的一種單一的、非物質的、永恒的實體。
在《論靈魂》長評注中,阿威羅伊承認,由于在他年輕的時候過度依賴亞里士多德的評論家而不是亞里士多德本人,所以被誤導了。這篇長評注批駁了亞歷山大和伊本·巴哲的觀點。亞歷山大現在被描繪成比以前更加具有物質主義者的色彩。
長評注中沒有提及中評注的妥協立場,雖然在長評注中人類思想的兩個主體之間的區別確實與前面提出的妥協立場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事實上,正如阿威羅伊所理解的,這篇長評注贊同了泰米斯丟斯的立場,將人的質料理智解釋為一個單一的、非物質的、永恒的實體,以某種非本質的方式依附于個人的想象能力。阿威羅伊補充說,在存在的等級結構中,質料理智直接處于積極理智之下,作為非物質智能的最后一種。《論靈魂》長評注的立場,重新以注釋的形式出現,合并在阿威羅伊的《論靈魂》短評注中,并在他的《矛盾的矛盾》中有所暗指。他對亞歷山大的《論理智》的評注提出了同樣的或相關的概念。
阿威羅伊的評注的日期,基本可確定短評注較早,長評注較晚。在亞里士多德《論靈魂》的評注中,短評注中包含的注釋明確指出,阿威羅伊在撰寫短評注之后對質料理智主題進行了重新思考,長評注提供了其修正的立場。這篇長評注——以及對亞歷山大的《論理智》的評注,與長評注有關——告訴我們這是阿威羅伊長期研究的成果。因此,《論靈魂》短評注顯然早于長評注。中評注的附錄與長評注的相對日期,只能推測。我們比較容易認為,阿威羅伊從一個極端開始,發展到中間,中評注采取了妥協的立場,然后發展到另一個極端;這是阿威羅伊質料理智學說的思想進展順序。中評注的主體支持亞歷山大的立場,而其附錄則批評亞歷山大,并暗中批評伊本·巴哲。因此,阿威羅伊的附錄可能比他所有在其中追隨亞歷山大或伊本·巴哲的著作都要晚。然而,附錄對第四種存在即潛能狀態下永恒的理智實體,一無所知,阿威羅伊在他的長評注中揭示了這一點,這使他能夠把質料的或潛在的理智,解釋為非物質的實體。此外,中評注的附錄對人的理智的論述比長評注要吝嗇得多,長評注則體現了阿威羅伊在此論題上最詳盡、最縝密的論述。
阿威羅伊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都在努力重新領會亞里士多德的意圖。為了正確理解亞里士多德關于潛能、質料和人的理智,他力圖追隨亞里士多德本人的觀點,而不是評論家的意見,但阿威羅伊并沒有走向現代學術界的共識,即對亞里士多德的歷史上的所謂正確解讀,而是朝著另一個方向前進。他以一種質料理智開始,那是靈魂的能力,并以一種似乎與亞里士多德相異的東西結束,這種東西就是把每個人從外部結合起來的單一的、永恒的、非物質的質料理智。阿威羅伊以前自然主義地解釋過的質料理智,現在卻將它描繪成了一個單一的非物質存在,且不斷地闖入物質世界,為個體的人服務。阿威羅伊關于質料理智的立場變化,究竟是思想自身的張力使然,還是與其伊斯蘭大法官的身份或當時的社會政治形勢有關,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和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