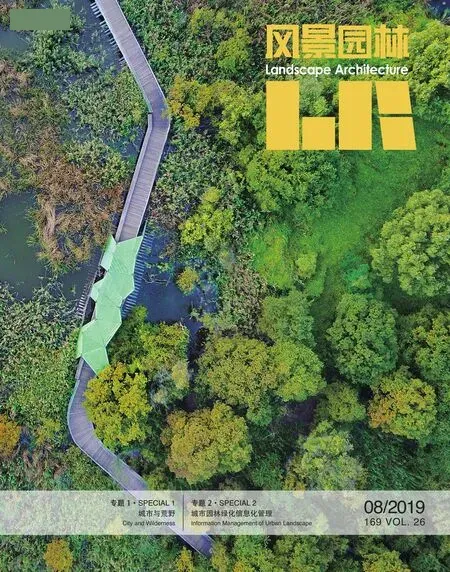城市野境:城市區域中野性自然的保護與營造
曹越 (美)萬斯·馬丁 楊銳
1 城市野境的定義與價值
至2050年,全球約70%的人口將居住于城市中。伴隨著全球城市化的進程,人類與自然之間的聯系正在急劇減弱,這一現象被稱為“體驗的滅絕”(extinction of experience)[1]。體驗的滅絕不僅會減弱人們在生態保護方面積極的情感、態度和行為,也會給人類自身的健康和福祉帶來負面影響。由于城市聚集了絕大多數人口,因此城市區域中的野性自然(wild nature),將成為重新連接人與自然的重要紐帶[2]。
“城市”和“荒野”(wilderness)分別位于大地景觀的兩個極端,是兩種差異極大,甚至截然相反的環境[3]。城市是人類對自然景觀改變程度最高、人類活動占主導的區域,而荒野則是大面積的、保留自然原貌或被輕微改變的區域,保存著自然的特征和影響力,沒有永久或明顯的人類聚居點[4]。根據以上理解,城市中不可能存在嚴格意義的荒野地(wilderness areas)。因此,將“城市”與“荒野”并置起來的“城市荒野”(urban wilderness)這一術語在某種程度上具有矛盾性。雖然荒野地有嚴格的標準,但是“野性”(wildness)存在于各種尺度的所有景觀之中。野性,可理解為生態系統中自然過程占主導,而人類控制和干擾程度較低的性質。事實上,城市區域中也存在著一些具有野性的自然[5]。在中文語境中,可以使用“城市野境”(urban wildness)來描述這些區域,其中“城市”界定了區域范圍,“野”意指“野性”,“境”意指“地境”[6]。使用“城市野境”這一術語,以避免“城市荒野”可能帶來的矛盾性。

表1 城市保護地案例Tab.1 Cases of urban protected areas
已有學者對城市野境的定義進行了探討。例如Jorgensen和Keenan[7]將城市野境(urban wildscape)定義為:城市中以自然而非人類占主導的土地,特別是在自然演替過程中出現植物自由生長的土地,例如自然林地、未利用地、河流廊道、被遺棄的場地或棕地等。王向榮[8]將城市野境界定為:城市中以自然而非人為主導的土地,這片土地能夠在人的干預之外進行自然演替,它的主人是土地本身和其上自由棲息的生命。參考上述定義及相關研究,本研究將城市野境定義為:城市野境,或城市區域中的野性自然,是城市內部或周邊區域中自然過程占主導的土地,其中人類開發和控制程度相對較低,允許自然演替和生態過程在一定程度上發生,各類野生生物能夠與人類繁榮共存。事實上,城市野境除了意指一類空間外,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種思考城市空間的視角和方式,它指明了即使是在城市區域中,依然存在著具有野性的、未被人類完全控制的自然。
基于上述定義,可以得到城市野境的特征。由于自然過程占主導,城市野境與嚴格意義的荒野地存在某些相似性,例如高效的自然過程、高質量的生態系統服務、有代表性的野生生物、卓越的自然美、遙遠感或孤寂感等[9]。另一方面,城市野境與嚴格意義的荒野地也有明顯的區別,城市野境在原真性、自然度、遙遠度、面積等方面要遠小于嚴格意義的荒野地,因此城市野境并不是嚴格意義的荒野地。
城市野境的價值,體現在生態、游憩、社會、文化、審美、教育、經濟等多個方面,特別是在重新連接人與自然、促進人類身心健康、保護生物多樣性、維持生態系統服務方面具有重要和獨特的價值,因此城市野境既是亟須保護的重要資源,也是對嚴格意義上自然保護地體系的補充。首先,由于城市野境的可達性要遠遠高于嚴格意義的荒野地,因此在游憩體驗和自然教育方面,城市野境具有獨特優勢,可以降低城市居民體驗野性自然的成本與難度,同時已有大量研究表明自然環境對促進人的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具有積極作用,生態療法中一種重要的方法就是荒野療法(wilderness therapy)[10-11]。其次,由于允許自然演替的發生,城市野境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棲息地類型和物種多樣性,Müller等[12]的研究表明,城市綠色空間的相對野性程度(relative wildness)與生物多樣性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允許自發的生態過程(降低管理強度、提升野性程度)能夠促進城市生物多樣性的提升。最后,在人工管理和維護成本較低的情況下,城市野境能夠提供高效的生態系統服務,包括支持、供給、調節和文化服務,特別是能夠提供獨特的野性自然游憩機會與審美體驗。
2 城市野境的保護與營造途徑
在國際上,城市野境這一議題在科學、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性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有多個專業團隊開展了專項研究工作。例如“世界城市公園”(World Urban Parks)、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自然保護地委員會中的城市自然保護戰略專家組(Urban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Specialist Group)、IUCN生態系統管理委員會中的城市生態系統專家組(Urban Ecosystems Specialist Group),以及IUCN發起的“城市自然聯盟”(Urban Nature Alliance)等。除此之外,許多城市也有地方性的組織致力于城市生物多樣性和野性自然的保護。總體而言,城市野境的保護與營造正在成為國際上風景園林與自然保護領域的重要議題。
在中國,由于快速的城市擴張,城市及周邊區域中大量的野性自然或被開發,或被大規模的“美化”而改造為公園綠地,城市野境及其價值面臨破壞[13]。在此背景中,有學者開始關注城市野境的價值。盧風[14]指出荒野與文明并非敵對關系,城市的健康發展必須以荒野的存在作為基礎;陳望衡等[15]建議在當代風景園林實踐中應該充分保護城鄉環境中的荒野。而城市野境的保護和營造也有多種途徑,例如初級荒野景觀的保護性開發、次級荒野景觀的更新修復、類荒野景觀的創造等[16]。基于文獻研究和案例研究,本研究進一步提出城市野境保護與營造的4種途徑,以期為相關規劃設計實踐提供思路和參考。總體而言,城市野境的保護與營造將成為中國風景園林師、城市規劃師、城市設計師、建筑師等實踐者共同面臨的重要議題[17-19]。
2.1 保護:在城市保護地中保護野性自然
建立城市保護地(urban protected areas)是保護城市野境的主要途徑。在城市用地和自然保護地同時擴張的背景下,自然保護地與城市之間的距離在急劇縮小,同時城市對自然保護地的負面影響也在加劇[20-21]。因此,亟須對城市區域內部和邊緣的野性自然進行識別和保護,并通過設立城市保護地來進行保護與管理。IUCN將“城市保護地”定義為:位于人口密集區域之中或其邊緣的自然保護地。城市保護地不是傳統意義上由草坪、花壇和運動場構成的城市公園,而是需要滿足IUCN對自然保護地的定義與標準。IUCN于2014年出版了《城市保護地:概述與最佳實踐指南》[22],其中分析了15個全球范圍內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保護地(表1,圖1~3)。與一般的自然保護地不同,城市保護地的特征包括大量訪客進入、與城市各類組織機構關系密切、受到城市擴張與發展的影響(例如空氣污染、光污染、噪聲污染、外來物種)等。總體而言,對城市保護地的有效管理是保護城市區域中野性自然的重要途徑,既保護生物多樣性、提供生態系統服務,也為大量城市居民提供在野性自然中的游憩機會。

1 中國臺北陽明山Yangming Mountain in Taipei,China

2 南非開普敦桌山國家公園Table Mountain National Park in Cape Town,South Africa

3 印度孟買桑賈伊·甘地國家公園Sanjay Ghandi National Park in Mumbai,India
香港的郊野公園(country parks)是城市保護地的典型案例。香港總人口約750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香港陸地面積約1 106 km2,其中約40%的土地被納入郊野公園。1972年,香港第一個郊野公園發展五年計劃獲得立法通過;1976年,《郊野公園條例》生效,由漁農處(現漁農自然護理署)設立郊野公園管理局負責郊野公園的管理。目前香港共有24個郊野公園、11個特別地區、1個地質公園、5個海洋公園、1個海洋保護區和1個濕地公園。香港郊野公園較好地實現了對城市周邊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通過與漁農自然護理署公布的物種分布數據對比分析可知,郊野公園和特別地區保護了香港大部分的重要生物棲息地[23-24]。除了對物種與生態系統的有效保護外,香港郊野公園也為當地居民和游客提供了體驗野性自然的游憩機會。香港郊野公園內一般包含3類游覽區域,即密集使用區(入口等旅游服務設施建設區)、不同難度的步行路徑以及偏遠的野性自然區域。其中步行路徑包括家樂徑、自然教育徑、郊游徑和長途遠足徑等,分布于不同區域并為游客提供了不同的游憩機會。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通過徒步俱樂部和青年活動團組等社區活動吸引居民和游客參與,非政府組織也提供公眾教育活動和宣傳活動。總之,香港郊野公園體系是在城市保護地中保護野性自然的成功案例,通過在城市區域保留大面積、高質量、具有良好連通性的野性自然區域,有效保護了重要物種及其棲息地,維持了多種生態系統服務,并提供了體驗自然的寶貴機會[25-26]。近年來,中國多個城市正在建設郊野公園,例如深圳、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天津、武漢等,這為城市保護地的認定與城市野境的保護提供了重要機遇。
2.2 修復:再野化部分城市區域
除了保護現存的野性自然之外,“再野化”(rewilding)是修復城市野境的重要途徑。通過提升適宜區域的荒野程度,再野化實踐能夠創造更多的野性自然[27]。大地景觀可被視為人類改變程度由極弱到極強的連續帶譜,即“環境改變光譜”(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spectrum)或“荒野連續譜”(wilderness continuum),再野化則意味著某一區域的人類改變和控制程度降低、自然程度提升的過程[28]。再野化這一術語被用于多種情景,即再野化可以發生在環境改變光譜的任一位置,既可以發生在嚴格意義的荒野地,也可以發生在城市和鄉村區域。在環境改變光譜的一個極端,可以是對某個荒野程度已經非常高的區域重引入一種頂級食肉動物,以恢復完整的營養級聯(trophic cascade),經典案例之一是黃石國家公園在園區內重新引入狼。在環境改變光譜的另一端,則是在城市或鄉村區域中介入或重現野性自然,可稱之為城鄉再野化區域(urban and rural rewilding areas)[29]。隨著城市的變遷,出現了許多城市區域再野化的案例,可分為被動型再野化和主動型再野化2類。
1)被動型城市再野化,是自然發生的。通常發生在交通基礎設施或城市廢棄地(wasteland),例如廢棄的鐵路廊道、工業區或居民區。通過風媒或者動物引入的種子萌發出一個生物多樣化的棲息地,被稱為“新型景觀”(novel landscape)或第四類自然。這種被動的、自然發生的再野化通常體現出自我調節的生態過程:首先出現的是先鋒類物種,進而是草本植物,最后是更為成熟的林木。這樣的新型景觀為昆蟲、鳥類以及其他野生動物創造棲息地[30]。德國出現了不少被動型城市再野化的案例,部分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大規模破壞,另一部分原因是前東德的工業衰落。其中一個案例是柏林市一個被廢棄了60多年的調車場(Südgel?nde Railyard),那里經歷了自然的、連續性的再野化過程,并且仍在繼續,現在已被作為一個正式的保護區域納入城市規劃之中[31]。
2)主動型城市再野化,是人為規劃和啟動的。主動型城市再野化正在世界上許多區域迅速發生,這得益于人們逐漸認識到野性自然的生態學價值及其對人類健康的益處。一些案例發生于已有的城市綠色空間之中。例如北京大學籌劃建立了中國第一個校園自然保護小區,提出了環境保護的整體策略,生態相關專業的師生也做出積極貢獻,共同促進校園生物多樣性的提升,開展了長期的生態監測,逐漸形成了“野生動物友好型”的校園環境,具有示范意義[32]。另外,值得關注對于濕地和河流廊道的生態修復與再野化。一個有趣案例是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名為Paco的市場運河(圖4、5)。該水道與一個重要的食品市場比鄰,曾經充斥著垃圾碎片并散發著惡臭。英國企業Biomatrix Water通過使用自主研發的“活躍島嶼”(Active Islands)技術,對水體進行了再循環和氧化,加上經過選擇的植物和“動態媒介”(Dynamic Media)來過濾污染物和病原體,創造出了一個美麗潔凈的水體環境。一項政府報告顯示,該項目所獲得的收益是項目成本的10倍以上[33]。通過對河流廊道的生態修復與再野化,恢復了自然生境,并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新的休閑場所。

4 修復前的Paco市場運河Paco market canal before restoration

5 修復后的Paco市場運河Paco market canal after restoration
2.3 設計:在城市公園中營造類荒野景觀
除了保護野性自然與再野化之外,在城市公園的設計中也能夠體現對野性自然的尊重。景觀設計師可以對野性自然進行保留或適度改造,設計出“類荒野景觀”,雖然不同于真正的荒野地,但具有野性自然的某些特征。在類荒野景觀的設計中,植物設計是一項重要因素。源于對野生植物的欣賞和對荒野景觀的敬畏,許多景觀設計師追求植物景觀營造的自然野態,這也成為植物景觀設計的重要思潮之一[34-35]。例如威廉·羅賓遜(William Robinson)在《野生花園》(Wild Garden)中提出了“自然化種植”的思想,提倡減少人為干預,讓植物自然生長,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園林美學[36]。格特魯德·杰基爾(Gertrude Jekyll)則在其公園設計中尊重場地基底,完成了許多經典的野生花園實踐。法國當代景觀設計師吉爾·克萊芒(Giles Clément)在《動態花園》中提出:“在自然中應留出一塊凈土,人們不應克制它的自然演變,這是理想園林的代表”,認為新型園林中應該盡量降低人的干預,尊重自然的生態過程,并在巴黎雪鐵龍公園中進行了“動態花園”(garden in movement)的實踐。派特·歐多夫(Piet Oudolf)引領了種植設計的“新多年生運動”(New Perennial Movement),倡導利用野生植物、禾本科植物、觀賞草等多年生植物來營造景觀。詹姆斯·希契莫夫(James Hitchmough)則提倡通過撒播來建立復雜的多年生草本植物群落,推崇兼具生態、美學、功能的“低成本生態景觀”[37]。上述追求植物景觀自然野態的實踐中,或多或少體現了有意圖的設計和人工管理,無法營造出真正的、原始的野性自然,但是其中對于野性自然價值的尊重態度和設計方法仍然值得借鑒。
在中國,江洋畈生態公園是以野性自然為基礎而設計成為城市公園的代表性案例[38]。原有場地為西湖疏浚后淤泥形成的次生荒野,該項目將其設計改造為一處生態公園,保留了大部分場地原有的自然特征,允許自然演替的發生,并以生境島的方式保留了部分原生植被,作為自然演替的樣本。在生物多樣性得以提升的同時,提供給游客關于自然演替的體驗和教育機會,同時提倡對于自然野態的審美[39-40]。這一案例對于野性自然的尊重、保留、審美和解說,使其有別于傳統的園林和城市公園,同時為在城市區域中設計“類荒野景觀”提供了諸多啟發。
2.4 融合:在城市空間中系統性融入野性自然
更具綜合性的解決方案是在城市空間中系統性融入野性自然。即將野性自然保護作為城市發展的關鍵戰略,并將上文提到的保護、修復、設計途徑進行統籌,從而將城市空間與野性自然進行系統性整合。倫敦的“國家公園城市”(National Park City)是一個正在進行的探索性實踐。“國家公園城市”的概念由David Raven-Ellison提出,致力于將倫敦打造為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城市”。在概念提出后,已發展出一個正式的慈善組織——國家公園城市基金會(National Park City Foundation),國家公園城市的建設也得到倫敦市長的大力支持。雖然“國家公園城市”的提出受到了“國家公園”概念的啟發,但是“國家公園城市”明顯不同于英國現有的鄉村型國家公園[41-43],它指向一種關于城市與自然環境的新型思考方式。該基金會給出了“國家公園城市”的工作型定義:“通過正式和非正式手段管理并兼用于自然保護的大面積城市區域,以提升景觀的自然資本。居民、游客和決策者達成廣泛而重要的承諾:允許自然過程的發生,從而為高質量的生活提供基礎。”[44]在上述定義的基礎上,倫敦國家公園城市的發展目標包括:1)促進更多人享受倫敦美好的戶外空間,連接人與自然;2)讓倫敦更綠色、更健康、更具野性,使藍綠空間達到倫敦總面積的50%以上;3)通過“國家公園城市”強化倫敦的城市品牌。為實現上述目標,國家公園城市基金會通過多方參與,與各類組織機構和人群合作,共同開展相關活動。例如,2018年底發布了由大倫敦市區居民通過眾籌方式資助的一幅倫敦國家公園城市地圖。這一地圖展示了倫敦3 000多個各式各樣的公園,以及林地、游樂場、保護區、城市農場、河流、運河和自然小徑。可見,“國家公園城市”是在城市空間中系統性融入野性自然的一次探索性實踐。類似的,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建筑學院Timothy Beatley及其團隊,致力于規劃與設計“生命親和型城市”(Biophilic Cities),旨在通過系統性與整體性的方式,將自然引入城市規劃與設計之中[45-46]。
3 結語
當絕大多數人口居住于城市之中,城市內部與邊緣區域的野性自然將變得愈發重要,成為連接人和自然之間的重要紐帶。當一座城市片面追求經濟發展、物質享受和新技術帶來的便利,而忽視野性自然的價值時,將對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當一座城市不能夠有效保護與營造野性自然時,很難將其稱為真正的宜居城市。
當下中國的城市建設中,存在著片面追求綠地率、忽視綠地生態功能與生態過程、過度人工干預和管理的現象,導致公園的生態結構單一、維護成本高、使用效率低等問題。在此背景中,建議重新思考野性自然對城市空間的意義。在思想上,應尊重城市區域中野性自然的內在價值,建立保護城市野性自然的哲學、倫理學和美學,同時運用生態學、保護生物學等科學知識,通過各種景觀規劃與設計的技術與方法,有效保護與營造城市野境。最終將野性自然的系統與城市人居環境的系統有機融合,從而創造出更加健康和可持續的“野性城市”,在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同時,促進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
致謝(Acknowledgments):
感謝張倩、侯姝彧、廖凌云在論文撰寫過程中提供的建議。
圖表來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
圖1來自作者,圖2來自K.Jerome,圖3來自Nayan Khanolkar,圖4、5來自Biomatrix water;表1內容由作者根據IUCN《城市保護地:概述與最佳實踐指南》第二部分相關內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