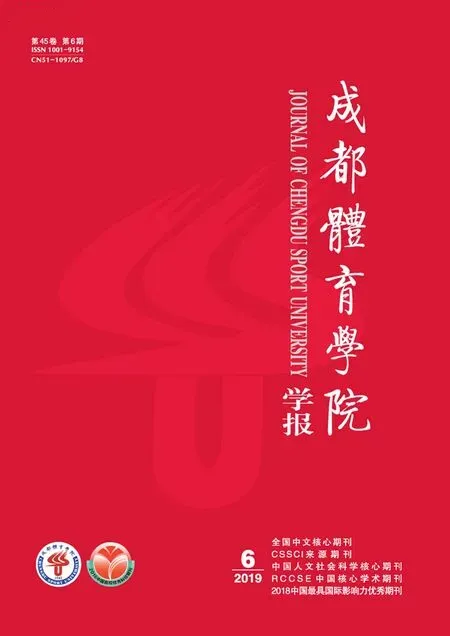論現代體育“文明競賽”的歷史生成
張 新
“文明”的反義詞是“野蠻”和“不文明”,從人的行為舉止來理解,“文明”是使人類脫離野蠻狀態的所有社會行為的集合。在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過程中,社會制度和道德觀念總是在塑造著更加“文明”的行為規范,盡力使人們表現得情感有節、行為有度,從而構建整個社會的公序良俗。而文明行為體現在體育競賽領域,就是競賽者以運動家的心態參與比賽,你不能輸了比賽就惱羞成怒,向對手施以拳腳,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遵守規則、尊重裁判、尊重結果、尊重對手的風度。所謂體育活動中的“文明競賽”,就是以文明的方式參加競賽,其核心是體現出“fair play”精神,“fair play”有兩層意思,從遵守規則層面講就是“公平競賽”,從體育道德的層面講,就是“光明正大”地去贏取比賽。
體育競賽與文明行為之間看似一個悖論,因為爭奪勝負的激烈對抗最容易引發情緒失控的攻擊行為。自工業革命開始,現代體育逐步形成了一個行業治理體系,各體育協會、職業體育聯盟不斷通過對規則、章程、仲裁等明文規定的修訂,來整治違規、違德的不文明行為。其中競賽規則針對運動項目的“玩法”,明晰了裁判判罰的尺度,避免比賽因規則爭議而中斷;章程針對運動競賽的組織管理系統,界定了運動員的參賽資格和獎懲辦法;相對獨立的體育仲裁機構則根據規章來解決競賽糾紛,處罰違規行為。這些有章可查的硬性規定和操作系統,對體育競賽行為形成了強制性的約束力,其目的意義是倡導現代文明“公平競爭”的法則,并承續古老體育競賽中逐步形成的道德傳統,在現代體育競賽中表達平等、友好、團結的時代精神。
體育“文明競賽”的法則為何陡然在工業經濟時代普遍確立,并隨著奧林匹克運動會高頌的體育精神而暢行世界?本文的邏輯出發點首先是在體育競賽悠遠的歷史中尋找“文明”的基因傳承,在前工業時代尋找直接影響現代體育的行為道德風范。
1 古代體育中的文明競賽基因
美國體育史學者阿倫·古特曼把資本主義時代早期發展至今的體育活動統稱為現代體育,認為現代體育發端于18世紀早期的英國倫敦,然后傳播至西歐、美國,以至全世界,而中世紀及其以前時代的體育則為古代體育。同時,阿倫·古特曼還持有一個重要觀點:體育脫胎于人類的游戲,是本能游戲(Play)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有組織”的游戲(Games)[1]。的確,游戲活動與人類相伴而生,是體育運動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源頭。初級的體育競賽游戲是個體之間自發相約的活動,而體育競賽游戲過程中緊張、期待、歡欣鼓舞等情緒體驗總是給人無窮樂趣,很容易吸引觀眾圍觀,發展成為在社會人群面前公開進行的競賽表演活動,或者體育競賽營造的歡樂氣氛與國家慶典融合為一體,成為國家慶典的一個儀式組成部分,使民間的競賽游戲演變而成公共體育競賽。荷蘭游戲理論學者胡青伊加就認為公共體育競賽是游戲發展的高級形式,他說:“另一類得到高度發展的游戲形式,是在傾慕的公眾面前進行正規的競賽和優美的表演。”[2]那么,無論是民間隨意的體育競賽游戲還是公共體育競賽,人一旦投入到這些體育競賽活動之中,會形成什么樣的基本范式并傳承哪些文明競賽的歷史基因呢?
1.1 競賽法則的約定俗成
動物和人的游戲都是天性所致,“人”一開始就與游戲相伴。游戲與功利性的日常生產勞動有本質不同,生產活動要直接創造滿足生活需要的物質產品,游戲就是人們“空閑時間尋找個人趣味的一樁事情,從游戲開始到游戲結束并不生產任何物質產品,愉悅松弛或者表演展示就是游戲的目的。非功利性是游戲的一個本質特征,Sports的詞源演進就印證了游戲的非功利性,port意為“搬運”“港口”,加dis否定前綴就意指離開勞動場地進入娛樂狀態,由中世紀英語單詞disports簡寫而來的sports一詞泛指各類娛樂活動,至工業革命時期sports才特指體育運動[3]。而體育運動競賽是游戲類別中有組織的高級形式,人們一旦擺脫日常生活軌道進入體育競賽的游戲世界,就必須聽從這個特殊行為現象自身規律的安排。
游戲總是在預先劃好的場地上進行,競技場、廣場、賽馬場、網球場、牌桌等,把日常生活隔離開形成臨時的游戲世界,游戲者首先需要承認競爭對手的對等身份,否則競賽的前提就不存在。最為典型的案例是15世紀法國的一個真實故事,法國諾曼底地區一個叫古貝維爾的莊園主在他的日記中記錄說,他在一次足球比賽中被自己的仆從撞斷了肋骨,臥床多日卻對仆從沒有任何抱怨[4]。可見,游戲是一個超現實的世界,有著自身的秩序。規則就是統轄這種特殊秩序的靈魂,哪怕是臨時不完善的口頭約定,參與者都必須遵從,因為游戲活動不同于被利益捆綁驅使的生產活動,游戲是易碎的,隨時會由于參與者的違規敗興而宣告無法進行。
規則是游戲的前提,個體間隨意的競賽游戲都要遵從規則的約定,而體育競賽一旦與國家慶典等社會活動相結合,上升為擁有一定規模的公共體育賽事后,這種規則意識就會得到國家、社會群體力量的強化。相比而言古代世界的體育競賽發展不均衡,因時因地不同。古代中國的蹴鞠、馬球、捶丸等活動,出現了文本化的比賽規章,單個項目的競賽形制已經發展得較為完備,只是階層等級的壁壘分野制約了全社會競賽共享機制的形成。西方的古希臘、古羅馬競技是古代世界運動競賽的發展高峰,古希臘把運動競賽的快樂與宗教慶典需要結合在一起,賦予了競賽一種“神圣”的社會功用,運動競賽具有“娛神”的功能,賽會參與者的“賭注”是自己的名望,違背公平原則的人將身敗名裂。古羅馬第一次在城市大競技場用職業競技來娛樂公眾,面對上萬觀眾的彩票下注與自身的名利獎勵,角斗士的勇敢與技能是贏得聲望的唯一途徑。遺憾的是古希臘、古羅馬的競賽傳承被中世紀蠻勇的民族征戰打破,游戲競賽形式重新回到民間散亂粗放的狀態。但在競賽游戲中埋藏著文明競賽的基因,在其悠長又曲折的歷史演進過程中,我們始終可以看到競賽規則的頑強生長。
1.2 騎士比武的文明禮儀示范
歐洲的競賽傳統被蠻族遷徙征戰中斷幾個世紀過后,于中世紀中期興起了騎士比武活動。騎士比武在時間和空間上與現代體育直接相連,不僅騎士比武的英語專用詞匯“tournament”沿用到現代變成“賽會”的意思,至今美國網球巡回賽等賽事還在使用這個詞匯,騎士精神也成為現代體育精神的主要來源。現代體育之父顧拜旦把騎士精神看作是現代體育精神的同義詞,認為高貴的騎士精神是一切耐力和純競技活動的基礎[5]。中世紀的騎士比武活動在其演進過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儀式化的競賽體系,同時在競賽道德風尚層面給后來的人們示范了一種高尚的行為舉止。
騎士比武經歷了從暴戾向典雅的轉變,一開始并沒有多少規則約束與情感限制。11世紀在法國北部地區,出現了一種極其有效的新型騎兵戰術,即一隊騎士手持重型長槍一起沖鋒。作為新型戰術的訓練手段,騎士比武應運而生,并迅速流行開來[4]。騎士們“將參與決斗野力全部宣泄到了決斗欲望的保留地,那便是由人類所開辟的競技場,決斗因為隸屬于自然法則,才顯得格外的放蕩不羈。”[6]早期的騎士比武像狂暴的戰爭演習,沒有多少規則可言,對雙方人數或武器裝備沒有明細要求,使用武器為真刀真槍,有時候群情激憤的平民觀眾也可能持械加入戰團,很容易造成重大傷亡事故。13世紀中后期,騎士比武的方式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在一對一策馬對刺比武中,規定了長槍刺中對方身體不同部位的記分辦法,由此根據二人幾回合比賽結束后的得分來判斷勝負;在群體比武中,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1292年頒布了一項法令,其中有三個關鍵條款:首先,騎士無論多富有,每人最多只能攜帶三名扈從上場;其次,無論騎士還是扈從都不允許攜帶鋒利的刀劍或鈍頭錘;最后,現場觀眾和步騎仆從一概不許攜帶武器[7]。由此控制了場上對抗雙方的人數,避免觀眾與隨從加入混戰。這個時期規定比武使用武器必須是鈍槍頭,并且要提供貴族身份證明。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變化,從競賽形式上把騎士混戰變成了貴族專屬的騎士體育。
與競賽方式“體育化”演進相對應,是騎士文明賽風的逐漸形成。騎士階層舉止風度的一點一滴變化,源自于生活境況的緩慢改變。早期騎士基本上就是打家劫舍的一勇之夫,通過攻守戰斗來分配調劑社會財富,殺戮搶劫完全符合當時騎士社會的道德水準,這種性格特征展現在比武活動中,就與后來的騎士精神大相徑庭。12世紀英國著名騎士威廉元帥的兩個案例,印證了當時騎士的一些道德缺失。一是采用詭計,把比武變成一場偷襲。英國的“青年國王”亨利在群體比武中多次吃虧,后來聽取了威廉元帥的建議,假裝不參加比武,等到場上的騎士打得筋疲力盡時,再帶領奇兵出襲去竊取勝利果實。二是乘人之危,一次威廉元帥和他的同伴去飯館吃飯,恰巧一個比武騎士在飯館門前摔斷腿,撲跌不起,威廉乘機把他俘虜了,用這名倒霉的騎士去換取贖金[8]。大約13世紀時社會力量與財富緩慢向大領主、國王方向集中,擁有小塊土地的自由騎士日益貧窮不得不向其投靠,成為宮廷侍臣或者拿餉的軍官。于是歐洲各國的國王或大領主們的宮廷便成為騎士的馴化之地。與騎士個人微乎其微的自我情感約束比起來,宮廷社會的規制要強大得多。宮廷社會對內部交往的暴力活動有某種程度的克制,上流社會人際之間建立了一種美好交往的方式。人們的一舉一動、一眼一瞥都十分講究,需要在言談舉止中體現文明教養。勇敢忠誠、堅忍不拔的品質不再是騎士的全部美德,榮譽、公正、體面、慷慨成為“騎士精神”內涵中的部分核心價值。宮廷社會這些道德共識,對騎士行為形成了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采用不光彩手段取勝就會使自己和家族名譽受損。于是,騎士不再像早期那樣乘人之危、恃強凌弱,而是在競賽中顯現出光明正大的品行,這些約束與品行也隨時間一起傳承至今天的體育競賽之中。
2 體育文明競賽的現代生成
中世紀后期,城市規模與貨幣經濟日益發展,使那些主要依靠鄉村庭院經濟生活的騎士們被邊緣化,他們不斷感受到物價上漲與貨幣貶值的無奈。歷史的前進終結了騎士的時代榮光,而市民階層卻作為上升的第三等級受到了歷史的恩寵。市民群體不滿足于平等原則只在上流社會的生活范圍內實現,他們要求普遍的社會公正。城市人群新的社會訴求與情感模式,推動了現代文明競賽機制的形成。
2.1 貨幣經濟背景下現代體育倫理的蘊育
體育競賽的發展歷史中,商業活動與體育競賽之間存在一種互通的共同法則,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呈現了兩者彼此的緊密關系。古代希臘體育競賽得以普遍流行,除了宗教祭祀賦予其神圣意義之外,城邦工商業經濟形態中也蘊涵著內在推動力量。城市工商業者要求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按契約關系實現市場交換,公平競爭是商業精神也是游戲競賽的法則,也可以說體育競賽是這種社會精神的載體和道德搬運工,兩類活動相得益彰、互相促進。
隨著中世紀晚期城市的興盛,體育競賽機制與商業經濟秩序同生共進的趨勢更加明顯,甚至兩類活動就生發于同一塊場地上,通過詞源考查我們可以隱約追尋到歷史演變的痕跡。英語“fair play”意為公平競賽,根據英語字典“fair”有多個意思,包括集市、集會、公共露天游樂場、美好的、公正的、光明正大的等等,在英語造詞的意義引申中這些多層含義有什么關聯呢?我們特別注意到,“集市”與“露天游樂場”兩個含義同出一詞恰恰符合了當時城市的建筑格局。中世紀歐洲的城市平面布局圍繞中心廣場一圈圈環形展開,街道圍繞廣場呈放射狀延伸。領主拿到國王的特許令后,除了建設城堡和鑄幣廠之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修建賦稅來源的市場,城市中心廣場就是集市交易場所,同時因為是開敞空間,也就順利成章地成為公共露天游樂場,足球、曲棍球等競賽游戲時常在這里開展。可見,商業活動與游戲競賽在同一個空間中進行,必然遵循相類似的法則。按照市場原則進行,就是公正的、美好的和光明正大的。“fair”可以組合成商業用語,比如公平價格“fair price”,也可以組合成競賽術語,15世紀英國詩歌中出現了“fair game”,16世紀末莎士比亞在他的歷史劇《約翰王》中使用了“fair play”一詞。1640年英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英國率先進入資本主義時代,“fair play”的使用頻率更高,到1792年,英國出版的第一本體育期刊就經常使用這個詞匯[9]。“fair play”一詞還傳播到了西歐其他國家,德語中至今還在采用這個外來的英語詞匯,標志著“公平競爭”觀念在更廣大地域的流行。
貨幣經濟的發展改變了社會競爭的方式,?競爭手段文明化了,不再主要通過爭奪土地等不動產的武斗方式來決定貧富,市民階層的競爭是對市場機遇的競爭,通過經濟手段來取得自己在同行業中的優勢地位,這樣的競爭方式把社會發展導向了一種新制度的建立,同時也引發了現代倫理觀念的塑造。隨著職能分工明細和學科專業發展,市民階層不同程度地具有一定見識和教養,特別是經濟條件優越的紳士階層承襲了騎士貴族的優雅美德,這是一個貴族精神市民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現代體育觀念生發的過程,紳士作為現代體育的開創者,樹立了公平競賽、尊重對手、尊重裁判等現代體育的道德準則。
2.2 工業生產背景下現代體育規則的誕生
與現代體育倫理同步發展的是運動規則的完善。“普遍的、以書面形式固定下來的法律準則從屬于工業社會所有制形式,法律準則的形成是以很高程度的社會聯系為前提”。[10]工業生產的分工協同,商業交換的日益頻繁,需要制訂更細密的法律條文來協調監管。除一系列的法律條文規范商業交換之外,改造公眾的休閑方式也是轉型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首當其沖就是對集市與街頭的競賽表演進行整改,立法機構從公共治安的角度限制隨地進行的競賽表演行為,1835年英國頒行的“公路法”授權警察可以監禁處罰這些街頭運動的參與者,對于街頭狂野的足球比賽與有獎格斗比賽等流行運動項目也進行了嚴厲打擊。1839年英國又出臺的“城市警察法”,授權房主可以在生活與營業受到干擾的情況下要求表演藝人離開[11]。中世紀式的集市、街頭競賽表演活動逐漸消失,取而代之是正規固定的競賽場所,權利機構立法支持建設運動場、健身場所、休閑公園、林蔭綠道等基礎設施,使公共競賽表演活動進入文明有序的發展軌道。
英國城市警察法和公路法的頒布,把集市、街頭競賽逐漸引向了專用體育場,標準的場地更需要規范的規則、章程來維護競賽活動的內在秩序。于是,各運動項目逐步開始了對傳統競賽游戲的文本化規則改造,在學校操場、賽馬場、公共運動場誕生了現代運動項目。賽馬是中世紀就流行的古老運動,也是現代最早在標準場地進行比賽的項目,倫敦以北約105公里的紐馬基特逐漸成為英格蘭的賽馬中心,1727年,紐馬基特的工作人員約翰·切尼把賽志匯集起來出版了《切尼的馬賽》一書,使競賽有章可查,由此翻開了現代賽馬運動的篇章。[12]足球同樣是中世紀的粗野游戲,15世紀法國諾曼底地區曾經流行的蘇勒球(Soule)比賽,兩個教區各自上場的參賽人數都超過了500人,這項對抗激烈的游戲是現代足球與橄欖球兩大運動的共同源頭。1848年,英國劍橋大學的學生們由于來自不同的公學,各校規則不同使比賽很難進行,于是他們討論制訂了著名的《劍橋規則》,框定了現代足球競賽的基本范式,也使足球在運動形式上與橄欖球分道揚鑣。拳擊比賽在英國曾經是赤手空拳的暴力格斗,1743年,著名的拳擊手杰克·布勞頓推出一套包括7條內容的規則,使拳擊運動向文明化方向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到1838年制定的《倫敦職業拳擊規則》進一步降低了拳擊野蠻色彩。其余如射箭、網球、擊劍等運動項目,普遍經歷了現代規則的重新設計。
有了標準的運動規則,使運動項目迅速跨地區流行開來,伴之而生的就是各類運動協會、職業體育聯盟的先后成立。1863年10月26日成立的英國足球協會就宣稱,其宗旨是“為了規范足球運動而起草一套明晰的規則。”[13]現代體育規則體現了工業經濟時代的科學精神,經過一個設計——實踐——再設計的過程,運動項目的玩法逐漸完善,仿佛工業流水線上生產出來的標準件,逐漸在世界范圍內通行。同時,針對運動競賽中不時出現的不良行為,各類體育組織陸續制訂了實施行業管理的相關章程。其目的用意正如《奧林匹克憲章》所描述:“努力在體育運動中發揚公平競賽的精神,消除暴力行為;采取旨在防止危及運動員健康的措施。”[14]自此,標準化的比賽場地、文本化的競賽規章、專業化的爭議仲裁、國際化的協會組織等程序規范,構建了文明競賽的現代機制,并依靠工業經濟對外擴張的壓倒性優勢把這種競賽模式推向了全球。
3 現代體育文明競賽的當代發展
社會文明的要旨之一即是對暴力行為實施法規管控,使身體強壯的人不能隨意對他人發泄攻擊欲望。體育文明競賽的意義,就是通過規則與倫理的雙重管制,對競賽情緒和行為施加長期有效的影響。循著這個思路,我們可以深層次理解當代體育競賽中的諸多現象。
3.1 體育規則對暴力色彩的改造和保留
人的內心深處埋藏著攻擊欲望,它與饑餓、情欲等其他情感因素構成了整體的心理狀態,社會總是要設法建立一種強迫機制,把情感宣泄限定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同時人們基于對處罰的懼怕,逐漸會形成一種自我約束的心理機制,一旦有突破他們心理接受程度的出格行為,就可能產生厭惡情緒。各個時代流行的不同運動項目,通常迎合了當時人們的情感水準和審美情趣。今天我們如果看到盛大的羅馬角斗比賽,在情感上會難以接受,但在羅馬人看來卻是視死如歸勇敢精神的體現,角斗場遺址的文物發掘證明,女性觀眾甚至一邊在看臺上看比賽一邊做著針線,反映了他們處之泰然的心理狀態[15]。
冷兵器時代西方最為流行的競賽項目,先后是角斗士競技與騎士比武等戰爭模擬游戲,現代體育卻朝著有節制的體能碰撞與人道主義方向發展,激烈的對抗項目都經歷了規則化改造,比如現代拳擊運動,1838年的《倫敦職業拳擊規則》明文規定不能攻擊對方腰帶以下的身體部位,并宣布踢人、咬人等都屬犯規,使拳擊運動變成了人有節制的攻擊與搏斗表現。現代足球運動也因為規則變化而日益“文明”,1848年的《劍橋規則》的一個核心條款,就是爭奪時只能踢球,不能踢對手的腳踵,劍橋大學的學生們在討論這條規定時發生了激烈的爭議,有的學生認為廢除踢腳踵就是廢止了該項運動體現出的勇氣和膽量,但最終還是通過投票表決出臺了“不能踢人”的規則。到1863年英國足球協會頒發第一套全國規則,進一步廢止了絆人、踢人、推搡等粗野傳統。[13]“文明”是時代發展的趨向,許多古代血腥的競賽項目都被看作是一種陋習,或者消失或者得到了改造,“松子酒巷、刑場買賣、狂飲酗酒、獸奸、穿上帶鐵釘的鞋為獎金而進行致命的打斗,所有這些的消失都不足以哀傷憑吊”[16]。
另一方面,體育競賽又適當保留了對抗競爭的暴力性,因為攻擊欲望始終隱匿于人的天性之中,當社會武斗活動被刑法嚴格管控之后,體育賽場就成為社會許可的宣泄戰斗欲與攻擊欲的“保留地”,觀眾在“觀看”中有節制地發泄了他們的情感。于是一部分運動項目保留的暴力性,就成為其運動風格的魅力所在。橄欖球被稱為“百碼戰爭”,美國體育史學者古特曼評論說:“在公園將一行人攔腰截住并將他摔在草地上是暴力行經,但中后衛球員在賽場上做同一動作就當然不是同一意義上的暴力。”[1]同樣,足球比賽中兇狠的鏟球,背后拉拽的戰術犯規;籃球運動中故意在對手罰球技術不好的球員身上犯規,都是爭奪勝負的戰術需要,可以使比賽更加緊張精彩。一些運動項目甚至包含了規則允許的暴力形式,冰球運動甚至默許打架,但這種打架行為是中世紀騎士體面比武方式的現代翻版,一般僅發生在兩名球員之間,開打之前還會用眼神示意通知對方,并且都會放下球桿、摘下頭盔等金屬器皿,避免造成過度傷害,偶爾打斗升級為多人群毆,裁判則有一套規則和辦法止息紛爭。當然,比賽場上的暴力性和運動員的暴力行為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身體合理沖撞呈現出的暴力性,是為了讓比賽更具觀賞性,而比賽場上惡意報復造成傷害的做法,則屬于暴力行為,將受到行業協會或者聯盟的嚴厲制裁。
現代文明競賽規則建立了競賽秩序,“貓眼”等攝像技術的運用,使比賽判罰更加精密,電視回放功能為裁判二次改判提供了便利,也為體育仲裁機構提供了呈堂證供,那些在比賽中飛踹對手、向裁判吐口水等不文明行為都難逃“法眼”,必然會遭到禁賽、罰款的重處,違規運動員自身的權益由此也會受到損失。而出于對違規處罰后果的畏懼,運動員的“暴怒”通常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避免了沖突升級和中途退賽等過激行為的發生,保障了體育競賽持續有序地激情上演,成為當代人類的一場精神狂歡。
3.2 道德對體育競賽行為的約束
體育規則是一種對體育競賽行為的外在約束,體育精神是引導競賽行為的內心驅動,哪怕符合規則的舉動,一旦違背了現代體育道德原則就會產生一種羞恥感。在足球比賽中就經常出現這類典型現象,當場上有球員受傷倒地后,持球一方球員通常會把足球踢出界外,以便暫停比賽讓傷員得到救治。恢復比賽后,獲得擲界外球機會的一方球隊,按理要把足球踢還給對方,這是一種不成文的約定。2012年歐洲冠軍杯比賽中卻出現反常,烏克蘭礦工隊在與丹麥北西蘭隊比賽時,礦工隊前鋒阿德里亞諾意外地搶斷隊友大腳踢還給對方門將的皮球,并且射門得分。根據規則進球有效,阿德里亞諾卻立刻遭到對方球員的圍堵譴責,阿德里亞諾沒有違反比賽規則,但他有失“fair play”的體面,這粒進球也被媒體評論為“不道德的進球”。[17]
現代體育規則并不能制約消極比賽甚至故意輸球,比如足球比賽中如果有意“自擺烏龍”,把足球踢進本方球門,現場裁判也無法根據規則實施處罰。可見在規則約定之外,需要體育道德的約束,2018年女排世錦賽小組賽最后一輪,中國女排只要“故意”輸給荷蘭女排,就能夠以小組第二身份進入四強淘汰賽,從而避開實力強勁的意大利女排,增加進入決賽乃至奪冠的機會。但中國女排沒有想過要“故意輸給誰”,在戰勝荷蘭之后,中國女排雖與意大利隊苦戰五局惜敗,無緣染指冠軍獎杯,卻很好詮釋了“公平競賽”的體育精神。現代體育精神賦予了競賽行為一種“正大光明”的風范,早期英國紳士在足球比賽中,當對方紅牌罰下一名球員后,為了避免以多打少,本方會主動安排一名球員退場。上世紀80年代,中國著名球員容志行面對場上經常性遭到的違規侵犯,從來表現得不慍不火,被媒體稱譽為“志行精神”。2015年12月16日,在西班牙舉行的一場自行車賽上,車手伊斯梅爾·埃斯特萬在距離終點300米時遭遇爆胎,他只能扛起自行車跑向終點,競爭對手奧古斯汀·納瓦羅拒絕超越,慢慢地跟隨在埃斯特萬身后。最終表現騎士風度的納瓦羅只獲得第4名,當埃斯特萬主動把銅牌贈予他時卻遭到婉拒,另兩名超越的車手分獲冠亞軍,按照規則也無可厚非,而納瓦羅的“古怪”行經卻使他站上了榮譽的制高點,這是對騎士“體面”觀念的久遠繼承,又體現了現代文明背景下的一種精神追求。
4 結語
運動競賽的基本形式是自古而然的,核心都是力量、速度、技能的較量,其有序進行的前提是競賽者必須遵從規則約定,最終以一個不可預知的勝負結局給觀眾帶來癲狂的情緒體驗。所以,現代體育文明競賽的形成過程中傳承了人類古老規則意識與競賽倫理的基因。但古代世界的審美情感與道德水準,使體育競賽活動更多帶有暴力血腥的野蠻習氣,甚至伴有角斗、決斗等戕害生命的行為。現代體育的生成背景是工業生產方式帶來的城市人口大量聚集,市場、財富、教育、娛樂的新格局要求建立相應的法治秩序與情感模式,尤其是生命意識與平等觀念的高漲,使得體育競賽也在歷史的累積中發生了質變,高尚道德牽引在前,嚴厲規章約束在后,猶如兩根縛繩制約了競賽者暴力情緒的肆意宣泄,把野蠻的競賽方式升華為體系完善的現代體育文明競賽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