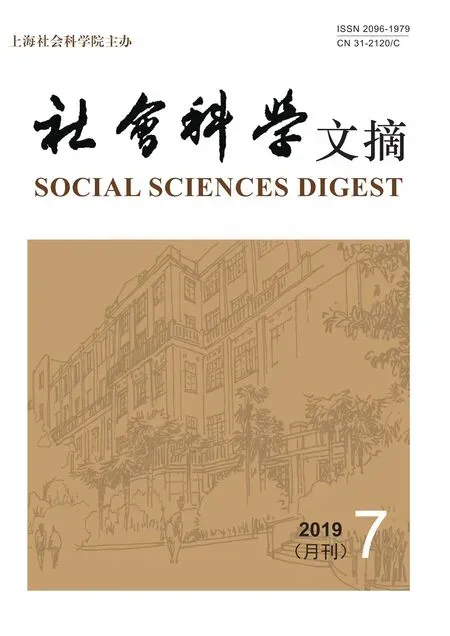梵蒂岡的權力資源及其在當代世界事務中的作用
在當代世界舞臺上,梵蒂岡是一個非常獨特而略顯神秘的國際行為體。甚至連“梵蒂岡”指什么,都有可能引起誤解。“梵蒂岡”這一稱謂本身具有含糊性:它可能是指占地只有0.44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一千的世界上最小的主權國家——梵蒂岡城國(Vatican City State);同時,由于整個羅馬天主教會的中央領導機構“圣座”(Holy See)駐地在梵蒂岡城國,所以,無論在日常實踐還是在學術語境中,“梵蒂岡”還經常被用于指稱天主教會的中央領導機構“圣座”,如同“白宮”指代美國政府的行政分支,而“華盛頓”指代整個美國政府那樣。廣義的圣座指教皇(Pope 或 Supreme Pontiff)和教廷(Roman Curia),而教廷又包括國務院、圣部、法院、宗座理事會等部門。梵蒂岡城國和圣座是兩個不同的實體:城國根據《拉特蘭條約》成立于1929年,而圣座的歷史可遠溯至基督教會發展早期。城國雖小,但卻是圣座如今能夠自治的地理保障和后勤保障,使教皇不必寄人籬下而能獨立行使主權。有學者這樣形容:梵蒂岡城國更像是圣座的“肉身”,而圣座則像梵蒂岡城國的“法身”。由于“梵蒂岡”能夠同時體現兩種身份,而且教皇和教廷經常利用兩種身份兼具所帶來的跨國參與優勢,所以本文也使用“梵蒂岡”這一概念。
梵蒂岡面積雖小,影響力卻大,被稱為“最小的大國”。在日本駐圣座大使上野景文眼中,梵蒂岡具有崇高的國際地位,這是“今日之現實”。在國際法中,梵蒂岡所指代的圣座是唯一擁有國際法人資格的宗教行為體,它能和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平起平坐,這一外交地位是所有其他宗教行為體都無法企及的。圣座的這一外交地位根本上源自它作為天主教會中央領導機構的身份。圣座領導著羅馬天主教會這一世界上最龐大、最古老、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前曾叱咤風云的跨國組織。到2016年,天主教徒有12.99億人,遍布歐洲、美洲、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將近13億的天主教徒組成了一個“無形國度”,他們把教皇當作精神領袖,圣座提供的觀念影響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時候是他們行動的指南。而圣座也通過中央集權、等級制的圣統制對全世界的教區進行管理和控制。曾任美國政務副國務卿的尤金·羅斯托在評價梵蒂岡在當代世界中的作用時曾這樣形容:梵蒂岡不僅是一個巨大的精神和文化共同體的中心,是一個活的觀念和價值系統的可見的象征,還是一個協調遍及全球的跨國官僚系統的秘書處。他認為,在精神維度和世俗維度上,梵蒂岡都在國際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梵蒂岡沒有軍事力量,經濟力量也微不足道,所以,在崇尚物質力量的人眼里,它的作用不值一提。例如,斯大林曾輕蔑地問:“教皇能有多少裝甲師?”丘吉爾則明白力量不僅僅有物質力量這一種形式,他對斯大林評論的回應是:很多軍團并不是總能在閱兵時看到的。后來,正是沒有任何裝甲師的梵蒂岡,在美蘇兩大陣營的對抗中對蘇聯及其東歐盟國造成了無法挽回的沉重打擊。為什么梵蒂岡的權力和影響力會被低估呢?美國駐圣座大使弗朗西斯·魯尼對此給出的答案是:梵蒂岡是一個極其復雜和獨特的機構,所以容易被擱置而不是被理解。那么,梵蒂岡在當代世界舞臺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和世俗國家相比,梵蒂岡具有無可比擬的精神資源。作為天主教徒的道德權威、全球意見領袖,它是規范倡導者,能夠塑造信徒和非信徒的認知和偏好,從而影響其行動。和多數宗教行為體相比,梵蒂岡所領導的天主教會非常重視制度建設,擁有古老、龐大而嚴密的組織網絡和規則體系,從而擁有優裕的組織資源。另外,梵蒂岡代表的圣座是唯一被國際法承認的宗教行為體,而其“肉身”梵蒂岡城國又有國際認可的領土主權,因此它具備其他宗教行為體不可企及的外交資源。精神資源、組織資源和外交資源,都可以被視為權力資源,也就是行為體用以影響世界的能力。梵蒂岡之所以能在當代世界發揮獨特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夠靈活運用這三種權力資源。
精神資源
梵蒂岡的精神資源,首先在于它是全世界天主教徒的道德權威,為其提供規范性的宗教觀念。天主教法典第331條規定:教皇是“世界主教團的首領、基督的代表、普世教會在現世的牧人;因此由于此職務,他在普世教會內享有最高的、完全的、直接的職權,且得經常自由行使之。”第333條規定:教皇“不僅享有對普世教會的權力,而且對所有個別教會及其信眾擁有職權的首位”,而且,對教皇的“判決和法令,不得上訴或訴愿”。可以說,梵蒂岡對近13億天主教徒擁有“精神主權”,它作為規范倡導者,為信徒提供一套規范性的宗教觀念,來塑造他們的認知和偏好。這些觀念往往以《圣經》文本、教會法典、教義問答、教皇通諭、勸諭、牧函等形式被梵蒂岡提供給信眾,涉及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意在成為他們的思想準則和行為指南。
梵蒂岡不僅是天主教徒的道德權威,還是全球公共領域最重要的意見領袖之一,試圖用自己的觀念來塑造全球公共領域的構成性規則。日本駐圣座大使上野景文認為,失去教皇國時代的世俗領土,反而讓梵蒂岡的道德權威地位得以鞏固。因為,當美國總統或印度總理就國際事務發言時,人們會把他們的言論解讀成自己國家利益的反映;而當教皇就國際事務發言時,人們就不會懷疑他是為了一國私利。通過失去世俗利益,反而提升了道德權威,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例如,本篤十六世在2007年的新年致辭中,談到了從貧困、裁軍、移民到氣候變暖,從非洲、中東到南亞的幾十個全球和地區性議題。上野評論說,如果不知道致辭者身份的話,還以為是聯合國秘書長在發言。也因此,他把教皇看作和聯合國秘書長一樣的“國際道德守護者”。在當今的全球化、信息化時代,教皇言論又能通過全球各種大小媒體迅速傳遍世界,進一步擴大了其影響范圍,強化了其道德權威的公共形象。
梵蒂岡的宗教觀念和道德權威影響的不僅僅是私人領域,通過影響大量信徒對世界的認知,塑造他們的社會認同,影響他們對自身利益的理解,梵蒂岡還能影響其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的行為選擇和政策偏好。例如,梵蒂岡關于經濟生活的教義能夠導引天主教投資者的金錢流向,關于婚姻生活的教導能夠影響天主教選民對相關立法法案的支持或者反對,等等。阿夫羅·曼哈頓認為,宗教原則直接影響倫理和社會領域,而從這些領域到經濟領域并最終到政治領域,只有一步之遙,并且,這種影響的傳遞在現實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要教會支持或譴責什么,不管它是否愿意,都會在半宗教領域甚或非宗教領域引起反響。所以,天主教會借助道德權威能在非宗教領域行使“長距離權力”。羅德尼·布魯斯·霍爾則明確將道德權威作為一種權力資源,認為教會能夠憑借道德權威把物質性的權力資源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因此,從規范性權力到現實權力的轉化是完全可能的,這就是梵蒂岡手握精神資源的要害所在。
組織資源
梵蒂岡精神資源的威力因天主教會組織龐大的規模、嚴密的結構、跨文化和跨區域的分布以及長期的持續存在而得到強化。從時間上看,封建王朝興了又亡,王國起了又滅,但天主教會仍然存在。組織的“韌性”是它的一個寶貴資產。從空間上看,由于十多億天主教徒遍布世界各國,這意味著教皇及其教會在幾乎每一種政治環境中都有制度性的存在和資源。美國駐圣座大使弗朗西斯·魯尼也認為,梵蒂岡能在很多地方和文化中有效運行,在范圍上超出了也許除聯合國之外的任何其他國際組織,而它比聯合國的影響更深、更遠,因為聯合國往往是從外部把自己強加于當地文化之上,而天主教會則總是任何一個地方內在的一部分。
天主教會還是嚴格制度化的宗教組織,實行中央集權、等級分明的“圣統制”。《天主教法典》第二編“教會圣統制”對天主教會的組織結構做了詳實的規定。教會按照地域把全世界劃分為不同的教區,或是自治監督區、宗座代牧區、宗座署理區等行政單位;然后通過一個縱向的等級鏈條(教皇和教廷—總教區/教省—教區—總鐸區—堂區—支堂/公所)把世界各地的教會聯成一個巨大的跨國網絡,而主教、司鐸(也就是神父)、執事等神職人員是這個網絡上的大小節點。
教皇和各地主教組成世界主教團,并定期召開世界主教會議,在教皇的領導下治理普世教會。主教是教區領袖,在自己的教區內擁有一切所需的、直接的職權。而主教由教皇自由任命或者批準,對于主教候選人的資格,由教皇做最后的決定。主教還要定期向教皇述職。教皇可以通過對主教的任命,來保證地方教會忠實執行自己的政策。教會的日常管理事務、國家主教會議也往往受到來自羅馬的中央權威的重要影響。平時,教皇通過教廷對各地教會行使管轄權。教廷傳統上包括國務院、九個圣部、三個法院,還有宗座理事會、宗座委員會、辦事處等。教皇方濟各上任后又增加了經濟秘書處等新的部門。教廷相當于教會的“中央政府”。由于各地主教都是特定國家的公民,有時還是所在國家國內政治進程中的重要行為體,所以,通過與各地主教的有機聯系,梵蒂岡擁有了一個影響特定國家內外政策的獨特渠道。同時,世界各地的教會之間通過主教和教皇彼此聯系,以“兄弟”關系達成共融。梵蒂岡借此可以調用其他國家天主教會的資源來支援特定國家的天主教會;同時,這種橫向的聯系也為梵蒂岡在處理不同國家之間的關系時提供了組織基礎和人員保障。另外,天主教會還是一個“超穩定”的組織:世俗國家的首腦數年就要輪替,還要討好選民,而教皇則是由樞機主教在封閉的環境下經過不斷的禱告、根據“神的旨意”最終選出的。一旦當選,他可以終身任職,并且不必討好“選民”,因為他不是通過“民主”產生的,而是“神”揀選的。而教皇任命的主教,只有到75歲才會被要求退休。所以,教皇和主教組成的治理結構具有超常的持續性和穩定性,這使他們可以在很多領域進行長期積累,形成持續的影響力。
在神職人員之外,對教皇效忠的對象還有大量的修士、修女、平信徒及其組成的機構。其中,各種天主教國際組織被視為梵蒂岡在公共領域中使用的“最有效和靈活的工具之一”。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這個由神職人員、修士、修女和平信徒們組成的廣泛而可靠的網絡,觸及世界上的每種文化和每個角落,遍布和平國家和戰亂地區,包括發達大國和貧弱小國,這給了梵蒂岡無與倫比的信息優勢,讓它能夠清楚細致地了解世界上發生的事件,有時它對事情的掌握讓美國國務院或者中央情報局都感到吃驚。這種信息優勢顯然是梵蒂岡處理世界事務的另一個法寶。
外交資源
梵蒂岡還具有其他宗教行為體所不具備的外交資源。早在現代主權國家體系建立之前,圣座就是國際關系中的重要行為體。教皇國消失后,圣座仍繼續在外交舞臺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929年成立的梵蒂岡城國使圣座又擁有了一塊小到只有象征意義的世俗領土,但它能夠保證圣座獨立于世俗政權的控制。與其他主權國家繼續維持或建立外交關系的,并不是梵蒂岡城國,而是圣座這個非領土性的主權實體。
目前,圣座和183個國家(包括地位有爭議的“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超過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它還是許多國際組織的正式成員或觀察員。因此,梵蒂岡擁有世俗主權國家享有的外交權利,在《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中,教廷大使是和其他國家大使同一等級的外交使節;在某些信奉天主教的國家,教廷大使的地位還高于其他使節,是外交團的當然團長。梵蒂岡與主權國家的外交關系,使它能直接接觸并影響這些國家的精英及民眾。而它在各種國際組織的成員或觀察員地位,也為它提供了其他宗教行為體沒有的外交平臺,能就廣泛的國際議題發表見解而不需由他人代言,從而直接影響國際公共事務決策。而作為一個主權實體,它對其他國家的外交承認能賦予該國在國際社會的合法性,所以新獨立的國家都紛紛追求梵蒂岡的認可。另外,梵蒂岡是永久中立國,而且沒有世俗的“國家利益”需要捍衛,又以促進和平為己任,所以它還經常被邀請在國際沖突中擔任調解人。
梵蒂岡有一支非常專業的外交人才隊伍。梵蒂岡的外交活動是在教皇的領導下,由教廷國務院通過下屬的“與各國關系部”進行協調。領導國務院的是國務卿樞機主教,“與各國關系部”的秘書長則相當于世俗國家的外交部長。梵蒂岡還向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派出教皇使節,其中教廷大使相當于世俗國家的特命全權大使,其主要任務是加強梵蒂岡與地區教會之間的團結,包括向梵蒂岡報告有關地區教會的情況和一切關于教會生活及人類利益的事,協助所在國主教團,并負責提名主教候選人或將候選人名單呈遞梵蒂岡等;同時在外交方面,處理教會與國家交往上的所有問題。教廷一直以來都重視外交。世界上第一個專門培養外交官的學校,是建立于1701年的宗座外交學院,幾百年來一直在為教會培養外交人才。梵蒂岡的這些精通數國語言、熟悉教會和外交事務的外交人才,是梵蒂岡在世界政治中發揮作用的重要保障。而教皇可謂教廷的首席外交官,也是教會最有名的形象大使,教皇的個人偏好、才能和風格直接關系到梵蒂岡的國際影響力。以約翰·保羅二世為例,他是歷史上最活躍的教皇,幾乎是個“永動人”。在作為教皇的9665天里,他訪問了129個國家,1022 個城市,行程超過75萬英里。教皇在全世界旅行,不僅是在訪問他的“羊群”,而且同時是進行國事訪問,通過與政府的對話、在議會的演講、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教皇能夠對擁有不同信仰和世界觀的民眾發聲,這些都大大擴大了梵蒂岡的影響力,而且實際上也是在建構一個跨文化、跨地域的全球公共領域。
結語
利用豐富的精神資源、組織資源和外交資源,梵蒂岡能對世界上不同層次的公共事務產生影響,而不僅限于國際領域,這一點是很多主權國家和國際組織都無法做到的。首先,在國家層次,由于所有國家的天主教會及其領袖都是這些國家的國內行為體,所以梵蒂岡能夠直接動員特定國家內部的社會行為體,借此影響國家的公共政策和政治進程。其次,在國家間層次,梵蒂岡可以作為主權實體直接與主權國家的中央政府打交道,影響國家之間的關系。最后,在超國家層次,梵蒂岡還經常超越國家和文化的邊界,面向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發言,試圖塑造全球公共規范。可以說,梵蒂岡具有多層行為體特征。而它的總目標主要是保護世界各地天主教會的利益,在全球范圍推進天主教會的影響,并按天主教會的觀念來塑造世界,影響人類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