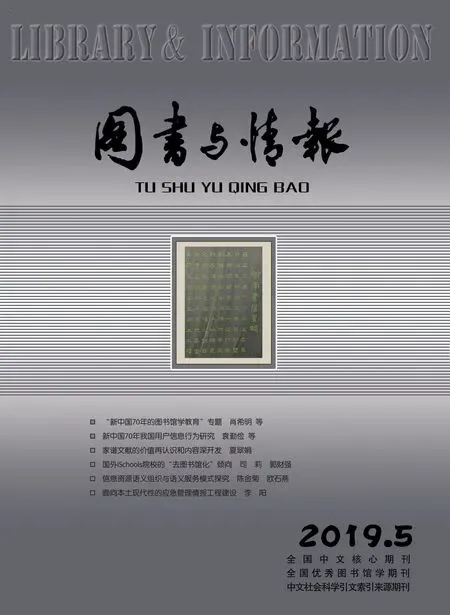厚積薄發 觸類旁通
——讀《劉瑞明文史述林》兼評劉瑞明的學術研究
方 銘
(1.北京語言大學孔子與儒家文化研究所 北京 100083)
劉瑞明教授, 甘肅省平涼市人,1934 年出生,1958 年畢業于西北師范學院中文系, 曾擔任中學語文教師十余年,后調入甘肅省慶陽師范專科學校(今隴東學院)任教。劉瑞明教授是一位博學勤奮的文史學者, 一生著述甚豐, 涉及的領域涵蓋古漢語詞匯學、敦煌學、民俗學等,其中尤以漢語詞匯學為重心。甘肅人民出版社于2012 年出版的 《劉瑞明文史述林》(以下簡稱《述林》)一書,收集了劉瑞明教授的文章413 篇,計370 余萬字。 網羅細致,篇幅宏富,比較完整地展現了劉教授一生主要的學術成果, 是我們學習和了解劉瑞明教授學術成就和學術路徑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文獻載體。
1 劉瑞明教授的敦煌學研究
1900 年,敦煌莫高窟17 號洞窟中發現了一批東漢至元代(公元2 世紀至公元14 世紀)約六萬余件珍貴文獻。 這些文獻除了佛教典籍以外,還包括經、史、子、集各類文獻,官私檔案,醫藥、天文、詩詞俗講等內容,是研究中國中世紀和中亞地區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的重要文獻。敦煌文獻發現之后,就出現了“敦煌學”這樣一門具有國際影響的新學術。一百多年以來,中外學者們在敦煌學的文獻整理方面投入了重要精力,敦煌藏經洞出土的重要文獻, 特別是佛教以外的涉及世俗社會的各種文獻,差不多都得到了關注。有些學者的目光甚至已經延伸到了敦煌出土漢簡的研究。學術研究沒有盡頭, 敦煌學研究在中國浩瀚的學術領域中,仍然屬于一門新興的學科,敦煌藏經洞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也還不可能達到盡善盡美的境地。
劉瑞明教授是20 世紀80 年代以后較早關注敦煌文獻整理的學者。《述林》這部論文集中,最能引起學術界關注的,無疑是《敦煌學論集》,這既是因為劉瑞明教授在敦煌文獻研究方面用力最多,同時也是因為敦煌文獻是20 世紀以來學術研究的顯學。 劉瑞明教授的《敦煌學論集》共收錄了25 篇敦煌學研究論文,這些文章大部分發表在敦煌學研究的專業刊物,如《敦煌學輯刊》《敦煌研究》《西域研究》《敦煌學》(臺灣)等雜志上。 劉瑞明教授的敦煌學研究,主要重心在敦煌文獻的整理方面,其中更多地是對前人校注成果的補充和完善。 這說明劉瑞明教授一直居于敦煌學文獻研究的前沿領域,也充滿了對學術真相的探索精神。 如四川大學項楚教授是著名敦煌文獻專家,所著《王梵志詩校注》一書,是項楚教授在敦煌學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收入“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 第四輯,1987 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10 年6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增訂本。 劉瑞明教授在項楚著作出版后,即撰成《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商兌與補遺》一文,分別刊于《敦煌學輯刊》1991 年第1 期,1992 年第1 期、第2 期。該文涉及對《王梵志詩校注》的補正九十余條,如《王梵志詩集序》條說“知先薄之福源,悉后微之因果”一句,項楚說:“二句言知悉由于宿世所修福緣甚薄,故今生所獲善報亦甚微也。 ”而劉瑞明認為將“果”加意解為善報“似不確”。 又如《撩亂失精神》條說“撩亂失精神,無由見家里”句,項楚引佛教凈土宗的觀點解釋,而劉瑞明認為這句話“全然不涉佛教之說”。 這些看法,大體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劉瑞明教授從事敦煌學研究,并不是為了追逐學術熱點效應,而是抱著求實的態度,踏踏實實地推進敦煌學研究的進步。因此,他的研究主要是針對過去研究的不足,糾正謬誤,拾遺補缺。西北師范大學著名教授趙逵夫先生在《述林》的《序》中,認為 “劉瑞明先生以深厚的語言學功力也從事敦煌學研究,同樣發人之所未發。 ”并舉劉瑞明所著《〈王昭君變文〉 再校議》《〈孔子項托相問書〉 再校義》等論文及對《韓擒虎話本》等的校釋成果為例,高度贊揚了劉瑞明教授在敦煌學文獻校勘詮釋方面的成就。
2 劉瑞明教授的諧音造詞法研究
《述林》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應該是第一部分《諧音造詞法論集》。 這一部分收有論文九十余篇,其中《諧音隱實示虛趣難詞與諧音文化概論》 一文可以看作是劉瑞明教授關于諧音造詞法的綱領。 “對這類詞語,筆者積十多年大量研究而發現,他們是漢語獨有的一種規律性造詞方法: 諧音趣難造詞法,用諧音的方法專門制造有趣難特點的詞語。 即把詞語真實理據的一個或幾個字,故意不用,而用同音或近音的字來代替。 故意形成理解的困難,甚或誤解,也就是隱實示虛,設難成趣。 可以稱為:諧音趣難造詞法。”劉瑞明教授的這段話雖然略顯拗口,但意思很明確:諧音趣難造詞法就是故意借用別字構成新詞,使人理解起來困難,理解以后卻覺得趣味盎然。 如“秋老虎”“羊水”“獨眼龍”“混蛋”“搗蛋”等詞,與老虎、羊、龍、蛋并沒有關系:“老虎”是“老糊”的別字;“羊水”是“養水”的別字;“獨眼龍”是“獨眼窿”的別字;“蛋”是“卵”的別字,“卵”又是“亂”的別字。 上述例子,我們過去一般都會認為是一種比喻的用詞方法,但經過劉瑞明教授這樣的梳理,則給我們又提供了一個理解這些詞匯意義及生成的新途徑。
劉瑞明教授認為,諧音趣難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詩經》的《豳風·七月》“六月莎雞振羽”和《陳風·株林》“朝食于株”等詩句。 諧音趣難詞是與通俗文化密切相關的,所以,神話、笑話、志怪、民俗、性文化中,這類詞匯非常豐富。 《諧音造詞法論集》考察的重點也在這類詞語之中, 如 “羅漢豆”“二百五”“半吊子”“拍馬屁”等一類詞語都是諧音趣難詞。 劉瑞明教授甚至考察了大江南北數十個地方方言中的諧音趣難詞,用工之勤,花費心血之巨,的確令人欽佩。
劉瑞明教授考察諧音造詞法詞匯的時候,網絡細 致,如《對 蜥 蜴100 個 稱 名 的 語 言 學 研 究》,竟然找到了100 多種蜥蜴的名稱,如“析尾”“四腳蛇”“蛇太醫”“蛇醫母”“蛇舅母”等,并論述這些詞時都是用諧音造詞法的方式建構的。又如《螳螂古今趣難系列名稱辨證通釋》一文, 對古今螳螂的諧音名稱也有深入挖掘。 劉瑞明教授的論文集《漢語諧音造詞法研究》, 曾于2004 年獲得甘肅省優秀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肯定。
3 劉瑞明教授的詞匯學研究
《述林》的第二部分是《詞義論集》,這一部分收集有論文近九十篇,涉及的內容包括楚辭的“周章”“章皇”,《詩經》的“云”字,《經傳釋詞》的“不”“丕”等助詞,以及《桃花源記》、元曲、《金瓶梅》《漢語大字典》中的一些詞匯,還有回應學者爭鳴的論文。 這些內容都是來自于劉瑞明教授日常教學中使用的教材和工具書中的問題, 劉瑞明教授只要發現其中存在有可探索的問題,就緊緊抓住不放,想方設法搞清楚本來面目。《述林》第三部分是《泛義動詞論集》,所收論文十余篇,討論了“作”“打、作、為”“為”“見”“混蛋”“神奇”“取”“行”“卻”等泛義動詞的使用特點,對泛義動詞的理論和系列性研究細致入微、拾遺補缺,使這一范疇之前近乎雜亂的語言現象綱舉目張,可以啟發我們深入理解這些泛義動詞的內涵和外延,對此類泛義動詞可謂豁然開朗,受益頗多。《述林》第四部分是《詞綴論集》,收有十五篇左右的論文,討論的是“自”“復”“持”“遲”“家”“落”“拔”“生”“日”等我們最常見的一些詞, 劉瑞明教授認為這些詞都具有詞綴功能。 劉瑞明教授這種見解,很具有獨特性,也能自成體系,自圓其說,這對于我們認識這些詞在詞尾的功能,無疑是有幫助的。
劉瑞明教授把他的主要研究精力放在詞匯學方面,他研究諧音詞,研究詞義、泛義詞、詞綴,都是他的詞匯學研究方向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古籍校勘方面,他把大量的心力傾注在敦煌文獻、元曲與元劇、馮夢龍三種民歌集等諸多方面。 他的敦煌學研究,也主要以探究敦煌文獻的詞匯釋義為目標, 且勇于探索,常言人之所避難和糾正粗心的失誤,同時,劉瑞明教授以研究詞匯學為主,又不僅限于詞匯學的研究,還更關注詞匯后面的民俗意義和文化意義。《述林》第五部分是《漢語人名文化》,既是民俗研究,又是文化研究,更是詞匯研究。 中國人的人名是包含有意義的詞匯,同時也是體現民俗習慣和文化情懷的人文符號。劉瑞明教授探討人名的主題與題材分類, 概括為愛國愛民、景仰前賢、自信自負等二十四種,同時又總結出制名方法十二種,如名含典故、連姓成義、語音相諧等,既充滿了趣味性,又有實用性,充滿了生活情趣。
4 劉瑞明教授的文學及民俗學研究
劉瑞明教授并不以文學研究見長, 但他對文學文本的關注卻是一貫的。 《述林》第七部分是《文學論集》,共收論文二十余篇,涉及的研究對象包括詩詞解詁、小說評論、楚辭等篇章分析、詞意辨析等。事實上,在這本書的其他部分,特別是研究詞匯和敦煌學的幾個部分,都有大量涉及文學作品研究的內容。而在這一部分中, 除了個別篇章的研究綜合運用了考古、義理、辭章的探究以外,大部分的論文仍延續了劉瑞明教授一向立足詞匯的研究路徑, 即把文學作品作為詞匯學研究和民俗學、 文化研究的重要素材,也有很多新見。 2005 年,劉瑞明教授在中華書局出版了《馮夢龍民歌集三種注解》一書,資料豐富,見解獨特,也是劉瑞明教授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述林》第八部分《說神道鬼話民俗》中所包含的鬼神篇、預測篇、婚喪篇、一般民俗篇,則充滿了地域民俗文化特色。甘肅隴東是先周故地,關中地區的核心區域。 在唐代,慶陽和平涼屬于關內道轄地,關內道原轄京畿地區,后來唐設立京畿道,關內道治所仍在首都長安。隴東地方的民俗,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節日、祭祀、神道教、占卜、解夢、婚喪禮俗,都淵源有自,傳承有序,但卻很少有人挖掘。 劉瑞明教授的工作,無疑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
劉瑞明教授在他的論文中,還關注到了絲路文化的倫理道德習俗。 隴山在平涼境內,從關內穿越隴山,即到隴右,唐代的隴右道從今天的甘肅天水往西,直達新疆和西亞,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主干道,而劉瑞明教授作為平涼籍人, 敏銳地注意到了絲路文化的意義,這充分體現了劉瑞明教授的學術敏感性。
5 劉瑞明教授的學術研究境界
《述林》除了附錄以外,正文共分八個部分。這八個部分的研究內容, 不但具有研究方法上的高度一致性, 即劉瑞明教授注重從日常教學工作和生活中尋找問題,并努力解決這些問題,具有很強的問題意識和創新意識,同時,各個部分的內容又是互相聯系的。表面上看起來,這八部分的分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很清晰的邏輯理路, 但這正說明劉瑞明教授研究的問題和研究問題的方法具有超越現代學科界限的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特點。 劉瑞明教授研究的問題,不是單一的研究視角所可以解決的,因此,他的這種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問題的方法,正是適應了他的研究對象。 劉瑞明教授學植深厚,見聞廣博,入乎其中,能出其外,不受學科界限的束縛,同時又始終沿著學術研究的路徑展開他的研究,因此,這些論文也是充滿了嚴肅的學術性,同時,又都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劉瑞明教授生活的地方, 學術研究環境和資料都比較匱乏,正如趙逵夫教授在《序》中所說:“但這些都并未影響到他成為一位有影響的學者。 他的文章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遺產》《文獻》《辭書研究》等刊物上刊出,也被同行專家所引用。 ”劉瑞明教授能做出如此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 是與他以學術為生活、以學術為生命的執著精神息息相關的。他的學術成就也告訴我們, 即使是在文獻資料缺乏的環境中,我們仍然可以把生活中所見所聞當作活體文獻,認真挖掘仔細研究,同樣可以做出一番成績。周奉真先生在《述林》的《跋》中說:“先生以語言學研究為基礎,四面出擊,在詞義學、古籍校勘、敦煌學、民俗學、性文學諸方面,均能考訂精審,闡發深微,觸類旁通,獨挺異姿,度越前修。縱觀先生,其涉世之深,學養之富,厚積薄發,迥異于同代諸學者矣。”雖然學術環境艱苦,研究資料也相對匱乏,但劉瑞明教授對學術研究的熱情和數十年堅持不懈的精神更值得人學習。 正如周奉真先生所說:“先生學術成就自然是辛勤耕耘的結晶。 繁忙教學之時,可頤養天年之期,在由發表文章得稿費轉變成不交費而‘不售’的情況下,數十年不輟撰述。 但若方法不科學,也會勞而無功。先生的方法是非常值得借鑒的。但卻也不是什么奇特偏方,仍然是常理之法,可謂‘執經燭機’。經,即經線、經典之經,即最基本的準則。 機,即關鍵或規律。 從基本準則而發現關鍵或規律, 這是眾人皆知的。 劉先生貴在于堅持。 ”正因為劉瑞明教授對研究的一腔熱愛,使得他能夠沉下心來做學問。而劉瑞明教授的堅持也有其自己的準則,“先生所堅持基本準則之一:遇到有疑難的詞義,首先應堅信而堅持常義,而不宜輕說新義。 堅持常義,相對來說是局部問題, 而立新義則涉及全局……先生所堅持基本準則之二:例不十,法不立。 辭書與有些文章用孤例或少例立詞的新義,先生否定所謂新義或自己立新義,都是用極多的例句來證明。 趙元任當年評審王力畢業論文的名言:‘言有易,言無難’。 毛澤東說:‘對敵傷其十指, 不如斷其一指。 斷其一指, 還要斷其十指’。 先生把此用到語言研究,說‘清理就要徹底,要打殲滅戰’。 ”體現了先生對學術研究的嚴謹態度和其不斷求知的鉆研精神,另其博聞強識,他的學術成果,正是他厚積薄發所得,深刻地體現出他中心突出、觸類旁通的學術研究境界。
當然,每一個學者都有自己認識的盲點,劉瑞明教授也不例外。 劉瑞明教授用力刻苦, 涉及領域廣泛,但卻難免有智者千慮之一失。他投入大量精力闡釋的諧音詞問題的研究,也存在部分可商榷之處。如他在解釋《陳風·株林》“朝食于株”的時候,把“朝食”這樣一個在春秋時期指向非常清晰, 并且在今天的日常用語中還是一個常語的詞語解釋為諧音趣難詞,其說服力無疑是不充分的。 此外,由于劉瑞明教授的研究內容太過豐富, 而且比較關注日常方言俗語, 這也導致劉瑞明教授的學術語言偶爾有隨意性現象。白璧微瑕,然瑕不掩玉,從先生的文學研究中,能深刻感知其對古文義的熱愛, 對學術研究的求精求知精神。 先生著書立作,半生奮筆不輟,其豐富的個人學術成果為后人研究探索打下了夯實的基礎,值得探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