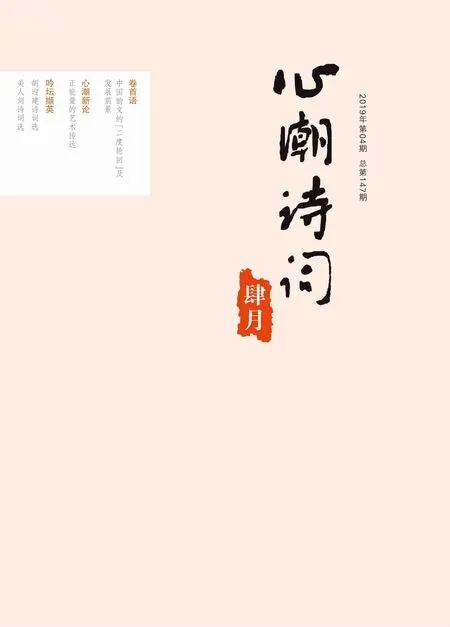惟俏是求
劉立玉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這首《卜算子·詠梅》一經問世,便風靡寰宇,膾炙人口,穿越時空,歷久彌香。難道僅僅因為它是偉人之作而寶之貴之乎?非也。
竊以為,姑且不論其鮮活、敏銳、深邃的政治性、思想性,單就其嫻熟的藝術手法就足夠令人佩服,尤其是一個“俏”字在兩闋間的首尾銜接,交集疊用,便妙不可言,令人拍案叫絕。
俏,集俏麗、俏皮于一身,端莊而不呆板,活潑而不輕佻,聰慧而不賣弄,“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者也。俏,出于美而勝于美,寓于巧而高于巧,正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冰生于水而寒于水。是否可以這樣說,好的詩聯不一定是俏的,但俏的詩聯必然是好的。
俏無止境。古今中外,人們對俏的追求從未止步,文人尤甚。賈島的“推敲”成千古美談,為俏而苦心推敲者,正不知幾何。眾所周知的王安石瓜洲詠詩,在確定“春風又綠江南岸”之前,曾擇字若干,已是經典的案例。“春入船唇流水綠;人歸渡口夕陽紅”,為了工對此聯,估計東坡先生必然是煞費苦心,最終拈一“唇”字,形象生動。為補“林花著雨胭脂□”這一“天窗”,蘇軾黃庭堅等四位名士各抒心機,分別填充為“潤、老、嫩、落”,各有千秋,似均無不可。那么,原作到底如何?遙想當初,杜甫也許一一嘗試過上述四字,甚至更多,結果呢?居然另辟蹊徑,最終選定一個“濕”字,出人意料,卻更為妥貼。——詩圣不愧為詩圣,畢竟技高一籌,難怪為四大才子折服。五代南唐江為的“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經北宋的林逋將“竹、桂”二字易為“疏、暗”,俏味倍增。諸如此類,在歷朝歷代,只不過滄海一粟,不勝枚舉。
至若現代,有佚名者《挽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聯:
身經白刃頭方貴;
死葬黃花骨亦香。
可謂字字珠璣帶血淚,感天動地泣鬼神,其構思縝密的悲壯之俏無與倫比。
無心作詩人而偶有所作的魯迅,有《所聞》詩云:
華燈照宴敞豪門,嬌女嚴裝侍玉樽。
忽憶情親焦土下,佯看羅襪掩啼痕。
一個“佯”字,迸射著強忍悲憤的俏的靈光。
至若當代,求俏競俏者更是趨之若鶩,屢見不鮮。有一首七絕《漁村》,結尾云:“雨后游魚天上□,蛙聲□出彩虹來。”填何字最佳?先后以“擠”與“抬”,鑲嵌其中,假中見真,趣中取境,新穎別致,別無替代,恰到好處。“燕翼飛梭,織成中國夢;春光釀酒,醉了小康年”(趙金龍),尋常字,巧搭配,合時事,春聯生俏味,金獎實至名歸。為詩聯者,其遣詞造句,倘如港珠澳大橋海底隧道沉管,絲絲入扣,分毫不差,渾然一體,穩穩當當,這便是世人嘆為觀止的訣竅。
毫無疑問,毛主席的《卜算子·詠梅》,就是一座美輪美奐、卓爾不凡的“大橋”,他用擬人手法,以一個“俏”字提挈全篇,“于莊嚴中寓輕松,于嚴謹中有跳蕩,于明快中富含蓄,于流暢中見豐厚”(石英),把他終生心儀有加的梅花,這個百卉之神、百卉之膽的美,寫得如此俊逸,如此機智,趣味橫生,給了千千萬萬讀者一個“俏”的詮釋,“俏”的洗禮,“俏”的饕餮盛宴和“俏”的深刻啟迪。
俏,人之所好,誰不愿得?固然,“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這里,第一是“妙手”,而非庸者;第二是“偶得”,而非常態。如果沒有堅定正確的政治信仰,沒有孜孜以求的真善美思想修養,沒有日積月累的博古通今的藝術涵養,也只能是做夢吃仙桃——想得甜。詩聯之道,容不得投機取巧,須雪地上拉車,一步一個腳印;像老燕子壘窩,一口一點泥團。毛主席早有明示:“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俏,亦我之所好,曾撰聯一副,是用來祝賀洪湖市一詩聯分會誕生的:
詩以童貞吻綠新灘鎮;
聯將巨擘捧紅開發區。
該鎮名新灘鎮,是武漢洪湖共管經濟開發區,分會首次成立,以“詩聯”冠首,開宗明義,特意用“童貞吻綠”,并著墨“巨擘捧紅”,——取“江山也要文人捧”之意,二者烘托氣氛,標明使命,亦欲爭得一點“俏”味。但愿不是畫虎類犬。
凡事皆有度。真理與謬誤只半步之遙。“俏”不會從天而降,唾手可得。千錘百練,字斟句酌是必須的,但并不是刻意雕飾,故弄玄虛。倘一味追求個別字句之俏,不過雕蟲小技,勢必脫離“群眾”,弄巧成拙,有傷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