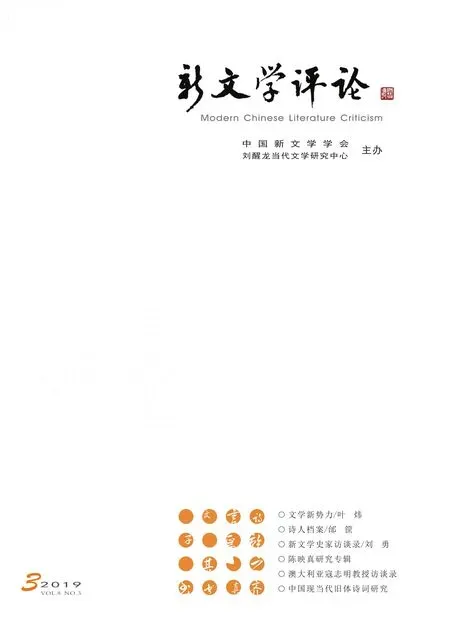從南海到長江
——劉醒龍近期散文的景觀書寫
□ 王 泉
在讀者眼里,劉醒龍是小說家,他的小說關注底層生活,凸顯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其長篇小說《天行者》獲得過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在全國影響廣泛。其實,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他就有不少散文作品問世。他在2016年和2017年創作的《南海三章》《上上長江》等散文從現場出發,融會歷史與傳說,以豐沛的感情書寫祖國的大好河山,突出了文學景觀的審美內涵。
一、 生態景觀書寫
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因地質和氣候變化不同,形成了千差萬別的地貌。南海作為自然之海,其優美的生態常引發人們的無限遐思與家園暢想,也產生了許多佳作。從古代詩人曹松的《南海》到當代詩人李瑛的詩集《南海》和樂冰的《南海,我的祖宗海》,南海無不維系著詩人的家國情懷。
在《南海三章》里,劉醒龍從漁民、水兵與南海須臾不可分離的關系想到了水的神圣及海洋生命的博大。“用不著太多,只要看見一只玳瑁在南海中蹁躚的樣子,就會明白幸福為何物。只要看見一只手從南海中悠然伸起來,將一件物什放進水面漂著的容器里,就會懂得如何收獲。雷電肆意暴虐,海鷗在抒發自由。”海洋生命的個體是如此的逍遙自在,當地的人們最懂得知足常樂。面對南海,劉醒龍展開了無限的遐思,他思考著南海與大陸、天空的相互映襯,思考著南海作為人類生命共同體中不可或缺的一員的重要意義。而南海邊的各種花草和椰子樹,則讓他想到了萬物之間共生共榮之理。藍洞的奇妙又讓他思考著捍衛家園的神圣使命與人倫的價值,甚至故土情懷。“文學是人的一只慧眼,專門用來看肉眼看不到的事物,存在的、可能存在的和根本沒有存在過的,都在其視野中。在文學中,理想主義者的靈魂是悲憫,浪漫主義者的骨子是真實。”面對南海,劉醒龍不僅看到了自然生命的千差萬別,而且看到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
自然之美始于生命的勃勃生機,而所有的生命都離不開水的滋潤。水滋潤大地,才有了多姿多彩的世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語),人類的生產與生活離不開水,人類的美也離不開水,水一旦進入審美的視閾,就成為言說不盡的話題。劉醒龍說過:“我從啟蒙到上高中,之后走向社會,整個成長時期一直待在山區。但我與其他山里孩子不一樣,走到哪里,都會對水有種特別的執著。”正是這樣的戀水情結促使他對南海和長江一往情深。南海的廣袤與深沉釋放了劉醒龍的豪情,當他第一次來到三沙時,就被她的慷慨所吸引,這是大別山之子走向真正的大海的開始。劉醒龍從南海的自然生態中感受到神圣的美,實現了從地理到心理的轉化。同樣,在他的長篇散文《上上長江》中,這樣的轉化變得更加多彩。
劉醒龍面對長江,倍感自豪與自信:“看一眼與長江日夜同在的漁翁,再看一眼從遙遠北方而來的黑天鵝,這樣的長江,比海洋還美麗。”這不再是柳宗元筆下“獨釣寒江雪”的漁翁,而是與滾滾長江同呼吸的漁民,這是長江漁民的真實寫照。翩翩起舞的黑天鵝,預示著新時代的氣象,而水文工作者老蒲則是這美麗家園的守望者與維護者。人與自然生命儼然融為一體,成為21世紀生態文明的審美表征。
他驚嘆于虎跳峽的鬼斧神工:“在虎跳峽里,天空是一種奢侈品,天空空闊無邊的權利被剝奪了,不再屬于天空,也不屬于比天空空闊的峭壁,更不屬于超越天空擁有源源不斷來水的流響。天空成了碧玉做的,琥珀做的,鉑金做的,成了一枚枚手指上的掛件。”這里寫出了一線天的險峻與自然天成,突出了其觸手可及的天然美。
動物是人類的朋友,但在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支配下,野生動物慘遭毒手的事件時有發生,導致了人類原生態家園的逐漸消逝。這不僅引起了環境保護工作者的警覺,也激發了作家的創作熱情。21世紀以來,涌現出《懷念狼》《藏獒》《狼圖騰》等關注動物生命狀態的作品。劉醒龍的《上上長江》以實地考察的方式,書寫動物的傳奇,帶給讀者不一樣的感受。
在青海玉樹,他一邊欣賞著長江源的美景,一邊品味著藏族人對于麝香的偏愛,繼而追尋麝香的神奇,彰顯了一個漢族人對于藏族文化的好奇心理。雄麝的分泌物轉化為人眼里的神奇藥物,這本身就說明了人類對于野生資源的渴求,但麝香往往通過犧牲雄麝的生命來獲得,人的自私與殘忍可見一斑。這是人與動物不和諧的一面,作家審視這種現象,表明了他對世俗的批判精神。
在通天河,他寫自己與一匹狼的遭遇,突出了狼性與人性的不同以及狼的高貴,表現出對于生態家園的渴求。誠然,狼有領地意識,在它的地盤,它可以漠視人的存在,但它不會像人那樣把自己視為萬物的主宰,它只是在適者生存中維持種族的繁衍。
他從黑頸鶴成雙成對的生活中看到了其自我保護意識,從藏羚羊的遷徙中看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他從藏族老祖母送給自己的孫女一只出生才三天的小羊羔作為將來的嫁妝的故事中領略出藏族人的智慧。在青藏高原的高寒地帶,自然生命沒有退化,反而變得更加堅強,這是自然界給予人類的啟示。
總的來看,劉醒龍散文中的水意象和動物意象,是具象與抽象的統一,包含了他對于人類自身命運的思索,具有普適價值。正如鄒建軍所言:“自然之美是具有超越性的,人類社會的任何成員,不論他們的文化傳統存在多大的區別,不論他們的社會制度有多大的不同,然而他們對于自然山川的美會有同樣的或相似的認識,對于地理的認知也會具有相似性,美之為美,丑之為丑,差別不會太大。”可見,對自然地理的感知成為作家審美感知的一部分,是由自然本身的特征所決定的,即客觀的物象制約著作家主體性想象的生成與審美情感的凝聚,并因此形成作家的審美風格。或壯美,或優美,都與自然物象本身的特質密切相關。南海與長江賦予劉醒龍一雙探知自然奧秘的銳眼,他游弋在江海的世界里,與自然對話,叩問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之道,呼應了全球化時代的生態主義訴求。
二、 歷史與記憶景觀書寫
歷史與記憶不可分離,“記憶作為一種內部視角是不可或缺的,它能對過去的事件進行評價,并形成一種道德立場;歷史作為一種外部視角同樣不可缺少,它能對記憶中的事件進行檢視和驗證”。歷史與記憶是個人的,也是民族的。當一個作家以自己的視角看待歷史與記憶時,其作品就有著明顯的個人色彩。任何歷史與記憶都發生在一定的時空里,通過作家的呈現,就成為一種文學景觀。如果說劉醒龍的《一滴水有多深》書寫的是其故鄉的歷史與記憶的話,那么,他的南海與長江書寫則走向了更為廣闊的領域。
南海是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中轉站,留下了許多關于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故事、神話與傳說,同時它地處國際交通的要道,成為周圍國家和地區博弈的焦點。如何書寫南海的歷史與記憶,不同的作家會有不同的取舍。張永枚的《西沙之戰》寫戰事,以豪邁的激情見長。劉醒龍的《去南海栽一棵樹》,側重于個人記憶。他在2004年12月底與陳忠實在三亞相識,并共同栽種了一棵樹,這既是二人友誼的象征,也見證了南海在作家心目中的神圣。作家書寫這樣的記憶,喚起人們對于已故作家的深深懷念。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友誼之樹常綠。
在劉醒龍的眼里,童年時的長江是在母親的懷抱里目睹的,記憶是模糊的。青年時見到的長江,則點燃了他對未來生活的希望。南京和鎮江作為長江沿岸的重要歷史文化名城,成為文人筆下的文學景觀。朱自清筆下那含情脈脈的秦淮河,銘記的是詩人的幽思。劉醒龍從歌曲《茉莉花》的誕生談起,他以李清照的愛情故事、甘露寺中的丈母娘和金山寺前白娘子的傳說,演繹出江南茉莉花的傳奇。“小小茉莉,小鎮江南,豐盈的不只是柔情,還有絲絲入骨的大雅大善大理大義。”江南的物產豐富,小小的茉莉花連接的不僅是江南秀麗的風光,而且維系著一個民族執著的家國情懷。
在采石磯,劉醒龍感懷于李白的浪漫人生,品讀著歲月的無情。在小孤山,他聚焦黃梅戲的歷史與傳說,并從宿松的口頭禪里演繹出當地發達的民間藝術以及自然美景與人文風情的相得益彰。在三峽,他迷戀的是王昭君出寨前香溪里的一滴淚、老船工撐船前行時的穩健步伐以及三峽大壩的雄壯,在古與今的對照中感嘆著人間的巨變。在涪陵,他聚焦石魚的傳說,談及傳奇小說、杜甫的詩,凸顯該地域的詭異與多變。在合江,他從這里盛產的荔枝聯想到民間的荔枝保鮮法和蘇軾的詩句,道出了蘇軾的真性情。在遍布化石的云南元謀,他從當地孩子們用石頭取火的古老文明中探尋著人類進化的蛛絲馬跡。在納西族小鎮石鼓,劉醒龍追溯中國工農紅軍四渡赤水的傳奇,凸顯對于英雄的敬畏。
不難看出,劉醒龍書寫關于南海與長江的歷史與記憶,匯聚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傳統,凸顯了地域文化的豐厚性。同時由此及彼,折射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這樣的書寫,使得其筆下的歷史與記憶景觀呈現出立體感。
三、 哲理升華
一般而言,在各種文體中,詩歌以抒發情感見長,小說以精巧的結構凸顯故事的魅力,優秀的散文以情貫穿其中,凸顯哲理,往往給人智慧與思想的啟迪。周作人、林語堂、豐子愷的散文以知識性和趣味性取勝,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化散文的基石。劉醒龍受到前輩作家的啟發,主張“好的散文一定要懂得心痛,一定要發現仁愛,一定要有從靈魂深處噴發或者流淌出來的感懷情愫”。他的近期散文是他體驗生活與感懷于心的必然結果。
在《南海三章》里,劉醒龍道出了海洋的哲理:“一棵椰子樹就能消解生存的絕望。礁石再小撐起的總是對大陸的理想。水霧再輕亦是甘霖對酷暑的普降。”這是生存之道,也是對海洋的敬畏,又不乏人生的思考。



散文之美,美在那種直擊心靈的頓悟。劉醒龍沒有沉迷于南海和長江的風光之中,而是在從歷史的塵埃與現實的生活情境出發,探尋著水對于生命和人生的意義,痛擊了當下一些人欲望的膨脹。因此,他在記人敘事時常常激情澎湃,自然灑脫,突出了思索的痕跡。
結 語
地域文化是在長期的歷史沉淀中形成的比較穩定的文化,書寫地域文化離不開自然地理,更離不開人文因素。縱觀劉醒龍筆下的南海與長江,筆者發現,他在書寫二者時,總在思考人存在的意義及人與自然的淵源,突出了其散文的鮮明特色:寫水,善于從水的變化中思考人性的變化;寫人,突出了不同地區的人對于自然的領悟;書寫歷史與記憶,不局限在歷史與記憶本身,而是通過現實同歷史與記憶的對照,聯想到個體的價值與民族的未來。因此,自然的地理空間與作家的心理空間相交織,成為詩性的空間,這使得這些散文成為21世紀文化散文的重要收獲。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湖南省社科成果評審委員會項目“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絲綢之路’沿線景觀書寫”(XSP18YBC245)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注釋:
①劉醒龍:《南海三章》,《人民文學》2016年第11期。
②劉醒龍、劉颋:《文學應該有著優雅的風骨》,《文藝報》2016年8月10日。
③劉醒龍、張屏:《一萬里,上長江》,《文藝報》2018年3月28日。
④劉醒龍:《上上長江》,《人民文學》2017年第10期。
⑤劉醒龍:《上上長江》,《人民文學》2017年第10期。
⑥鄒建軍:《江山之助——鄒建軍教授講文學地理學》,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頁。
⑦阿萊達·阿斯曼著,陳國戰譯:《歷史、記憶與見證的類型》,《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⑧劉醒龍:《上上長江》,《人民文學》2017年第10期。
⑨劉放:《作品不在大小,在于刻骨銘心——劉醒龍訪談錄》,《姑蘇晚報》2014年6月9日。
⑩劉醒龍:《南海三章》,《人民文學》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