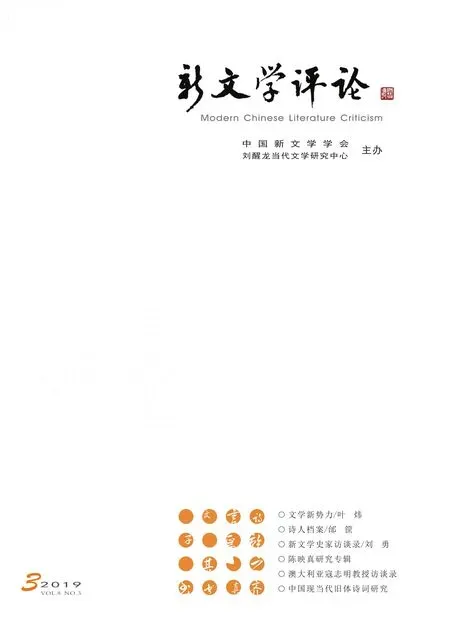趙南棟之殤
□ 李廣益
當我還是一個小學生的時候,每年11月27日,學校都會組織我們去歌樂山下的烈士陵園,為重慶解放前夕被國民黨當局屠殺的革命烈士掃墓、獻花。山城的秋天總是陰冷而多雨,青松翠柏環繞的墓地此時越發肅穆。我們在雄偉的“紅巖魂”雕像前列隊、敬禮,然后繞墓一周,將自己親手制作的小白花投入圍欄。凄風冷雨中,層層疊疊的花朵瑩白而純凈。
雖則行禮如儀,孩子們并不能充分理解犧牲和紀念的意義。對于我來說,最深刻的記憶是面對那座埋葬著三百多位烈士的墳塋的恐懼,以及在紅巖魂陳列館中看到一具火焚殘軀的照片后的驚駭,后者是我童年時代許多噩夢的源泉。年復一年的掃墓持續著,直到中學不再組織對紅巖烈士的祭奠。二十多年來,烈士墓的意義不斷發生著變化,既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也是重慶的一張文化名片,乃至“紅色旅游”的資源,其間既有《紅巖》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熱映于大江南北的風光,也不無過度開發之弊。然而,紅巖終究是紅巖,無論怎么包裝依然沉重,依然凝聚著對生與死、信仰與自由、革命的意義等一系列命題的追問,撥動著人們蒙塵的歷史心弦,無法被但求輕快的消費欲望收編。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習慣于用“美食、美女、美景”向外地朋友推介重慶,而避免提及白公館、渣滓洞這類“政治性”名勝。這并不只是時代氛圍的潛移默化,也和幾次被斷然拒絕的尷尬有關。間或來客有回首歷史的愿望和定力,他們想看的,我會帶他們去的,也是另一處陰森的歷史所在。
對紅巖的所知所感漸漸沉入記憶深處,直到負笈海外時的一堂討論課。這堂課的討論主題是《紅巖》這部發行量逾千萬冊的“紅色經典”,但教授和選修課程的同學們都對產生《紅巖》的歷史語境不甚了然,進而對黑白分明、善惡斗爭的敘事或冷漠視之,或出言不遜。唯一曾經身臨紅巖的我,卻不知該如何為這個文本辯護。在《紅巖》講述的年代,共產黨人的忠誠和犧牲,比小說的追思更加動人;在講述《紅巖》的年代,用文字樹立的豐碑浸潤著國家意志,體制運作的痕跡顯而易見,革命者的理想和信念在章法井然的傳頌中反而漫漶難辨。失語的憋屈和困惑,多年后讀到《趙南棟》時才得以紓解。我看到,自己那些壓抑良久、難以言表的情感,都在陳映真的真摯、深沉而熱烈的筆下流淌出來,一時感慨莫名。
小說的開頭,1984年的秋天,曾被囚禁二十五年的趙慶云,在病榻上奄奄一息。敘事從這里開始,不斷閃回到革命者蒙難的1950年代初,趙慶云被“特赦”釋放的1975年,以及他的兩個兒子趙爾平、趙南棟兄弟的成長經歷和現實處境。在大肆搜捕、屠殺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的白色恐怖中身陷囹圄的趙慶云,出獄時發現臺北已經是一座截然不同的城市。無獨有偶,同樣困于縲紲多年的葉春美回到故里的最大感受是:“在她不在的二十五個寒暑中,叫整個石碇山村改了樣,像是一個邪惡的魔術師,把人們生命所系的一條路、一片樹、一整條小街仔頭完全改變了面貌,卻在人面前裝出一副毫不在乎、若無其事的樣子。”身為“鄉土文學”主將的陳映真,借由左翼孑遺的滄桑之眼,再次道出了對自矜經濟騰飛的這段歷史的不滿。人生如戲,但在劫余歸來的趙慶云眼中,社會舞臺上已經沒有自己的容身之地:
“主要是,整臺戲里,沒有我這個角兒,我也沒有半句詞兒,你懂嗎?”他說,“關了將近三十年,回到社會上來,我想起那一臺戲。真像呢。這個社會早已沒有我們這個角色,沒有我們的臺辭,叫我說些什么哩?”
趙慶云用戲劇來喻指自己的困境,這讓我不禁想起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中對憤世嫉俗者的規勸:
有一種哲學,深知自己活動的舞臺,能適應要上演的戲,并巧于扮演須擔任的角色,這種哲學對政治家更合于實用。這是你必須采用的哲學。不然,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當普勞塔斯的喜劇演出時,一群家奴正在臺上彼此即興打諢,你卻披上哲學家的外衣走上舞臺,朗誦《屋大維婭》悲劇中辛尼加對尼祿皇帝的爭辯。如此不合時宜的朗誦,把一場戲弄成又悲又喜的雜燴,那豈非扮一個啞巴角色還好些嗎?你會使一場演出大殺風景,如果你摻入不相干的東西,縱使這些東西從其本身說價值更高。不管您演的是什么戲,要盡量演好它,不要由于想起另外更有趣的戲而把它搞壞了。
這是改良的主張,前提是心存不滿的思想者還能走上前臺,附和或沉默不致消弭他的存在,他還有機會改寫劇本,至不濟尚可作“不合時宜”的黃鐘之鳴。趙慶云、葉春美等人卻難有機會伸張心底的信念和哲學,只能追憶自己在多年前的時代悲劇中曾經扮演的角色,“最激蕩的歷史、最熾烈的夢想、最苛烈的青春,和狂飆般的生與死”。
他們在五十年代退場,對社會這出大戲有何妨礙呢?得益于美援扶持也罷,受惠于越戰供給也好,臺灣究竟實業大興,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在世界舞臺上光鮮閃亮。沒有他們,這個豐饒富足的現代化社會豈不是更加安穩嗎?
答案蘊藏在革命后代的人生中。幼失怙恃的命運使得趙爾平學習英文,目的不是教書育人,而是抓住機會進入更能出人頭地的軌道,他最終如愿以償地成為德國Deissmann大藥廠的業務代表。兩年后,“Deissmann要在臺灣上市一種全新的,據說是長效、安全,卻尚未通過美國F.D.A.核可的止痛消炎劑,特地從香港派了當時的國際行銷工作負責人Martson先生來臺灣,做密集的推銷訓練”,英文出色的趙爾平把握了這樣的“機遇”脫穎而出,成為業務經理。這不啻為巨大的諷刺:父母為了自強自立的中國和人民大眾的福祉而獻身,兒子卻成了跨國資本唯利是圖、戕害人民的買辦。也正因此,趙爾平可謂臺灣社會的具體而微:脫離革命的羈絆,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依附經濟中找到了通向現代化的門徑。收獲豐厚,“換了車子,換了辦公室,也換了一間臺北東區又貴又大的房子”,代價卻也沉重。道德操守在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和生活方式面前的退讓,并不僅僅發生在工作中。“就這樣,趙爾平步步為營地,滑進了一個富裕、貪嗜、腐敗的世界。他對金錢、居所、器用、服飾和各種財貨的嗜欲,像一個活物一樣,居住在他的心中,不斷地肥大。”很快,他的歡場流連,導致了家庭的破裂。趙爾平相信自己還沒有沉迷女色,卻也不得不承認,“除了這一點,他的少年時代對進德修業的生命情境的向往,于今竟已隨著他勠力以赴,奔向致富成家的過程中,崩解凈盡了”。
對父親的溫情,成為自知墮落的趙爾平努力抓握的一根稻草。他在繁重的工作中幾乎每天都抽時間來探望住院的父親,以此“現代社會的現代人”中“難得的孝行”,被人交口傳頌。然而,聯結父子的,并不僅僅是血緣關系。三十年來大部分時間不在身邊的父親,是支撐趙爾平去生活和奮斗的“中心”;盡管他不理解父親的民族情懷和革命理想,這間凝聚著一代革命者痛徹心扉而又永不悔恨的生命記憶、散發著信仰的圣潔光輝的臨終病房,成為趙爾平反省和懺悔的場所。他收受經銷商賄賂一事被人告發,不得不拋下父親,和同伙連夜部署,消滅證據,制作假賬,最后僥幸過關。在“荒蕪的三天”之后,趙爾平重返醫院,發現父親已經陷入彌留。準備陪伴父親度過最后時光的趙爾平“看著那干燥、潔凈的行軍床,忽然感到三天來不曾回去洗澡的自己的齷齪”。這自然是一個隱喻:在骯臟的生意場上摸爬滾打的他,在即將逝去的父親那清潔的思想和人格面前,自慚形穢。
趙爾平的沉淪,無疑是一個在經濟的迅猛發展中物欲橫流、道德失范的社會在個體身上的投影,但“去革命”的影響并不僅僅由他來彰顯。趙爾平和趙南棟雖為兄弟,卻像是兩代人,前者是現代社會的象征,后者是后現代癥候的集合體。通過趙南棟,我們看到了現代社會的弊病將如何延伸、變異。
陳映真幾乎沒有提到趙爾平的外貌,卻不厭其煩地一再描摹趙南棟的“秀美”,顯然有其深意。“大而清澈的眼睛;朱紅的,小小的嘴唇,笑起來就露出一排細細的白牙齒;深黑柔軟的頭發……”,“兩道濃而粗健的眉毛,一對有些女性化的,在下眼瞼躺著兩小條臥蠶的眼睛,經常漾動著某些絲毫不知道心機的純粹和溫柔”。趙南棟“出奇的”,“日甚一日的”,甚至因其對任何年齡段的女性都具有的超強誘惑力而顯得迷離恍惚的“秀美”,以跡近超現實的方式喻示著某種優良基因的傳承,但出生在獄中、得名于監舍的他,并未得到父母的后天教養,其女性化的“秀美”和老照片上的青年趙慶云的“方臉”、“不遜地往后梳著”的頭發、“緊緊地、認真得有些叫人發喙地抿著”的嘴唇、“向著鏡頭逼視”“顯得特別的精神”的雙眼所構成的剛毅、硬朗氣質之間顯而易見的張力道出了父子之間的斷裂。趙慶云追求的是國家獨立、民族尊嚴,趙南棟卻連個人的自立都無意為之,從小馴良地跟在哥哥身后,以至于趙爾平覺得,“如果弟弟不依附著他,仿佛就無法存活了”。趙爾平尚有成家立業、撫育幼弟的抱負,并據以奮斗,趙南棟則根本無所適從,學業荒廢,浪蕩人間,如同一縷漫無歸宿的游魂。
小說很有意思地借趙爾平之口強調,趙南棟的本性是“善良”的:“他喜歡吃,喜歡穿扮,喜歡一切使他的官能滿足的事物。但他不使大壞。他不打架,不算計,不訛詐偷竊。”其實,“大壞”和“大好”一樣,都需要勉力為之,也就是生命力的噴薄,而趙南棟的旺盛官能底下,是無法掩蓋的虛無。根本上,他是一棵還未茁壯便枯萎了的小樹。用趙爾平的說法,“整個時代,整個社會,全失去了靈魂,人只是被他們過分發達的官能帶著過日子”,但弟弟和自己還是不一樣,因為前者會赤裸裸地表達和追逐欲望,“一點也不掩藏”。吊詭的是,由于這種欲望極為浮淺,趙南棟無法將之固著于特定對象:“舉凡一旦得手的,不論是人和物品,他總是很快地,不由自己地喪失熱情。”與之相應的是主體深度的缺乏——四個主要人物中,唯有趙南棟的心理活動,小說不曾描寫,或者說沒有那個必要。
陳映真設置了一組有趣的人物組合,即趙家兄弟和莫葳、莫莉這對姐妹。姐姐莫葳在被趙南棟魔咒般的熱切眼神俘獲后,為之瘋狂,以至于在他遭陷害鋃鐺入獄后不離不棄,花大錢請律師幫他上訴減刑,趙南棟卻故態復萌地移情于代替當空姐的莫葳探監的妹妹莫莉。可是,即便是飛翔于世界各地、對“旅人之戀”司空見慣、又在趙南棟身上傷了心的莫葳,仍然要嫁人走入家庭,這使得她能夠以面對同類的姿態告訴趙爾平,你的弟弟和我的妹妹是同一類人,“他們按照自己的感官生活……是讓身體帶著過活的”。莫莉的出現讓趙南棟不再是孤立的個體,而成為一群乃至一代青年的心靈之鏡。但趙南棟仍有他的特異之處。莫莉除了官能容易麻木之外,最大的疾病是“不能愛”,趙南棟恰恰相反,他對每一個女子都能真心去愛(雖然無法持久),以至于風塵女子也能從他這里得到溫暖。這種驚人的博愛,和他的俊秀外表一起,成就了趙南棟形象的“純粹”。正是這種純粹,和“趙南棟身上復雜的虛無”一起,像陳光興說的那樣,“讓他表面上看來充斥著富裕時代人們的膚淺,但是骨子里是左翼大失敗的結果,底色是紅的,只是脫落了思想的內涵”。
大陸讀者很容易感到,《紅巖》和《趙南棟》之間存在著某種對應關系。趙家兄弟的母親宋蓉萱飽受酷刑而堅貞不屈、沉靜赴死,和江姐有幾分神似,“長得小而且分外的結實,像個臺灣野番石榴”的“小芭樂”(獄中姐妹對趙南棟的昵稱)也讓人想起“小蘿卜頭”,臺北的共產黨人在就義前高唱的《赤旗歌》更是遙遙呼應著響徹重慶的牢獄和刑場的《國際歌》。但也正是這樣的對比,讓我們進而思考,革命勝利之后,歷史又將會如何曲折。趙南棟的精神夭亡可以歸咎于白色恐怖斬斷了他從父母的斗爭歷史中汲取養分的根須,革命理想在大陸的衰退卻是更加復雜的問題。在獄中就參加了革命斗爭的“小蘿卜頭”宋振中倘若幸免于難,應該不至于變成趙南棟那樣的人,但他的兒孫就難說了。在一個擁抱“現代化”、見證了遠比“亞洲四小龍”更為宏偉的經濟奇跡,與此同時又“告別革命”,將犧牲、理想、信念“博物館化”,或棄置于迢遙的“革命年代”,或植入非空洞即重新闡釋的“愛國主義”的社會,趙南棟式的虛無并不鮮見,我的不少90后學生都能在這個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在這個意義上,《趙南棟》不僅和《山路》《鈴鐺花》等作品一起構成了陳映真接續臺灣左翼精神傳統、唱起挽歌撫慰白色恐怖死難者及其親人的努力,還以1980年代臺灣社會尤其是青年狀況的真切寫照,為他念茲在茲的中國大陸留下了未雨綢繆的箴言。20世紀50年代的臺共黨人之所以“死而無憾”,是因為“又找著了中國”,這中國自然是海峽對岸在他們心目中代表著光明、解放和希望的人民共和國。“心懷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臺灣,籍不分大陸本省,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在監獄中繡出五星紅旗的紅巖烈士亦有這般歷史音容。但沒有遺憾,不等于沒有擔憂。難友中知識淵博、洞燭機先的蔡宗義,早在朝鮮戰爭爆發后便意識到,歷史已經“暫時”改變了它的軌道,共產革命在臺灣的勝利不會很快到來。然而,讓老蔡憂悒的,尚只是冷戰世界格局造成的國家分斷乃至民族分裂,八十年代的陳映真則要面對大陸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和困頓,徘徊太息。為了安頓自己的身心,他必須正面和妥當地回應(而不僅僅是提出)《山路》和《趙南棟》中以不同表述方式反復出現的關鍵問題:社會主義中國的危機重重,是否意味著革命者的前仆后繼被歷史證明為無意義,甚至被誤認為是誤入歧途?
受制于特定時代的歷史真相所導致的心靈創傷,陳映真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功過是非未能給出足夠準確的評說。事實上,只要臺共黨人的“人間原點”確如陳映真忍不住讓穩重的老蔡在小說中以阮籍長嘯的方式呼喊出的,讓“人的解放、幸福的光明之夢”“在臺灣、在中國、在全世界”熊熊燃燒起來,就不能不承認,無論社會主義中國在建設過程中遭遇到了怎樣的歷史曲折或挫折,革命在這里的成功還是給“全世界受苦的人”帶來了莫大鼓舞,并在革命的旗幟下向世界各國(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仁人志士提供了各種支持,這就為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斗爭做出了巨大貢獻。即便失之過簡,陳映真仍以高度的真誠和毅力,返回自己的社會主義理想對“既恰切又飽滿的社會生活形式和生命精神形式”的追求,重建了自己的民主想象和民族情懷,進而在創辦《人間》雜志的具體實踐中,避免了把“文化生活越來越庸俗、膚淺”、“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廢、枯索”簡單歸咎于“現代性狀況”或新殖民主義的宰制,最終覓得左翼知識分子思想工作的可能空間與可行方式。《趙南棟》正是以否定性的方式,在社會精神的荒蕪和革命理想的隱遁之間,建立起了歷史性的關聯,復以存亡續絕的態度,讓趙南棟葆有“愛”的情懷,使葉春美引領行尸走肉般的趙南棟走向鄉間的努力成為一個不無希望的結局。三十年前中國大陸知識分子難以把握的這個文本,在今天,對于不滿于世界狀況的有心人,尤其是“文學者”,可謂彌足珍貴。
注釋:
① 托馬斯·莫爾著,戴鎦齡譯:《烏托邦》,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40頁。
②賀照田:《當信仰遭遇危機……——陳映真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論(二)》,《開放時代》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