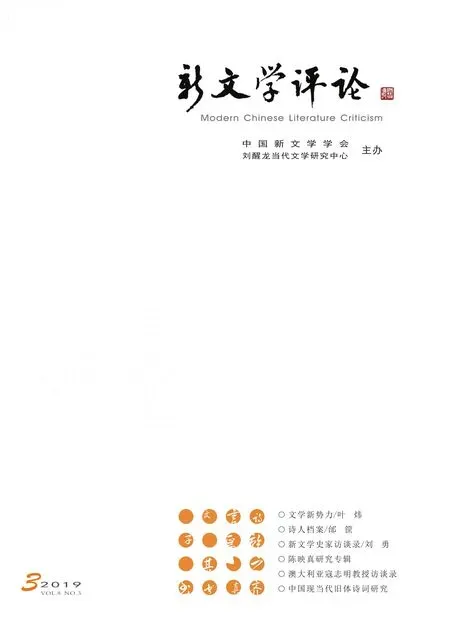風吹過城市,也吹來震驚
——關于邰筐“城市”視域的詩
□ 霍俊明
北島在“文革”時期將偷偷寫好的《百花山》給父親看,結果卻遭到父親的不解與震怒。而幾十年后的今天當城市化時代全面鋪張開來的時候,我們是否還能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中國歷來缺乏公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但是我們應該相信詩人無論是面對城市還是更為龐大的時代都能夠發出最為真實的聲音。當年顧城關于北京有一組極其詭異和分裂的詩《鬼進城》,這是極其準確的城市寓言。而今天我們看到的城市更像是一個巨大的機器。它使人神經興奮、官能膨脹,使人處于迷茫而不自知的境地。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鎮化的時代,詩人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霧霾籠罩的城市、城鎮和城鄉接合部。但是多少年來成熟的“城市詩歌”仍然闕如。對于當代中國詩人而言,城市、廣場、街道、廠區、農村、城鄉接合部、“高尚”社區、私人會館無不體現了空間以及建筑等的倫理功能。城市背景下的詩歌寫作很容易走向兩個極端,一個是插科打諢或者聲色犬馬,另一個則是走向逃避、自我沉溺甚至憤怒的批判。
1971年寒冷的正月,邰筐在山東臨沂的古墩莊降生。1979年當父親帶回來的紅色封皮的《毛澤東詩詞》被一雙黑乎乎的小手和同樣弱小的紅通通的心靈所一起接受的時候,似乎就注定邰筐的命運將與詩結下不解之緣。邰筐在1996年9月用7天的時間走完長達2100里的沂河的壯舉對其詩歌寫作的幫助以及對文化地理學意義上的鄉村和城市的重新確認都大有裨益。如果說當年的芒克、多多、根子、林莽等人是為白洋淀寫詩,海子為麥地寫詩,于堅為尚義街6號寫詩,那么邰筐就是為臨沂、沂河和曲柳河寫詩,為他所熟知的這些事物再次命名。邰筐詩歌中的城市和事物更多是浸染了深秋或寒冬的底色,盡管詩人更多地是以平靜、客觀、樸素甚至諧趣來完成一次次的抒情和敘寫。如果說優異的詩人應為讀者、批評者、詩人同行以及時代提供一張可供參照、分析、歸納的報告的話,邰筐就在其列。邰筐的詩與欺騙和短視絕緣,他的詩以特有的存在方式呈現了存在本身的謬誤和緊張。工業文明狂飆突進、農耕情懷的全面陷落,“心靈與農村的軟”與“生存與城市的硬”就是如此充滿悖論地進入了生活,進入了詩歌,也進入了疼痛。在邰筐的詩歌中我們不僅可以日漸清晰地厘定一個詩人的寫作成長史,更能呈現出一代人尷尬的生活史與生存史。詩歌和生存、城市與鄉村以空前的強度和緊張感籠罩在“70后”一代人身上,“2004年一天的晚上,我來到了臨沂城里。沿著東起基督教堂西至本城監獄的平安路往西走,妄圖路過苗莊小區時,到在小區里買房子住下快有一年的邰筐家里留宿一宿,和他談一些生活上的瑣事,以及具體生活之外的人生小計,實在無話可說了,甚或也說一些有關詩歌的話題”(江非《記事》)。當談論詩歌的時候越來越少,當談論生活的時候越來越多,甚至當沉重得連生活都不再談論的時候,這些在臨沂城的某一個角落席地而坐的青年,似乎只有沉默和尷尬能夠成為這一代人的生存性格,甚至也可能正是這一代人的集體宿命。
邰筐在經歷1990年代后期自覺的詩歌寫作轉換之后,他的詩歌視角更多地轉向了城市。收入“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的詩集《凌晨三點的歌謠》就是邰筐在農村與城市的尷尬交鋒中的疼痛而冷靜的跡寫。邰筐在城市中唱出的是“凌晨三點的歌謠”。凌晨三點——黑夜不是黑夜,白天不是白天。這正是城市所天生具有的,它是如此的含混、曖昧、扭曲。而揮舞著掃帚的清潔工、詩人、歌廳小姐、糝館的小伙計在“黎明前最后黑暗”的時候的短暫相聚和離散正是都市的令人驚悚而習以為常的生活場景。而出現在“骯臟的城市”里的一個一年四季扭秧歌的“女瘋子”無疑成了城市履帶上最容易被忽略卻又最具戲劇性的存在:“這是四年前的事了 / 我每天回家的路上都會看到的一個場景 / 她似乎成了我生活的一個內容 / 如果哪天她沒有出現,我總覺得少了點什么 / 甚至會有點惆悵和不安 / 她病了嗎?還是離開了這座骯臟的城市 / 后來,她真的就消失了 / 好像從來都沒出現過 / 每次經過那個路口 / 我都會不由自主地朝哪兒 / 看上一眼”(《扭秧歌的女瘋子》)。2001年冬天,青年詩人邰筐發出的慨嘆是“沒有你的城市多么空曠”。如果說此時詩人還是為一個叫“二萍”的女子而在城市里感傷和盡顯落寞,而沒過多久連邰筐自己都沒有預料到在擴建、拆遷和夷平的過程中他即將迎來另一個時代和城市生活——凌晨三點的時間過渡區域上盡是那些失眠、勞累、游蕩、困頓、賣身、行乞、發瘋、發病的灰蒙蒙的“人民”。邰筐、江非、軒轅軾軻三個年輕人于一個個午夜徘徊游蕩在臨沂城里——精神的游蕩者已經在中國本土誕生。而在被新時代無情拋棄和毀掉的空間里,邰筐寫出的詩句是“沒有人住的院落多么荒涼”。這種看似日常化的現實感和懷舊精神正在成為當代中國詩人敘事的一種命運。我同意江非對邰筐詩歌的評價,“他正是直接以鋒利的筆觸,以囊括一切的胸懷切入了時代的正在‘到來’的那一半工商業文明之下的城市化進程中的宏大歷史場景,而爆發出了強大的詩歌威力,成為一個無愧于時代的詩人,一個以足夠的詩歌力量回報時代的人”(《當一個人的詩歌與時代建立了肉貼肉的關系》)。
2008年秋天,邰筐扛著一捆煎餅由山東臨沂風塵仆仆地趕到了北京。此時,山東平墩湖的詩人江非則舉家來到了遙遠海南的澄邁縣城。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巧合,是否印證了我在《尷尬的一代》中對“70后”一代人詩歌寫作和生活狀態的一句話——漂泊的異鄉。似乎這一代人從一出生開始就不斷追趕著時代這輛“卡車”后面翻滾的煙塵,試圖在一個時代的尾聲和另一個時代的序曲中能夠存留生存的穩定和身份的確定。但是事實卻是這一代人不斷地尋找、不斷地錯位,不斷在蒼茫的異鄉路上同時承擔了現實生存和詩歌寫作的尷尬與游離。城市生活正在撲面而來。可是當詩人再度轉身,無比喧囂的城市浮世繪竟然使人心驚肉跳。靈魂的驚悚和精神的迷醉狀態以及身體感受力的日益損害和弱化都幾乎前所未有。與此同時,面對著高聳強硬的城市景觀每個人都如此羞愧——羞愧于內心和生活的狹小支點在龐大的玻璃幕墻和高聳的城市面前的蒙羞和恥辱。詩人以冷峻的審視和知性的反諷以及人性的自審意識書寫了寒冷、怪誕的城市化時代的寓言。而這些夾雜著真實與想象成分的白日夢所構成的寒冷、空無、疼痛與黑暗似乎讓我們對城市化的時代喪失了耐心與信心。多年來,邰筐特殊的記者身份以及行走狀態使得他的詩歌更為直接也更具有“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凜冽和尖銳。而相應的詩歌語言方式上卻是冷靜和平淡的。這種冷峻的語言與熱切的介入感形成了撕裂般的對比和反差。邰筐的詩歌葆有了他一以貫之的對現場尤其是城市現代化場景的不斷發現、發掘甚至質疑的立場。《地鐵上》《登香山》《致波德萊爾》《活著多么奢侈呀……》《西三環過街天橋》《暮色里》等詩大抵都是對形形色色的城市樣本的透析和檢驗。邰筐的詩歌,尤其是對城市懷有批判態度和重新發現的詩歌都印證了我對“70后”一代人的整體印象——他們成了在鄉村和城市之間的尷尬不已的徘徊者和漂泊者。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不能成為這一代人的最終歸宿。所以,邰筐在這些詩歌文本中所愿意做的就是用詩歌發聲,盡管這種發聲一次次遭受時代強大的挑戰。由此,“像一個人一樣活著”甚至“像詩人一樣活著”的吁求就不能不是艱難的。邰筐詩歌的視點既有直接指向城市空間的,又有來自內心淵藪深處的。而更為重要的還在于他并沒有成為一個關于城市和這個時代的廉價的道德律令和倫理性寫作者,而是發現了城市和存在表象背后的深層動因和晦暗的時代構造。而他持續性的質疑、詰問和反諷意識則使得他的詩歌不斷帶有同時代詩人中少有的發現性質素。當臨沂及城中的沂河、曲柳河、平安路、苗莊小區、金雀山車站、人民醫院、人民廣場、尚都嘉年華、星光超市、發廊、亞馬遜洗浴中心、洗腳屋、按摩房、凱旋門酒店一起進入一個詩人生活的時候,城市不能不成為一代人的諷刺劇和昏黃遺照中的鄉土挽歌。邰筐在天橋、地鐵、車站、街頭等這些標志性的城市公共空間里透析出殘酷的真實和黑冷的本相。邰筐在這些場景中為我們所熟悉的城市生活完成了類似于剝洋蔥的工作。在他剝開我們自以為爛熟的城市的表層和虛飾的時候,他最終袒露給我們的是一個時代的痛,陌生的痛,異樣的痛,麻木的痛,不知所措的痛。而“城市靠左”“鄉村靠右”“我靠中間”正是一個清醒的觀察者、測量者和詩歌寫作者最為合宜的姿勢。邰筐的敏識在于深深懂得詩歌寫作絕不是用經驗、道德和真誠能夠完成的,所以他做到了冷靜、客觀、深入、持久而倔強的個性化的發聲。邰筐所做過的工地鋼筋工、地攤小販、推銷員、小職員等近20個工種對他的人生歷練和詩歌“知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邰筐近期的詩作中時時出現一個“外省者”形象。他所承擔的不只是一個城市化生活的尷尬寓言的發現,同時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外省者”的心態、視角能夠更為有效地呈現城市生活中的“詩意”和“非詩意”地帶。尤其是在《一個男人走著走著突然哭了起來》這首詩中,在一個現實或想象中的城市里“外鄉人”的感傷與哭泣正像當下時代的冷風景。這也是一個個城市生存者痛苦不已的靈魂史和精神見證,“他看上去和我一樣 / 也是個外省男人 / 他孤單的身影 / 像一張移動的地圖 / 他落寞的眼神 / 如兩個漂泊的郵箱 / 他為什么哭呢 / 是不是和我一樣 / 老家也有個四歲的女兒 / 是不是也剛剛接完 / 親人的一個電話 / 或許他只是為越聚越重的暮色哭 / 為即將到來的漫長的黑夜哭 / 或許什么也不因為 / 他就是想大哭一場”。邰筐詩歌中的城市敘事具有大量的細節化特征,但是這些日常化的城市景觀卻在真實、客觀、平靜、樸素和諧謔的記錄中具有了寓言性質和隱喻的特質。因為邰筐使詩歌真正地回到了生活和生存的冰點和沸點,從而在不斷降臨的寒冷與灼熱中提前領受了一個時代的傷口或者一個時代不容辯白的剝奪。邰筐的很多相關詩作并不是現在流行的一般意義上的倫理性的涉及公共題材的“底層寫作”,而是為這類題材的文本提供了豐富的啟示性的精神元素以及撼動人心的想象力提升下的“現實感”。而對于時下愈加流行的“打工詩歌”和“城市寫作”我抱有某種警惕。這不僅來自大量復制的毫無生命感以及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的缺失,而且還在于這種看起來“真實”和“疼痛”的詩歌類型恰恰是缺乏真實體驗、語言良知以及想象力提升的。換言之,這種類型的詩歌文本不僅缺乏難度,而且缺乏誠意。吊詭的則是這些詩作中不斷疊加著痛苦、淚水、死亡、病癥。在這些詩歌的閱讀中我越來越感覺到這些詩歌所處理的無論是個人經驗還是“中國故事”都不是當下的。更多的詩人仍在自以為是又一廂情愿地憑借想象和倫理預設在寫作。這些詩歌看起來無比真實但卻充當了一個個粗鄙甚至蠻橫的仿真器具。它們不僅達不到時下新聞和各種新媒體“直播”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而且就詩人能力、想象方式和修辭技藝而言它們也大多為庸常之作。我這樣的說法最終只是想提醒當下的詩人們注意——越是流行的,越是有難度的。我不期望一擁而上的寫作潮流。然而事實卻是在各種媒體上,“非虛構寫作”現在已經大量充斥著關于鄉土、城中村以及打工者、發廊女等底層、弱勢群體的苦難史和階層控訴史。在社會學的層面上我不否認自己是一個憤怒者,因為這個時代有那么多的虛假、不公、暴力和欲望。但是從詩歌自身而言我又是一個挑剔主義者,因為我們已經目睹了20世紀在運動和活動中詩歌傷害的恰恰是自身這個真相。城市就像寒冷大雪背景中的那個鋒利無比的打草機,撕碎了一個個曾經在農耕大地上生長的植物,也同時撲滅了內心向往的記憶燈盞。郊區、城鄉接合部、城市里低矮的棚戶區和高大的富人區都在呈現著無限加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的現代病,而其間詩人的鄉愁意識、外省身份、異鄉病和焦灼感都“時代性”和“命運性”地凸現出來。
“70后”一代人在鄉村和城市面前不是單純的鄉土主義者,更不是沉溺的城市市儈,而是在鄉村和城市的左右夾擊中受到無窮無盡的擠迫的一群人。所以,邰筐的城市是黑色的,其發出的聲調是反諷和嚴肅的。作為一個清醒而沉痛的城市和鄉村的言說者,邰筐的詩歌意義在于他比之其他年輕詩人擁有更為敏銳、更為深邃的詩歌寫作意識和更能介入與沖撞時代噬心主題的刁鉆視角。所以,邰筐等“70后”詩人對城市的抒寫,無論是批判還是贊同,都是在鄉土視野下完成的。所以,當城市化的進程不斷無情而無可阻擋地推進,當黑色的時光在生命的軀體上留下越來越沉重的印痕,往日的鄉土記憶就不能不以空前的強度擴散、蔓延開來。而邰筐的城市詩正是在時間、歷史、體驗和想象力的共同觀照下獲得了直取時代核心的力量。在突進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景觀中,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但是也有一些似乎從未改變。正如那只撈沙子的木船,日復一日地重復著擺渡、裝載的程序。城市里的陽光并不充足,霧霾重重。城市里的冬天萬物蕭條,邰筐所能做的就是打開一個個潮濕、陰暗的地下室;就是點亮內心的燈盞,在迷茫的風雪路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