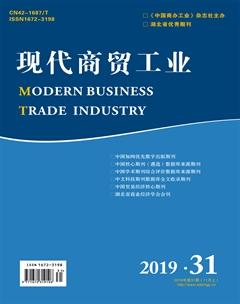美國青年學者馬特?奧賈對蘇聯農業集體化動因的多維審視
任冬梅
摘 要:美國喬治敦大學哲學博士馬特·奧賈主要從消除城鄉差別、工業—烏托邦風氣以及城市中心論等視角,對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動因展開分析,觀點較為新穎,通過梳理其主要觀點,可以為國內學人提供必要的參考。
關鍵詞:蘇聯;農業集體化;社會主義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31.069
蘇聯農業集體化是蘇聯通過合作社把個體的小農經濟改造成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過程。1929-1933年蘇聯大規模開展將個體小農私有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大集體經濟的運動。為適應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的要求,1928年11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加快農業集體化步伐。到1937年,大多數農戶參加了集體農莊。農業集體化消滅了富農階級,為農業機械化、現代化開辟了道路。關于蘇聯農業集體化的起源和動因,海內外學界眾說紛紜。筆者選取美國青年學者中觀點較為新穎的喬治敦大學哲學博士馬特·奧賈(M.A.Matt F.Oja)的相關研究成果,梳理其主要觀點,為國內關注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學人提供必要的參考。歸納起來,馬特·奧賈主要從消除城鄉差別、工業—烏托邦風氣以及城市中心論等視角,來探尋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深層次動因。
1 消除城鄉差別的途徑
在馬特·奧賈看來,傳統的布爾什維克強調生產基礎對文化上層建筑的影響,生產領域的融合預計也會帶來社會和文化其他方面的融合。這一假設認為,對無產階級革命在這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家所面臨的無數問題而言,農業集體化為消除城鄉之間由來已久的鴻溝,為解決農民問題帶來了希望,而農民問題是整個20世紀20年代蘇聯共產黨人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如果農業能夠按照與工業相同的生產原則進行重組,農業勞動力就會自然而然地具備城市無產階級的文化和心理特征。1929年在農業部門進行的集體化,通過變革生產關系,應該能夠在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中造就新的農民階級——一個深刻的社會和個人轉變農民的橋梁在城市和農村的差別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這次文化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農業集體化的現代生產組織及其所帶來的生產力提高所產生的農業日益發展的產物。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層普遍認為,當農民有了更多的食物、體面的住房和更多的閑暇時間,他們就會更愿意學習讀書,養成城市生活的習慣和態度。但也有人認為,生產過程本身會對落后農民的心理產生迅速而根本的改變,而這一點往往是黨的領導人明確提出的。布爾什維克長期以來的決定論傳統認為,生產是一切進展的基礎,這進一步助長了對農業集體化生產組織的廣泛崇拜。1929年,斯大林革命來到了農村,這場革命不僅在經濟和政治控制領域,也在文化領域發起了攻擊。的確,甚至很難作出這樣的區分,因為整個農村改造的目的是通過同時改造農村生活的所有方面。然而,生產是關鍵。斯大林的土地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種假設所驅動的,即農民的落后文化和保守的政治觀點是他們不發達的生產水平的產物。解決辦法很明顯:把農業轉移到最先進、最先進的生產體系——即像工業那樣進行集體生產。其直接后果是,農民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態度——正如斯大林所說,他們“對城市的不信任”——也將迅速變得先進和進步。簡而言之,它假定農民的思想和行為就是農民階級的,因為他們像農民一樣工作;因此,如果能讓他們像無產階級一樣工作,他們很快就會像無產階級一樣思考和行動。至少在理論上,解決農民長期代表的經濟和政治問題的關鍵在于一場真正的農業集體化革命:不是通過恐嚇和驅逐農民,而是通過迅速把他們轉變為文化和政治上進步的農村無產階級。最終的結果將是永久解決農民問題。通過農業集體化來將農民的世界無產階級化,斯大林不僅希望在工農之間產生一種戰術意義上的調和妥協,而是農村和城市的真正和最終的統一。
2 工業—烏托邦主義的影響
在馬特·奧賈看來,蘇聯農業集體化背后的假設是不可阻擋的馬克思主義唯物決定論邏輯的產物。當時的蘇聯人普遍認為,技術和生產組織是辯證相互依存的,當其中一個發生變化時,另一個也必須發生變化。蒸汽機徹底改變了工業生產的性質,帶來了一種全新的組織體系;正如蒸汽機在最初的工業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一樣,拖拉機的引進——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拖拉機在“當前農業工業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不罕見——同樣注定會徹底改變農業組織。現代技術有望大大提高生產率,但前提是它能與最現代的組織系統相結合。這個系統就是大規模生產流水線——亨利·福特和蒙大拿農民湯姆·坎貝爾的系統都是泰勒主義及其變種。因此,強調物質世界的力量,特別是生產方式對文化、心理和態度的改造,當然是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直接繼承。馬特·奧賈將這種思維稱之為工業—烏托邦主義。這并不是指斯大林主義在20世紀20年代構思和培育的一個精確的總體計劃或藍圖,然后在適當的時候有條不紊和毫不留情地執行。正如摩西·萊文(Moshe Lewin)所言,斯大林主義多數派在1928年初決定結束新經濟政策,那時他們還不清楚替代新經濟政策的形式和行政結構。在1928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組織和經濟結構存在著某種真空,工業—烏托邦主義的主流思想和假設在填補這一真空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工業—烏托邦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按照現代工廠制度的模式改造生產過程而實現的,現代工廠制度的顯著特點是用規模更大的集體企業取代個人生產;現代技術與電氣化的應用引進了現代科學的生產組織方法。這一模式被認為是改造農民、實現真正的農村社會主義化、徹底解決農民問題、實現農業部門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在斯大林發動農業集體化革命的時候,蘇聯工業烏托邦的風氣非常普遍。這種風氣廣泛存在于共產黨領導層的思想中,也存在于農村較低層的活動人士中,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蘇聯20世紀20年代的幾種主流知識潮流。理查德斯蒂茨(Richard Stites)對20世紀20年代俄國各種烏托邦思潮進行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由于缺乏理論指導,20世紀初俄國知識分子對土地的社會主義性質進行了大量的思考。1917年前后,這種猜測是經常就烏托邦式的愿景未來進行激烈論戰。到20世紀20年代,這個問題已經成為城市化者和去城市化者之間爭論的核心。正如理查德斯蒂茨所指出的那樣,斯大林主義本身并不是烏托邦主義的終結,而是這場曠日持久的在彼此競爭的各種烏托邦思想之間所進行的混戰的終結,這一終結是通過強制推行一種單一的強制性烏托邦愿景而實現的。斯大林在20世紀末粉碎了革命烏托邦的自由競爭,取而代之的是他自己的統一的烏托邦。這個愿景就是馬特·奧賈所說的工業烏托邦主義,從本質上說,它非常類似于最極端的城市主義者/工業主義者在城市主義者/反城市主義者軸心上的地位,這條軸心貫穿了俄羅斯烏托邦思想的整個傳統。斯大林主義工業—烏托邦主義正是直接從這一知識傳統中產生的。換句話說,馬特·奧賈認為,蘇聯農業集體化不過是這種工業—烏托邦主義合乎邏輯的產物。
3 城市中心論的產物
馬特·奧賈指出,馬克思對農民并不重視,馬克思認為農民在社會的革命性變革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觀點,是眾所周知的,幾乎不需要詳細闡述。馬克思把法國農民比作一袋馬鈴薯,認為農民是一個保守的階層,在即將到來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他們充其量只能扮演一個被動的角色。馬克思幾乎所有關于階級斗爭和歷史進步的理論預言,當然都是以城市工人及其意識的覺醒為中心的。這種壓倒性的城市中心論的理論背景,在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經驗中得到了反映和加強。正如摩西·萊文所說,“布爾什維克是一個杰出的城市政黨,對農村的現實并不了解,對農村落后和保守的農民大眾表現出很少的耐心。”因此并不奇怪,關于農民應該在1917年革命之前或革命之后扮演何種角色,布爾什維克內部也沒有達成真正的共識,只有一些非常模糊的想法,即按照俄國農村公社傳統,認為農業部門應當在一些大型集體生產單位中進行組織和得到發展。簡而言之,在20世紀20年代蘇聯共產黨人關于農村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方面,存在嚴重的理論真空,關于如何才能真正把社會主義帶給農民,甚至農村的社會主義會是什么樣子,并不清楚。按照馬克思的名言,社會主義將見證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的出現,如何將其與蘇聯1920年代初的實際情形進
行協調,存在著巨大的困難。當時蘇聯的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差距似乎呈現出差距日漸增大的趨勢,農民在革命之后,又回到其古老的生活和生產方式之中。列寧對這件事尤其感到不安;他的結論是,如果要實現社會主義,這些階級必須以某種方式聯合起來。考慮到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基本屬于城市中心論的范疇,因此人們就不難看到,列寧經常對俄國農民的文化落后表示遺憾,并明確地支持城市文化。例如列寧1923年1月在文章中指出,最近的一份報告在識字率方面“顯示,我們還是要做大量艱苦的工作,來使農民達到普通西歐文明國家的標準。”正是從這種城市中心論出發,布爾什維克提出了工農之間的具體聯合方法,這就是布哈林在其極具影響力的入門著作《共產主義ABC》中對集體農業的討論在題為“為什么未來屬于集體農業?”的一節中。布哈林將大型農村公社描述為:一個更完善的農業體系,一個共產主義的體系,它將有能力把我們的農村人口從現存的侏儒農業體系中野蠻浪費的能源中解救出來;把俄羅斯從野蠻的土地枯竭中拯救出來。
參考文獻
[1]王瑞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M].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14,(10):640641.
[2]M.A.Matt F.Oja,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Smychka: Stalinist Utopianism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oviet Agriculture,1929-1941[D].Georgetown University,1994:25.
[3]Moshe Lewin,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System[J].Pantheon,1985:91.
[4]Richard Stites,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M].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