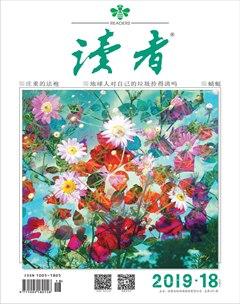莊重的法袍
崔雋
脫去莊重的法袍,史久鏞是一位普通的老先生。
不過,國際法官的素養和習慣在史久鏞身上仍然有跡可循。為了表示對來訪者的尊重,即使在家里,他也要穿上熨帖的夾克和襯衫,再配一雙光亮的皮鞋,白發梳理得一絲不茍。對哪年哪月哪件案子的記憶仍然清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英文法律詞匯常常脫口而出。
93歲,史久鏞的年歲比聯合國國際法院(以下簡稱國際法院)的歷史還要長。從外交部法律顧問到中英香港問題談判工作組成員,再到國際法院法官、院長,他說自己的人生經歷,恰恰也是中國在國際法領域發展的一個縮影。
放大鏡和錄音筆不離手
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辦那天,史久鏞沒有到現場領取改革先鋒獎章。家人說,已經年逾九旬的史久鏞,如果到現場參會,身體確實會有點吃不消。
那枚獎章現在就擺在史久鏞家客廳的陳列柜里。“我沒想到國家給我這么高的榮譽,做夢也沒想到。”坐在記者面前的史久鏞重復了幾遍“沒想到”。
這些年,從國際法院退休的史久鏞常常為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見。上了年紀,腿腳不如從前麻利,他常用口述錄音的方式將咨詢意見送給有關部門做參考。放大鏡和錄音筆成為他不離手的工具。
2013年,菲律賓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單方面將中菲南海有關爭議提起國際仲裁。2016年7月12日,臨時仲裁庭對南海仲裁案作出“最終裁決”,妄圖否定中國在南海的部分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整個過程中,中方態度鮮明:對于仲裁,不參與,不接受;對于有關裁決,不接受,不承認。
當時,史久鏞認為所謂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對中菲南海有關爭議并沒有管轄權,這是原則性、根本性的一點。當“裁決結果”公布時,中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于應菲律賓共和國請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決的聲明》,鄭重聲明,該裁決是無效的,沒有拘束力,中國不接受、不承認。
對于當前的國際形勢,史久鏞也很關心。談到中美貿易爭端,史久鏞用了“艱巨”二字來形容。“貿易爭端涉及國際法與國際規則。美國依據‘301調查對華采取的單邊貿易報復制裁并不具有國際法依據,有違WTO(世界貿易組織)基本原則中的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原則,完全違反了自由貿易的精神,也與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多邊體制相悖。”
中美貿易爭端拼的是實力,但打的是規則。“這次我們的態度很鮮明,外交部不是說了嗎,我們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從國際法的角度出發,這些年中國正在利用國際法與國際規則處理國際爭端、規制其他國家的違法行為,以保證自己的國家利益不受侵犯。”
“正是因為中國,我才能有這樣的機會”
在史久鏞家的陳列柜里,有一個刻有銘文和法官簽名的紀念銀盤,簽名特意按照當時在職法官的資歷排序。這是2010年史久鏞卸任國際法院法官時收到的告別禮物。“對我來說,它代表著我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經歷,十分珍貴。”
1978年,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一重要講話中,提出“要大力加強對國際法的研究”。此后,一批國際法學人走向世界。他們活躍的身影被視為中國在國際法學界受到重視的標志。
1993年,史久鏞當選國際法院法官。同一時期,王鐵崖、邵天任、端木正和李浩培當選國際常設仲裁法院仲裁員,趙理海成為國際海洋法法庭的法官。
國際法院要就國家間的爭端行使訴訟管轄權,以及就聯合國有關機構提交的法律問題發表咨詢意見,行使咨詢管轄權。被提交至國際法院的案子,均涉及復雜的法律問題和領土主權等國家核心利益,因此法官的工作非常繁重。
“雙方的起訴詞、辯詞摞在一起有一米多高。”史久鏞張開手臂比畫了一下。那時他每天從法院回到家,吃飯之前要在床上躺20分鐘以休息調整。
開庭那一天是最忙碌的。隨著禮賓官一聲“La Cour(開庭)”,15位大法官身著法袍,依次從側門進入大廳落座,法院正式開庭。上午法官們要聽取雙方律師的辯護,下午庭審辯詞會以復印文本的形式送達法官桌上,法官要在下午進行閱讀分析。
2003年,77歲的史久鏞高票當選國際法院院長,成為首位擔任院長的中國籍法官。時任中國外交部部長唐家璇向史久鏞發了賀電:“您的當選,是國際社會對您卓越學識和公正品格的肯定。這是您個人的榮譽,是中國法學界的榮譽,也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榮譽。”
擔任院長期間,史久鏞參與審理了16宗案件,創下迄今國際法院院長審理案件數量之最。“國際法院的法官是來自各國的法律精英,他們都有‘我是天下第一的自信姿態。如何形成判決,當院長的就得仔細聽,要考慮怎么引導大家,最起碼要形成一個多數意見。”
史久鏞最近正在關注中東局勢。美國繼續增兵中東地區,伊朗宣布突破濃縮鈾存量上限,波斯灣上空彌漫著緊張的空氣。在國際法院工作時,史久鏞對美伊之間的復雜關系深有體會。2003年,他還負責審理了伊朗訴美國石油平臺案。
此外,以色列隔離墻案也是史久鏞審理的經典案例。自2002年6月起,以色列沿以巴邊界線及占領區修建了高8米、長約700千米的安全隔離墻,摧毀了140棟房屋,影響到87.5萬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令來自400個家庭的2300多人流離失所。
經過5個月的法庭審議,2004年7月9日,史久鏞在國際法院司法大廳宣布咨詢意見:以色列修建隔離墻違反國際法,應終止修建,同時拆除已修建的隔離墻。
“關于隔離墻的咨詢意見,影響之大,直到現在,阿拉伯國家的大使一見到我就說,在你手下作出的隔離墻的咨詢意見公正合理,現在阿拉伯人民還把你看成英雄。”史久鏞說。
在國際法院的答疑手冊上有一句話:國際法院的大法官一旦當選,就不再代表他們各自國家的政府,他們的首要職責就是保證絕對公正。“我在國際法院的唯一身份就是法官,我的法律信仰就是按照現行的國際法從事審判。任職那么多年,中國政府從來沒干預、影響過我,沒問過我對某個案子怎么看。”史久鏞說。
但是,在國際場合不講不利于祖國的話,是史久鏞一直堅持的立場。有一次,史久鏞參加一名英國法官的家宴,一個荷蘭少數黨人問史久鏞:“我看了您的履歷,1954年您回到中國,我不理解,您當時難道不知道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嗎?”這是一句別有意味的發問。
“我的回答很簡單——如果我留在美國,你覺得我現在能坐在這里,以國際法院院長的身份和你交流嗎?我甚至連法官都當不上。正是因為中國,我才能有這樣的機會。”史久鏞說。
“中國對香港歷來擁有主權”
1984年12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以下簡稱《中英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史久鏞在現場近距離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
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逐漸融入國際體系,外交領域急需具有國際法背景的專門人才。1980年,史久鏞調入外交部條法司擔任法律顧問。兩年后,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此后,中英兩國就香港回歸問題開始了共22輪的漫長談判。
史久鏞是談判工作組和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法律顧問,參與了《中英聯合聲明》的3個附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關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關于土地契約》的起草工作。
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如何表述香港的回歸,考驗著中國國際法學者的智慧。英方提議,聲明中使用英方“放棄”香港的表述。但這樣一來,英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的歷史就被粉飾成了英國曾在香港行使所謂“主權”的歷史,實質是將英國非法取得的權利合法化,中方不能接受。經過幾個月的談判,最后的聲明使用了中方主張的“交還”的表述方式。“‘交還意味著香港是英國非法占領的,現在要還回來,意味著香港從來不屬于英國,中國對香港歷來擁有主權。”史久鏞說。
與英方代表通宵達旦地談判、磨合、試探、拉鋸,是史久鏞的工作常態。在一場關于香港民航的談判中,史久鏞擔任中方首席代表,與英國交通運輸部的一名司長直接交鋒。談判持續了整整一夜。最后,這名英國司長握住史久鏞的手說:“盡管我們的分歧很大,但這是一次友好的談判,沒有拍桌子,與你談判很過癮。”
再次回憶參與談判的這段歲月,史久鏞認為最大的亮點是“一國兩制”被寫入《中英聯合聲明》,這是中國對國際法的一大貢獻。
“為國家做些事、出些力”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史久鏞在《紐約時報》上看到這則消息后急忙給家里撥越洋電話,詢問家人是否安好。掛了電話,他心情激動,難以平復。
當時23歲的他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公法系深造。“我記得《聯合國憲章》公布時,里面有一句: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我成長在戰爭年代,學國際法就是不想再看到國家山河破碎,想推動國與國的關系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
喪權辱國,是史久鏞最深刻的少年記憶。上中學時,史久鏞一家居住在上海英租界。那時行人經過崗哨林立的外白渡橋時須向日本憲兵鞠躬行禮。“這是一種無法忍受的屈辱。”史久鏞回憶道。
1950年11月28日,以伍修權為特派代表、喬冠華為顧問的中國代表團出現在聯合國紐約總部。針對“美國侵略臺灣案”,伍修權在安理會控訴美國的侵略行徑,擲地有聲。這是年僅一歲的共和國在國際舞臺上的首次亮相。
“我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中國人民,來這里控訴美國政府武裝侵略中國領土臺灣(包括澎湖列島)非法的和犯罪的行為……任何詭辯、撒謊和捏造都不能改變這樣一個鐵一般的事實:美國武裝力量侵略了我國領土臺灣!”
史久鏞坐在電視前見證了這一幕。他看到伍修權指著時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奧斯汀痛斥,仿佛將中國人民100多年的怒氣傾瀉而出,他只能用“震撼”來形容當時的心情。
此后,共和國的主張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1953年,周恩來在接見印度代表團時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從此確定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視為中國對國際法的一個重要貢獻。
1954年,史久鏞等不及修完博士學位,直接踏上歸程。如今,隔著近70年的時光回望,史久鏞仍然能回憶起那時急切的心情——迫不及待想看到一個新中國。“當時的愿望很樸素,就是為國家做些事、出些力。”這個念頭,直到現在也沒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