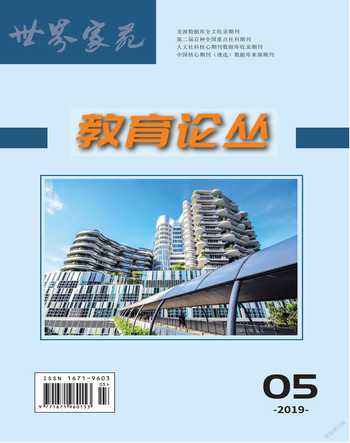淺談音樂與文學的美學
張媛媛

音樂與文學是兩個不同類型的藝術形式。音樂使用有組織的樂音來表達人們的思想感情,反映現實生活的一種藝術。它最基本的要素是節奏和旋律;文學則是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形象化反應客觀現實的藝術。但是語言和音響在表現形式上又有某種同一性。雖然,音樂和文學二者都是通過聲音來展示出來,可是音樂和文學在展前上又有不同的異處。音樂的聲音是音樂的生命,它的美主要存在與聲音自身之中,而文學語言表達的聲音并不是文學的特征,它的美存在于語言的函文中。由此,我們知道,音樂在傳輸的實踐過程中,借助純粹的音響因素灌注到人們的耳鼓內,刺激、鼓動人們的聽覺器官。因此,人們只有通過聽音樂,才能品嘗音樂,理解音樂,托爾斯泰說:“音樂的魅力,足以使一個人對未能感覺的事有所感覺,對理解不了的事有所理解,使不可能的事一變而為可能。”屠格涅夫也說過:“真正的音樂卻能將千百種美好的事物灌注心田”。
文學語言的要素則和音樂語言要素大不相同。即就在文學范疇內的詩歌,也絕非僅僅為了聽。它的語言音調,也不完全像音樂音調那樣純粹的感覺對象,而是在讀者閱讀時提供文學的內在感覺,欣嘗其內在涵義的美。讀者借助象爐中火一樣的文學,點燃自己,而后再借給別人,以致為大家所共有。
音樂給人們展示的形式和文學展示的形式不同。音樂展示的是音調符號,文學展示的是語言符號。但是,文學和音樂在展示過程中各有特點。文學作品中展開的是客觀世界過程,它所揭示的故事情節,不外乎是過去已經發生的或當前或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這些事件的由來和發展,都體現出人與社會和自然等客觀世界的聯系。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別”。真實描繪了當時社會老百姓的凄涼景況。音樂作品所展現的一切部與人的內心生活聯系在一起的。是一種建立在模仿、象征、暗示和表情基礎上的表現過程,它所表現的對象主要是人的內心世界。
例如: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富有象征或暗示意義的情感因素。它的結構和文學的結構邏輯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的。雖然,它的開始、發展和結束。盡受它的顯示部主部、明朗、溫柔和富有幻想的顯示部副部緊張、激烈的展開部,熱情、激動的再現部,以及悲怨、凄婉的尾聲,我們無法通過有強烈切音的粗暴結構節奏、驚慌、憂郁的不和諧弦聲的一系列音樂事件中,判斷這一戲劇的來龍去脈。這一時間只能和人們的內心相通,抒發人們的感情體驗。雖然音樂過程不等于文學過程,但音樂過程,都為人們提供了文學性聯想的依據,進而,以音樂中感受到富有過程性的文學性內容。
文學和音樂是水乳關系。我國古籍:《尚書·舜典》就有關于文學、音樂的記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清代李漁說:“詩文之詞采貴典雅而賤粗俗,宜蘊藉二總分明:詞曲不然,話則本之街談巷議,事則取其直說明言”。希臘的學者,亞里斯多德也認為:“史詩和悲劇,喜劇和酒神頌以及大部分雙管簫樂、豎琴樂——這一切實際上都是模仿,只有三點差別,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對象不同,所采用的方法不同”,晉樂用“節奏”和“音調”來模仿,詩“只能用語言來模仿”“或用不入樂的散文或不入樂的韻文”。這就是說,文學與音樂都是經由聽覺抵達知覺中心,但音樂比時能提供給我們更豐富多彩的激動心境的東西。
文學的抒情表現在表達感情,描寫感情、借景抒情。例如:杜甫的《春夜喜雨》這首詩表達了詩人對春雨的喜愛,也抒發了詩人淡薄閑適的心情。“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再如,刻畫工細,色彩綻麗,音律和諧,自然流暢,韻味悠長的七絕:《江畔獨步尋花》“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從視覺、從聽覺都給人以美的享受,同時也傳達了是人本身愉快安逸的心情。音樂的抒情,既無主觀明顯地表達,也無絕對的客觀表達。它的抒情是借客觀的描述表達到主管表述的效果。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就可證明。
從前所述,文學與音樂都具有“寓情于景,情景相即”的藝術境界。這種情是“無我三情”或叫曰“有情而無我”的超越之情。文學在它的篇、章、段、句上,和音樂在它的主題、過渡、發展、結尾上,在美的范疇內都賦予讀者聽者,從視、聽覺的傳送,注入心田的理解,而后受到美的陶冶。讓“美”在心靈回蕩,擴展,豐富美的空間。
我把學習文學與音樂理論后的理解、感受,寫成這篇淺識,有不妥之處,望能得到造詣根深的學者、專家的指教、批評。
(作者單位:陜西省西安市青少年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