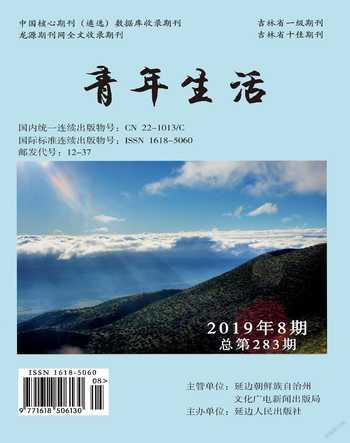文學史中的沈從文
胡萍
摘要:80年代以來,由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發端,“重寫文學史”一波波地走向了高潮,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格局發生了根本上的變化,曾經不被關注甚至是被排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秩序之外的沈從文成為了新的神話,占據了現代文學史的高峰。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沈從文的高度評價與贊揚重新確立了沈從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是通過將夏志清對沈從文的研究進行整理分析,來探討沈從文及其小說的風格特征。
關鍵詞:沈從文;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小說特征;
導言
在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里,毫無疑問,夏志清先生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認識到中國作家感時憂國、注重現實干預的心態,以及少悠遠的烏托邦式的藝術想象,但他也同時關注到有的作家能夠展現個人風格和獨特的視野。說起來沈從文的“下半生”之所以能再熱鬧起來,也是有幸于夏志清先生的賞識,在《小說史》中用了史筆推許一番,他認為沈從文的作品顯現出一種特有的性格和道德問題的熱情,創造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世界,而且這一道德熱情并不會限制他對藝術的琢磨。王德威在《重讀夏志清教授<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提到在沈從文被兩岸史家評者刻意忽略、湮沒的年月里,夏志清是少數記得他并賦予極高評價的知音。[8]讀完夏志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我們也確實能夠感受到夏志清賦予沈從文的高度贊揚與肯定。
一、通過夏志清評茅盾等作家再認識沈從文
夏志清強調“探求真理”而反對“訴諸情感”,他批評茅盾在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以后,作品里面無論是思想上或情緒上的描述,都已經很難見到先前真誠的語調了,小說家的感性已經惡俗化了,同時他為了順應革命的宣傳,也浪費了自己在寫作上的豐富想象力,在作品中多呈現出宣傳的調子,以至于小說的真實性就削弱了許多。
在分析完老舍的《駱駝祥子》后,夏志清提到老舍固然慢慢脫離了早先個人主義的立場,而在抗戰時期的緊張氣氛里,老舍為了反日救國,重新倡導英雄式的行動,但只是在宣傳上這樣做,并且缺少他先前對中國的需要和缺陷的深思卓識。而巴金的作品無論在人物還是場面上,都無法造成一種真實感,他的作品故事中到處充斥了反帝的宣傳,所以一個山窮水盡的人所產生的奇思妄想并沒有提升到悲劇的境界。
不同于以上夏志清對于魯迅、茅盾等吝于給予過高評價的態度,他對沈從文給予了高度的贊揚,“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中一個最杰出的、想象力最豐富的作家,是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30年代的中國作家,再沒有別人能像沈從文一樣在相同篇幅內寫出一篇如此富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豐富的小說來。”夏志清對沈從文給予的高度的評價和贊揚,也就確定了沈從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二、沈從文小說中的“自然人性”
沈從文在寫作過程中將中國文學的傳統寫法與西歐文學的描寫長處結合起來,使作品呈現出新的狀態,他認為人類如果要追求更高的美德,非得保留如動物一樣的原始純良天性不可,他筆下的蕭蕭所處的,是一個原始社會,所信奉的也是一種殘缺偏差的儒家倫理標準,可是當蕭蕭與花狗的事情瞞不住時,她固然是害怕家庭的責難和懲罰,但是這段時間并不長,而且也沒有在她身心留下什么損害的痕跡。沈從文向我們展示的是一種原始、質樸、和諧、健全的生命形態,對湘西人民的自在狀態和“質樸堅韌”的生命本性的贊美,展示的是一種未被都市商業文明污染的健康、優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在他的作品中多表現出的是對下層人民的同情,對人民從勞動中長期養成的善良品性與堅韌性格的贊賞,即“自然人性”。
三、沈從文小說中的“田園牧歌性”
夏志清在談及沈從文小說的牧歌性時,主要從三個方面入手:一是諷刺性的批判,比如在描寫現代都市生活小說中,將現代中國的病態一針見血地寫了出來,他在描寫“湘西世界”優美和諧的氛圍之余,也用諷刺的手法表達出了憤怒、悲痛與憎恨。二是沈從文在成熟時期對幾種不同文體隨心所欲的運用。如山水人物呼之欲出的牧歌式的文體《邊城》以及受佛家故事影響的筆調簡潔生動的敘述體,還有他模仿西方句法成功后的文體(《主婦》)。三是沈從文的田園視景,與他的文體構成一個整體。他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他能夠憑著特好的記憶隨意寫出景物與事件,能不著痕跡,輕輕的幾筆就把一個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類微妙的感情脈絡勾畫出來,如在《靜》這篇小說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他描寫情景的印象派手法和他對處于戰亂憂患中的人類尊嚴的關心,以及一種由各主角無怨無助的心境所襯托出來的靜穆的氣氛中的悲情。
四、沈從文小說中的“悲劇意蘊”
夏志清說沈從文筆下的露西型的少女(如三三、翠翠)與飽經風霜、超然物外的老頭子這兩種小說人物都是他用來代表人類純真的感情和在這澆漓世界中一種不妥協的自然人性美的象征。沈從文的小說中表現了人性的簡陋,比如《邊城》中翠翠最后的悲劇其實是她自己造成的,一個一個關于愛情的誤解最后造成了命運的悲劇,沈從文他看到了現實撥弄人的方面,但小說的結局都體現出一種人性的溫情與希望,他以“開放式結局”的方法寓悲于美: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這種“開放式結局”使人感到美好又充滿希望,但其唯美之中又透露出哀傷的特點。
結語
沈從文在他的小說里其實一直在試圖表現,生活中到處都是“偶然”,生命中還有比理性更具勢力的“情感”,一個人的一生可以說就是由“偶然”和“情感”相加而形成的,即使你并不迷信命運,但出其不意的“偶然”和“情感”也可能在形成你的明天,并決定你的后天。在沈從文這里,受偶然支配的人生,盡管帶有悲劇性,但仍然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形式”,他強調要從他的作品中發現一種燃燒的感情,對于人類智慧與美麗永遠的傾心,康健誠實的贊頌,并且在他具有明顯的裝飾風格的作品中也體現了他不一樣的情調和創作態度,正如他在《<長河>題記》中所說的:“特意加上一點牧歌的諧趣,取得人事上的調和。”[9]
參考文獻
[1]王曉明:《潛流與漩渦》[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2]沈從文:《湘女蕭蕭》[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5.
[3]沈從文:《邊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8.
[4]溫儒敏,趙祖謨:《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5]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6]王向輝:論沈從文小說的悲劇意識 [J]. 河南教育學院學報 ,2006(1).
[7]張光芒 , 張立杰:論沈從文小說的宿命意識 [J]. 山東師大學報 ,2000(4).
[8]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9]沈從文:《<長河>題記》,《沈從文全集》第1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