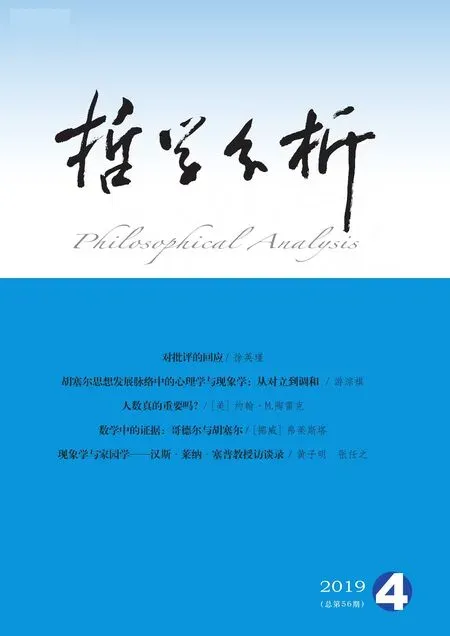規(guī)范性、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評徐英瑾的新著《唯物論者何以言規(guī)范》
徐 竹
導(dǎo) 論
在當(dāng)代分析哲學(xué)的發(fā)展中,主張自然主義立場的哲學(xué)進(jìn)路,與偏重規(guī)范性立場的哲學(xué)進(jìn)路之間形成持續(xù)的分野與爭論,已經(jīng)成為一種非常常見的學(xué)術(shù)景觀。前者從哲學(xué)與自然科學(xué)的連續(xù)性上立論,主張任何有意義的哲學(xué)思考都必須在本體論和方法論上追隨科學(xué)的教導(dǎo);后者則更多地繼承了早期分析哲學(xué)所謂“意義澄清”的工作籌劃,認(rèn)為存在著一個特殊的領(lǐng)域,自然科學(xué)的知識與方法在其中并不特別有助于哲學(xué)工作,這就是規(guī)范性議題的研究。類似的論證與爭論遍布于當(dāng)代哲學(xué)的許多領(lǐng)域,特別是在心靈哲學(xué)、知識論、科學(xué)哲學(xué)和元倫理學(xué)的研究中,一再地以各種改頭換面的方式反復(fù)呈現(xiàn)。
從學(xué)理邏輯上說,受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傳統(tǒng)影響的中國學(xué)者,在這場爭論中是不應(yīng)該缺席的。因為,從哲學(xué)上的自然主義到物理主義,再到唯物主義,存在著一條暢通無阻的學(xué)理路徑。馬克思本人在其經(jīng)典著作中所做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的工作,論證了人類社會中的上層建筑,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和法律等規(guī)范性的存在本質(zhì)上都不過是具體的生產(chǎn)方式、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產(chǎn)物。這既是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同時也是對規(guī)范性議題作出的自然主義解釋。然而,囿于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的差異,真正能夠從唯物論觀點出發(fā),在規(guī)范性與自然主義的爭論中提出一家之言的理論努力尚不多 見。
徐英瑾教授的新著《唯物論者何以言規(guī)范——一項從分析形而上學(xué)到信息技術(shù)哲學(xué)的多視角考察》 (以下簡稱“《唯論》”)就是這一方向上的杰出成果。縱觀全書,一方面徐英瑾充分利用了“從自然主義到物理主義再到唯物主義”這個暢通的學(xué)理路徑,引入分析形而上學(xué)的思想資源來豐富唯物論觀點;另一方面,他又用精致化了的唯物論觀點反觀規(guī)范性,對傳統(tǒng)的規(guī)范性議題提出解釋和思考,為這場爭論中的自然主義立場提供了新的辯護(hù)。
如果筆者的上述理解是正確的,那么,評判《唯論》這項工作的價值,就要看它對規(guī)范性議題的解釋是否深入和有效。全書寫作計劃非常宏大,筆者的考察將集中關(guān)注書中的兩個要點。一是《唯論》在解釋規(guī)范性方面的總體工作設(shè)想,即它對“唯物論需要怎樣的規(guī)范性理論?”這個問題的回答;二是《唯論》對一個具體的規(guī)范性議題的處理,即是否存在不能以非規(guī)范性詞項描述的“規(guī)范感”?①《唯論》書中實際討論的是“道德的感受質(zhì)”或“道德的主觀感受”。但嚴(yán)格說來,道德只是眾多規(guī)范性議題之一,而對它的感受質(zhì)問題并非特殊的,而是在幾乎所有規(guī)范性的方面,譬如遵從法律或交通規(guī)則等,都可以提出類似的疑問。因此,真正在規(guī)范性的理論層面提出的是有無特殊“規(guī)范感”的問題。對這兩個方面的討論將試圖較為完整地勾畫出一種唯物論的規(guī)范性理論,幫助我們較為具體地評判這一理論的內(nèi)涵與意義。
一、規(guī)范性理論的唯物論進(jìn)路
唯物論需要怎樣的規(guī)范性理論?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好問題。而這種探究首先依賴如何界定唯物論。在《唯論》一開始,作者便提出了一個“本體論范疇樹形圖譜”(見圖1),用以概括作出探究出發(fā)點的唯物論基本立場。具體說來,它將所有存在的事體(entities)分為三個框:甲框是只能做主項的具體存在物,包括事物、事件和“蘊相殊”(tropes)②通常多被譯為“特普”,是指普遍的屬性共相被當(dāng)作具體殊相的概念。例如,紅色一般來說是屬性共相,但此花的紅與彼花的紅又是不同的“特普”,所以一般意義上的“紅”只不過是眾多紅色特普的集合。(徐英瑾:《唯物論者何以言規(guī)范——一項從分析形而上學(xué)到信息技術(shù)哲學(xué)的多視角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頁) 《唯論》中采用“蘊相殊”對譯“tropes”,為保持一致,這里也采用此譯法。,乙框是既可以做主項也可以做謂項的抽象物,包括集合、命題與事物的“分體論之和”①按照《唯論》的說法,分體論之和是“一個整體的某些部分所構(gòu)成的和”,而這樣的加和關(guān)系“并不是諸實體所構(gòu)成的堆”(第35頁)。這意味著分體論和要求有某種整體論的關(guān)系存在,組分內(nèi)在地依賴于整體。(mereological sums),而丙框則是只能做謂項的共相,主要是指屬性和關(guān)系的存在。
按照徐英瑾的看法,上述甲、乙、丙三框的分類,實際上厘定出了唯物論—反唯物論之爭的概念空間。從唯物論的立場上說,甲框中的對象是最基本的,其他類型的存在物都必須或者被視作并不真實存在,或者被視作是甲框?qū)ο蟮倪壿嬔苌铩7次ㄎ镎撜摺貏e是柏拉圖主義者則必須視丙框為最基本的對象,而將甲、乙兩框的對象看作是衍生出來的存在物。所以,在“唯物論—反唯物論”的爭論中,乙框就是雙方膠著論爭的戰(zhàn)場,它并不是任何一方的基本盤,但又同時是任何一方都試圖爭取拉攏的“中間地帶”。“一種完善的唯物論或柏拉圖主義理論,也勢必應(yīng)當(dāng)努力將這個中介地帶中的本體論對象,化約為自身‘基本盤’的理論衍生物。”③同上書,第36頁。但是,不管是唯物論還是反唯物論,都不能否認(rèn)乙框的對象有其不可取消的相對獨立性。例如,作為乙框?qū)ο蟮拿}就有獨立評價的維度。我們可以僅僅立足于命題的層面上討論它的性質(zhì)、命題間的推論關(guān)系,而不需要介入唯物論—反唯物論的爭論。所以,完備的唯物論觀點還要為乙框?qū)ο蟮南鄬Κ毩⑿粤舫龊侠淼目臻g。《唯論》的這個本體論范疇框架對規(guī)范性理論尤為重要。總的說來,規(guī)范性的存在也是乙框的對象,因而它們也必須是甲框的邏輯衍生物,但同時又是相對獨立的,可以僅僅在規(guī)范性的層面上討論相關(guān)議題,而并不需要總是回溯到其唯物論的基礎(chǔ)上去。這樣的規(guī)范性理論才是唯物論所需要的。然而,從理論建構(gòu)上走到這一步,還需要更多鋪墊。其中一個必要的環(huán)節(jié),就是如何從描述跨越到規(guī)范。毋庸贅述,規(guī)范性問題的緣起就是“是”與“應(yīng)該”的二分,所謂“休謨的鍘刀”是也。如果這種二分可以從理論上被接受,那么意味著從“實際如何”的描述推不出“應(yīng)該如何”的規(guī)范性判斷;反過來,從“應(yīng)該如何”的判斷也無法揭示“事實究竟如何”。而《唯論》的上述本體論范疇都是分析形而上學(xué)的成果,其本質(zhì)就是要回答“在世界中實際上存在著什么”的問題。①徐英瑾:《唯物論者何以言規(guī)范——一項從分析形而上學(xué)到信息技術(shù)哲學(xué)的多視角考察》,第39頁。那么,這樣的范疇框架如何能夠運用于對規(guī)范性問題的討論呢?
徐英瑾的思路是,在回答“唯物論需要怎樣的規(guī)范性理論”之前,先要思考它需要怎樣的模態(tài)理論。這其實也是討論規(guī)范性問題的常見路數(shù)。描述性判斷不僅僅對規(guī)范性判斷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實際上,它與因果必然性或自然定律的判斷之間,也存在類似的鴻溝。如果我們僅僅描述了“世界上實際存在著什么”,那么似乎既不能由此推出“應(yīng)該怎樣”,也不能推出“必然”或“可能”怎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規(guī)范性與因果性、必然性、自然律等一起都屬于模態(tài)范疇。模態(tài)判斷區(qū)別于純粹描述性的判斷,因為對模態(tài)判斷的真假賦值,不僅需要考慮事實上的“世界是怎樣的”,而且更需要支持反事實條件(counterfactuals)的考察。譬如,如果“人不應(yīng)該說謊”為真,那么即便在謊言帶來利益的情況下,人也沒有理由說謊;如果“鈾235超過臨界質(zhì)量必然發(fā)生鏈?zhǔn)椒磻?yīng)”,那么這種必然性就體現(xiàn)在,假設(shè)月球是全由鈾元素組成的,那么月球的質(zhì)量也不能超過臨界質(zhì)量。不難想見,僅靠純粹描述現(xiàn)實世界的判斷無法決定上述反事實條件成立與否。
因此,對模態(tài)理論來說,最關(guān)鍵的是如何評價反事實條件的真值。徐英瑾認(rèn)為,對唯物論立場來說,恰當(dāng)?shù)哪B(tài)理論可以是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的“組合論”。按照這種觀點,模態(tài)屬性只不過是“在對世界的構(gòu)成要素進(jìn)行不同形式的組合之后所自動產(chǎn)生的衍生性性質(zhì)”。例如,對“必然性”這一模態(tài)性質(zhì),組合論可以解釋如下:“如果現(xiàn)實世界中存在著n個基本對象,那么這一點就是必然成真的:無論你如何排列這些對象,任何排列方式都不會導(dǎo)致少于n的基本對象數(shù)量。”②同上書,第58—59頁。換言之,盡管模態(tài)性質(zhì)并不直接由對現(xiàn)實世界的描述所決定,但模態(tài)性質(zhì)可變的界限卻是由現(xiàn)實的描述決定的。一方面,這種模態(tài)理論的確是唯物論的,因為模態(tài)存在作為“乙框”對象的確是“甲框”對象的衍生物;另一方面,模態(tài)判斷的相對獨立性也得到了保證,因為在現(xiàn)實世界厘定的界限之內(nèi),每一個模態(tài)性質(zhì)并不需要通過追溯其對應(yīng)的描述性質(zhì)而得以確定。基于這兩點,唯物論的規(guī)范性理論也就呼之欲出了。
二、規(guī)范性的功能主義解釋
當(dāng)代哲學(xué)對“規(guī)范性”的討論涉及諸多領(lǐng)域的話題。普通人一提到“規(guī)范”二字,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人不應(yīng)該說謊”之類的道德規(guī)范。但哲學(xué)上的討論要遠(yuǎn)遠(yuǎn)廣義得多。例如,規(guī)范性概念在心靈哲學(xué)上是心理表征的誠實性(veridicality)要求,在知識論上是對知識與真信念的辯護(hù)(justification)與保證(warrant),在科學(xué)哲學(xué)上是對科學(xué)研究作方法論上的“合理重構(gòu)”(rational reconstruction),等等。《唯論》特別強(qiáng)調(diào)的是認(rèn)知科學(xué)哲學(xué)的視角,“認(rèn)知”幾乎已經(jīng)涵蓋了包括道德判斷在內(nèi)的人類心智活動的一切方面,而《唯論》的工作就是致力于推進(jìn)一種“認(rèn)知科學(xué)化的規(guī)范性研究”①徐英瑾:《唯物論者何以言規(guī)范——一項從分析形而上學(xué)到信息技術(shù)哲學(xué)的多視角考察》,第63頁。。
基于這樣的認(rèn)識,徐英瑾在規(guī)范性理論方面主要借助了柏芝(Tyler Burge)在《客觀性的起源》中的論述。柏芝所討論的主要是心理表征的規(guī)范性。在他那里,規(guī)范性意義之所以存在,首先是由于存在著一種不同于生物學(xué)功能的“表征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而人們在表征功能方面做得好不好,完成到怎樣的水準(zhǔn),決定了心理表征的規(guī)范性意義:
某些完成的水準(zhǔn)也就是作為規(guī)范的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就是可能的行為表現(xiàn)的標(biāo)準(zhǔn),那些表現(xiàn)在某種意義上能充分完成某個功能或目標(biāo)。對任何功能而言,這種意義上的規(guī)范乃是先天存在著的。
有的規(guī)范是自然規(guī)范。我所說的“自然規(guī)范”,并不是指在自然主義的意義上可還原的規(guī)范,而是指某種行為表現(xiàn)的水平,它足以完成某個功能或目標(biāo),構(gòu)成了某種在解釋上相關(guān)的類型,且無關(guān)乎任何個體究竟是以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態(tài)度對待此功能或規(guī)范。②Tyler Burge, Origins of Objectiv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11.
所以,柏芝對規(guī)范性概念的刻畫,一言以蔽之,就是作為“功能實現(xiàn)的完成度”的標(biāo)準(zhǔn)。這也是通常容易被想到的自然主義解釋策略。的確,很多規(guī)范之所以成立就在于它們對實現(xiàn)某個目的或功能提出了標(biāo)準(zhǔn)和要求。例如,學(xué)習(xí)射箭時,你需要遵從教練提出的指導(dǎo)性規(guī)范,它們的意義就在于幫助你完成“射中靶心”的目標(biāo)。自然主義的解釋從中提取出“功能—完成”的模式,作為規(guī)范性存在的一般依據(jù),進(jìn)而拓展到其他非人類、非意識層面的功能實例。例如,正在捕食的老虎追逐它的獵物,胃的正常蠕動實現(xiàn)胃酸對食物的分解和消化,這些都是有目標(biāo)設(shè)定的功能過程,都有一個完成度標(biāo)準(zhǔn)的問題,因而也都存在柏芝意義上的“自然規(guī)范”。當(dāng)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類行動的規(guī)范都需要還原為非人類、非意識層面的自然規(guī)范,因為只有在具體的功能過程之中才有規(guī)范性的存在,而不同的功能從內(nèi)涵意義上說并不能相互替換。正如柏芝所強(qiáng)調(diào)的,表征功能并不是任何生物學(xué)功能,心理表征的規(guī)范性也未必一定有還原論意義的解釋。但這至少表明,所謂規(guī)范性的存在其實并不神秘,并沒有什么超越于自然主義—唯物論的意義。
在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科學(xué)解釋的討論中,有一個爭議性的話題就是“功能解釋是不是基于定律和因果性的科學(xué)解釋”。圍繞這一話題,科學(xué)哲學(xué)家在“功能”與“自然定律”“因果解釋”這幾個概念之間展開了復(fù)雜的辨析與推論。這里并不試圖深入呈現(xiàn)其中的復(fù)雜性,但回顧這些關(guān)聯(lián)有助于我們理解柏芝思路的另一個面向:功能過程并不能脫離定律與因果必然性而存在。以前面的例子來說,如何完成射中靶心的功能?老虎如何能追捕到它的獵物?胃如何能正常地發(fā)揮消化食物功能?顯然,要從科學(xué)上徹底解釋這些功能完成的可能性,就必須訴諸一系列具有因果必然性的關(guān)聯(lián):譬如,射出箭的速度與風(fēng)向、距離等環(huán)境因素的關(guān)系,老虎的加速度與周邊環(huán)境的配合,支持胃正常蠕動的自主神經(jīng)活動,等等。在這些必然性關(guān)聯(lián)的層面上,我們可以得到訴諸定律與因果性的解釋;與此相比,功能解釋則更像是一種限定范圍的理解。如果我們把解釋的努力限定在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tǒng),那么就有一個相對明確的系統(tǒng)目標(biāo):射中靶心、捕食獵物、消化食物,于是就有功能解釋。但如果我們的解釋并不預(yù)設(shè)任何系統(tǒng)目標(biāo),那么就會看到,所有功能解釋的有效性都需要定律和因果必然性的解釋提供依據(jù)和支撐。
如果上述理解是對的,那么規(guī)范性的意義依賴某種具體與之對應(yīng)的功能解釋,而功能解釋又進(jìn)一步地依賴定律和因果必然性的存在,所以規(guī)范性的概念也最終奠基于定律與因果性的概念。這其實也是規(guī)范性的自然主義解釋的大體歸宿。前面提到,規(guī)范性與因果性都是模態(tài)概念,并在這個意義上都區(qū)別于純粹的事實描述。然而,在自然主義—唯物論的解釋中,這兩種模態(tài)概念的地位是不對稱的。從解釋的優(yōu)先性上說,規(guī)范性的存在最終需要由定律和因果性的意義來解釋,反之則不成立。我們已經(jīng)看到,根據(jù)阿姆斯特朗的組合論觀點,任何因果必然性的模態(tài)性質(zhì)歸根到底仍然是現(xiàn)實世界要素組合的衍生物,所以,由這種模態(tài)性質(zhì)來解釋的規(guī)范性意義最終也是現(xiàn)實世界要素組合的衍生性質(zhì)的。需要注意的是,邏輯上的衍生并不必然意味著還原的可能性。因為,以“功能—完成”關(guān)系作為規(guī)范性與因果性之間的中介,并非可有可無,而是恰恰保證了規(guī)范性意義的相對獨立性:盡管功能解釋最終依賴定律與因果必然性的關(guān)系,但當(dāng)我們限定解釋系統(tǒng)的邊界時,我們的確可以面向所預(yù)設(shè)的系統(tǒng)目標(biāo),僅從功能上解釋現(xiàn)象,而不同的功能過程之間在內(nèi)涵層面無法被替代或還原。《唯論》針對柏芝的觀點也作出了類似的評論:
當(dāng)他[柏芝]說什么“心理學(xué)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為感覺系統(tǒng)的生物學(xué)功能的確與表征功能比較相近;心理學(xué)之所以有趣,又是因為前述兩種功能并不同一”的時候,他實際上想表達(dá)的,無非就是下面這層意思……“乙框”中的規(guī)范性描述之所以可能,乃是因為這種描述在所指的外延方面與“甲框”中的事實描述所指涉的外延足夠接近;而“乙框”中的規(guī)范性描述之所以有趣,乃是因為“甲框”與“乙框”各自的描述層次在內(nèi)涵方面無法彼此替換。①徐英瑾:《唯物論者何以言規(guī)范——一項從分析形而上學(xué)到信息技術(shù)哲學(xué)的多視角考察》,第65頁。
回到《唯論》一開始給出的本體論范疇劃分,唯物論解釋的基本盤是“甲框”的具體對象,而規(guī)范性的存在則是“乙框”中可主可謂的抽象對象。我們還曾說,完備的唯物論觀點一定要將乙框?qū)ο笞鳛榧卓驅(qū)ο蟮倪壿嬔苌铮瑫r又保證其相對獨立性,即可以僅僅在抽象對象層面談?wù)撘?guī)范性的存在及其相互關(guān)聯(lián)。由上可見,將規(guī)范性刻畫為“功能實現(xiàn)的完成度”的標(biāo)準(zhǔn)的確兼顧了這兩個方面。因此,它就是唯物論所需要的那種規(guī)范性理論。
三、因果與規(guī)范:何為優(yōu)先?
那么,這種規(guī)范性理論是否會有什么問題?以“功能—完成”的關(guān)系刻畫規(guī)范性,是否會有所遺漏?實際上,20世紀(jì)的美國社會學(xué)曾經(jīng)有過值得汲取的教訓(xùn)。20世紀(jì)60年代之前,美國的主流社會學(xué)是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結(jié)構(gòu)功能主義理論。功能主義將社會類比作生物有機(jī)體,認(rèn)為任何制度規(guī)范都必須從它保持并發(fā)展社會有機(jī)體的功能必要性上來解釋。在帕森斯的理論框架中,“結(jié)構(gòu)”與“行動”深陷于不平衡的關(guān)系,個體行動者的作用越來越被邊緣化,完全淪為實現(xiàn)制度結(jié)構(gòu)之宏觀功能的工具。因此,帕森斯的批評者指出,在功能主義綱領(lǐng)下,行動者不過是一個“傀儡”,他的存在僅僅是為了完成社會有機(jī)體運轉(zhuǎn)所必需的功能角色。
帕森斯功能主義中的“結(jié)構(gòu)”與“行動”的不平衡關(guān)系,與唯物論的規(guī)范性理論的一個要點是相互聯(lián)系的。這就是規(guī)范性與因果性在模態(tài)地位上的不對稱性,或者說是在自然主義—唯物論框架中,因果性相對于規(guī)范性概念具有解釋上的優(yōu)先地位。如果我們把“規(guī)范性”理解為個人行動上的合理意義,而把社會宏觀的結(jié)構(gòu)和功能看作是因果機(jī)制的體現(xiàn),那么模態(tài)地位上的不對稱關(guān)系立刻就被轉(zhuǎn)化為帕森斯那里的“結(jié)構(gòu)”與“行動”的不平衡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可以用于解釋行動,而行動卻不是結(jié)構(gòu)的解釋項。
當(dāng)代美國哲學(xué)家布蘭頓(Robert Brandom)是在規(guī)范性問題上建樹較多的學(xué)者。在他看來,由因果性解釋規(guī)范性的不對稱關(guān)系,甚至是由現(xiàn)實世界的要素決定模態(tài)衍生性質(zhì)的“組合論”觀點,都不僅僅應(yīng)該被放棄,而恰恰是應(yīng)該被顛倒過來:不是描述性質(zhì)決定模態(tài)性質(zhì),而是使用模態(tài)概念的能力決定了作出描述性判斷的能力;不是因果性在解釋上優(yōu)先于規(guī)范性,而是所有“真性模態(tài)”(alethic modality)①布蘭頓區(qū)分了兩種意義的模態(tài)概念。定律和因果性意義屬于“真性模態(tài)”的概念,而規(guī)范性的存在屬于“道義模態(tài)”(deontic modality)概念。的意義都取決于規(guī)范性的模態(tài)意義。這就是所謂的“康德—塞拉斯論旨”:
1.在普通經(jīng)驗詞項的使用中,人們已經(jīng)做了所有需要他們做的事情,以便引入并掌握模態(tài)詞項的使用。
2.真性模態(tài)詞項的特殊表達(dá)功能在于清晰闡釋語義的和概念上的聯(lián)系與承諾,這些聯(lián)系與承諾原本已經(jīng)隱含在普通經(jīng)驗詞項的使用之中。②Robert Brandom, Between Saying and Do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02.
布蘭頓主要討論的是語言哲學(xué)中的規(guī)范性話題,在他那里,規(guī)范性的存在主要就是概念間的語義關(guān)系與推論性聯(lián)系。布蘭頓自身又是實用主義在當(dāng)代的主要辯護(hù)者,這決定了他不會像分析形而上學(xué)那樣討論本體論問題,但當(dāng)布蘭頓試圖在不同類型的詞項使用之間確立秩序時,他的確是在考察具有本體論意義的優(yōu)先性關(guān)系。例如,在“康德—塞拉斯論旨”的第1項,布蘭頓實際上主張,模態(tài)性質(zhì)在本體論上優(yōu)先于經(jīng)驗中的描述性質(zhì)。這表明布蘭頓并不是唯物論者,他潛在地希望“乙框”對象作為“丙框”的而非“甲框”的邏輯衍生物,所以這對于唯物論的規(guī)范性理論并無特別的幫助。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第2項,它主張定律和因果性的模態(tài)性質(zhì)“表達(dá)”了規(guī)范性的語義關(guān)系,因而應(yīng)該用規(guī)范性的性質(zhì)來解釋定律和因果必然性,而不是相反。所以,在布蘭頓這里,是規(guī)范性而非因果性處于模態(tài)解釋上的優(yōu)先地位。這對唯物論的規(guī)范性理論來說倒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話題。
為了讓一個解釋深入和有效,解釋項必須站到被解釋項的“背后”,以便提供更深層的和有教益的(informative)的解釋。如何澄清這個“背后”的隱喻?在筆者看來,布蘭頓與《唯論》所詮釋的柏芝分別代表了兩種“站到背后”的路徑。在柏芝那里,這意味著追溯功能實現(xiàn)的鏈條。規(guī)范性意義是這個鏈條的起點,它之所以存在,乃是為了以某個標(biāo)準(zhǔn)完成相應(yīng)的功能目標(biāo),進(jìn)而任何功能目標(biāo)的完成都立足于某些普遍存在的定律與因果必然性。所以,因果性必須站在規(guī)范性的“背后”,因為若沒有這種必然性,我們就無法確立規(guī)范性的意義。
而在布蘭頓看來,這是要對使用各種概念從事語言游戲的能力作一種追溯前提的考察。在這種追溯中,定律和因果必然性不僅不是已經(jīng)在“背后”的解釋項,而恰恰應(yīng)該是追溯的起點。因為對因果必然性的概念把握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我們之所以具備使用這類概念的能力,恰是因為我們已經(jīng)知道如何利用它們開展有效的推理。例如,“鈾235超過臨界質(zhì)量必然發(fā)生鏈?zhǔn)椒磻?yīng)”,這是定律必然性,它意味著我們可以從“鈾235超過了臨界質(zhì)量”必然推出“馬上要發(fā)生鏈?zhǔn)椒磻?yīng)”的結(jié)論。概言之,定律與因果必然性這樣的模態(tài)判斷,在語言游戲中的實際功用,恰是表達(dá)了不同判斷之間“必然推出”的語義關(guān)系,而這正是規(guī)范性的存在。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規(guī)范性反倒站到了因果性的“背后”,因為它才是發(fā)展更豐富的語言能力的前提:只要我們開始使用概念、作出判斷、進(jìn)行推理,我們就已經(jīng)是在一個規(guī)范性的意義空間中生存和思考。
這兩種路徑的分歧與對立,就與對“規(guī)范感”的討論聯(lián)系了起來。《唯論》中具體討論的是主觀的道德情感,它本來就是眾多類型的“規(guī)范感”之一。主張“規(guī)范感”存在的人可能提出一個類似于心靈哲學(xué)“僵尸論證”的辯護(hù):可以設(shè)想物理層面與人類相同,而缺乏對規(guī)范性存在的“現(xiàn)象體驗”的哲學(xué)僵尸,而這樣的僵尸無法真正成為規(guī)范性行為的主體,所以生物學(xué)無法說明道德情感這樣的“規(guī)范感”。而對這一觀點的反駁也基本套用了物理主義對“僵尸論證”的反駁,也就是否認(rèn)哲學(xué)僵尸的可設(shè)想性:“我們很難相信:就兩個在見到孺子入井后就立即去伸手救援的人而言,如若兩者行為相同,在救人時所經(jīng)歷的神經(jīng)活動也相同,其中的一‘人’(即所謂‘僵尸’)竟然會缺乏‘惻隱心’而另一者則有之。”①徐英瑾:《唯物論者何以言規(guī)范—— 一項從分析形而上學(xué)到信息技術(shù)哲學(xué)的多視角考察》,第188頁。
從柏芝所代表的路徑上看,這一反駁是完全成立的。如果“規(guī)范感”只不過是對規(guī)范性存在的現(xiàn)象體驗,而所有規(guī)范性關(guān)系在功能上都依賴某些定律與因果必然性的奠基,那么只要我們從認(rèn)知科學(xué)中把握到這樣的模態(tài)性質(zhì),就沒有理由認(rèn)為它會在規(guī)范感方面有所缺失。然而,如果從另一條路徑上來理解,情況就稍有不同了。對布蘭頓來說,規(guī)范感并不僅僅是像“惻隱心”這樣的感受,而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它可以是對概念間語義推理關(guān)系的現(xiàn)象性把握,某種對人類話語實踐規(guī)則的模糊的體會。借助認(rèn)知科學(xué)的概念對神經(jīng)活動的描述和判斷,既是人類話語實踐的組成部分,也是對這種語義推理關(guān)系作清晰闡釋的努力,而規(guī)范感作為被因果必然性表達(dá)的東西反倒具有模態(tài)地位上的優(yōu)先性。所以,哲學(xué)僵尸的不可設(shè)想性恰好表明,只有以規(guī)范感——對神經(jīng)科學(xué)概念的語義關(guān)系的隱性把握為前提,我們才能具備使用這些概念并作出定律與因果必然性判斷的能力。
四、歷史唯物論的規(guī)范性理論:一種新可能
那么,我們有可能采納布蘭頓那樣的路徑嗎?不要忘記,《唯論》的目標(biāo)是建構(gòu)一種唯物論所需要的規(guī)范性理論,其中并未借助布蘭頓的工作,可能主要也是考慮這其實是反唯物論的思路。不過筆者認(rèn)為,似乎可以將“康德—塞拉斯論旨”的第1項與第2項分開來看,這樣把布蘭頓的解釋路徑從其反唯物論的立場中解脫出來,也并非不可能。因為我們所要建構(gòu)的并不是一般唯物論的而是“歷史唯物論”的規(guī)范性理論。
《唯論》其實已經(jīng)花了很多篇幅討論歷史唯物論,但主要是從分析形而上學(xué)的視角為歷史唯物論提供本體論的基礎(chǔ),卻沒有特別將這一思想資源引入對規(guī)范性理論的討論中,殊為遺憾。筆者并非馬克思哲學(xué)的專家,但就愚見所觀,歷史唯物論區(qū)別于一般自然主義—唯物論立場的精彩之處,就在于它為“個體—整體”“行動—結(jié)構(gòu)”的張力關(guān)系提供了內(nèi)涵特別豐富的闡釋。一方面,歷史唯物論像所有唯物論立場一樣,強(qiáng)調(diào)個人受制于整體,行動限定于結(jié)構(gòu)——用《唯論》的語言說,就是所有乙框的對象都只是甲框具體對象的邏輯衍生物。但另一方面,歷史唯物論又肯定了這樣的可能性:具有特定特征的個體——無產(chǎn)階級——的行動能夠重塑結(jié)構(gòu)與整體,因為這樣的個體能夠?qū)ⅰ芭械奈淦鳌鞭D(zhuǎn)化為“武器的批判”,即是將規(guī)范性的存在重塑為現(xiàn)實世界中可以描述的具體性質(zhì)或?qū)ο蟆?/p>
不難看出,歷史唯物論的后一個面向很容易與布蘭頓的解釋路徑相聯(lián)系,因為它們都可以承認(rèn),對規(guī)范性關(guān)系的把握的目的在于獲得變革現(xiàn)實世界的能力。當(dāng)馬克思批評哲學(xué)家們只是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時,他更是實質(zhì)性地接近了這個思路。但歷史唯物論的解釋畢竟不同于布蘭頓的反唯物論立場,因為通過對規(guī)范性存在的把握實現(xiàn)的只是對世界的革命性重塑,而不會是從無到有的創(chuàng)生。用《唯論》的話來說,“乙框”中的任何規(guī)范性存在都不過是“甲框”要素排列組合的產(chǎn)物,其基本可能性不會超出本體論上多重組合的可能性。但“武器批判”的革命性恰恰在于,由于意識形態(tài)或“虛假意識”的存在,某些重要的“組合可能性”已經(jīng)被默認(rèn)為不可能了,只有通過對乙框中規(guī)范性關(guān)系的把握,才能將這種被壓抑的可能性重新召喚出來,而這就是對世界的革命性重塑和全人類解放的實現(xiàn)。
筆者不得不說,就一種歷史唯物論的規(guī)范性理論而言,類似的話題還有必要繼續(xù)延伸下去,但對《唯論》的評論卻可以止步于此了。事實上,話題延伸的可能性已經(jīng)揭示了《唯論》這項工作毋庸置疑的價值。如果說還能從方法論上作一點批評的話,我愿意提及這樣的觀察:自馬克思創(chuàng)立歷史唯物論學(xué)說以來,很多人都說馬克思本人用力甚多的是“上半截子的唯物主義”,但還需要“下半截子唯物主義”的補充,也就是本體論存在論的部分。從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到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jīng)驗批判主義》,都是在嘗試做類似的工作。《唯論》似乎也在同樣的方向上提供補充,只不過它更多地借助分析形而上學(xué)的當(dāng)代成就。但我們還必須看到,也有很多人并不贊同這種分“上半截子”與“下半截子”的解讀方式,因為歷史唯物論并不是唯物論原則在社會歷史領(lǐng)域的簡單應(yīng)用,而毋寧說是馬克思哲學(xué)革命后的成熟形態(tài)——它本身就是新哲學(xué)的成熟本體論。這種解讀也未必見得完全正確,《唯論》中也確實指出了其中的偏頗與疏漏之處①徐英瑾:《唯物論者何以言規(guī)范——一項從分析形而上學(xué)到信息技術(shù)哲學(xué)的多視角考察》,第70—71頁。,但就規(guī)范性問題的討論來看,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