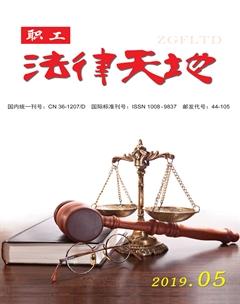盜竊三輪車內熟睡被害人的財物是否構成扒竊
金翔翔
扒竊犯罪在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甄別難題,現有規定不能完全現實案件。筆者試以案例更加深入辨析扒竊的各項實質構成要件。
案例:2018年某日凌晨2時許,被害人張某在駕駛三輪車過程中產生倦意,就將車子停在馬路邊,車門未上鎖,手機放在車內的前擋風玻璃處,自己就坐在三輪車的駕駛座上睡著了。清晨4時許,犯罪嫌疑人李某散步時趁被害人睡著之際,從張某三輪車車窗內伸手進去盜竊其手機。案發后經鑒定,該手機價值人民幣98元。
公安機關認為李某行為系扒竊構成盜竊罪,移送審查起訴。但檢察機關認為,三輪車是交通工具,三輪車內部非公共場所,除非將三輪車整體視為可隨身攜帶的財物,但顯然不是,故不構成扒竊,作出不起訴決定。還有意見認為被害人處于熟睡狀態,對近身財物的控制力減弱,一般不認為是隨身攜帶的財物。
該案的爭議焦點:一是在公共場所的三輪車車廂內能否認為是在公共場所,二是被害人處于睡著狀態下對財物的控制能力減弱,近身財物還能否認為是隨身攜帶的財物。
一、筆者認為三輪車廂是一個相對隔離于外界環境的半封閉空間,不能視為公共場所
1.公共場所的定義和特征
《刑法》第291條“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對公共場所的定義采用列舉式的定義,即“車站、碼頭、民用航空、商場、公園、隱劇院、展覽會、運動場或者其他公共場所”。其基本具有人員的高流動性、密集度,人員相互間的陌生性,活動的公開性等特征,符合公眾對公共場所的常情常理認知。這是一個客觀判斷標準,認定不隨時間和人數的變化而改變其應有屬性,比如夜間的網吧或者公共汽車,并不因為夜間、人數稀少而改變其應有屬性。
2.為何主張在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
筆者認為該立法考慮的因素,是實踐過程中的打擊障礙和打擊緊迫性。第一,陌生人之間有個安全距離的概念,特別是在公共場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被害人會保持警惕心,這就要求扒竊行為人具備技能和膽量,反映其主觀惡性;第二,較常會有共同犯罪,盜竊與掩護相配合容易既遂;第三,扒竊人會隨身攜帶案工具,在公共場所可能會有不特定人員的人身傷害;最后,就是該作案行為的習常性,這本來也是盜竊犯罪的通性,以行為人刑法來看待,就是這類行為人通常具有工作惰性,容易陷入犯罪循環圈。而相比在非公共場所區域發生的盜竊,比如封閉的單位大樓、戶內、轎車內,被害人因為有安全的空間感,對財物的持有警惕心會下降,作案相對容易,原本的盜竊罪名能夠在刑法范圍起到應有作用。
3.三輪車車廂非公共空間
本案案發地理位置在市區街道屬于公共場所,雖然案發時間在清晨,但公共場所的屬性不因清晨、人跡較少發生改變。
車主在車內休息期間,車輛未上鎖,車窗打開,仍屬于有一定與外界阻擋,但未與外界完全隔離的狀態。公安機關認為犯罪行為發生在公共場所,可以是在公共場所一個較小的私人控制的空間內。本案被盜財物在改裝的三輪摩托車內,車窗敞開,任何行為人在路上就可以完成盜竊行為,符合扒竊標準。公安機關混淆了私人控制空間的理解,將他類案件的概括直接推論及本案。以往認定公共場所一個較小的私人控制的空間,是在于私人控制的空間被人所攜帶,依托于人的攜帶行為,認定了扒竊,而三輪車并不能被攜帶,這已經超出了攜帶的語義范圍。
筆者分別從公共場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兩個角度論述三輪車廂不屬于公共場所的理由:
本案中盜竊實施行為人確實立足在馬路上這個公共空間,但他的肢體通過三輪車窗伸進了相對隔離的三輪車空間內,被害人在三輪車空間內,發生的盜竊行為仍舊是在車內。評價一個空間是否是公共場所的延伸,要視其依托的中介,舉一個在鬧市區戶的例子,不能因為有門未關而延伸了公共場所范圍,認為戶內也能視為公共場所,同樣,三輪車與鬧市區不能因為未關窗而融為一體。此外,行為人在路上并無構成對他人人身安全的現實緊迫威脅這個實質性的評判標準。即使在鬧市區一個住宅發生盜竊貼身財物的行為,仍然因為房屋的空間相對隔離不構成扒竊。因此,該案中三輪車是一個相對阻隔于公共場所的空間,伸手進三輪車廂也不能認為是在公共場所行扒竊。
從公共交通工具角度分析。三輪車在營業期間被評價為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的認定不做是否開窗的區別。雖然三輪車本來是一個針對人群不確定的交通工具,但三輪車承載人數有限,區別于公共汽車承載能力,不能視為公共交通工具,司法解釋已經規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盜竊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才能認為是扒竊。
二、第二個問題,筆者持肯定意見,被害人意識狀態減弱不影響對隨身攜帶財物的認定
1.“隨身攜帶財物”的認定標準
司法解釋出臺后,“隨身攜帶”在具體案件中的適用,理論與實物界爭議較大。張明楷主張“在火車、地鐵上竊取他人置于貨架上、床底下的財物,均屬于扒竊”[1]。對此,兩高認為“對于被害人攜帶,但不隨身攜帶,而是放在觸手難及地方的財物,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放置在行李架上的財物,不應認定為隨身攜帶”。但最高法持“貼身說”,最高檢持“近身說”。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否危及人身安全,與距離人的身體遠近并沒有直接的正比關系[2]。2015年浙江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公安廳印發《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見》,司法實踐就引用了“隨手可及或者觸手可及”的近身說,運用常情常理來判斷財物與人身的“一體性”。該爭議在實踐應用暫告一段落。
2.被害人意識減弱是否影響對“隨身攜帶”的認定
有觀點認為,被害人熟睡對近身財物的控制力減弱,改緊密控制為松弛支配,脫離了近身的原有之意,一般不認為是隨身攜帶的財物。筆者對此有不同的意見。一是從刑事政策與司法實操性角度,無法提供甄別的明確標準。二是,人的睡眠分為非快速眼動(NREM)、快速眼動(REM),兩者交替一次即完成一個睡眠周期。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覺醒,通俗說,有的人睡覺警覺,他人的手伸到身邊就會醒來。而深度睡眠的人,即使伸手從其懷中掏取財物也不會致其醒來。盜竊行為人和司法工作人員不可能判斷被害人是否熟睡,只能看到睡著的模樣,據此是無法判斷被害人是否處于意識減弱,控制力明顯削弱的程度。故不能也沒必要就行為人的睡眠程度差異來區分是否減弱控制能力以及程度。
綜上,筆者認為盜竊鬧市區三輪車上熟睡車主的觸手可及財物不能認定為扒竊。
參考文獻:
[1]張明楷著.刑法學[M].第四版第881頁,法律出版社,2011年10月.
[2]車浩.竊取他人騎行電瓶車車籃內的財物是否屬于扒竊[J].刑事實務,第4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