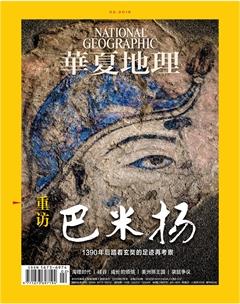硅谷在成長(算是吧)
米歇爾·奎因 黃秀銘譯

在圣克拉拉的一次“黑客馬拉松”編程集會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學生靠零食、能量飲料和健怡汽水提神,為開發一款供攝影師使用的增強現實應用程序出謀劃策。
停車場里有12個電動車充電站,特斯拉司機們爭先恐后地搶位。這是在計算機歷史博物館,前廳聚集了一大群人,多半是男性。有些人互相擁抱致意。有個人向房間另一頭的什么人喊了一嗓子:“我的投資怎樣啦?”鐘聲響起,我恍惚間好像置身教堂。喧鬧的人群魚貫進入禮堂。門一扇扇關上,演示日即將開始。
在接下來兩天里,來自132家初創公司的企業家們就如何改變世界發表了經過精心排練的兩分鐘演講。原來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多得數不清:養老院臥室天花板上的雷達傳感器,檢查公用設施線路的無人機,為貨運公司設計的機器學習,針對男性的洗衣用品訂購服務。
創業孵化公司“Y組合子”首席執行官兼合伙人邁克爾·賽貝爾告訴硅谷的投資者們,平均下來每個演講日會產生一個日后規模上十億美元的公司。“你的任務是判別哪個創意會中彩。”他的公司專門幫助創業者開發創意。
第一個上場的項目是“公共休閑”,創意是為訂購其服務的用戶組辦集體健身活動,場地選用停車場和其他開放空間。人們紛紛鼓掌的時候我在想,這市場夠大嗎?怎樣應付雨、雪、蚊蠅?但緊接著,下一個了不起的創意已經上臺——使用預測算法優化港口集裝箱。會場靜了下來,是一種出于敬意的安靜。
作為記者,多年來我一直在寫關于硅谷的文章。見多不怪,我已經學會不再一聽到匪夷所思的創意就啞然失笑。我曾經斥之為兒戲的一些初創公司如今已經賺了幾十億,它們推出的產品或服務我以前壓根兒沒想到會有人需要。如果A計劃不靈,“公共休閑”就轉而采用B計劃,直播平臺Justin.tv就是這么干的:它最初只直播賈斯汀一個人的無厘頭搞怪,接下來擴展到隨便什么人的搞怪,然后變身為游戲視頻社區Twitch。2014年亞馬遜公司以9.7億美元的價碼將它納入麾下。
長期觀察硅谷的保羅·薩佛說,硅谷是一個總在“遁入未來”的地方。在演示日,創業者們描繪著一幅因為無處不在的人工智能、增強現實、機器人、無人機和傳感器而變得更加美好的生活畫面。

蘋果是第一家價值萬億美元的美國上市公司,在硅谷開創先河,并在持續擴大其影響力。蘋果設在庫比蒂諾的新總部大樓于2017年投入使用,人稱“太空船”。大約有1.2萬名員工在那里工作,不到蘋果灣區陣容的一半。最近,蘋果公司一直在對硅谷提出批評,強調保護客戶隱私的重要性,抨擊某些科技公司的做法。
硅谷的樂觀主義和使樂觀精神長盛不衰的務實夢想家們一直令我著迷,但近來卻出現了某種迷夢知返的趨勢。
“責任”和“共情”是最新流行語。硅谷知道,人們正在把一切變化歸因到它頭上:勞動力的人口結構特征,被顛覆的傳統產業,技術帶來的失業之痛。連一些年薪六位數的工作人員都為高房價或高房租所困。在世界其他地方如玻利維亞,新型電子產品暴增所推動的鋰礦開采引起人們對資源剝削和環境污染的擔憂,而那些產品正是硅谷的發明。
技術主宰未來,但業內之人也不得不勉強承認:有時我們的初心是為了讓事情變得更好、更有效率,但執行中難免有人會受到傷害。
安妮·武伊齊茨基說:“我們身邊盡是胸懷大志的人。”她是個人基因組學生物科技公司“23和我”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硅谷的現狀是順應歷史流向的——不管我們喜不喜歡,世界已經變了。我認為,對于所有受到轉變沖擊的地方,我們都有一份責任。”
人人心懷夢想
外地人常常問我:“硅谷在哪兒?”硅谷沒有首府,沒有發源點。山坡上沒有好萊塢式的醒目標志宣示“高科技城在此!”硅谷是一片馬蹄形的平原,布滿辦公室和居民區,東邊和西邊有一些不高的山脈。在硅谷的中心地帶,舊金山灣碧波蕩漾。我把臉書公司的大拇指“點贊”標識指給來客們看——在該公司不斷擴建的總部外面一眼就可以看到。臉書不對訪客開放參觀,大多數科技公司也一樣。
當然,“點贊”標識也許并不讓每個人都開心。據悉臉書的數據政策未能保護好用戶,因為一名研究人員將個人信息出售,隨后有人利用這些信息向用戶發送政治廣告。俄羅斯特工還把臉書用作宣傳工具,在美國煽動政治紛爭。硅谷科技的中心可能是山景城的一個住所,晶體管的發明者之一當初在這里創辦了公司。蘋果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曾專程拜訪此地,只為觸摸一下那棟房子,見證歷史標記。中心也可以是在洛斯阿爾托斯一條死胡同的住宅里,一名印度裔軟件工程師晚上把孩子們安頓上床,然后回到網上繼續籌劃創業。或者,中心竟是斯坦福大學附近停放的一輛房車,四個輪胎有三個是癟的,從海軍陸戰隊退役后做勤雜工的吉姆和他的狗住在車里,每天只能用濕紙巾擦洗身體。
我曾經斥之為兒戲的一些初創公司已經賺了幾十億,它們推出的產品或服務我以前壓根兒沒想到會有人需要。
如今的硅谷與1982年相比,景象已大不相同。當年,《國家地理》雜志曾描繪硅谷“放任自流的平等主義取代了鄉村的生活節奏”,并說“這種動態增長發生在一個看似平靜的外表后面……一片 單調的低層長方形建筑物,各家公司的名牌賣弄著高科技詞匯的雜燴,很難看出建筑物里面在干什么。”
周圍山坡上道路蜿蜒,鹿低頭吃草,令人不禁遐想此間人們鄉村生活的閑適節奏。這個山谷曾有多座杏、李果園,而今年剛剛見證了一個地標性水果店的關閉,大蕭條期間于圣何塞創立的“果園五金器具”(連鎖店也已經關門大吉。盡管如此,硅谷仍然可能騙過你的眼睛:這里的氣氛看起來平等、開放、隨意,首席執行官穿著連帽衫,風險投資人穿著自行車緊身短褲,隨性之舉隨處可見,比如工作場所要求人們脫鞋,或允許員工帶狗上班。
但硅谷對它的勃勃雄心毫不輕忽。24歲的特里斯坦·馬提阿斯抱怨道:“人們只對你的初創公司感興趣,你叫什么名字才沒人在意。”
硅谷如今的吸引力肇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那時我以一名記者的身份來到這里,還感覺這地方有點死氣沉沉。冷戰結束后國防工業衰落和經濟衰退導致了整個加州的裁員潮。當時的熱門產業類別是多媒體光盤和電子游戲。
一個想法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傳播開來:如果人們可以憑借計算機互聯,生活就會隨之改變。“美國在線”公司問世,推出數字商城,人們可以上網買花。其服務反應遲緩,難以使用,但一件意義非凡的事物已經初露端倪。
在北邊的西雅圖,一場派對就要開場。微軟公司正在使計算機大派用場,并因此財源滾滾。1995年8月,微軟就像一場贏家通吃的技術競賽的勝者,高管們午夜時分在電器商店外面跳舞,慶祝Windows 95操作系統推出。與此同時,一枚“炸彈”正在硅谷引爆。
網景公司造出了供用戶在互聯網上游逛的瀏覽器軟件,并在其標志性產品發布不到一年后上市。盡管網景是一家尚未證明自己實力的公司,警示投資者的風險概述占了好幾頁,其股票仍在開盤日收于58.25美元,使公司的即時市值高達29億美元。
網景首次公開募股(IPO)是互聯網熱潮的開端,大潮中,人們見證了亞馬遜和雅虎等偉大公司的誕生,也目睹了若干公司的倒閉。
互聯網上可以做的一切——賣化妝品、租卡車、找約會對象等等——令人激動,進而引發了投機性股票市場。僅1999年就有四百多家公司上市,其中大多數是科技股。
接下來的2000年,市場崩潰。二十多萬個工作崗位被淘汰。
尷尬。痛苦。然而,“所有那些初創公司都是對的,”蘋果聯合創始人沃茲尼亞克告訴我,“關于互聯網能為人們做些什么。但問題是,人們的生活方式不能那么快改變。”
對于如何把壞事變好事,硅谷有自己的一套說法。“迭代”意味著先讓產品進入市場,即使其并不完美——微調的事可以過后從容進行。“戰略轉向”(要面不改色地說出來)表示趁錢還沒燒完趕緊改變經營方向。
失敗和挫折為新創意和后來者掃清了道路。谷歌占據了“硅圖”原址的一部分,后者是一家計算機公司,其聯合創始人參與創立了網景。臉書在擴展地盤的過程中改造了曾經的“太陽微系統”園區。把互聯網和電視連接起來的努力遇到過重重難關,然后來了油管視頻。

喬書亞·卡彭蒂爾是帕洛阿爾托一家初創企業的員工,在由“游戲場全球公司”提供的辦公室上班,可以坐在游樂區工作。場地提供方資助并支持初創企業開發新技術,重點是人工智能。卡彭蒂爾說:“我上班時堅持每天去滑一次滑梯,提醒自己要享受樂趣,別把手頭的事看得太嚴肅。”去年10月單位裁員30%,卡彭蒂爾也被下崗了。
社交媒體時代來臨。臉書的聯合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搬到帕洛阿爾托,用黑客信條“行動迅速,打破常規”來發展公司。在舊金山,一群朋友和同事找到方法,讓人們能隨時用140個字符進行消息更新,推特由此誕生。
硅谷的洪流掩蓋了個人的遭際。對許多人來說,創新帶來的巨大“創造性破壞”周期不是從10公里外觀察到的現象,而是個人層面上的切膚感受。失業,技能過時,家庭傾覆。
蘋果提供了另一個模板:復出。1997年,在蘋果收購了史蒂夫·喬布斯創辦的另一家公司NeXT之后,喬布斯重掌帥印,蘋果隨之開始緩慢復蘇。公司發布了iPod,繼之以數字娛樂商店iTunes。iPhone于2007年推出,兌現了十多年前做出的智能設備承諾。快進到今天,科技公司正想方設法解決高科技對人們生活的巨大沖擊所帶來的問題。它們的掌門人被召集到美國國會,就客戶數據的使用、境外分子如何利用重要技術擾亂選舉、控制人們所見信息的算法中的潛在傾向性等問題作證。
隨著人工智能——學習像人類一樣思考的計算機——的出現,數據和計算速度已經成為最重要的資源,正如舊時代的石油。如果計算機有一天能“思考”并做出決策,世界會怎樣?
“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近旁,100萬美元一棟的房子正在興建。”——保羅·貝恩牧師
在三千多名谷歌員工簽署抗議信后,該公司決定不續簽與國防部合作使用人工智能來分析無人機圖像的項目合同。隨后在11月,全球兩萬名谷歌員工罷工抗議公司對性騷擾和薪資公平問題的處理。“銷售力”軟件公司在與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署的合同遭到批評后,設立了“符合倫理和人道的技術使用辦公室”。
我拜訪了斯坦福大學前校長約翰·亨尼西,他現在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董事長,人很隨和,但少了學術界人士常有的那份放松。他說,科技行業目前經歷的“報應”引來更深層次的問題——關于硅谷存在的意義。
“現在的棘手事情是,各個公司要考慮如何承擔責任,對公司的治理不僅要符合股東利益,還要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他說。
創業生活
外地的年輕人不斷涌入。
“坐在咖啡館里,聽見鄰座在拉投資,或一幫人大侃加密貨幣和谷歌,諸如此類的東西會讓一些人生厭,但我喜歡。”來自紐約州北部的產品經理施麗婭·內瓦蒂亞說道。她從塔夫茨大學畢業后離開了波士頓。
在一個林木蔥蘢的帕洛阿爾托社區,喬舒亞·布勞德坐在后院泳池邊。2004年夏天臉書開始流行時,老板扎克伯格就住在那里。房子里面,布勞德的幾個同事坐在餐桌旁,調試他公司的手機應用DoNotPay。這個程序扮演機器人律師的角色,能就停車罰款單提出抗辯,或尋找航空公司和酒店預訂的價格漏洞。但這只是黑客式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工作、吃飯、睡覺全在一個地方,一切只為盡早推出產品。在科技公司傳奇中,過去和現在交織在一起——人們生活、工作、向科技公司投資。沃茲尼亞克是一位廣受歡迎的演講者,每年收到超過一千份邀請。他的吸引力部分在于,他是硅谷最被人津津樂道的蘋果公司發家史中“另一位史蒂夫”。他經常復述一個故事:1980年公司首次公開募股時,他以IPO前的便宜價格把自己的部分蘋果股票賣給了80名員工。
他說:“我很在意財富的分配。”
“兄弟文化”經久不衰
如今,硅谷也不妨稱為移民谷。外國裔的涌入有助于抵消人才向美國其他地方的流出。在一些領域,如計算機和數學,外裔員工現在占60%以上,78%的女性員工生于他國。印度人、中國人、越南人是該地區科技行業的主要外國人群體;2015年硅谷的技術崗位有42人來自津巴布韋,106人來自古巴。
硅谷的國際性意味著這里的公司不論大小,已經成為諸多文化和語言的融合體。但這也凸顯出哪些人沒有實現硅谷夢。平均而言,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國人加起來只占主要科技公司勞動力的12%。在所謂的硅谷“兄弟文化”中,女性所占比例也非常低:谷歌、蘋果和臉書的員工中,女性僅略多于30%。2018年9月發布的一項調查發現,女性僅占初創公司創立人的13%,持有創始人股權的6%。
但女性獲得的支持在逐漸增加。根據非營利組織AnitaB.org對80家美國公司的調查,2018年女性占技術崗位的24%,公司領導層的18.5%。
在薪酬方面,招聘公司Hired的一份報告顯示,在超過60%的情況下,從事科技行業的女性在相同職位上獲得的薪酬低于男性 (平均差距為4%)。各大科技公司表示,他們樂意擁有更多樣化的團隊,但是很難一下子改變員工的人口結構特征。
“我曾經聽到年輕女性說硅谷對女性很苛刻,她們是咬緊牙關才挺下去的,” 產品經理施麗婭·內瓦蒂亞一邊喝茶一邊告訴我。她創建了一個名為“紫色社會”的團體,幫助女性和非二元性別人士在闖蕩科技領域的頭十年里創業。她對男性的廣泛人際關系網很感興趣,這種關系在大學期間通過同學、室友關系建立起來,并在早期職業生涯中得到發展鞏固。通過看似偶然的聯系建立起來的公司,實際上是經由這些人際網絡產生的。“我們需要更多女性來促成或然事件發生,”內瓦蒂亞說。
在繁榮的重壓下
隨著外來人口持續涌入硅谷,推高房地產和租賃價格,許多游離于科技經濟之外的人——也包括一些身在其中者——發現生活變得日益艱難,主要原因是居住成本上漲。
東帕洛阿爾托可能比什么地方都更難擠進去。這是一個擁有大約3萬人口的城市,夾在令人生畏的鄰居中間:北倚臉書,南臨谷歌。過去50年間,此地大體上是一個非裔和拉丁裔家庭雜居的城市。現在許多新家庭正在搬進來,很多是白人和亞洲人。據地產數據平臺Zillow統計,此地的房價中位數已經超過100萬美元——而2011年是26萬美元。100萬美元,在這座從舊金山延伸到圣何塞的半島,已經算是比較可以負擔的住房價格。
對許多居民來說,他們并沒有從當前的科技繁榮獲益,租金一再上漲,而購房根本沒有可能。許多人只好搬到遠郊,上下班要開車幾個小時。或者,干脆撤離這一地區。“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旁,100萬美元一棟的房子正在興建,”牧師保羅·貝恩斯說。他和妻子謝麗爾在東帕洛阿爾托經營一家非營利救助機構。
帕特里夏·卡特住在東帕洛阿爾托,有一大家子人:已經成人的兒子和他自己的三個年紀都在四歲以下的小女兒,她女兒,再加上兒子的前配偶——也就是三個小女孩的母親,眼下租住在她家車庫里。帕特里夏是個運貨卡車司機,2003年以44.7萬美元買下這棟三居室住宅,后來險些因付不起按揭而被銀行收回拍賣。
“Y組合子”首席執行官邁克爾·賽貝爾認為,如今硅谷已經發生了屬跨代性質的轉變。較年輕的從業者希望公司雇傭的員工更加多樣化,在公司運營中體現更高的社會良知。
賽貝爾的目標是什么?從耶魯大學畢業時,賽貝爾打算在二十來歲時掙錢,三十來歲時養孩子,四十來歲時從政。他2006年搬到舊金山,創立了一家公司。他曾是Justin.tv和Socialcam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后者在2012年出售給歐特克公司,而Justin.tv最終變身為Twitch。現年36歲的賽貝爾剛剛成為父親,但從政已不在計劃之列,他覺得現在的身份擁有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如果硅谷有其精神中心,那可能就是互聯網檔案館,它是設在舊金山一座前教堂里的非營利組織。在那里,服務器日夜不停運轉,以多種形式將無數公共網頁存檔。維基百科的幾乎每篇文章,每天大約400萬條推特,每周逾50萬個油管視頻。該館已經歸檔了超過3400億個網頁,堪稱互聯網的失物招領處。
在檔案館大廳散布著超過120尊1米高的塑像,紀念為該館貢獻了至少三年時光的人們。互聯網的兵馬俑。這個場景既詭異又極具震撼力,其中一些人我能叫出名字。
栩栩如生的群像有點瘆人:有的手里拿著書,有的端著杯子,有的抱著吉他,仿佛被來訪者打擾前正在做項目或飆歌;又或者,是在爭論接下來怎樣做才問心無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