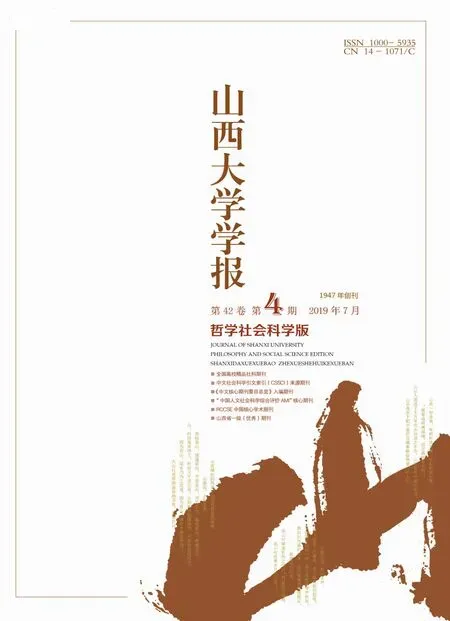維特根斯坦式寂靜主義:解讀與批判
陳常燊
(山西大學 哲學社會學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 引言
人類思想史上的“寂靜主義”(quietism)具有多種不同形式:亞伯拉罕傳統、基督教神秘主義、伊斯蘭政治寂靜主義、中國道家寂靜主義等。本文聚焦于一種相對狹義的“哲學寂靜主義”(philosophicalquietism)版本,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哲學所引發的:語言的本質及其與世界的關系問題,通常被視為語言哲學的基本問題;作為當代語言哲學的一個思潮,寂靜主義者在諸如語言本質及其與世界之關系問題上的看法,明顯地與后人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的解讀密切聯系在一起。然而,考慮到寂靜主義是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的諸多解讀方法之一,況且還是其中富有爭議的一種,他本人又從未直接使用“寂靜主義”一詞定位自己的哲學,因此不便稱之為“維特根斯坦的寂靜主義”(Wittgenstein’s quietism),而只是一種“維特根斯坦式的寂靜主義”(Wittgensteinian quietism)。此外,我們將會看到,維特根斯坦式的先驗進路為我們理解寂靜主義提供了一道絕佳的風景,而某些經驗視角則對之提供了必要的補充,最終拓展和豐富了我們在語言的本質及其與世界之關系問題上的寂靜主義觀點。
二 寂靜主義的哲學特征
首先我們來看“維基百科”對寂靜主義的權威解釋:哲學上的寂靜主義是一種看待哲學的方法,它把哲學的作用視為廣泛地診斷性或治療性的;寂靜主義的哲學家們認為哲學沒有積極的論點可以作出貢獻,認為它的價值毋寧在于消除包括非沉默主義哲學在內的其他學科的語言和概念框架中的混亂;通過以一種使錯誤推理顯而易見的方式重新表述假定的問題,寂靜主義者希望終結人類的困惑,并幫助恢復理智的安寧狀態。[1]
在筆者看來,這個觀點簡直是為維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學治療學”(philosophical therapeutics)量身定制的,盡管沒有直接提及維特根斯坦的名字。也許有人會說,作為一個簡明扼要的定義,它仍然可能忽視了某些更進一步的細節,譬如它未能考慮到維特根斯坦前期哲學中的寂靜主義特征。此外,即便僅就其后期哲學而言,“沒有積極的觀點”(no positive thesis)這樣的說法也應當有所限制。對此,威廉·恰爾德(William Child)的觀點可以補充進來,他認為,緊縮論(deflationism)或寂靜主義是這樣一種哲學立場:它“從字面上看待現象”(taking phenomena at face value),承認它們具有我們通常認為的那些特征,但拒絕任何一種通過訴諸哲學理論來解釋這些特征的企圖。維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學常被視為某種緊縮論或寂靜主義。一些評論家認為,《邏輯哲學論》對形而上學問題也采取了緊縮論的態度[2]261。
就其拒絕任何一種理論化企圖而言,寂靜主義哲學的確并不急于提供任何一種“積極的觀點”,但它同時堅持的“從字面上看待(語言)現象”,本身仍然是一種“觀點”,盡管它不像理論化企圖那么“積極”。舉例來說,《邏輯哲學論》反對就自我與世界本質、邏輯形式以及“神秘之域”提供任何一種積極的觀點,后期他在《哲學研究》中圍繞遵守規則的悖論,同樣拒絕任何一種積極的觀點。但在筆者看來,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治療學,內涵并不限于此。我們未必能在其前期哲學中領會到什么叫“從字面上看待現象”,但不管如何它都是維特根斯坦式寂靜主義的應有之義。
類似地,托馬斯·赫卡(Thomas Hurka)認為,維特根斯坦主義者的這種沉默態度,是“堅決反技術的和反理論的”[3]249,“他們否認(常識的)道德觀點可以被系統化或抽象的原則所俘獲”,因此他們斷定“倫理學理論化從根本上是錯誤的”[3]249。此外,大衛·斯特納索(David Sternalso)還強調了寂靜主義的反理論特征:據這位寂靜主義者說,維特根斯坦對生活形式的訴求并不是一種積極的實踐理論或實用主義意義理論的開端,而是旨在幫助讀者擺脫對心靈與世界、語言與實在的理論化的沉迷。[4]169
然而,在對維特根斯坦的寂靜主義的所有解釋中,最有影響的來自當代著名哲學家約翰·麥克道威爾(John McDowell)。作為他對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的一種解讀,同時也作為他自己在《心靈與世界》中所追求的目標,寂靜主義是一種不發表哲學論文而從事哲學的方式。他用維特根斯坦的方法來舉例說明后者的規則遵循,他特別關注跟隨“路標”的簡單情況,它被看作是到達目的地的規則的表達。在他看來,維特根斯坦揭示了一個挑戰,我們將會發現從“路標”中學習如何走這一點是很神秘的,維特根斯坦不是通過發起一個哲學議題,而是通過提醒我們關于“路標”我們已經知道的事情,從而化解了這個威脅,用維特根斯坦自己的話說,“哲學只確認人人認可的東西”[5]599。就維特根斯坦的工作而言,其目標就是要讓哲學回歸安寧,因此“寂靜主義”的標簽是合適的。麥克道威爾進一步認為,維特根斯坦關于寂靜主義的文獻,并不代表他揭示了對“積極的哲學工作”的需要,而只是使用寂靜主義作為拒絕自己做這項工作的理由。然而維特根斯坦式寂靜主義不是自滿或懶散的姿態,維特根斯坦所做的事情既困難又費力,它需要準確而有同情心的參與,其中積極的哲學似乎又是必要的。[6]365-372
麥克道威爾所解讀的維特根斯坦式寂靜主義被認為是一種實踐整體論(practical holism),它訴諸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的習俗、實踐和生活形式等概念,強調遵守規則活動的非語義的(non-semantic)、非意圖的(non-intentional)、非規范的(non-normative)特征。在《心靈與世界》中,麥克道威爾指出,寂靜主義回避任何實質性的哲學問題,這一點恰恰是其關鍵所在。諸如“意義如何可能”之類的問題。“表達一種恐怖的感覺,維特根斯坦的觀點是,我們不應該沉溺于恐怖的感覺,而是要驅除它。”[7]176在其他文獻中,麥克道威爾進一步指出,如果把維特根斯坦看成是提供了關于意義和理解如何可能的建構性的哲學解釋,吸引那些用沒有預設意義理解的術語來描述的人類互動,那么人們會直面他的哲學所體現的明確觀點:這里沒有所謂的普遍原則,也沒有實質性的理論訴求。這種哲學觀是克里斯平·萊特(Crispin Wright)所說的“寂靜主義”[8]277。
筆者發現,當代學界對維特根斯坦式寂靜主義的主流解讀側重于《哲學研究》中著名的遵守規則議題。在威廉·恰爾德看來,規則的緊縮論者或寂靜主義者認為,正確運用規則的重要性是以“從字面上看待現象”為依據的。寂靜主義者認為,關于正確性規則和標準的事實是基本的和不可還原的,它們不能通過訴諸任何哲學理論來解釋。因此,寂靜主義者拒絕了規則的建構主義觀點:他們會說,在某個給定點上,什么算作系列“+2”的正確延續,并不在于我們達到那個點時將什么樣的做法預先在理論上判斷為正確,而在于在那個位置時實實在在地做了一件“+2”的行動。此外,寂靜主義者還駁斥了柏拉圖主義者所主張的如下觀點:存在一種延續一個數列的絕對正確的方式,它絕對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更加簡單或更加自然。[2]261
三 寂靜主義及其對立面
前述威廉·恰爾德、托馬斯·赫卡、大衛·斯特納索,尤其是約翰·麥克道威爾對維特根斯坦式寂靜主義的解讀,呈現出如此面貌:寂靜主義反對傳統上那種實質性哲學,后者主張對問題進行理論化,通過訴諸“超級概念”,獲得對于實在、心靈或語言的某種本質主義理解,最終使得整個哲學變成康德所說的“形而上學上紛爭不息的戰場”[9]viii。與之相反,維特根斯坦式寂靜主義力圖使哲學擺脫紛擾和喧囂,回歸安寧和寂靜。用“從字面上看待現象”取代傳統上那種“透過現象看本質”;用“實踐的觀點”取代傳統上那種“理論的觀點”;從概念考察和經驗描述,取代傳統上的范疇演繹或理論建構。
然而,理論建構的工作即便在當代仍有很大市場,寂靜主義的事業任重而道遠。布萊恩·萊特(Brian Leiter)在新近出版的一本名為《哲學的未來》的著作集導論中,將英語世界哲學分為“自然主義者”和“維特根斯坦式的寂靜主義者”兩個陣營。關于后者,他總結道,寂靜主義者的一個宗旨是,哲學上并不存在什么與眾不同的研究方法,哲學也不能像其他學科那樣實質性地解決問題;哲學變成一種智性治療的工作,它消解(dissolving)哲學問題,而不是解決(solving)它們[10]2。在他看來,自然主義者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在很大程度上,后者同意維特根斯坦學派的觀點,即哲學家沒有能夠解決問題的獨特方法,然而不同于維特根斯坦學派的是,自然主義者相信困擾哲學家的問題(思想、知識、行動、現實、道德的本質,諸如此類)確實是真實存在的。”[10]2-3在萊特看來,自然主義者是當代的實在論者,而寂靜主義者則類似于當代的唯名論者,二者分別體現了對待傳統哲學問題的兩種態度:前者把問題看作是實質上的,進而探索某種實質性的解決方案;后者則把問題看作是表面上的、似是而非的,并針對我們深受其困擾的一系列偽問題開出智性治療的“哲學處方”。
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在《自然主義與寂靜主義》一文中,進一步將這種分歧解釋為當代英語哲學世界中最深刻、最棘手的分歧。根據羅蒂的說法,寂靜主義者,至少就他本人所隸屬的那個寂靜主義陣營而言,支持以下觀點:
(1)寂靜主義是一種實踐哲學,“對實踐沒有影響的東西不應該對哲學家有影響”[11]149。
(2)寂靜主義是語言哲學或概念哲學,“一個人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使用的詞匯。”[11]149
(3)寂靜主義反對原教旨主義,主張沒有什么比其他任何東西更重要。
在羅蒂看來,寂靜主義有三個對立面:一是“理論哲學”,也就是那種認為一種東西的重要性首先體現為其在理論上的重要性的哲學立場,從這里可以看出羅蒂的實用主義背景;二是“語言工具主義”,也就是那種認為語言或概念只是思想交流或哲學論證的工具,對于實質性的哲學討論并不起決定性作用的觀點;三是基礎主義或“原教旨主義”,它認為有些東西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基礎,任何事物的重要性或合法性都必須基于它而得到辯護。
此外,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提出了一種“哲學在兩個極端之間發揮作用”的觀點:一方面,存在一種“寂靜主義”的觀點,認為“(傳統理論化的)哲學在實踐中沒有地位”[12]304。在生活中,它是一種安寧而惰性的存在,并不執著于對其他領域發揮其自身影響。[12]304而另一個極端是“存在主義”的觀點,它肇始于克爾凱郭爾,接著在馬克思、薩特以及當代的法蘭克福學派那里產生了極大反響。這種觀點認為,從許多方面看來,哲學“應該改變探索它的人,重新塑造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感知方式和行為方式。哲學最終能夠通過付諸實踐而得以實現……這種哲學能夠為哲學家自身的人生經驗和人格塑造帶來一種全新的方向或品質。”[12]304在佩蒂特看來,寂靜主義持有一種非常徹底的實踐觀點,這種觀點認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天塹是不可跨越的,理論化的哲學對人們的實際生活很難產生正面影響;存在主義則是一種廣義的實在論,它不僅認為哲學問題是實質性的,并且不管是對于哲學家們所處的那個時代還是對于他們自身的人格塑造都具有極其重要的變革作用,人類生活唯有在哲學的指引下,才能稱之為真正的實踐,人們所感知并對之有所行動的世界才能稱得上是一個有意義的世界。
四 維特根斯坦式寂靜主義的四種形態
根據前述哲學家的解讀,維特根斯坦關于實在、意義、意圖、遵循規則之本性等議題,持有一種寂靜主義的態度。當然,毋庸諱言,其中有些解讀是富有爭議的。下面我們嘗試將維特根斯坦式寂靜主義劃分為四種相互聯系的類型:語義學寂靜主義、本體論寂靜主義、語用學寂靜主義和方法論寂靜主義。

表1 寂靜主義的四種形態
(一)語義學寂靜主義
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斯坦認為有三個領域中的東西存在于可理解的語言(intelligible language)的限度之外,換言之,它們是“不可說”的,因此只能以沉默待之:語言和世界的邏輯性質;倫理學、美學、人生意義和“神秘之域”;哲學自身。
6.41 世界的意義必定在世界之外。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是真實的,一切都是按它發生的那樣發生的:其中不存在價值——如果世界之內確實存在價值,那么世界本身將沒有價值。
6.42 也不可能有道德命題。
命題可以表達更高的東西。
6.421 很清楚,道德無法用語言來表達。
倫理學是先驗的。
(倫理學和美學是同一個東西。)
6.432 超越世界之上者,對世界上的事物是怎樣的這一點毫不關心。上帝不會在世界上顯露自己。
7 對于我們不能談論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13]7。
關于倫理、美學、生命意義和“神秘之域”,我們對它們的寂靜主義特征沒有太多爭議。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維特根斯坦堅持說,這些詞的命題本身就是無意義的。此外,關于邏輯形式和世界的本質,我們遇到了與倫理學不同的情況:如果倫理學超出了可理解語言的界限,那么邏輯形式就是界限本身。換句話說,即使在《邏輯哲學論》中,我們仍然面臨著維特根斯坦式寂靜主義的其他形態。
(二)本體論寂靜主義
圍繞《邏輯哲學論》中“對象”(objects)的本體論地位問題,威廉·恰爾德分析比較了三種觀點:實在論的、觀念論的、寂靜主義或緊縮論的觀點。[2]56-57
2.02 對象是簡單的。
2.0201 關于復合物的每一個陳述都可以分解成關于其組成成分的陳述,分解為完全地描述該復合物的一些命題。
2.021 對象構成世界的實體。因此它們不能是復合的。[13]7
恰爾德指出,實在論與觀念論之間的爭論點在于,實在被劃分為《邏輯哲學論》中的對象,這是實在的一個內在特征,抑或只不過是我們用來描述世界的語言的一個產物。但是緊縮論者拒斥這兩種解釋,他認為關于維特根斯坦對以下問題持何種看法,實在論和觀念論提供了兩種互相競爭的回答。這個問題是,簡單對象是內在的和絕對的簡單嗎?他認為這兩種立場所提供的回答都是難以理解的。在他看來,存在一種關于簡單性的直截了當的標準:某物是一個簡單對象,僅當在完全分析的水平上,是由一個簡單名稱所挑選出來的。而一旦根據這種標準決定了某些簡單之物,我們也就不能再進一步追問其他的實質性問題了,比如,簡單對象是否還能被進一步分析?為什么與簡單對象相對應的是名稱而不是別的東西?最終使“對象內在地是簡單的嗎?”這個問題變得毫無意義。而一旦這個問題沒有意義,那么任何對它提供回答的嘗試都是沒有意義的。根據緊縮論者的看法,真相就是如此。語言的簡單成分是存在的,實在的簡單成分也是存在的,兩者之間是一一對應的——而這些就是要說的全部。
(三)語用學寂靜主義
語義學與對象(實在世界)打交道,這里預設了語言與世界的二元關系。語用學與言說本身(語言的具體使用、交流語境)打交道,這里沒有做語言與世界的二元關系預設。從語用學上看,語義問題終歸是語用問題,所以維特根斯坦后期在《哲學研究》中會直言“語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中的使用”[5]§43。我們進一步看到,語句的意義在于它在特定語境中的使用。
從語用學的角度看,寂靜主義是人類在語言使用上的“節制”美德的一個極佳例子。這種美德秉持兩個原則:首先,“對于我們不能談論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13]7除了語義上的考慮外,“保持沉默”是一個哲學語用學上的問題。有句拉丁諺語頗能指點迷津:“Avt tace, avt loqvere meliora silentio.”(“請保持沉默,除非你覺得說話比沉默更有意義。”)其次,當說話不可避免時,我們應該“從字面上看待現象”,反對超越字面意義的過度解釋。這種觀點也被稱為意義緊縮論。換言之,寂靜主義并不主張放棄所有話語,而是強調在命題意義的限制和話語解釋的可能性等問題上需要保持高度的“節制”。我們在維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學和后期哲學中,都能找到某些寂靜主義的痕跡,即現象具有我們通常認為它們所具有的特征,并且拒絕任何通過訴諸哲學理論來解釋這些特征的企圖,特別是理智主義和本質主義。
(四)方法論寂靜主義
戴維·瑟伯恩(David Cerbone)說,“邏輯不能被描述”和“邏輯必須照看好其自身”[14]309這兩個評論都呈現出在他看來乃是維特根斯坦所提倡的那種寂靜主義,這種寂靜主義僅僅把我們留在原地,那里有我們的思想和語言,還有所有的令人困惑的和引人誤解的對于“從流通中撤出”[14]309的限制。在《邏輯哲學論》中,當維特根斯坦談到世上萬物的本體論特征時,他說:“世上萬物正如其所是而是,正如其所發生而發生。”[5]124然而,當我們讀到《哲學研究》中關于哲學的任務的闡述時,正如大衛·瑟伯恩所指出的,我們能夠聯想到的那種寂靜主義體現在哲學“讓一切如其所是”[5]124這一觀點之中。與《邏輯哲學論》中關于世界和語言的本質主義主張相比,這種“讓一切如其所是”的觀點具有反本質主義的特征:世界中的一切都只是與形形色色的語言游戲交織在一起并借助它們得以描述的諸多生活形式,而所有的語言游戲在外延上都具有家族相似特征,在內涵上則無法滿足傳統上提出的語法規則和行為規則的本質主義要求[14]308。
在《論確定性》等作品中,維特根斯坦指出,理性總是走到盡頭的,從那開始,理性就要為實踐和信仰讓出地盤:
某人說,“我知道他覺得疼”,盡管說話者未能對此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這等于是說“我確信他……”嗎?——并非如此。“我確信”告訴你的是我的主觀確定性。“我知道”意味著那個知道這一點的人正是我,而不知道這一點的人被一種理解上的差異與我區別開來了。(也許是基于某種經驗上的程度差別)。
如果我在數學上說“我知道”,那么為了表明這一點,所做的工作就是給出一個證明。
如果在這兩種情況下,不說“我知道”,而說“你可以信賴它”,那么在每種情況下,實質上都是不同的。
實體化的過程就到此為止了。[15]563
五 寂靜主義之批判:誰的困境?何種終結?
從某種角度看,寂靜主義是一種“激進主義”(radicalism),因為它不時地在通常被視為極其重要的哲學問題上公開主張保持沉默,堅決拒斥對實在之本質或語詞之意義的理論化解釋,甚至不留情面地將傳統哲學家們為之殫精竭慮的許多問題斥責為“偽問題”。贊成它的人歡呼道,這不失為解決哲學問題的一個釜底抽薪之法,它不僅深刻,而且頗富有實踐感,同時又符合很多人的直覺。常言道,譽之所至,謗亦隨之。反對它的人批評道,這種觀點過于輕描淡寫地處理了那些重要而真實的哲學問題,與其說它“消解”了問題,不如說它回避了問題的實質。
維特根斯坦本人從未像羅蒂那樣,明確在字面上稱自己是一名“寂靜主義者”,因此學界對維特根斯坦式的寂靜主義的解讀也好,批評也罷,都是基于學者們自己對于維特根斯坦的一手文獻以及解讀性的二手文獻的把握。譬如,針對麥克道威爾對維特根斯坦的寂靜主義解讀,伯恩斯坦(J. M. Bernstein)如是批判道:“針對麥克道威爾的寂靜主義,一個最好的批評是,維特根斯坦的先驗理論提醒我們注意的材料,對于它們應該引導的實踐的實際細節,無論是制度性的還是非制度性的,只有極微小的把握。”[16]239誠然,就遵守規則議題而言,維特根斯坦的工作只是框架性的,他從未對人類遵守規則的復雜情況進行過細致的梳理,未能區別對待制度性實踐和非制度性實踐,更未能對形形色色的規則——也就是“規則”的概念家族——進行過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的工作,相比之下,康德、羅爾斯(John Rawls)、哈特(Herbert Hart)、塞爾(John Searle)等人出于各自目的而對規則所做的區別則要細致得多。
根據大衛·斯特恩(David Stern)的闡述,寂靜主義的批評者回答說,寂靜主義者面臨一個非常煩人的兩難困境:他們要么給我們提供某種哲學論證,以使我們相信某些問題是錯誤的,但這樣一來,他們就違背了自己放棄哲學論證的立場,要么他們真的放棄了哲學論證,但這樣一來,她或他的東西根本就沒有哲學上的說服力。[4]169對這個兩難困境的一個簡要回應是,支持寂靜主義的論證,作為一種從外部反對理論化哲學的論證,與哲學家們在理論化哲學內部所從事的論證,不是同一種類型的論證。借用維特根斯坦自己的話說,我們對寂靜主義的特征刻畫是一項“概念考察”或“語法研究”的工作,它并不試圖提供某種替代性的備選方案,而只是認為任何一種可能存在的備選方案,只要是理論化的、本質主義的、基于“超級概念”的,通常都是寂靜主義者們所反對的。因此那些通過一種獨特的維特根斯坦式哲學描述來達到寂靜主義目標的擁護者們可能會說,斯特恩所說的“寂靜主義的兩難困境”,并不是一個真實的兩難困境。
面對這個兩難困境,羅蒂做出了某種程度的妥協。他把自己歸入寂靜主義陣營,但表現出與多數寂靜主義者不同的理論旨趣。他認為寂靜主義確實容易陷入某種哲學上的悖論,因此他提出了自己更加合理也更加折中的建議:“像我一樣,大多數認為自己身處寂靜主義陣營的人不敢信心十足地說,他們那些持有積極觀點的同事們所研究的問題是不真實的。他們沒有把哲學問題分為現實的和虛幻的,而只是把哲學問題分為那些與文化政治保持一定相關性的問題以及那些與文化政治不相關的問題。”[11]149羅蒂的這個妥協意味著,在那些與文化政治不相關的領域,有可能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實質性的哲學問題,而寂靜主義者所關心的是另外一種問題,這些問題不再訴諸文化政治不相關的那些理論基礎,它們有自己的專屬地盤,也有自己的非理論化的說話方式。
筆者認為,維特根斯坦若地下有知,當不會對斯特恩的“寂靜主義困境”感到驚訝。在他的《邏輯哲學論》序言中,清楚地意識到如下悖論:“這本書討論哲學問題,并且表明,——我相信——那些問題之所以被提出,乃是基于對我們語言邏輯的誤解。”[13]6.41毋庸諱言,這里有一個字面上的“佯謬”:《邏輯哲學論》所處理的問題是不應該被提出的。但由于這些問題為傳統哲學家們津津樂道,這本書唯一能做的就是化解它們,因此它并不涉及任何傳統的實質性問題。維特根斯坦所做的工作正是一種新的哲學:一種“語言批判”,也就是一項“劃界”的工作。在界限的內部(通常是在自然科學領域),他對那些實質性問題作出語義處理,界限的外部則屬于“神秘之域”,唯有以沉默待之。如果我們只在邊界內部劃一條界線,這個悖論是真實的,但維特根斯坦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他說:“因此這本書的目的是為思想劃出界線,或者毋寧說,不是為思想而是為思想的表達劃一個界線”[13]6.41,也就是為可理解的語言劃定界線,我們不能對不可思考之物有所思考,但是能夠對不可言說之物,為其不可說性提供一個二階說明——這個說明的對象在本體論上不同于可言說的對象。“定界悖論”就是通過訴諸思想與思想的表達之區分從而得以消除的,由此可見,大衛·斯特恩的“寂靜主義困境”源于對“定界悖論”的誤解。
科拉·戴蒙德(Cora Diamond)認為,這種“寂靜主義困境”并沒有威脅到倫理的目的:這個倫理目的是通過該書尚未明確言說的方式而實現的,也就是說我們只能“從內部”來界定倫理事項之可能所是。這種做法與該書序言中的下述說法有所不同:我們只通過限制思想的表達來限制思想。我們從內部劃出界線,要想明確地獲知什么東西是不存在的,這是唯一方法。而維特根斯坦希望通過這本書所達到的目標,亦即通過命題的一般形式的呈現所達到的,也就是從內部來為表達劃出一個界線。[17]156后來,維特根斯坦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繼續他的“語言批判”——當然他寧愿用諸如“綜觀”(surveyability)和“語法研究”之類的詞來代替傳統的“哲學論證”:我們對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個主要根源是我們不能綜觀語詞用法的全貌。——我們的語法缺乏這種綜觀。綜觀式的表現方式在兩者之間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們“看到聯系”。從而,發現或發明的中間環節是極為重要的[5]122。
哲學根本上是治療性的,因此,誠如施太格繆勒(Wolfgang Stegmuller)所說,哲學上的混亂與其說像提出理論上的問題,不如說更像一種精神上的疾病。由于這種原因,一種適當的哲學主張是一種治療或療法,而不是一種學說。為了完成這種治療,我們并不需要依靠新的知識,如同一種學說所要求的那樣[18]587。在并不存在“哲學病”的地方,無須通過哲學論證建構任何一種理論;相反,這恰恰是因為我們誤解了語言語法,誤用了理論化和哲學論證,從而在實在、意義、意向和遵守規則議題上才會出現那么多的“哲學病”。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玩語言游戲,也在哲學上玩語言游戲。從游戲角度看語言,像語言替代為語言游戲,這對于日常生活來說是本真性的,而對于哲學來說是治療性的,因為傳統哲學已經不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那樣玩各種語言游戲了,哲學家們通常對那些“大詞”或“超級概念”情有獨鐘,比如實在、真理、知識、規則。然而與此同時,他們不得不面對諸如造成概念混亂、抹殺概念差別、產生虛假問題、陷入兩難困境、形成錯誤類比這樣的指責。他們研究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一些在極其重要的方面可能是錯誤的圖像。通過哲學的診斷,寂靜主義者希望杜絕人類的智慧困惑。這意味著我們的哲學活動必須在某處終結——而在思考的反思的終結處,恰恰是實踐的開端,關于實踐,并沒有進一步需要解釋的,無需任何理論化的意義或意向。哲學治療所終結的那種理論化哲學,旨在通過對于實在、意義和實踐的進一步解釋,從而獲得某種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理論建構。
佩蒂特指出了生活實踐與哲學理論之間的“不必要的張力”,而這種張力恰恰又是提倡寂靜主義的后果。他認為寂靜主義若走到頭,就必然會給我們留下不幸的前景,它迫使人們不得不相信,我們在實踐中可能發現自己在哲學上不能認同的東西。這不禁讓我們反思,寂靜主義是否表明人們可能不得不在視角之間切換我們的生活,其中一個是實踐的,另一個是哲學的;一個是生活上的經驗和行為,另一個是理論上的反思,并且不同的視角提供了不同和不相容的世界的視角,他希望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同時他認為確實并非如此。[12]306對此,寂靜主義的捍衛者可以回應道,寂靜主義仍然是一種哲學,它所批判的是傳統上那種理論化的哲學,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哲學:哲學上所需要的正是對于生活實踐的一種寂靜主義的哲學思考方式,而不是生活實踐本身,因此這里只有不同的哲學觀之間的切換,而不是生活實踐的世界觀與哲學上的世界觀之間的切換。
像麥克道威爾那樣,佩蒂特同樣認為哲學沒有止境,倘若寂靜意味著哲學的終結,他寧愿不要。佩蒂特認為哲學有形而上學冥想、方法論和道德教導這三大功能,它們依托于各式各樣的標準對普通的生活實踐產生影響。他們重新塑造了先于哲學事業而存在的那些感知方式和心理傾向性,而這并不意味著就是存在主義所設想的那套東西,但他們確實證明了似乎作為唯一的被選項而或隱或現的那幅寂靜主義圖景是不切實際的。筆者認為,佩蒂特在這里誤解了寂靜主義與哲學的關系:寂靜主義所終結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哲學,而是某種特定類型的哲學。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哲學并不是單獨坐在扶手椅上的東西,哲學家應該從辦公室回到家里,讓自己的身心從理論研究中解脫出來。[12]304無論如何,佩蒂特都無法令人信服地表明,治療型哲學意味著哲學的終結,因為實際情況恰恰相反:維特根斯坦所倡導的這種“綜觀”、語法研究,以及在它們影響下所進行的經驗反省和觀念批判工作,都屬于廣義的哲學治療的領域,而在本質主義哲學的終結之處,“治療型哲學”才剛剛起步。
六 余論
維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學都有兩條主線,一是語言批判,二是寂靜主義。寂靜主義是語言批判的自然結果,前后期語言批判的具體進路有所不同,決定了前后期寂靜主義的具體內容也有所不同。舉例來說,他前后期都反對一種“理論化”的哲學。哲學不是一種理論,抑或不是一種學說,而是一種活動。哲學是一種劃界的活動,哲學也是一種治療的活動,只有在語言“休假”也就是不正常工作的時候,才有哲學問題產生。哲學的任務就是消除語言借助理智對我們的蠱惑,治療我們受語言蠱惑而撞墻所留下的腫塊。這種語言的蠱惑在于,讓我們誤以為任何一個概念都是有意義的,可以對之進行涵義/指稱分析,哪怕它是一個完全抽象的概念。而哲學的任務就在于揭示這些抽象概念背后的本質。然而這實際上是對語言的一種誤用,因為語言背后并沒有更為“基礎”的東西,而這恰恰是傳統哲學困惑的來源。
傳統哲學并不滿足于只是在字面上給出我們對于世界的整體理解,總希望通過其字面含義而隱藏著或者揭示出其“后面的”“內在的”東西。維特根斯坦式寂靜主義恰恰相反,它主張哲學研究不再是理論化的解釋,而是描述和綜觀。它如其所是地描述出事物在我們面前所呈現的樣子,至于其背后的寓意或本質是什么,這已超出了日常語言的功能范圍,對之應當保持沉默。從字面上理解,“綜觀”就是從各個角度去看,它要求我們憑借關于語言使用的回憶或“提示物”,以及對它在諸多可能語境下的使用的想象,多角度、多面相地為人類經驗或生活形式給出充分完整的描述。我們所縱觀之物,就是公開地擺放在那里的東西,它們是在字面上就能一覽無遺的東西,并沒有刻意向人們隱藏什么,因此對于它們的任何進一步解釋都是無的放矢、南轅北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