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guó)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與《泰晤士報(bào)》涉藏報(bào)道探析
何兢 韓磊
(①華東師范大學(xué)歷史學(xué)系 上海 200241 ②哈爾濱商業(yè)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 哈爾濱 150028)
1899年1月,主張對(duì)西藏采取強(qiáng)硬政策的喬治·寇松出任新一任印度總督,英國(guó)政府開(kāi)始針對(duì)西藏醞釀新一輪的武裝侵略。1903年12月,在距離第一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僅僅15年之后,為與俄國(guó)加緊爭(zhēng)奪西藏,擴(kuò)大自身在西藏的經(jīng)濟(jì)利益,英國(guó)政府悍然發(fā)動(dòng)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并于1904年8月攻陷拉薩之后脅迫清政府簽訂《拉薩條約》。英國(guó)的主流媒體對(duì)本國(guó)政府發(fā)動(dòng)的這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給予極大的關(guān)注,進(jìn)行了跟蹤報(bào)道。盡管近年來(lái)學(xué)術(shù)界對(duì)英美主流媒體涉華涉藏報(bào)道研究給予了越來(lái)越多的關(guān)注,但是,對(duì)英國(guó)在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期間的涉藏報(bào)道尚缺乏專門的論述。本文試以英國(guó)第一主流媒體《泰晤士報(bào)》的報(bào)道為主要史料,利用《泰晤士報(bào)》全文數(shù)據(jù)庫(kù),對(duì)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前后的涉藏報(bào)道進(jìn)行梳理,探析英國(guó)媒體的政治傾向性及其對(duì)英國(guó)政府對(duì)外擴(kuò)張政策的影響。
一、英國(guó)發(fā)動(dòng)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前后《泰晤士報(bào)》涉藏報(bào)道基本概況
(一)基本數(shù)據(jù)
《泰晤士報(bào)》從1856年開(kāi)始出現(xiàn)最早的涉藏報(bào)道。從表1可以看出,《泰晤士報(bào)》從1880年代中期開(kāi)始便不斷刊載有關(guān)中國(guó)西藏的消息,例如西藏的風(fēng)土人情,英國(guó)人在西藏的游歷等,此外還有西藏與印度、錫金、緬甸之間關(guān)系等,為英國(guó)政府武裝侵藏制造輿論聲勢(shì)。但從整體看來(lái),在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之前,《泰晤士報(bào)》涉藏報(bào)道的數(shù)量非常有限。
1899年,主張對(duì)西藏采取強(qiáng)硬政策的寇松擔(dān)任印度總督,他于1902至1904年間任命當(dāng)時(shí)的少校榮赫鵬為英國(guó)的西藏特派員。1903至1904年,在寇松的命令下,榮赫鵬與錫金政治專員約翰·克勞德·懷特一起,率領(lǐng)英國(guó)“使團(tuán)”(實(shí)為軍隊(duì)),進(jìn)入西藏。這次行動(dòng)表面上是力圖解決錫金—西藏邊界和通商問(wèn)題,與西藏訂立新的條約,而其真正目的是武裝侵略西藏,建立英國(guó)在西藏的霸權(quán)。這便是1903年至1904年英國(guó)發(fā)動(dòng)的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作為當(dāng)時(shí)英國(guó)的主流媒體,《泰晤士報(bào)》對(duì)這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進(jìn)行了密集而詳細(xì)的報(bào)道。
從表1可以看出,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發(fā)生時(shí)的1903年至1904年,《泰晤士報(bào)》的涉藏報(bào)道數(shù)量急劇增加。從1903年11月至1904年9月,以Thibet、Tibet、Tibetan為關(guān)鍵詞,在《泰晤士報(bào)》數(shù)據(jù)庫(kù)中進(jìn)行檢索,獲得各類涉藏報(bào)道數(shù)量共計(jì)171篇。這個(gè)數(shù)量占1883年至1905年全部涉藏報(bào)道數(shù)量的63.6%。將這些報(bào)道綜合起來(lái)看,完全就是一份完整的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期間英軍“行軍日志”。可見(jiàn),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的相關(guān)報(bào)道在《泰晤士報(bào)》涉藏報(bào)道中占有重要地位。當(dāng)西藏發(fā)生諸如戰(zhàn)爭(zhēng)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的時(shí)候,新聞報(bào)道數(shù)量便會(huì)激增,這是《泰晤士報(bào)》涉藏報(bào)道的顯著特征。

表1 1883-1905年《泰晤士報(bào)》涉藏報(bào)道數(shù)量統(tǒng)計(jì)
(二)新聞信息源
信息源的呈現(xiàn)是構(gòu)建報(bào)道事實(shí)的關(guān)鍵節(jié)點(diǎn)。《泰晤士報(bào)》是第一張擁有駐外記者的報(bào)紙,也是第一張派駐戰(zhàn)地記者的報(bào)紙。1903年至1904年英國(guó)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期間,《泰晤士報(bào)》派遣隨軍記者(Military Correspondent)進(jìn)入西藏。隨軍記者不斷向《泰晤士報(bào)》發(fā)回大量消息,對(duì)英國(guó)侵略西藏的整個(gè)過(guò)程進(jìn)行了跟蹤式報(bào)道。此外,《泰晤士報(bào)》還大量援引了俄國(guó)、法國(guó)、德國(guó)等國(guó)主流媒體的涉藏報(bào)道。
(三)新聞主題
記者通過(guò)新聞主題表達(dá)對(duì)客觀事實(shí)的看法、態(tài)度和主觀意圖。《泰晤士報(bào)》在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期間的報(bào)道,主要涉及如下幾個(gè)主題:①對(duì)戰(zhàn)爭(zhēng)期間英國(guó)軍隊(duì)的裝備、補(bǔ)給、行軍路線、作戰(zhàn)任務(wù)、傷亡數(shù)字、交通運(yùn)輸、天氣等信息進(jìn)行全程跟蹤式報(bào)道。②《泰晤士報(bào)》在對(duì)戰(zhàn)爭(zhēng)進(jìn)程進(jìn)行跟蹤的同時(shí),利用相關(guān)研究人員的科研成果,穿插報(bào)道了西藏春丕(Chumbi)、帕里(Phari)、堆納(Tuna)、康馬(Kangmar)、江孜(Gyangtse)、拉龍(Ralung)、浪卡子(Nagartse)等地獨(dú)特的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社會(huì)風(fēng)俗。這主要源于在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期間,多名地理、地質(zhì)、博物學(xué)家跟隨英國(guó)軍官榮赫鵬的部隊(duì)進(jìn)入西藏,他們?cè)陔S軍途中對(duì)動(dòng)植物學(xué)、氣象與氣候、地質(zhì)等領(lǐng)域進(jìn)行了大量的探察活動(dòng)。③對(duì)關(guān)鍵人物——印度總督榮赫鵬和率軍將領(lǐng)麥克唐納的報(bào)道。如1903年12月3日的一篇報(bào)道,對(duì)麥克唐納1888年在非洲烏干達(dá)和蘇丹的帶兵作戰(zhàn)情況進(jìn)行了回顧。[1]
二、《泰晤士報(bào)》對(duì)“西藏貿(mào)易問(wèn)題”的報(bào)道與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的爆發(fā)
英國(guó)是以貿(mào)易為立國(guó)之本的,為了獲得貿(mào)易權(quán)利,甚至可以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zhēng),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的爆發(fā)與英國(guó)為奪取在西藏的貿(mào)易權(quán)有密切關(guān)系。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帝國(guó)主義列強(qiáng)掀起了瓜分中國(guó)的狂潮。英國(guó)在經(jīng)歷了1888年第一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之后,并不滿足于自己在西藏已獲得的經(jīng)濟(jì)利益,意欲擴(kuò)大對(duì)西藏的經(jīng)濟(jì)侵略。擴(kuò)大在西藏的貿(mào)易,成為英國(guó)在第一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結(jié)束僅僅15年之后又迫不及待地再次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zhēng)的經(jīng)濟(jì)動(dòng)因。在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之前,“西藏貿(mào)易問(wèn)題一直是引人注目的問(wèn)題”。[2]《泰晤士報(bào)》開(kāi)始頻繁刊發(fā)涉及西藏貿(mào)易問(wèn)題的報(bào)道,分析西藏貿(mào)易的基本形勢(shì),著力渲染英國(guó)對(duì)西藏貿(mào)易的悲觀前景,并在報(bào)道中為英國(guó)政府爭(zhēng)奪西藏的經(jīng)濟(jì)利益提出了詳細(xì)的計(jì)劃,為英國(guó)對(duì)西藏進(jìn)行經(jīng)濟(jì)侵略大造聲勢(shì)。
英國(guó)商人在印度北部的山區(qū)建立了大面積的茶葉種植園,依靠廉價(jià)的勞動(dòng)力、充裕的資金支持、先進(jìn)的制茶設(shè)備和現(xiàn)代化的交通運(yùn)輸工具,印度茶葉在19世紀(jì)末產(chǎn)量激增,故而價(jià)格低廉,擁有較強(qiáng)的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力。而西藏人又普遍有飲茶的習(xí)慣,英國(guó)商人便企圖利用占領(lǐng)西藏市場(chǎng),為印度茶葉尋找商品傾銷地,進(jìn)而加大英國(guó)對(duì)西藏的經(jīng)濟(jì)侵略。與此同時(shí),雖然清政府也從印度進(jìn)口部分茶葉,但為保護(hù)數(shù)量眾多且以種植和出售茶葉為生的四川茶農(nóng)的利益,清政府便對(duì)印度茶葉課稅,并提高英印商人的房屋租金,規(guī)定未經(jīng)允許禁止外國(guó)商人進(jìn)入亞?wèn)|以北地區(qū)。[3]因此,英國(guó)政府認(rèn)為英國(guó)在西藏的貿(mào)易毫無(wú)利潤(rùn)可言,英國(guó)商人甚至叫囂通過(guò)戰(zhàn)爭(zhēng)來(lái)解決問(wèn)題。在這種背景下,《泰晤士報(bào)》積極配合英國(guó)商人的輿論,刊發(fā)報(bào)道表達(dá)對(duì)清政府及西藏地方當(dāng)局的茶葉禁運(yùn)政策的不滿,積極鼓吹英印政府以茶葉為武器打開(kāi)西藏市場(chǎng)。[4]《泰晤士報(bào)》在1883年11月27日的一篇題為《印度與西藏之間的貿(mào)易》(Trade Between India And Tibet)的報(bào)道中稱:“過(guò)去十年里印度茶葉貿(mào)易的顯著擴(kuò)大使茶葉種植者們將殷切的目光投向西藏。在西藏,茶葉被視作生活首要必需品之一,但是其茶葉質(zhì)量粗劣且價(jià)格昂貴……而大吉嶺的茶園卻能夠提供價(jià)格合適的茶葉,但目前在西藏卻見(jiàn)不到我們的茶葉。”[5]
《泰晤士報(bào)》在分析印產(chǎn)茶葉銷路不暢的原因時(shí),全然不顧印產(chǎn)茶葉不受歡迎主要是因?yàn)槲鞑孛癖姼珢?ài)四川出產(chǎn)的茶葉口感的事實(shí),將原因一方面歸結(jié)為西藏地方當(dāng)局的貿(mào)易壟斷政策,該報(bào)的一系列報(bào)道對(duì)貿(mào)易壟斷政策表達(dá)了強(qiáng)烈不滿。[6]“拉薩的僧侶們以壟斷作為(英國(guó)商品進(jìn)入西藏)回應(yīng)。如果沒(méi)有護(hù)照,他們不允許商人進(jìn)入邊境。商人或者將所獲得利潤(rùn)的大部分支付給西藏地方當(dāng)局,或者以百分之四的利率向他們借款,以此為條件才能夠獲得護(hù)照。”[7]“喇嘛們的壟斷是最為嚴(yán)重的障礙,他們會(huì)武斷地停止貿(mào)易若干個(gè)月。正是由于喇嘛們壟斷了貿(mào)易,印度茶葉才會(huì)被排斥在西藏之外……所有經(jīng)過(guò)亞?wèn)|的有關(guān)茶葉的貿(mào)易都被禁止。”[8]1901年11月4日,《泰晤士報(bào)》的一篇報(bào)道也認(rèn)為,印度茶葉是英印政府對(duì)藏貿(mào)易的主要商品,但自1900年以來(lái)出口額有所下降。該報(bào)道認(rèn)為,西藏貿(mào)易的兩個(gè)最大障礙之一便是西藏的排他性政策。[9]
另一方面,《泰晤士報(bào)》將原因歸結(jié)為1894年藏印條約的限制,強(qiáng)烈要求重新修訂條約,進(jìn)一步打開(kāi)西藏市場(chǎng)。《泰晤士報(bào)》發(fā)表社論稱:“在1894年的藏印條約之下,印度茶葉完全被禁止進(jìn)入西藏。英國(guó)為該產(chǎn)業(yè)投入了數(shù)以百萬(wàn)計(jì)的資金,因此解除這些限制是非常必要的。西藏人是世界上數(shù)量最為龐大的飲茶民族,每年約消耗1200-1500萬(wàn)磅茶葉;但是由于中國(guó)的‘關(guān)門’(closed door)政策,這項(xiàng)貿(mào)易卻受到了諸多限制……我們需要‘門戶開(kāi)放’(open door),在未來(lái)的若干年,西藏將不僅是印度茶葉的市場(chǎng),也將是英國(guó)其他諸多工業(yè)品的龐大市場(chǎng)。”[10]從《泰晤士報(bào)》的報(bào)道可以看出,該報(bào)完全是從英國(guó)國(guó)家利益的立場(chǎng)出發(fā),得出有利于自身的論斷,向讀者表明英國(guó)在西藏行動(dòng)的正當(dāng)性,為將來(lái)發(fā)動(dòng)戰(zhàn)爭(zhēng)制造輿論。
如何一勞永逸地解決西藏貿(mào)易問(wèn)題呢?隨著英國(guó)政府對(duì)藏政策的調(diào)整,《泰晤士報(bào)》的報(bào)道傾向也隨之發(fā)生變化。1899年之前,該報(bào)主要通過(guò)煽動(dòng)性報(bào)道鼓吹英國(guó)政府重新與清政府簽訂涉藏條約。例如1896年8月25日,《泰晤士報(bào)》發(fā)表題為《通過(guò)錫金發(fā)展印藏貿(mào)易》的署名文章,宣稱“西藏對(duì)農(nóng)業(yè)品和手工業(yè)品的需求量是增加的,一旦壟斷、限制和偏見(jiàn)消失的話,這種需求將會(huì)膨脹。”[11]
而1899年主張對(duì)西藏強(qiáng)硬的寇松上臺(tái),《泰晤士報(bào)》也主動(dòng)配合寇松政府的強(qiáng)硬論調(diào),在報(bào)道中強(qiáng)調(diào)外交途徑是無(wú)用的,只能使用武力解決問(wèn)題。乃至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前夕,該報(bào)鼓吹“一直以來(lái),英印政府與西藏的貿(mào)易額很小,而且持續(xù)下降也不是令人驚訝的事情。現(xiàn)在的貿(mào)易總額大約僅為16萬(wàn)英磅,目前有一種觀點(diǎn)甚至認(rèn)為為了擴(kuò)大貿(mào)易額我們應(yīng)當(dāng)宣戰(zhàn)。”[12]在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期間,《泰晤士報(bào)》赤裸裸地為英國(guó)政府的戰(zhàn)爭(zhēng)政策張目,稱“外交被證明是無(wú)用的,貫徹針對(duì)敵人的行動(dòng),展示武力是完全必要的。”[13]
三、《泰晤士報(bào)》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涉藏報(bào)道中的國(guó)家主義傾向
《泰晤士報(bào)》作為英國(guó)主流報(bào)刊,深刻影響著近代中國(guó)報(bào)刊的誕生與發(fā)展。近代中國(guó)的報(bào)業(yè)在經(jīng)營(yíng)理念、體例規(guī)劃、報(bào)道方式上都效仿《泰晤士報(bào)》,“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人心之所趨向也。”[14]英國(guó)《泰晤士報(bào)》雖然一直秉承“獨(dú)立地、客觀地報(bào)道事實(shí)”的宗旨,但縱觀其200多年的歷史,該報(bào)的政治傾向基本上是保守的,在歷史上歷次重大國(guó)內(nèi)及國(guó)際事務(wù)上支持了英國(guó)政府的觀點(diǎn)。而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的20世紀(jì)初,正是《泰晤士報(bào)》的政治觀點(diǎn)轉(zhuǎn)向保守主義時(shí)期,因此,《泰晤士報(bào)》的涉藏報(bào)道并沒(méi)有體現(xiàn)出客觀、獨(dú)立、公正的原則,相反與英國(guó)政府在西藏的侵略訴求保持高度一致,體現(xiàn)出鮮明的國(guó)家主義特征,儼然成為英國(guó)政府的喉舌。具體到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gè)方面:
第一,對(duì)侵略戰(zhàn)爭(zhēng)的支持流露于字里行間,極盡美化之能事。盡管隨軍的多名地理、地質(zhì)、博物學(xué)家在沿途進(jìn)行了大量的地理學(xué)和動(dòng)植物學(xué)等方面的探察活動(dòng),并在動(dòng)植物標(biāo)本采集、氣候與氣象、地質(zhì)等領(lǐng)域取得了大量成果,但這絲毫掩蓋不了榮赫鵬率軍大規(guī)模軍事入侵西藏的實(shí)質(zhì)。《泰晤士報(bào)》秉承國(guó)家主義原則,站在英國(guó)國(guó)家利益的立場(chǎng)上,極力美化這場(chǎng)侵略戰(zhàn)爭(zhēng)。立場(chǎng)決定敘述,敘述決定修辭,《泰晤士報(bào)》為了掩蓋英國(guó)政府武裝入侵西藏的真實(shí)面目,在報(bào)道中凡涉及英國(guó)軍隊(duì)之處,一律稱之為“使團(tuán)(mission)”或“考察隊(duì)”( Expedition);英國(guó)軍隊(duì)的軍事行動(dòng)一律稱為“考察”(Expedition),還大言不慚地宣稱“真誠(chéng)地希望此次考察活動(dòng)……會(huì)直接建立起與達(dá)賴?yán)镏g的友好關(guān)系,這對(duì)雙方來(lái)說(shuō)是互利互惠的事情。”[15]“寇松爵士完全是為了和平的目的才派出遠(yuǎn)征軍的。”[16]
在維護(hù)英國(guó)國(guó)家利益立場(chǎng)的驅(qū)使下,《泰晤士報(bào)》無(wú)視客觀、公正、獨(dú)立的新聞報(bào)道原則,對(duì)戰(zhàn)爭(zhēng)中英軍所犯暴行進(jìn)行遮掩和辯護(hù)。1904年3月31日,榮赫鵬以談判為誘餌,包圍并殺害了集中在骨魯一帶的藏軍近千人,這就是發(fā)生在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期間的“骨魯大屠殺”。《泰晤士報(bào)》僅僅在1904年4月1日的報(bào)道中提及該事件。這篇題為“赴藏使團(tuán):藏軍損失慘重”的報(bào)道,不僅沒(méi)有對(duì)英軍的暴行進(jìn)行任何揭露,而且不顧新聞報(bào)道的最基本原則,對(duì)這一慘絕人寰的暴行進(jìn)行了完全歪曲的報(bào)道。該報(bào)對(duì)英軍偽裝談判一事只字不提,反而將事件的責(zé)任全部推卸給藏軍,稱“整個(gè)事件完全由藏軍自己引起,榮赫鵬和麥克唐納將軍保持最大限度的容忍和克制”。為了向全世界掩蓋英軍的暴行,該報(bào)謊報(bào)藏軍死亡數(shù)字,聲稱藏軍“損失大約400或500人”。《泰晤士報(bào)》對(duì)英軍暴行的唯一“反思”是“這場(chǎng)戰(zhàn)役對(duì)于我們來(lái)說(shuō),最重要的意義是……發(fā)現(xiàn)了俄國(guó)提供的裝備”[17]。
第二,涉藏報(bào)道中呈現(xiàn)出了明顯的選擇性報(bào)道傾向,借以誘導(dǎo)讀者支持這場(chǎng)侵略戰(zhàn)爭(zhēng)。為了獲得公眾的輿論支持,《泰晤士報(bào)》竭力向英國(guó)國(guó)內(nèi)讀者傳遞有關(guān)英軍的利好消息,盡量規(guī)避英軍陷入困境的負(fù)面新聞。一是極力美化英國(guó)與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友好關(guān)系”。按照《泰晤士報(bào)》的報(bào)道,榮赫鵬此次率軍入侵西藏得到了西藏上層分裂勢(shì)力和普通百姓的歡迎和支持。1903年12月16日的報(bào)道稱,“西藏當(dāng)?shù)毓賳T對(duì)榮赫鵬正式友好的接待是一個(gè)好的信號(hào)”,“西藏官員非常友善”,[18]“春丕的居民對(duì)代表團(tuán)表示歡迎”。[19]《泰晤士報(bào)》認(rèn)為由于“藏人整體上馴順而平和”,[20]再加上“藏人沒(méi)有步槍,只有原始武器……清政府在拉薩和其他地方部署的軍隊(duì)主要負(fù)責(zé)為防御提供供給,不足為慮。”[21]
二是對(duì)于英軍的行軍進(jìn)展情況報(bào)以樂(lè)觀自信的態(tài)度,《泰晤士報(bào)》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行軍看上去沒(méi)有困難”。[22]按照《泰晤士報(bào)》的報(bào)道,英國(guó)軍隊(duì)能夠較為容易地克服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所帶來(lái)的困難,順利向拉薩進(jìn)軍。例如,英國(guó)軍隊(duì)于1903年12月中旬翻越吉普拉山口進(jìn)入西藏境內(nèi),來(lái)到春丕。《泰晤士報(bào)》報(bào)道稱,“這條路線沒(méi)有任何困難,翻越山口的時(shí)候非常容易。”[23]12月的喜馬拉雅山地區(qū)氣候非常寒冷,《泰晤士報(bào)》在進(jìn)行報(bào)道時(shí)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英印軍隊(duì)能夠解決行軍過(guò)程中的各種困難,能夠承受惡劣的自然條件。”[24]“雖然天氣寒冷,但是英印軍隊(duì)健康狀況良好。”[25]總之,在報(bào)道英軍行軍過(guò)程中,“容易”(easy)、“沒(méi)有困難”(no difficulty)、“和平”(peaceful)等詞匯出現(xiàn)的頻率非常高。與之相反,在報(bào)道西藏軍隊(duì)的情況時(shí),往往對(duì)西藏軍隊(duì)的失利大加渲染,經(jīng)常使用“損失”(loss)、“被擊退”(be repulsed)、“頑固的抵抗”(obstinate resistance)、“絕望的、孤注一擲的抵抗”(desperate resistance)等負(fù)面詞匯。
第三,涉藏報(bào)道充斥著西方式的居高臨下的種族優(yōu)越感與對(duì)西藏民族的歧視。“這些報(bào)道努力消除人們的各種疑惑,愈合了劫掠和暴行在歐美人自我認(rèn)知上撕開(kāi)的傷口。”[26]晚近以來(lái),伴隨著西方人對(duì)西藏的興趣的加深,西方人按照自己的想像開(kāi)始構(gòu)建觀念中的西藏,對(duì)西藏的認(rèn)知充滿誤讀、傲慢與偏見(jiàn)。《泰晤士報(bào)》的涉藏報(bào)道在刻意渲染英國(guó)政府的正義行為的同時(shí),突出描繪西藏人的愚昧及野蠻。1903年12月4日的一篇題為“向西藏進(jìn)軍”的報(bào)道,毫不掩飾地將西藏人稱為“未開(kāi)化的、野蠻的部族”。[27]1904年8月27日,《泰晤士報(bào)》刊發(fā)社論,更是妄稱西藏民族是“從來(lái)不尊重生命的東方民族”。[28]
綜觀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期間《泰晤士報(bào)》的涉藏報(bào)道,可以看出,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世紀(jì)之交的中國(guó)面臨帝國(guó)主義列強(qiáng)瓜分的民族危機(jī)。英國(guó)是侵略中國(guó)西藏的主要角色,英國(guó)理所當(dāng)然地將中國(guó)西藏看作是自己的勢(shì)力范圍,并不容其他列強(qiáng)染指,任何覬覦中國(guó)西藏的企圖和行動(dòng)都會(huì)遭到英國(guó)的有力回?fù)簟_@從《泰晤士報(bào)》在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前后,對(duì)中國(guó)西藏的密集關(guān)注可以窺見(jiàn)一斑。從創(chuàng)刊以來(lái),《泰晤士報(bào)》向來(lái)以報(bào)道獨(dú)立、客觀、公平公正自居,但從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前后的一系列涉藏報(bào)道來(lái)看,該報(bào)對(duì)英國(guó)對(duì)英國(guó)發(fā)動(dòng)第二次侵藏戰(zhàn)爭(zhēng)起到了推波助瀾的煽動(dòng)作用,對(duì)國(guó)內(nèi)輿論、英國(guó)政府決策、國(guó)際輿論產(chǎn)生了惡劣影響,這充分暴露了《泰晤士報(bào)》充當(dāng)英國(guó)政府喉舌,為英國(guó)國(guó)家利益服務(wù)的本質(zh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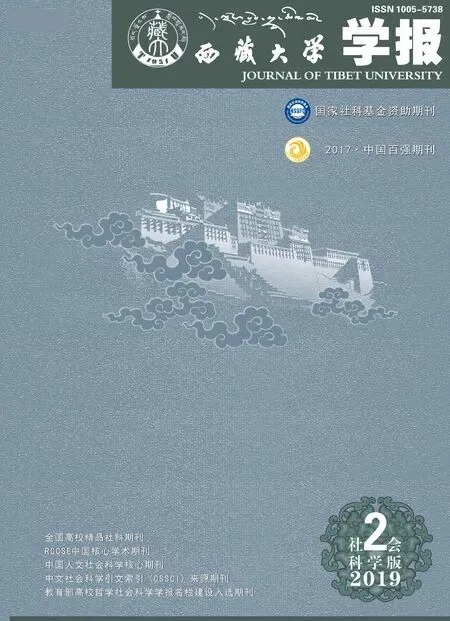 西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年2期
西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9年2期
- 西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論西藏基礎(chǔ)教育教研工作改進(jìn)方略
- 旅游負(fù)面體驗(yàn)喚醒機(jī)制及游客策略性行為研究
——基于進(jìn)藏游客的扎根分析 - 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中績(jī)效目標(biāo)的價(jià)值與困境
——基于中央和17省級(jí)區(qū)劃鄉(xiāng)村振興指導(dǎo)性政策文件的NVivo質(zhì)性研究 - 20世紀(jì)國(guó)外涉藏學(xué)術(shù)演化研究
- 國(guó)內(nèi)藏文學(xué)術(shù)期刊論文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分析
——以《中國(guó)藏學(xué)文摘》藏文版為中心 - 澳大利亞西藏研究現(xiàn)狀及發(fā)展趨勢(sh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