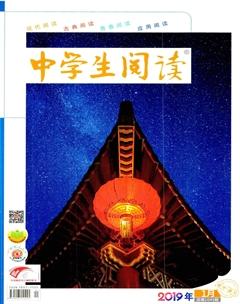麻雀的氣性
2019-06-26 09:04:36沈軼倫
中學生閱讀·初中·讀寫
2019年1期
關鍵詞:校園
沈軼倫
校園像個海灣。下課鈴一打,學生擁到操場上玩,如漲潮。上課鈴一打,學生回教室,校同安靜下來,如退潮。
退潮的時候,食堂的師傅燒菜,門衛整理收發室信件,司機在車庫沖洗校車。小羅背著他的修理箱走來走去,去修跑道的護欄,修花圃的柵欄,修領操臺的臺階。偌大一個校同,每天總有東兩壞,小羅總有東西要修。任何人都可以差遣他,老師的辦公室要裝個燈泡、修個抽屜,只要對著校園空地喊一聲“小羅”,他總會小跑著來應一聲。
其實小羅當時已到中年,只是老師們大都比他年長些。后來,即便新分配來做老師的大學生,也跟著叫。“小羅去做那個”“小羅過來修這個”,小羅滿臉笑著應承,聽憑這些比他小十幾歲的老師指揮。
小羅沒有辦公室。平時忙完了,就在自行車棚里搭個椅子棲身。每逢周五有勞動課,高年級的學生被要求去打掃校園,包括擦自行車棚。,到了車棚,就是到了校同的背陰處,老師們看不到了,調皮的男生認出校長的自行車,要去拔氣門芯。
小羅見狀,緊張地起身,像驅趕瓜田里的猹一樣揮手,要把他們趕走。但學生知道他的身份,并不岡為他是成年人而畏懼。帶頭的孩子撿起石頭敲著自行車棚的鐵欄桿,整個車棚震動起來,大家浪潮般有節奏地大叫“小羅,小羅,獵玀,豬玀”。小羅青著一張臉。
我見過他一個人把一棵臺風天倒下的羅漢松從花嘲拖走,見過他用鋸子將廢棄的大塊黑板分開。但現在他對著一群半大的孩子,雙手插在褲兜里,一句話也不回。……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兒童故事畫報(2019年2期)2019-01-22 20:01:06
兒童故事畫報(2019年1期)2019-01-18 00:40:46
兒童故事畫報(2018年12期)2018-12-20 23:14:52
兒童故事畫報(2018年11期)2018-11-15 23:48:04
兒童故事畫報(2018年10期)2018-10-24 21:22:06
兒童故事畫報(2018年9期)2018-10-23 19:25:02
兒童故事畫報(2018年7期)2018-10-23 19:24:54
南方周末(2018-06-28)2018-06-28 08:11:04
琴童(2017年3期)2017-04-05 14:49:04
小天使·二年級語數英綜合(2017年3期)2017-04-01 17:17:48
- 中學生閱讀·初中·讀寫的其它文章
- 《我對文學的判斷》閱讀
- 寫作什么
- 規劃閱讀時間
- 熱點素材
- 我所見的葉圣陶
- 2018年廣西北部灣經濟區中考作文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