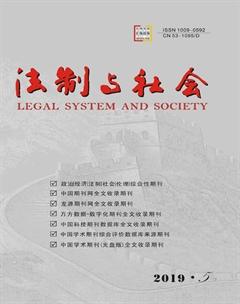物化理論:盧卡奇與霍耐特之比較
摘 要 作為社會批判有力武器的“物化”理論,一直是學者們所討論的焦點。盧卡奇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開創者承繼馬克思的思想,分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所出現的物化現象。而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當代的領軍人物霍耐特,在倫理維度指出物化現象是對“預先承認”的遺忘,為現代社會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解決思路。兩者雖然都將“物化”作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實踐訴求上是一致的,但在理論特性上卻有著很大的不同。
關鍵詞 盧卡奇 霍耐特 物化
作者簡介:楊佳星,天津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哲學。
中圖分類號:B5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5.342
對于“物化”理論,是學術界一直研究的問題,對解決當代社會中的物化現象也具有現實性意義。1923年,盧卡奇在其《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提出了物化理論。盧卡奇從他當時所處時代中的經濟現象出發,提出物化現象與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密切相關,并且從多個領域內對物化現象進行了細致分析,尋找揚棄物化的方式,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與上世紀相比較,為何在對人與物未曾消解的21世紀,曾經激起深刻反思的盧卡奇的“物化”概念,卻不再為人引用?究竟是哪些因素,弱化了批判“物化”現象的聲音與力道?在當代,霍耐特試圖從他的承認理論出發,重啟“物化”概念。霍耐特對“物化”理論的新的詮釋是在當代批判理論中復興物化概念的一次重要嘗試。
在當今社會,經濟發展速度極快,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提高,越來越多的人也憑借著科技的進步擺脫了一些困苦的工作。但物化現象卻依然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存在于經濟、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影響人們走向美好生活的步伐。在當今社會,人們如何擺脫物欲的干涉,如何過有意義、有價值的人生,是我們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因此,將盧卡奇與霍耐特的物化理論進行對照與審視對于推進當代社會實際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意義。
一、盧卡奇對物化的界定
盧卡奇曾明確地給出了物化的定義“在這里關鍵問題在于,由于這種情況,人自己的活動,自己的勞動成為某種客觀的、獨立于人的東西,成為憑借某種與人相異化的自發活動而支配人的東西。”對于這一定義還可以從以下四個層面來理解:
第一,生產勞動的物化。盧卡奇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人自己的活動,他自己的勞動,成為客觀的,獨立于他的某種東西,成為借助于一種與人相對應的自發運動而控制了人的某種東西”。人的勞動脫離人,而是化為控制著人的客觀性過程。在這里,盧卡奇引用了黑格爾的“第二自然”來說明生產勞動的物化,人類社會通過勞動創造的經濟王國,仍然表現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運動的客體世界。
第二,勞動者的物化。“人既不是在客觀上也不是在同他的工作關系上表現為勞動過程的真正主人。相反,他是被結合到機械體系中的一個機械部分。”在資本主義工業體系下,勞動者的勞動過程逐漸被越來越細化的分工轉變為專門的操作,工人們被規劃到一個個工業流水線上,每天重復著同樣的動作,他們體會不到生產完整的一件產品所帶給他們的意義。工人的時間被空間化,他們仿佛失去了時間性的概念,只是在一個特定的空間中不斷重復著做同一件事情。在這時,人真正成為了機器。
第三,人的意識的物化。盧卡奇認為,“隨著對工人工作過程的近代‘心理學的分析(在泰勒制中),這種合理的機械化被一直擴展到工人的‘心靈中。”隨著資本主義社會越來越追求生產與資本,物化也越來越深地浸入到勞動者意識中去。在整個勞動過程中,勞動者沒有了自身的精神追求,機械化力量壓制著他們的身體與精神,使他們的人格與精神分離,變成一種商品。人本身所具有的意志、思想和樂趣,都被攪碎到一架自動運轉著的機器中去。
二、物化:承認的遺忘
與盧卡奇不同的是,霍耐特認為不能只單單從經濟范疇去理解物化現象,這樣是不夠的。霍耐特認為,“物化就是預先承認的遺忘,我把它作為物化概念的核心。”霍耐特在倫理層面上從人與人、人與對象和人與自然三個視域對物化現象進行了批判。
第一,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物化。霍耐特在此特意舉了一個打網球的例子:當打球者一心想追求勝利時,他會忘記他的對手是他的好朋友,而他原先是為了對方才來打這場球的。雖然霍耐特在后來也認為這個例子不合適,但是他想要在此說明的是如果我們在實踐過程中太過于偏狹地專注于一個單一目標,以至于我們會不再注意到原初的動機或目標。還有一種就是各種各樣僵化的思考范式,例如對一些事物的偏見或者是刻板觀念會影響到我們的行為,迫使我們否認了先行的承認關系。
第二,人與對象之間的物化。這一物化,其實是從屬于人與人之間的物化的。在認知對象時,我們只是采用了同一性的思維方式,而沒有注意到認知對象對他人所具有的的意義。霍耐特在此還討論了對自然的物化,與物化他人一樣,物化自然也是一種認識上的“特殊盲目”——我們僅以客觀指認之方式看待動物、植物或無生命之物事,未能憶起,它們對周遭之人以及對我們自己而言,有著多元的存在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