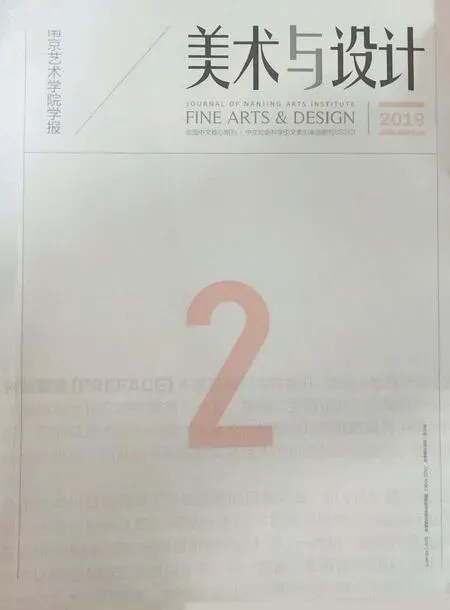藝術風格與歷史事件
——關于董其昌新穎畫法成因的三種史學解釋
王洪偉(清華大學 中國藝術學理論研究所,北京100084)
明代唐志契在《繪事微言》中有如下一段描述:“(雪景山石)當在凹處與下半段皴之。凡高平處,即便留白為妙。古人有畫雪只用淡墨作影,不用先勾,后隨以淡墨漬出者,更覺韻而逸,何嘗不文?近日董太史只要取之不寫雪景。嘗題一枯木單條云:吾素不寫雪,只以冬景代之。若然吾不識與秋景異否,此吳下作家有‘干冬景’之誚。”[1]這條畫論可能是關于董其昌“干冬景”山水稱謂緣起的較早記載。從風格形態上看,“干冬景”山水具備以下幾個典型特征:方向感明確的“直皴”筆法、凹凸感強烈和邊緣留白的山石造型(亦可稱為具備光影效果的“貝殼形”山石)、“取勢”效果明顯的畫面結構。在過去的數十年里,多位學者都曾關注過董其昌此類新穎創作手法的來源問題,提出了很多頗具啟發性的見解。然而,在這個看似微小的畫法問題上,目前學界既存在一些誤解,也還有很多細節問題尚未考證清楚。那么,針對新穎藝術手法來源的解釋為何會出現諸多分歧呢?主要原因在于畫家改變了以往雪景山水的慣常手法。那些慣常手法是前代畫家們經過長期實踐,在特定主題、風格形式及內在畫意之間,早已構成一種默契的表意系統。大多情況下,它們不再需要借助超出主題與風格之外的復雜線索就能清晰呈現,并被生存于類似歷史情境的人們所感知。董其昌創造的“干冬景”山水則不然,不僅在視覺觀感上缺乏自然雪景意象,而且,現代學者基于不同的學術訴求將其與某些歷史事件聯系起來,進而使之產生了文化價值歸屬的歧義。
一、美國學者高居翰的“一面之緣”說
美國學者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在上世紀70、80年代曾主張,要將晚明時期一些較為“新穎”的創作手法和風格元素,從中國既有師資傳統的連續性形態中解放出來,以此坐實晚明畫風變革普遍受到西方藝術的“外來影響”,使之能在古代中國晚期階段的山水畫風、畫法變革進程中切實地分得一杯羹。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這樣一個令人詫異的推論:晚明畫家董其昌在萬歷壬寅(1602)創作的《葑涇訪古圖》(圖1)中所運用的那種塑造形象怪異、“幻像錯覺感”強烈的“貝殼形”山石的明暗對照法,主要是受到了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所攜西方銅版畫的風格元素影響所致。其證據是:“董其昌在1602年時,曾經數度前往南京,他不但對利瑪竇有所知,而且也在著作中提到過利瑪竇,也可能與他有過一面之緣。”[2]82顯然,其論述意圖是想借助董其昌這位主流文人畫家來驗證“外來影響”觀念。然而,文章所說,“雖然沒有證據顯示董其昌確曾遇見過利瑪竇,但此一可能性極高”這句話,又實實地暴露出論者在缺乏確鑿史實證據時的主觀猜測態度。

圖1 (明)董其昌《葑涇訪古圖》,1602年,紙本水墨,80.2厘米×30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
高居翰本人似乎也考慮到,以如此輕描淡寫的文字作為西方影響一說的理論基礎,或許顯得過分薄弱[3]10,進而,他又對這件作品中“有反常之嫌”的山石結構和光影手法,做出了如下精心的風格描述與來源分析:“(此作)皴法乃是用來強化造型運動的方向動力,使觀者的眼睛隨著畫家所選擇的造型角度,平順柔暢地在物表上游移。不僅如此,這些皴法還提供了一種明暗效果,畫家在筆觸上由重而輕,由輕而至留白,系以漸層變化的方式呈現。……畫中有些地方,特別是左側中景地帶的貝殼形巖堤,董其昌在塑造巖塊時,運用了光影的手法,意外地予人以一種誤以為真的幻像錯覺感——令人意外的原因在于,無論是哪一種幻像手法,只要在董其昌的作品里出現,似乎就有反常之嫌。事實上,如果我們說他跟當時其他畫家一樣,或許受到了歐洲銅版畫中明暗對照技法(chiaroscuro)影響的話,那么,想必有許多研究中國繪畫的學者會認為這樣的看法根本荒謬透頂,連提都不敢提。”[2]81-82接下來,他又借助其所擅長的風格理論,將董其昌《葑涇訪古圖》與描繪西班牙風光的書籍插圖《圣艾瑞安山景圖》做了比較,試圖從作品風格特征比較方面尋求更多的支持。此種比較顯然是兩件作品在中國境內的出現具備共時性基礎。此圖來源《全球城色》第五冊。這部書的第一冊出版于1572年,大約17世紀初期才被引進中國。第五冊出版于1598年,進入中國的時間應該更晚。那么,董其昌當時是否有歷史機緣見過第五冊中的這件或者與之類似的作品呢?這依然無法得到證實。從畫面內容看,《圣艾瑞安山景圖》(圖2)畫中那種較為真實的描寫自然光影的手法,似乎難以和《葑涇訪古圖》畫面效果產生有效聯系。《圣艾瑞安山景圖》主要描繪了一種接近真實自然的山野田園風光和鄉間勞作場景,山石林木都表現出很強的自然形態,遠景中的城堡或莊園也沒有太多抽象化手法。畫面上那種較為真實的描寫自然光影的手法,與羅樾形容《葑涇訪古圖》時所說的“莫可名狀的物質形體”“完全與感覺絕緣”[3]42,以及與高居翰本人提出的董氏畫作有著很強抽象性和“人為秩序”的風格描述都決然不符。兩件作品殊異的風格特征,很難證實其間借鑒關系的存在。高居翰雖然認為,《葑涇訪古圖》中新穎的明暗光影手法“具有描寫物體陰影線的特性”,但實際上,它們絲毫沒有表達出任何類似西方繪畫以陰影線刻畫物體立體形象的真實感覺,缺乏《圣艾瑞安山景圖》山體呈現的自然紋理。山石間刻意的堆疊感趨向于抽象化,極大程度地消弱了山石和土坡的自然形態,與描繪受光效果的自然主義手法頗為不合。其山體受光與背光關系極為混亂,如平行并列的兩處山脊,一處受光,一處卻幾近背光。山石褶皺的陰影與光面的對比度,也沒有真實的自然光照射的感覺。幽邃的山坳幾乎不著絲毫筆墨,顯得極為明亮,襯得本應受光的前景山石愈發暗昧。高居翰的比較過程讓我們時時感到,藝術手法的近似或光影效果的強弱,已經成了其個人的一種直觀感覺。事實上,北宋時期很多山水畫作都具備強烈的光影明暗對照效果,如郭熙《早春圖》、范寬《溪山行旅圖》等。所以,這種藝術手法是借鑒于西方藝術,還是復興了北宋傳統,在高居翰的解釋下都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圖2 佚名,西班牙《圣艾瑞安山景圖》,銅版畫,《全球城色》第五冊
事實證明,自20世紀中期日本學者米澤嘉圃提出晚期中國繪畫受“外來影響”觀點之后,它已然在域外學界形成一股學術風氣。當風格描述與藝術史家本人看重的歷史證據和文化結構聯系在一起的時候,那么,關于這些“新穎”的風格手法的真實歷史淵源及其思想史價值,會被高居翰的推論導引到何方呢?這的確是一個令人憂慮的問題。他即便領悟了董其昌那種“擾攘不安的山水”風格形式是對晚明衰敗時局的回應,代表著“一種方向迷失以及世界已經歪斜崎嶇的感受”,但對《葑涇訪古圖》明暗對照手法來源的錯誤判斷,致使董其昌借助雪景山水畫法與畫意隱喻士大夫政治理想的深層意圖,基本沒有被呈現出來。藝術史家在諸多史料之間發揮著想象力,甚至會以某種臆想形態解釋過去的歷史事件,使得一系列零散史實在論者所看重的學術觀念下與藝術風格產生聯系。但是,在它們之間聯結成一種特定的影響關系是一回事,在史料證據方面做到取信于人,卻又是另一回事。毫無疑問,董其昌與利瑪竇“一面之緣”,以及其新穎畫法與西方銅版畫之間借鑒關系,只不過就是高居翰在“外來影響”觀念下借助豐富的想象力做出的一個主觀猜想而已。或許,他所坦言的——“不同的學科在某些方面有賴于各自的系統闡述,因此藝術史家的過失會造成其他學科學者的誤解”[4],注定會成為其自身研究的一句讖語!
二、臺灣學者石守謙的“杭州之行”說
萬歷丁酉(1597)八月,董其昌奉命出使江西南昌擔任鄉試考官。考試結束后,他于十月左右又順便回到松江小住,期間拜訪了好友陳繼儒的小昆山讀書之所——婉孌草堂,并為其創作了《婉孌草堂圖》(圖3)一作。這件作品在風格與畫意等諸多方面都有值得關注的新穎之處,是了解董其昌早期畫法創變的重要途徑。自從高居翰提出以上觀點之后,“外來影響”觀念在董其昌研究中就不斷地發酵。例如,時隔十六年,另一位美國學者班宗華(Richard Barnhart)于1998年發表了《董其昌與西學——向高居翰致敬的一個假設》一文。原本,代表美國東部學派的班宗華(上世紀60年代曾在普林斯頓大學跟隨方聞學習藝術史)在很多問題上都與代表西部學派的高居翰持不同意見,而在董其昌新穎畫法受西方藝術影響觀念上卻積極贊同,并進一步推進了影響關系發生的時間節點。這一事實說明,無論西方學者之間存在怎樣的學術分歧,但就晚明藝術與“外來影響”關系問題上卻能達成一定的共識。他在文章中進一步肯定了董其昌新穎畫法與西方藝術的關系——“毫無疑問,董其昌所親見的這些古畫經典作品,必然與筆者即將要辨識探討的另外一些文化元素,在董其昌不知疲倦、充滿旺盛企圖心、好似坩堝熔爐一般的頭腦中,共同而和諧地發揮作用,產生出現代中國山水畫原型《婉孌草堂圖》。”[5]334那么,“另外一些文化元素”究竟指什么呢?請看他文章的這段論述:“不論董其昌是否見過利瑪竇,董其昌應該知曉廣交中國士紳的利瑪竇之種種事跡。而且可以合理地推測:董其昌看過當時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為耶穌會傳教工作而帶到中國、包括歐洲繪畫樣本在內的那些遠西奇器異物。……根據董其昌1597年滯留南昌期間確實見過各色各樣的歐洲藝術品之假設,可以合理地推測董其昌這段時間可能拷貝了若干歐洲圖畫,隨后將新的元素加進了他當時正在進行的,對繪畫藝術與藝術理論的重新建構。依筆者之見,某些董其昌最令人關注的藝術技巧與理論模式,必然與他對歐洲藝術形象的反應緊密相關。”[5]336從基本觀點上看,班宗華一方面承繼了高居翰提出的董其昌新穎畫風受西方藝術影響之說,并且將董其昌和利瑪竇似是而非的“一面之緣”,提前至“1597年”的“南昌”一地,《婉孌草堂圖》就是此次會面的直接成果。

圖3 (明)董其昌《婉鸞草堂圖》,1597年,紙本水墨,111.3厘米×68.8厘米,臺北林百里藏
事實上,在班宗華表達《婉孌草堂圖》受西方藝術影響觀點四年之前,臺灣學者石守謙就已發表了《董其昌〈婉孌草堂圖〉及其革新畫風》(1994)[6]一文。雖然,班氏在文中也提及了,但對其觀點并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石守謙盛贊此作標示著一種全新風格的誕生,“開啟了繪畫史上可以稱之為‘董其昌時代’的契機。”文章對董其昌新穎皴法與傳統雪景畫法之關系做出極好的形態學闡釋,也借助這份個案研究深化了風格、畫意與畫史“重建”這項長期而艱巨的學術工程。若與高居翰等美國學者在“外來影響”觀念下解讀董其昌新穎畫風相比,這份研究成果自能體現中國學者問題意識的關注點所在。從學術淵源上看,石守謙對很多古代畫史問題的關注明顯受到其師方聞的影響,《婉孌草堂圖》研究亦不例外。1992年,方聞在堪薩斯舉辦的“董其昌國際討論會”上發表《董其昌和藝術的復興》一文。文章從“藝術復興”和“風格結構分析”兩個角度,專門關注過董其昌《婉孌草堂圖》這件作品的歷史意義。他認為此作主要取法于王維《江山雪霽圖》和董源《龍宿郊民圖》兩件作品。董其昌由《江山雪霽圖》而悟出披麻皴的由來,從中轉化出自己的藝術“家法”——以平行重復的“直皴”塑造凹凸山形。由“直皴”筆法構成的抽象山石形體,被置于平展的空白中,暗示出一種新的體量和實感關系。其畫面結構也以一種全新的“取勢”結構,將古代山水畫圖式引入新的階段。借畫面構成之“勢”,董其昌給山水畫帶來了一種新的綜合[7]。在方聞看來,董其昌對傳統藝術的復興并不是一味地摹擬傳統,而是通過深入師法古人而發現自我,在作品中所展示的不全然是其所師法的前代畫家,而是經過轉化的圖像[8]。

圖4 石守謙繪制的董其昌“杭州之行”路線圖
較之方聞單純的風格分析,石守謙將這種風格的成因與當時一個具體歷史事件聯系在一起:即董其昌創作《婉孌草堂圖》之前曾刻意繞道杭州。他根據董其昌現存的零散題跋描述了此行曲折的路線:萬歷丁酉(1597)九月上旬結束典試江西南昌任務之后,董氏本應取道鄱陽湖進入長江水路,順流而下至南京。全程雖長達一千二百里,但由此路回松江較為順暢,時間僅需十余日左右。而實際上,他卻選擇從南昌出發經由瑞虹、龍津、貴溪、弋陽到廣信府的上饒,再由之經玉山走衢江而至浙江衢州府,經龍游、蘭溪到建德縣富春驛,再走桐江、富春江,經富陽縣而抵至杭州,復行運河經嘉興再至松江。這條路線頗為波折,可謂水路兼程,異常辛苦,整個行程至少要耗費二十多天的時間(圖4)。那么,董其昌為何要選擇如此辛苦的行程呢?“杭州”一地對他又有著怎樣的吸引力呢?石守謙給出了這樣的解釋:即董氏想再度到杭州高濂家觀覽郭忠恕的《摹王維輞川圖》,甚至還期望有機會再次看到馮開之家藏的王維《江山雪霽圖》。這兩件作品是董其昌此時探尋王維畫風畫法的關鍵資料。所以,這次刻意規劃的杭州之行雖然路途周折,頗為勞頓,但“在第二次看完《輞川圖》摹本后三個月所作的《婉孌草堂圖》,即首度具體地呈現了他在此實踐的結果。”可以看出,石守謙對董其昌此次杭州之行事件的描繪,幾乎將這個時期與董其昌畫法變革相關的所有經歷,整合成了一幅帶有敘事性的歷史畫卷,也使得其多次“杭州之行”成為當前研究者們重點關注的一個“歷史事件”。
《婉孌草堂圖》的皴法究竟與藏于杭州的《江山雪霽圖》有何關聯呢?此作雖然是董其昌杭州之行后呈現的一件受王維影響的作品,但在石守謙眼里,它卻并未完全忠實于其范本。因為,《江山雪霽圖》巖石畫法的明暗效果,是為了刻畫接近自然特征的雪景之目的,白雪覆蓋的部分多為巖石裸露突出之處,顯得較為明亮,石塊下部或褶皺間的空隙出現較深的陰影效果。山石巖塊的表面,除了一些少量的線條勾勒外,也缺乏細皴,陰暗面主要依靠墨染而成,未見那種由皴筆層疊的現象。由于畫家的創作本意與描繪自然雪景已經無關,《婉孌草堂圖》中巖石坡岸上的明暗關系,僅僅是延續了雪景的視覺觀感特點,遂可以隨意地將“有皴”面加以延伸,“無皴”面予以縮減。從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陰暗面的擴大,而由明暗的虛實關系來說,此則是原關系的顛倒。但兩者筆墨的視覺效果卻有類似之處,都在巖塊簡易的平行重復分面之中,呈現平面的強烈明暗對比。依此結論,我們也可以推斷,《葑涇訪古圖》中特殊光影與明暗效果,與雪景山水創作手法有密切關聯,只不過在董其昌排除對雪景的自然主義表現后,視覺觀感趨于“風格化”了。可以說,石守謙對董其昌“新穎”畫法與《江山雪霽圖》等傳統雪景山水之間的形態學分析,功不可沒,在師古以創化的傳統畫學框架當中合理而有效地建立了二者關系,在去除西方藝術“外來影響”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那么,石守謙所看重的萬歷丁酉(1597)這次“杭州之行”,是否決定了《江山雪霽圖》對董其昌新穎畫法的影響呢?事實上,早在萬歷乙未(1595)下半年,董其昌就從馮夢楨那里借觀《江山雪霽圖》,并留存長達九個月。他對此作推崇備至,為之心摹手追。之前學界也極力肯定這件雪景山水對他早期畫法變革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價值,并力求找到一些可靠的作品依據。然而,根據記載來看,似乎只有已經佚失的《寒林遠岫圖》一件作品與《江山雪霽圖》有一點臨仿關系,卻也僅是“想象之作”。這種現象與董其昌當時高漲的推崇熱情,以及歸還馮氏之后多次感嘆“如漁郎出桃源”相比,顯得極不相符。從時間關系上看,《燕吳八景圖》作于萬歷丙申(1596)“夏四月”,此時董其昌還沒有將《江山雪霽圖》歸還給馮夢楨。經過數月的觀摩,想必他此時已經對這件雪景山水的風格畫法了然于胸了。按照“創意性模仿”的習慣,董其昌不可能對《江山雪霽圖》只鑒賞不臨仿。那么,《燕吳八景圖》能否提供一些借鑒依據呢?筆者比較發現,第三開《西山秋色》一作多處風格元素與畫面情境,就是直接取法或改造于現存日本的《江山霽雪圖》。從形制上看,《西山秋色》略顯局促的圓形構圖,似乎很難呈現橫卷《江山霽雪圖》上的諸多景致。然而,它經過巧妙地取舍壓縮、景致重構之后,以一種“環形集合”的方式改造了原來手卷自左向右緩慢的敘述結構。《西山秋色》最前景山石的“︿︿”形波浪式留白,與《江山霽雪圖》前段坡腳山石手法幾乎完全一致(圖5、圖6)。《江山霽雪圖》中段的訪友情境在《西山秋色》中也得到了巧妙的借用,只是山間平臺自左向右發生了扭轉(圖7、圖8)。后者所描畫的草堂居所面積稍顯局促,上有兩株枯松側出崖腳,示人以險絕之勢,但邊際有圍欄護佑,可供人憑欄遠眺。山外訪客可依“之”字形的山間石階到達此處。近景坡石上的樹木后面的確就隱約地畫有三位來訪之人,前面是兩位騎驢者,后面一人被山石樹木遮掩只現半身,似乎徒步而行,可能是隨行的仆人。最前面一人邊前行邊回首與后面兩位問答,左手指向前方的隱居之所,神情姿態與董其昌所論“畫人物須顧盼語言”一語極為相合。這件作品山石“凹凸”之形與“留白”手法也直接受到《江山霽雪圖》的影響。如左側山體以墨筆直皴表現出強烈的“凹凸”效果,原本以墨染表現“陰崖積素”的雪景效果,此時被轉化成直筆皴面,由墨筆的濃淡疏密劃分著山體的崚嶒與幽峭之勢。石體分面邊緣處的筆墨濃密逐漸過渡到較為疏淡,最后基本消失。隔鄰的另一片巖面則由此未著筆墨的邊緣皴起,再開始另一個體面的由濃密轉疏淡的漸層變化。如此往復,一座較大的石體就形成一種平行積疊的形態。為了增強山體向上的“取勢”能力,《江山霽雪圖》原來極為細碎的山石塊面組合被連續遞進的“凹凸”石體所取代。石面上的皴線勾勒也融匯在重復層疊并缺少明顯交叉編結的“直皴”筆法當中。因而,石守謙看重的這次“杭州之行”在董其昌畫法創變中就不具備決定性。

圖5 (明)董其昌《燕吳八景圖》之《西山秋色》,1596年,絹本設色,26.1厘米×24.8厘米,上海博物館,(局部)

圖6 傳(唐)王維《江山霽雪圖》,年代不詳,絹本水墨,縱28.4厘米,日本京都小川家族,(局部)

圖7 (明)董其昌《燕吳八景圖》之《西山秋色》,1596年,絹本設色,26.1厘米×24.8厘米,上海博物館(局部)

圖8 傳(唐)王維《江山霽雪圖》,年代不詳,絹本水墨,縱28.4厘米,日本京都小川家族,(局部)
再有,石守謙又是如何理解《婉孌草堂圖》這件作品的內在畫意的呢?這將關系到董其昌“干冬景”風格創變的基本動機與價值訴求問題,非常關鍵。他看重董其昌新穎畫法與雪景之間的關系,但又認為其畫法創變僅是相當“偶然”地受到雪景山水這個題材影響,創作本意與雪景畫意早已無關。事實上,石守謙的論述從始至終都將董其昌一生行跡看作是一位穿著朝服的閑散“山人”,其服官的主要用意僅僅就是追求經國之大業之外的個人藝術理想。顯然,這種理解沒能將董其昌選擇雪景手法的基礎性原因與其現實的政治境遇聯系起來,偏離了畫家借助雪景山水實施畫法變革的原始本意,使其所關注的畫法創變價值僅僅停留在追溯畫法技術這個表象層面。從“朝服山人”角度對《婉孌草堂圖》畫意的理解,固然可以上接文人隱居山水的主題畫意,但石守謙顯然對萬歷丁酉(1597)董其昌的政治境遇和創作意圖都缺乏深入認識。誠然,董其昌不斷地通過山居、招隱等題材的山水作品,表達著自己“素無宦情”的心態,但這也可能只是一種表象。事實上,歸隱題材的背后深刻地體現出士大夫身份的董其昌,對皇權制度下長期存在“出”“處”與仕隱選擇困境的一份自我思考。即便他的“服官”經歷為其藝術創作帶來很多便利條件,但這些卻不能否認其畫法創變起因及題材的內在畫意與其現實仕宦境遇的隱性聯系。《婉孌草堂圖》(1597)一作,絕非昭示他當時僅有歸隱之思,其筆墨手法也不完全是為了追求“元氣充沛”的文人趣味。孤高的“婉孌草堂”周圍,巖岫盤郁,怪石嶙峋,云水飛動不安的隱居環境,顯然令觀者有一種絕境難通之感,帶有一絲“風塵違壯志”的幽憤情緒。傳統高隱題材的靜謐幽居意境,被一種莫名的“擾攘不安”打破。畫作運用了李成“寒林”和郭熙“平遠”等北宋山水元素,這種內涵的現實指向,一方面是對受畫人陳繼儒數次科舉落第后選擇絕意仕進的同情與慰藉;另一方面與數月前發生的焦竑“科場案”更是密切相關。顯然,《婉孌草堂圖》的創作情境關乎晚明科舉與朝臣流放等多方面的政治主題。
三、筆者提出的“雪夜送歸”說
可以肯定,石守謙對《婉孌草堂圖》畫法元素與雪景山水關系的追溯,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學者的“外來影響”觀點,也凸顯了董其昌畫法變革的內部連續意義。但在畫意內涵與創作情境方面的誤解顯然將董其昌畫法變革的政治思想史意義簡單化了。目前,擺在我們面前不得不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深度探求董其昌究竟于何時對雪景山水產生了濃厚興趣,又為何無限掩飾自然主義風格的雪景意象呢?
就其畫風轉變時間而言,辛卯(1591)這一年絕對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轉折點。在將近兩年的政治生活中,諸多內、外因素的交合,使他對自己的藝術風格與主題畫意有了新的思考與創變方向,絕非限于樹立文人畫正統地位或分宗立派的單純意圖。那么,這種判斷的依據是什么呢?坦白地講,主要線索都隱藏在一幅不起眼的冊頁山水當中。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紀游圖冊》,不僅無法與董其昌一些風格成熟的“大作”相提并論,甚至連它自身的真偽,目前都成了備受爭議的話題。這件圖冊共計十九開,其中包含三十六幅山水畫作和兩份書法墨跡。絕大部分作品可能都是壬辰(1592)春,董其昌途經黃河期間,因“阻風待閘,日長無事”而作。所繪內容,多取自他辛卯(1591)三月中旬以來所游經的各處勝景。與冊內其他作品相比,第十九開右側的那幅山水至少有以下四點特別之處:
其一,它是整件圖冊當中唯一一幅有獨立畫題的作品,名曰《西興暮雪圖》(圖9)。其余作品上雖也不乏跋語,有的甚至長達近百字,但卻都沒有以如此明確的畫題來點醒畫意的。其二,董其昌當時雖然途經錢塘江南岸的西興一地,但從風格和畫意來看,它與“聊畫所經”的紀游玩賞性山水不甚相合。這是一幅典型的雪景山水,群峰積雪、林木僵仆,意境荒寒的景致帶著明顯的情感內容。畫題之“暮雪”一詞,也不禁令人聯想起《瀟湘八景圖》之《江天暮雪圖》所描繪的那種夜幕降臨、漫天飛雪之際,遭遇貶謫的士大夫天涯羈旅之窘境。其三,畫上跋文雖僅寥寥數語,看似簡率,了無深意,但卻提到數月前在“爭國本”事件中被迫致仕的一位朝廷要員——內閣二輔許國,即董其昌的座師。這種即便很隱晦但又的確涉及現實政事的題跋現象,在董其昌的藝術創作生涯中并不多見。其四,從創作時間上看,這幅作品較之冊內其他畫作,至少要早上近兩個月左右,理應位列整件圖冊之首,實際上卻被“刻意”藏匿于圖冊之末。或許,正是因為處于圖冊之末的緣故,長久以來,這幅冊頁山水的特別之處從未引起過人們的注意。但其中隱藏的歷史信息卻不可小覷,它們暗示出這位初涉政壇的翰林院庶吉士內心里的那股政治性焦慮情緒。下面,筆者也圍繞當時的一個“歷史事件”展開分析。
從政治前景來看,萬歷辛卯(1591)這一年對于董其昌個人而言,絕對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在兩年前的己丑(1589)科試中,他高中二甲第一名,當年六月十八日即獲選翰林院庶吉士(亦稱“庶常”),開始了為期十年的第一階段的政治生涯。從明代的選官制度看,翰林院庶吉士多選自當年成績優異的進士,是日后仕途升遷的重要基礎。這對于任何一位獲選者而言,都代表著良好的政治開端。截至萬歷辛卯(1591)二月底,董其昌在翰林院的學習時間已近兩年,要不了多久,庶吉士期限就即將結束。“解館”之后的具體任職及去向,都已提上了議程。毋庸置疑,他憑借二甲第一名的科考成績,其座師許國又是內閣二輔,再加上翰林院諸位館師的褒揚與舉薦,未來的仕途前景應該是極為光明的。然而,若就實際形勢而論,當時朝廷里發生的諸多人事變故,喻示著萬歷辛卯這一年對董其昌而言又絕非是一個好的年景。因為在之后的數月間,他就相繼失去了兩位重量級政治人物的護佑,一位是館師田一儁,一位是座師許國。突如其來的人事變故,對這位剛剛踏上仕途并躊躇滿志的年輕庶吉士而言,無疑會帶來不小的打擊,其內心的焦灼不安可想而知。

圖9 (明)董其昌《西興暮雪》(《紀游圖冊》“臺北本”第十九開),絹本,31.9×17.5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令人感興趣的是,董其昌對待這些政治變故的態度與行為顯得有些吊詭。先是辛卯(1591)三月初,時任禮部左侍郎并執掌翰林院的館師田一儁“辭疾歸,未行卒”(《明史·田一儁傳》)。身為學生,董其昌自覺有著義不容辭的責任,堅持要護送其師棺槨回福建。隨后,他專為此事“請急”,對即將散館后的個人去向、官職封授等仕途大事都置之不顧。這次護送行為在當時顯得極為高調,不僅明確見載官方正史、好友文集,如《明史·董其昌傳》專門記載了這次護行壯舉:“禮部侍郎田一儁以教習卒官,其昌請假,走數千里,護其喪歸葬”;好友陳繼儒(1558—1639)云其“匍匐數千里,輿其櫬,送還閩中”(《陳眉公先生集》卷三十六)。《松江府志》“名宦四”中也明確記載了此事。而且,董其昌本人在書畫題跋中也時有提及,表面上看似不著意,但處處透顯出一絲得意之感。此舉在當時也誠實受到朝中同僚們的贊嘆,如邢侗(1551—1612)在《松江董吉士玄宰以座師田宗伯喪南歸,慨然移疾護行,都不問解館期,壯而賦之》一詩中云:“射策人傳董仲舒,玉堂標格復誰知。環堤御柳青眠幾,近苑宮桃匠笑初。鄉夢數過黃歇水,生芻先傍馬融居。多君古誼兼高尚,碩謝銅龍緩佩魚。”[9]“緩佩魚”一語,即指董其昌不顧翰林院解館后封授官職之事。護行往返之旅,大致從辛卯(1591)三月中旬持續到秋季,前后長達六個多月的時間。旅途跋山涉水,曉行夜宿,身心之勞頓自非尋常之出行游歷可比。
另一件政治變故發生在萬歷辛卯(1591)九月前后,董其昌此時應該在完成護行任務后的返京途中。這次變故直接起于“爭國本”事件。當時,工部主事張有德貿然“以儀注請”之舉和“群臣爭請冊立”等行為,違反了去年“廷臣不復瀆擾,當以后年(1592)冊立”的約定,極大地忤怒了萬歷皇帝。當時,內閣首輔申時行“適在告”,身為內閣二輔的許國“欲因而就之,引前旨力請”,但遭到萬歷皇帝“大臣不當與小臣比”的嚴辭批評。他深感不安,“遂求去。疏五上,乃賜敕傳歸。”(《明史·許國傳》)于是,許國就在這次突如其來的事件中被迫致仕了。這次變故是“爭國本”初期發生的一件較大的政治事件,可謂朝野轟動。內閣首輔、二輔不僅都被迫致仕,而且二人原有的矛盾公開化,朋黨門生也互相攻訐,政治遺患甚多。董其昌在事情發生的當下可能并不知曉,但回到京城后對座師許國的政治遭遇定會有所耳聞,依照情理甚至還應該親自登門安慰。但據目前所掌握的歷史資料來看,他就此事并未明確地發表過任何公開或私下的個人意見。與董其昌己丑(1589)同科登第的焦竑,同尊許國為座師,在許國被迫致仕之后,曾專門撰寫了《贈尊師少傅許公歸新安詩序》以表學生慰藉之意。所以,董其昌這種極為冷淡的態度,與數月前“高調”護行館師田一儁歸葬閩中之舉反差極大,著實令人費解。當然,我們并不是苛求董其昌對座師的政治變故非得擺明其個人立場,只是從情理上講,他似乎不應該表現得如此冷淡。畢竟,許國對有兩次鄉試落榜經歷的他來說,有著莫大的知遇之恩。誠然,董其昌就算有著李日華所說“憂讒畏譏”的性格特點,但就其操行和交友情況而論,他卻又絕非那種趨炎附勢、見利忘義的小人。終其一生,無論是出于何種目的,他都非常看重自己與師友們的情誼。這些人既有一時得勢的權貴,亦有仕途艱窘的謫臣。那么,董其昌在許國因“爭國本”而被迫致仕這件事上,到底持什么態度呢?他有沒有一些具體的舉動呢?或許,董其昌內心實在不愿被后人誤解為冷漠無情缺乏感恩之心,所以就以一種“曲筆”的方式,在《紀游圖冊》第十九開那幅不起眼的雪景山水的角落里,為我們留下了一點蛛絲馬跡式的線索。畫面右上方題有這樣一則楷書跋文:“西興暮雪。予時送新安許太傅還家。不值宿于逆旅,厥明及之。辛卯冬歲除前五日也。”這則跋文雖然只有寥寥數語,卻有微言大義之效。它確鑿地證明了董其昌在座師許國致仕后不久,就與之有過一次親密接觸。具體時間為萬歷辛卯(1591)年末,主要目的是護送座師回老家新安。但跋文語意過于簡要,讀者很難全面了解這次送行之旅的行蹤始末,越發突顯了這次師生會面行為的私密感。目前,可知的歷史信息似乎顯得有些支離斷續,甚至還被董其昌本人刻意地加上了層層“密碼”,盡其所能地遮掩著他與座師許國的私下接觸,也極力壓制自己的內在情緒。不過,畫題之“暮雪”與實際送行途中遭遇的“逆旅”兩相映襯,處處使人聯想起“桂棹兮蘭枻,斲冰兮積雪”“暮雪天地閉,空江行旅稀”等詩句描述的行旅窘境。這幅群峰積雪、滿目荒寒的雪景山水,顯然關乎著流放主題。它是否在暗示座師許國剛剛被迫致仕之時,那種“榮衰之際,人所難處”(董其昌《許伯上配鮑太孺人墓志銘》)的落寞心境呢?圖文之間的互襯,不禁令筆者又想起了董其昌送歸另外一位新安友人(可能是汪宗孝)時所寫的詩句:“寂寞玄亭路,蒼茫釣客舟。何當送歸夜,風雨滿西樓。”[10]若將最后一句中的“雨”字換成“雪”字,并配以《西興暮雪圖》之景致,再進一步聯系許國被迫致仕和董其昌雪夜送歸的“逆旅”現實境遇,觀者一定會被彼情彼景所感染,內心頓生一股真切的同情之感!
從畫意傳統來看,《西興暮雪圖》一作繼承了《瀟湘八景圖》之《江天暮雪圖》所蘊含的士大夫面臨崇辱榮衰之際真實心境的畫意。美國學者姜斐德對此種繪畫主題與宋代士大夫政治境遇關系,作過較為深入的研究。她認為,受到毀謗和冤屈的人,很自然地會被凄涼的境象所感染,“親眼目睹個人世界的傾頹,也使那些失掉尊崇的士大夫們開始探究關于絕望和衰亡的主題”。《江天暮雪圖》呈現了“陰”的極致情形:夜幕降臨,飛雪飄飄。對11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流放者而言,與他們心境更為接近的是以冬季而“陰”之主導的范式。對于在遲暮之年遭受政治厄運的宋迪而言,“江天暮雪”中的冬天景象很可能就是衰亡的象征。“雪埋沒了熟悉的路標,方向迷失了,大自然的層次隱匿不見。它使行動(仕途的發展)變得盲目而危險”[11]86。姜斐德還進一步分析了這種詩畫意境的更早淵源:在楚辭中,“冬景”較之“秋景”要少見,一旦下雪,就總是帶有負面的象征。在《九歌·湘君》中,冰雪是阻止詩人前行的眾多障礙之一。如“桂棹兮蘭枻,斲冰兮積雪”,漢代王逸注云:“言已乘舟,遭天盛寒,舉其棹楫,斲斫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已勤苦”。唐代張銑在王逸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徒為勤苦,而不得前”的解釋,進而更使得意境苦寒、前途渺茫。南宋朱熹的注顯得更加全面:“此章比而又比。蓋此篇本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之不偶,而此章又別以事比求神而不答也。棹,楫也;枻,船旁板也;桂、蘭,取其香也;斲,斫也,言乘舟遭盛寒,斲斫冰凍,紛如積雪,則舟雖芳潔,事雖辛苦而不得前也。”[11]87諸多解釋都表明,士大夫“得君行道”之理想往往在現實中會遭遇“冰雪”(政治斗爭)之阻。故此,《西興暮雪圖》這件作品之所以令人感興趣,就在于其反映出天意與人事之巧合。座師許國被迫致仕這個政治事件,對董其昌早期藝術風格手法創變的推助力是不可忽視的。其間的因果關系,恰是以士大夫類型畫家為主導的雪景山水風格與畫意演生的深層機緣。從風格題材到畫意內涵,從政治窘境到歸途“逆旅”,都具有了內在的統一性,“雪夜送歸”這個事件具備了真實的史學意義。有了它的佐證,筆者對董其昌畫法變革基礎及深層意圖的判斷,就有了一個合乎情理和史實的敘述基礎。
“爭國本”事件引起的政治動蕩對董其昌本人最初的影響,可能就是座師許國被迫致仕這次變故了。按常理來講,親自護送座師還家本應是一件非常榮幸之舉,但董其昌卻將這次師生會面的事實,深深地藏匿于《西興暮雪圖》一作角落的題跋里,又將之置于紀游性質的圖冊之末,并且終其一生從未再提及過此次送歸之旅。這種情形與董其昌數次回憶護送館師田一儁歸葬的做法,形成了極大反差。究其本因,恐怕還是基于當時朝中政治斗爭的考慮。董其昌送兩位老師歸家的不同方式,本質上反映出“爭國本”事件的變化。館師田一儁“辭疾歸”之舉,雖然也與“爭國本”事件有些許關聯,但時間發生在萬歷辛卯(1591)年初,他本人最終也是“未行卒”。為此,萬歷皇帝還專門派遣福建布政使司分守建南道左參議吳嶙諭祭田一儁,以示皇恩浩蕩。故此,董其昌“移疾”護行之舉不至于在政治上給自己帶來不良影響,反而還備受嘉議。而數月后的張有德“以儀注請”之舉惹得萬歷皇帝龍顏震怒,“爭國本”局勢急劇惡化。緊接著,內閣首輔申時行、二輔許國不僅都被迫致仕,而且二人原本就有些宿怨,這件事后便公開反目,朋黨門生之間也互相攻訐。此時朝中當政者又都是申時行臨走前提拔的人,如張位、趙志皋等,各個府縣也都有其羽翼,實可謂大僚爭于朝,小吏斗于野。董其昌此時若以過分親密的態度送座師歸家,難免會使自己陷入復雜的政治斗爭當中,甚至將引起萬歷皇帝本人的反感。所以,他護送座師許國歸家之舉,就必須采取極為隱秘的方式。因目前相關文獻記載的缺乏,筆者推測這次秘密的“雪夜送歸”,有以下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董其昌先于十月中下旬南歸,在松江小住一段時間后,即回京護送座師許國歸家,連上行路時間總算起來,可能不超過兩個月。然而,在不足兩個月的時間里,董其昌如此頻繁地南歸北返的可能性似乎比較小,如何有寬裕的時間去“大搜吾鄉四家潑墨之作”呢?而且,在皇帝震怒及朝內政敵虎視眈眈的情形下,這種做法恐怕過于明目張膽了;另一種可能就是,董其昌完成護送田一儁歸葬的任務后先回京復命,在告歸松江之前,曾與座師許國有過私密的接觸。二人提前商議好還家的具體日程計劃,并約定中途會面地點,再由董其昌親自護送老師一起回離松江并不算遠的老家新安。這種可能性較大,也較為隱秘,外人很難知曉。
就表面價值而論,“雪夜送歸”這個微小的歷史事件實在是微不足道的。但因天意與人事的偶合,以及被刻意隱藏的行為而展開的因果聯想,將掀起對董其昌早期(翰林院時期)風格畫法變革的現實動機與歷史意義的追問,也促使我們將其獨創的“干冬景”山水與其士大夫身份及政治境遇結合起來一并考慮,由此而展現雪景山水在晚明時期變得更加深邃而隱晦的政治性內涵。萬歷時期,由于皇帝與大臣之間的關系日漸緊張,文官集團內部也有著錯綜復雜的矛盾與沖突,無論是在朝為官者還是辭官歸隱者,行為舉止都變得異常地謹小慎微,甚至整個晚明時期都彌漫著一股濃重的“政治性”焦慮,這也是晚明時期雪景山水在風格上愈加抽象化的本質根源。在此期間,董其昌若仍以世人皆能領會的傳統雪景山水手法進行創作,顯然不太適合當時復雜的政治斗爭局勢,很可能會被曲解為是創作者對其政治遭遇的不滿,甚至是直接針對最高統治者萬歷皇帝本人怠政與不公的抱怨。所以,正是基于對萬歷一朝政治狀況的審慎觀察,董其昌逐漸拋棄了傳統“暮雪”題材較為直觀的自然主義手法,將原本趨近于自然主義風格的雪景山水,轉換為一種更加含蓄、抽象,充滿形式感的“干冬景”風格,以此避免政治風險。現存上海博物館的《山居圖》一作大約作于萬歷壬辰(1592)左右,其風格是從傳統雪景山水向“干冬景”過渡的一種中間狀態,大致提供了董其昌實施新穎風格畫法創變的起始時間。“雪夜送歸”一事及《山居圖》的風格形態,不僅將有力反駁西方學者提出的“1597年”(班宗華)或“1602年”(高居翰)的“一面之緣”說,同時也降低了石守謙極為重視的那次“杭州之行”的史學價值。
翰林院期間,藝術創變訴求與特定政治境遇的交織,促使董其昌不得不借助某些具有歷史觀念和象征意圖的畫法、畫意隱衷自己的仕宦處境與政治理想。從接近實景的《西興暮雪圖》開始到成熟“干冬景”風格的出現,他成功地借助傳統雪景畫法,完成了從風格形式到畫意內涵的巧妙融合。來自復雜政治境遇方面的壓力,使得自然主義風格的雪景山水在“君子思不出其位”政治哲學觀念指導下變得極其抽象化,原本直觀的主題畫意也就變得愈加隱晦起來。這種抽象化的雪景山水,是董其昌經歷了翰林院政治生活之后的一份創造,代表著晚明時期一種新的政治生態,曲折地表達著萬歷王朝的士大夫們所身處的更加復雜的政治境遇,以及他們因此而提升的更為智性的生存智慧。可貴的是,“干冬景”山水并未失去豐富的思想內涵,在雪景畫意上“入乎其內”,在風格形式上卻又“超乎其外”,在“可見”的風格形式中彌散著很多“不可見”的人文思想與時代特征。這樣的風格形式逐漸會轉化成一種復雜的思想代碼或圖像象征,亦要求我們具備從圖像經驗或創作手法的“習俗慣例”,轉向對新“象征符號”的體察與解釋能力。當然,對于熟稔雪景山水手法的古代士大夫而言,即便是異化的新穎風格元素,或許,憑借其知性也是可以達成一種共情的。
結 語
任何一種歷史意義,幾乎都是歷史學家結合現有史料證據和現實學術訴求綜合敘述而成,每一個受到關注的歷史事件也帶有類似的特點。基于此,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本身真實性的關懷程度,與其在建立特定歷史意義過程中表現出的樞紐能力相比,有時會稍顯遜色。本質上,一位畫家或一種藝術風格與某個歷史事件之所以能夠被聯結成歷史結構進行敘述,一定程度上說明關于它們的現存記憶與其歷史真相之間,有一部分內容是可以被研究者豐富的想象力所填充。那些“填充物”必然與研究者的學術旨趣和文化立場密切相關,平衡著歷史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的動態關系。因而,藝術史既然不是那種外在于思想的純物質世界,那么,關于以往事件的想象與重構就一定要考慮它能夠承載的的現實文化意義。這也可能使得藝術史研究的重心將不完全局限于對事件本身真實性的關注,而是在一種特殊文化語境中努力地創造出一個合乎情理的敘事結構。天然的時空彈性與各種不期而遇的機緣巧合,最終呈現出史學研究最曼妙和最令人著迷的一面。不過,任何一個史學論斷的說服力與持久力,必須符合其證據與其他文獻史料或價值觀念不發生沖突的前提下,才能夠成為史家所建構的歷史綜合體的有機組成部分。換言之,在排除史學家過度臆想之后,史學解釋的學術效力一定要述諸于事件本身的客觀性,以及它在發生當下的真實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