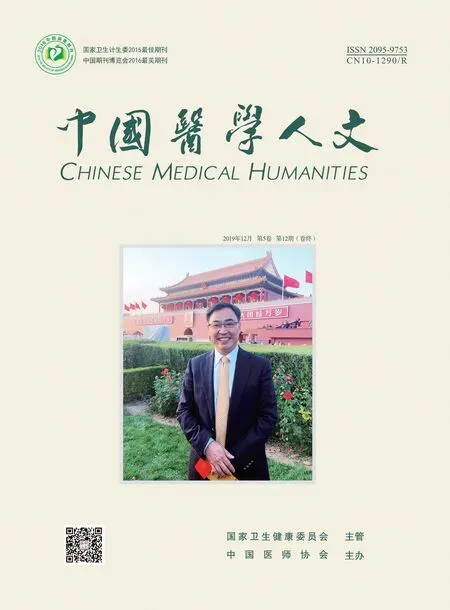愿你幸福
文/何雨田

自從事醫院宣傳工作以來,無論是機緣巧合也好,職責所在也罷,我常會碰到形形色色的患者,而其中的大部分,都與“求助”脫不開干系。下面我所說的三段故事,分別來源于三個患者。他們雖承受著病痛的折磨而苦不堪言,卻在不知不覺間,讓我見到與疾病抗爭過程中的那些令人感動的瞬間。
不可減損意志一根可能被壓彎的脊梁
我叫他湯老。彼時我剛剛入職,正在三樓門診部東張西望找選題,卻突然被一個聲音擋住了去路。“同志,我想請你幫個忙,可以嗎?”循聲望去,他身上一件白色的運動T恤因為穿得久了被汗漬啄出了一個個針眼大的破洞,一條卡其色的長褲褲腳被擼得高高的,留下兩根麻稈樣的腿在空中閑晃,一頭花白的頭發像思維般發散著并不十分貼合,僅有皺紋縱深的臉上架著的一副顫巍巍的金絲眼鏡顯示出他知識分子的身份。
他真的好瘦啊!真正的“皮包骨”說的應該就是他了。他說,由于未確診的類似于腸胃炎癥狀的疾病,他已經不能進食,甚至連水都難以負荷。現在的他疲累交加,連說話的力氣也快喪失。“請問同志,你們這里的住院費用是怎樣算的?有沒有條件好些的病房?”他有氣無力地問,身邊的阿姨幫他拍著胸膛順氣。得知老年醫學科病房條件較好但須有相應資格時,他一邊說“我有的,我有的”,一邊拿出資格證書,這才和我說起了他的故事。
別看湯老皺紋滿面、頭發花白,他其實還不到60歲,而身邊那位看似他女兒的阿姨實際是他的妻子。作為新中國最早一批出國的杰出人才,湯老早早地就在迪拜開始了生物研究。然而,事業順風順水的他,卻在幾番思忖下,決心放棄大好事業回國。待得知我也曾留洋,湯老好似找到知音般開懷大笑,疾病仿佛去了大半:“What a coincidence!”隨后竟用英語與我交流,他樂此不疲地說他的理想,說他的成就,好似瞬間把我當作了自己人。
我望著說得眉飛色舞的他,心想疾病折磨著他的身體卻不能消磨他的意志、掩蓋他的靈魂。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執拗地固守著曾經的輝煌,雖然陳舊,卻也是病痛中象征希望的救命稻草,將他帶離疾病的困擾,哪怕僅是瞬間的快樂也好。金絲眼鏡折射出他眼中不屈不撓的鋒芒,那是超越破敗軀殼之外的智慧與理想之光。
不可喪失尊嚴你是我的眼
初見他們是在眼科病房,我帶著記者去采訪。他叫施云希(化名),她叫吉朝華(化名),夫妻雙盲。此次入院是為了他們剛剛出生的孩子:僅僅5個月大的嬰兒,由于患有先天性白內障和小眼球,小嬰兒生下來就很難見光。聽說省人民醫院可能讓孩子復明,他攜妻子義無反顧地離開蕪湖老家,走上了艱難的求醫之路。
雙盲夫妻,如何養育孩子?我見到他們的第一眼,就有這樣的疑惑。不要說雙盲了,就是尋常夫妻,初為人父母也該是慌亂的;而作為日常生活都需要他人幫助的盲人,做出生兒育女的決定不得不說是一種勇敢。
然而,你能看出他們很幸福。作為一個父親,施云希對孩子的親近無可比擬。他的臉上,一直蕩漾著初為人父的喜悅,雖然看不見,可他的手卻總是習慣性地輕撫著孩子的面龐,用觸摸去感知這個小生命的長度、用雙手去感知他的重量,聽見別人說孩子長得像他,他就會心一笑。相比之下,吉朝華卻表現得很尷尬。施云希是后天失明,而吉朝華生下來就沒有見過太陽。對于這個孩子,她好似很無措,孩子哭了她抱在手里怎么哄都哄不好,只得交給丈夫,多數情況下她都甘愿做一個影子,生怕動一下就會連累到別人。
“你們是怎樣認識的?”我問施云希。“推拿。”他說。原來,施云希在當地的推拿中心做按摩師傅,吉朝華曾是他的患者。“她結過婚的。以前有那個多囊卵巢,她前夫說她生不出孩子整天打她,我給她按摩按好了。”雖不知真假,可施云希的臉上滿是自豪。“有一次按摩,按著按著我就問她要不咱倆試試,她就嫁給我啦。”施云希說這句話的時候,吉朝華害羞地低下了頭。此時,我才意識到為什么這個女人會如此的無措,為什么她會甘愿做一個無聲的影子。生來失明,她已把自己當作負擔,第一次婚姻中遭遇家暴,更是有苦難言,興許生下孩子亦是聽命于現任丈夫,單純如她,并不知道這意味著怎樣的責任。
記者團里有人突發奇想,想讓夫妻倆幫孩子換尿布,以表現出他們照顧孩子的無措。于是,攝影師和編導一干人等圍著病床,就像在等著看一個笑話,我也在等。只見抱著孩子的施云希將孩子輕放在病床上,三下五除二揭下了孩子的紙尿片,同時還用手碰了碰孩子有些濕潤的小屁股,隨后熟練地為兒子換上了新的紙尿片。他手法那么嫻熟,大概只耗費了兩三分鐘,我看著這位靈活歡樂的奶爸,覺得他根本未有殘疾,他只是一個尋常的父親,他只是在做一個尋常父親該做的事。那些所有等著看笑話的人,包括我,都挨了現實的一記耳光。
末了,我領著施云希去超市,他說要給妻子買些牛奶喝。拄著盲人拐杖的他并不需要我提點腳下的路。只是當有人經過與他撞到,他會習慣地說“對不起”,而后盡量貼墻走。當時我問他,究竟對孩子的病是怎樣想的,他說,孩子他媽并不是很想治療,但是他還沒有放棄,因為他不想讓孩子今后也在撞到人后習慣性地說“對不起”。
我想,即使人礙于病痛,也不可喪失尊嚴,就像施云希在眾人圍觀時能夠嫻熟地幫兒子換紙尿片,就像雜草在風雨中堅強扎根,就像我們在苦難之中微笑,就像我們在悲傷當中祈禱。所以我希望患者們不論能否治愈,都能堅強地昂首活著。
不可忘記友愛你生橋南,我生橋北
她們是雙胞胎,姐姐叫徐嬌楠(化名),妹妹叫徐嬌北(化名),姐妹倆都在讀高中。看見她們的時候,姐姐正臥病在床,手里握著本經書。醫生的診斷書很明確: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而且是惡性度極高的那一種。
雖然知曉疾病并不樂觀,嬌楠還是會與我開玩笑:“你知道我們的名字有什么來歷嗎?”一邊問,一邊眼里閃著狡黠的光。“因為媽媽是在送去醫院的路上生的我們倆。我們一個在橋南出生,一個在橋北出生。”她說著,眼睛里還帶著笑。我讓她好好休息,然后把妹妹嬌北請出病房。

我告訴她,我也是雙胞胎。她立馬興奮地問:“你們是同卵還是異卵?”我說是同卵。瞬間,她就像是蔫了的皮球,無精打采地說:“要是我和姐姐也是同卵就好了,那樣配型就更容易成功,我就可以救她了。”言語中流露出與年紀大不相稱的成熟。
同在一起的親戚說,嬌北是最近才明白什么是同卵、異卵的,也是剛剛知道什么是骨髓配型,成績一向拔尖的她在家里一向是小霸王,受盡萬千寵愛。可是自姐姐生病以來,她仿佛變了一個人,為姐姐打飯,為姐姐讀書,為姐姐蓋被,為姐姐整宿不睡盯住輸液瓶,凡事都親力親為。
我問嬌北:“姐姐對你好嗎?”她說好。她說往常晚自習結束,姐姐都會趕在她之前回家,然后給她暖被窩,等她回來。她說姐姐腿上出現紫癜并常流鼻血的時候,還是會幫她洗衣服。她說著說著就哭起來了,她說要趕快,要趕快對姐姐愈加好。
我不忍心再問。疾病帶給我們痛苦,同樣也將這悲傷賜予我們的親人。此時,任何言語都顯得蒼白;此時,唯有不忘友愛,唯有施與關懷,才能不枉此生,才能獲得雙方靈魂的共同救贖。
這些患者和我們只是生命中的偶遇,但他們教我學會珍惜,珍惜生命中每一次的擦肩而過,珍惜生命中每一句的噓寒問暖,珍惜每一朵野花、每一口糧食,珍惜友愛、珍惜自我。愿他們都能獲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