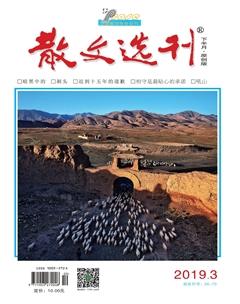一條游向老家的魚
曹學林

有人在喊,聲音不很清楚,人影也有點模糊,似乎喊的是我的乳名,似乎有什么急事在喚我。誰呢?——哦,是父親,正站在老宅門前向我招手呢!竹子一叢叢在屋后立著,知了在河邊高樹上嘶鳴。我向老家奔去,可兩腿沉重得一步也邁不開;我大叫著“爸爸”,可嗓子眼兒像被堵住發不了聲。我只能跳到河里,變成一條魚,拼命地向前游。父親好像也跳入水中,也變成一條魚。離我很近,又似離我很遠,我總是抓不到他。心中一急,倏然驚醒——原來做了個夢。
思緒如一只“吱吱”鳴叫的蟬,穿過夜空,真的飛回了老家,飛回了那個生我養我的、住著我年邁雙親的老家。
想到老家,心中卻生出不安和愧疚。父母不愿隨兒女進城,他們住慣了那個生活了一輩子的“老窩”,在那里舒心、自在。兒女在滿足他們心愿的同時,理應“常回家看看”,可就是這個唱著感人、說著輕巧的五個字,做到卻不易。遠在天涯姑且不論,近在咫尺也難有歸期,一個“忙”字常成托詞,其實,哪里就忙得連回家看父母的工夫都沒有了呢?即便如我,家離不遠,只要愿意,用不了一小時,就可與它親近。可是半年多來,我只回去過兩次,用于陪伴父母的,用于跟父母說話嘮嗑的,加起來不到一天的時間。
再近的家要是不回,也無異于遠在天涯啊!
夢中父親已在呼喚:歸去!歸去!
然而,還沒來得及安排歸程,翌日下午,家里突然打來的一個電話,卻讓我立即就往家趕,而且是叫了120急救車,在傍晚天色將暗、天氣悶熱得將要下起雷雨的時刻,回去了。
父親病了,躺在床上,發寒發熱,上吐下瀉,連一點站的力氣都沒有。中午還在地里薅了黃豆草的,吃午飯時人還好好的,下午突然就犯病了——電話里大嫂說得急迫,說得讓人驚駭。這大熱的天,莫不是中了暑,或者食物中了毒?要知道,父親已是八十歲高齡,可不能出什么意外啊!
急急忙忙,將老父接到城里,住進醫院,請來醫生會診、治療。等一切都安頓下來,得知沒什么危險后,我才細細詢問父親生病的緣由。而這一問,讓我猛然醒悟,因為不常回家,我對老人的生活了解得實在太少。他們每天在干什么?心里在想什么?每天吃的是什么?他們有了一點頭疼腦熱、身體不適是不是能撐就硬撐著?是不是一切還都想自己扛著,不愿給子女增添麻煩?……這些,我竟都不知道,竟都忽略了!
父親在醫院住了幾天,這讓我有了一次照料、陪伴父親的機會。母親在家不放心,要來醫院,我將母親也接過來。母親生過大病,身體一直很瘦弱,但她來了就不肯閑著,還叫我晚上回家,有她在這里就行了。我不讓母親操心,只要她陪著父親就行。晚上,病房里靜下來,我就跟父母說話。我說地已經流轉給種植大戶了,哪里還有黃豆田呢?父親說是河邊的一點廢地,荒在那里可惜,就種了點黃豆,長得不錯,估計能打幾十斤黃豆呢!父親說完笑了,笑得還有一點得意。母親說,我叫他不要弄,他一定要弄,那天中午,死熱的天氣,他一定要去薅草,回來吃飯時就喊頭有點暈,不過不弄點活計做做,你叫他在家閑著,難過呢!母親還說,已經發熱發寒瀉肚子了,他還跳到河里去洗了一個澡。父親說,不到河里去洗怎么辦?身上都臟了……我本想說說他們,但又不知如何開口。
我能責備他們嗎?我能說為了幾十斤黃豆弄出病不值得嗎?一輩子跟土地、莊稼打交道,勤勞、儉樸慣了的人,你怎么能夠讓他割斷跟泥土的那份情?你怎么能夠改變他那已經深入骨髓的秉性?只是父親“跳到河里洗澡”這件事讓我心驚,我在夢中分明見到父親也跳下了河,難道這是父子之間的一種心靈感應?
看著老邁、瘦弱的父親、母親,看著他們臉上流露出的不甘和無奈,看著他們那既不想給兒女增添麻煩又不得不依賴兒女的神情,我的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我想,每個父母都希望子女能“遠走高飛”,能走到更遠更廣的天地,可作為子女,在父母年老之后,最大的孝順、最好的感恩是什么呢?無疑是能多多回到父母身邊,多多陪伴自己的父母!
晚上,躺在醫院病房里,聽著父母輕微的鼾聲,我漸漸入睡。我又做了一個夢,我真的變成了一條魚,擺著尾巴,向一個叫作老家的方向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