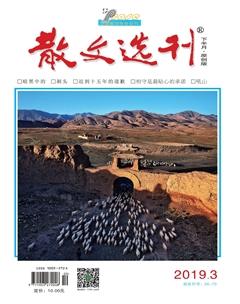黑土地的魂靈
王建生

八月,應(yīng)“從延安到北安”文學(xué)采風(fēng)活動(dòng)之邀,我第一次來(lái)到了比哈爾濱更北方的北安,踏上了名副其實(shí)的黑土地。
從哈爾濱去北安,車程約四個(gè)小時(shí)。車窗外,浩浩長(zhǎng)空,藍(lán)天白云,一眼望不到邊的大地,波瀾起伏,時(shí)而率性而上,堆起一道山梁,脊背上的那排大樹(shù),拽著頭頂?shù)陌自撇环牛袷遣ǚ迳系囊皇鴽](méi)有散開(kāi)的浪花。時(shí)而又平緩而下,現(xiàn)出一片草甸,草甸敞開(kāi)熱氣騰騰的胸懷,任憑那溪河九曲十八彎地流淌。這是一片濕地,成群的不知名的鶴鸛之鳥(niǎo)自由地在草尖上飛翔,發(fā)出嘰嘰喳喳的嬉笑聲。客車在這一碧萬(wàn)頃的海面上劈波斬浪,犁一條水花四濺的航線。兩旁撲面而來(lái)的高稈玉米,低禾大豆,來(lái)不及招呼一聲,便擦肩而過(guò)。
當(dāng)?shù)匦麄鞑康呐笥褵崆榈亟榻B說(shuō),黑土地是大自然給予人類的得天獨(dú)厚的寶藏,是一種性狀好、肥力高,非常適合植物生產(chǎn)的土壤,因而珍稀可貴。全世界僅有四塊,除中國(guó)的東北平原之外,另外三塊分別位于烏克蘭平原、美國(guó)的密西西比平原和南美洲的潘帕斯大草原。資料顯示,彎月?tīng)畹暮谕恋兀瑱M跨黑龍江、吉林兩省,面積達(dá)千萬(wàn)公頃。糧食產(chǎn)量占兩省的60%以上,已成為中國(guó)最大的商品糧產(chǎn)地……他還熱情地回答了大家的提問(wèn):“玉米、土豆的銷路不錯(cuò),每畝純收入800元以上;稻谷的產(chǎn)量高,大米品質(zhì)好,是市場(chǎng)上的搶手貨,每畝收入可達(dá)1200元左右。”
我的思緒,穿越在舊時(shí)光里。
我對(duì)黑土地的印象是從小學(xué)開(kāi)始的。那位年輕的男老師指著地圖上的“雞頭”講述北大荒,講得新鮮而神秘。印象中的北大荒土地是黑的,江水是白的,遍地松花,狼群出沒(méi),草長(zhǎng)鶯飛。后來(lái),在電影屏幕上看到知識(shí)青年上山下鄉(xiāng),一個(gè)個(gè)稚氣未脫的大孩子,胸配紅花,站在紅旗飄飄的敞篷車上,意氣風(fēng)發(fā)地開(kāi)進(jìn)了北大荒。看電影的我們心里頭有說(shuō)不出的感慨——驚訝?擔(dān)心?羨慕?高中畢業(yè)后,遠(yuǎn)在南方農(nóng)村的我,像獵奇少數(shù)民族的風(fēng)情一樣留意北大荒,像關(guān)心國(guó)家大事一樣關(guān)心那群知識(shí)青年。聽(tīng)說(shuō)有本《今夜有暴風(fēng)雪》的小說(shuō),就特地跑去十幾里外的縣新華書(shū)店,結(jié)果撲了空。有一天,在生產(chǎn)隊(duì)犁地,望著腳下一壟壟板結(jié)的黃土,我大汗淋漓,牛也喘著粗氣。停下手中的活計(jì),坐在田埂上,我忽然想起了北大荒,想起傳說(shuō)中那用油浸泡出來(lái)的黑土地, “一兩土二兩油”,抓一把黑土,用力一拽,指頭縫里都能冒出油水。那犁翻的土渣一定很松軟,犁溝溝里應(yīng)該有滲透出的青油。拉犁的牛一定不會(huì)如此費(fèi)勁,扶犁的人也會(huì)輕松得多……我莫名其妙地想去東北看一看,甚至冒出荒誕的念頭,去北大荒當(dāng)幾天農(nóng)民,犁幾犁流油的黑土地。
中學(xué)的歷史課,讓我們記住了“九一八”這個(gè)屈辱的日子,記住了為保衛(wèi)黑土地而戰(zhàn)斗的東北抗聯(lián),記住了楊靖宇、趙一曼、趙尚志、李兆麟等英雄的名字。然而,百聞不如一見(jiàn),在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紀(jì)念日的前幾天,我在哈爾濱參觀了“東北抗日聯(lián)軍烈士紀(jì)念館”和“東北抗聯(lián)博物館”, 進(jìn)一步了解了東北抗戰(zhàn)的歷史。在那里,我獲悉了一組驚人的數(shù)字:長(zhǎng)達(dá)14年的斗爭(zhēng),東北抗聯(lián)從鼎盛時(shí)的五萬(wàn)人戰(zhàn)斗到最后只剩一千人,卻鉗制住了東北戰(zhàn)場(chǎng)數(shù)十萬(wàn)日軍!而這次的北安之行,我們參觀了抗聯(lián)六軍“冰趟子戰(zhàn)斗”遺址,瞻仰了趙尚志烈士的雕像,聽(tīng)說(shuō)了抗聯(lián)女戰(zhàn)士為保全部隊(duì)而不惜舍棄親生骨肉的催人淚下的故事……心頭依舊隱隱作痛。但是,趕走侵略者的揚(yáng)眉吐氣和成功搶占東北的歡喜愉悅,很快讓悲憤成為過(guò)去時(shí),我們跟著中國(guó)革命的步伐大踏步向前!
2017年,北安市委書(shū)記黃士偉同志在中央黨校學(xué)習(xí)期間,寫(xiě)了一篇題為《從延安到北安》的文章,暢談了傳遞紅色基因的工作打算。文章一經(jīng)刊發(fā),引起了社會(huì)的廣泛關(guān)注。北安市與延安的寶塔區(qū)建立起友好聯(lián)系,延安的紅色血脈流淌在北安的城市、鄉(xiāng)村,流進(jìn)了黑土地的屯屯寨寨。
在北安,我還采訪了一位農(nóng)民。
他叫劉明啟,北安市楊家鄉(xiāng)新榮村大架子屯屯長(zhǎng)。今年34歲,中等身材,勻稱標(biāo)致,黑黝黝的面龐,眼睛大而有神,瘦精精的手臂透出使不完的干勁。
那天,我和明啟海闊天空地聊了一下午,崔久成也坐在旁邊。
劉明啟與崔久成結(jié)緣,起源于放牛。崔久成患有先天性智力缺陷,其母又去世得早,多年來(lái),他和父親一起生活。那時(shí)候,上初中的劉明啟經(jīng)常抽空幫家里放牛,他像大人一樣照顧也在放牛的崔久成,帶著久成玩,好吃的東西兩人分著吃,還處處護(hù)著他,不讓村里的孩子欺負(fù)他。久而久之,劉明啟成了崔久成的靠山,十分依戀。而崔增田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多次萌生把久成托付給明啟的念頭。可每次嘆口氣又放下了,“這么大個(gè)負(fù)擔(dān),人家能接受嗎?”在糾結(jié)中,他鼓起勇氣,來(lái)到劉明啟家,紅著老臉把話說(shuō)開(kāi)了,“托劉明啟照顧兒子”。劉明啟的母親一聽(tīng),蒙了,兒子才16歲,已經(jīng)有一個(gè)傻子哥哥,再添個(gè)殘疾人,誰(shuí)家的姑娘還愿意給他做媳婦?可站在旁邊的劉明啟不等娘說(shuō)話,就一口應(yīng)承。母親急了,問(wèn)他想好沒(méi)有,明啟說(shuō):“他們生活不容易,我愿意照顧他們爺兒倆。”從此之后,劉明啟隔三岔五地就往崔家跑,給他們送吃的用的,打掃衛(wèi)生,還幫助干農(nóng)活。
這樣的日子過(guò)了4年。
20歲那年春天,劉明啟結(jié)婚了。老天飄起了雪花,為一對(duì)新人送來(lái)了潔白的祝福。婚后第三天,小夫妻歡天喜地回娘家。然而,門前的一幕讓他們驚呆了,崔家父子不知跪了多長(zhǎng)時(shí)間……
“跪著干什么?”我也有點(diǎn)驚訝。
“求劉明啟收養(yǎng)我。”崔久成搶著回答。
原來(lái),經(jīng)歷這個(gè)冬天,已年過(guò)八旬的崔增田肺氣腫病情加重,他知道自己時(shí)日不多,一口氣上不來(lái)就可能沒(méi)命,必須盡快地安頓殘疾兒子的去處。于是出此下策,求小兩口開(kāi)恩。這天是正月二十一,屯子的人沒(méi)事根本就不出門,哪還有一清早給人下跪的?瞅著那可憐的爺兒倆,夫妻倆的心徹底地軟了……
我問(wèn):“你們當(dāng)時(shí)是怎么說(shuō)的?”
劉明啟用媳婦劉林莉的話說(shuō):“就多一雙筷子唄。”
從第二天開(kāi)始,小夫妻就著手整理院子里的兩間空房。接著,幫爺兒倆搬了進(jìn)來(lái)。
劉明啟說(shuō):“開(kāi)頭幾天,講情講理的崔老頭不上他家的廳堂里吃飯,說(shuō)是自己肺病不好,避免傳染。劉明啟夫婦輪換送飯,每送一餐,就勸說(shuō)一次,一家人就該生活在一起呀!”老崔總算順從了。
崔增田肺病經(jīng)常復(fù)發(fā),冬春時(shí)節(jié),臥病不起。劉明啟像親生兒子一樣,給老人洗臉、喂藥、擦身子。2011年1月,老人病危,在醫(yī)院二十多天,劉明啟日夜陪護(hù)在病床前,為老人送終。
近幾年,崔久成的“大骨頭”病愈來(lái)愈重,右手右腳行動(dòng)不便,劉明啟帶他先后去了北安市人民醫(yī)院、哈爾濱骨科醫(yī)院做治療,來(lái)回一趟路費(fèi)、檢查費(fèi)加藥費(fèi)合起來(lái)一萬(wàn)多。
我問(wèn):“花這么多錢,你是怎么想的?”
明啟說(shuō):“自家人生病哪有不花錢治的道理。”“在一起生活十幾年了,看著他生病受罪,我心里頭也不好過(guò)。”
以幫助別人為樂(lè)趣的人,一定是個(gè)有愛(ài)心的人;有愛(ài)心的人就有事業(yè)心、責(zé)任心。劉明啟這個(gè)北安漢子,完整地繼承著黑土地的肥沃與情懷,以一個(gè)農(nóng)民的身份默默地為社會(huì)作貢獻(xiàn)。
他的家庭成員有高齡的奶奶、多病的母親、崔家的父子、智障的哥哥,還有兩個(gè)孩子,九口人的大家,生活的重?fù)?dān)全在他的肩頭。
可他樂(lè)觀豁達(dá),眉宇間沒(méi)有一點(diǎn)晦氣。他說(shuō),他去北京打工,一個(gè)月收入也有一萬(wàn)多,但是,心頭不舒暢,總感覺(jué)不是自己的家。他的魂在黑土地,他自信,種地一樣能養(yǎng)活一大家人。因此,村里給他的殘疾哥哥低保待遇,也被他婉言謝絕。
談到收入來(lái)源,劉明啟說(shuō):“一種地,二養(yǎng)車。”
在我刨根到底的追問(wèn)下,他報(bào)了近幾年的賬:2012年,黃豆爬窩(干旱,不結(jié)角),五十多坰地,賣了不足一車糧,才收回4萬(wàn)多元錢,虧了17萬(wàn)多。第二年是個(gè)豐收年,黃豆產(chǎn)量高,價(jià)格也好,掙回了上年的虧損。中途的兩年,地種得少,收成一般。去年,耕種面積擴(kuò)大到160坰,養(yǎng)著3臺(tái)“大馬力”(拖拉機(jī)),1臺(tái)收割機(jī)。農(nóng)忙季節(jié),他一邊搶時(shí)間種自己的地,一邊還開(kāi)著大型機(jī)械為別人代耕掙錢,全年毛收入達(dá)37萬(wàn)元。
劉明啟是一個(gè)拼命干活的農(nóng)場(chǎng)主,曾經(jīng)六天不停車。他說(shuō),2011年,耕種東崗的那一片地,活趕得急,他一臺(tái)“大馬力”在前頭耕,后面兩臺(tái)播種機(jī)跟著播。六天六宿干完140坰地,平均一天一宿賺錢一萬(wàn)多。“困了就在車上打個(gè)盹兒,餓了就隨便吃點(diǎn)媳婦送來(lái)的東西,累了就想想自己的一家老小,為了他們,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2015年11月,劉明啟被推選成了屯長(zhǎng)。大架子屯四百幾十號(hào)人,在家常住的只有69人,他是最年輕的勞動(dòng)力。盡管肩頭擔(dān)子有點(diǎn)重,但是,作為一屯之長(zhǎng),他必須得頂上來(lái)。
問(wèn)到今后的打算,劉明啟朝我微微一笑,說(shuō):“把自個(gè)的良心放正,種好黑土地,養(yǎng)好自己的家,養(yǎng)好這個(gè)屯。”
看到他癡心不改的樣子,我想到了他的那句話——“我的魂在黑土地”。我以為,他才是新時(shí)期黑土地上的魂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