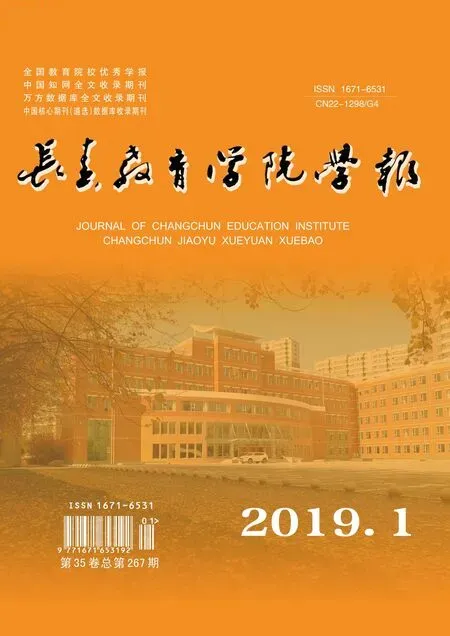儒家生命觀與青少年生命教育
姜旭晨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我國的青少年生命教育尚不完善。調查顯示,有近3000萬青少年處于心理亞健康狀態,甚至有大量青少年曾經有過自殺傾向;同時,青少年犯罪不斷加劇,20歲以下犯罪已達到犯罪總數的1/3,其中暴力犯罪和傷害犯罪的比例也不斷增加。[1]青少年群體表現出對生命價值的冷漠和缺乏尊重令人擔憂,其中教育的失位自然是重要因素之一。
在我國,教育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獲得生存技能的手段,應試教育、灌輸教育盛行,片面追求科學性和功利性,忽視對學生健全人格的培養,缺乏人文精神和社會責任教育;在教育過程中教育對象被物化,學生缺乏主體意識;而道德教育更是長期被意識形態和形而上的說教空洞化,學生的自我意識被泯滅在集體的海洋中。功利性和工具性的“何以為生”式的被異化的教育,亟待向“為何而生”式的人文性和價值性的教育轉化。
人類因其獨有的生命自我意識而成為區別于其他自然生命的特殊存在,生命于人僅有一次,如何認識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如何實現對生命本我的超越和生命價值的升華,自然是教育目標的題中之義——生命天然具有教育之原點的屬性,而教育也自然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之一。對此意大利教育家蒙臺梭利有精辟的敘述:“教育的目的在于幫助生命力的正常發展,教育就是助長生命力發展的一切作為。”
西方教育界早已認識到生命教育的重要性,1915年施韋澤在歐洲創立的以“敬畏生命”為核心的生命倫理學成為生命教育的思想開端,20世紀初期,美國率先提出對學生進行生命教育,之后生命教育在歐洲,日本,新加坡,我國港臺地區逐步發展,并取得相當的成效。生命教育昭示著教育思維范式從“對立競爭”到“和諧共生”的根本性轉變,這恰好契合了教育人文性和價值性的內在需求。生命教育強調了生命的整體性,認為在任何一種活動中,人都是以一個完整的生命體方式參與其中。雅斯貝爾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生命是完整的……作為生命的自我存在也向往著成為完整的,只有通過對生命來說合適的內在聯系,生命才能是完整的。”[2]生命觀的核心問題是對生命問題的反思。它主要包括對生命價值和生命意義的反思,而這種反思的終極價值,終將歸結與提升生命的意義:通過對生命問題的反思,激發生命的熱情,提高生命的品質,從而最終達到對生命價值的實現和超越。
儒家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寶貴財富,蘊含著豐富且充滿智慧的思想,而儒家哲學對生命問題進行了豐富的探索與思考,并最終形成了系統的生命觀體系。儒家教育思想具有天然的人文性和價值性,同時包涵了豐富的和諧生命觀,這恰好契合了我國教育的現狀,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將儒家思想引入教育觀念中,能很好地彌補我國教育人文性缺失、生命教育的不足,從而促進青少年道德和生命教育的完善。
二、儒家生命觀的內涵及其教育價值
近代以來,工具主義、科學主義思潮雖然促進了現代文明的迅速形成和發展,但也出現了對生命本質的冷漠與忽視等惡果,而儒家教育觀念講求對人的存在和人的價值的終級關懷,具有強烈的人文主義和價值主義精神,儒家生命觀所蘊含的敬畏生命、對人情感的終極關懷等特質,使其對現代生命觀教育有著極大的啟發與推動。儒家生命觀的內涵極為豐富,是一個由內而外的多層次和諧并存的體系。筆者認為對儒家的生命觀體系,可從三個遞進的層次進行分析,即生命的本體論、價值論和實踐論。
(一)儒家的生命本體論
儒家認為,生和死都是自然的產物,是世界運行之道的自然結果,既不可選擇,也不可避免,即所謂的“命定”“命數”,荀子說:“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禮論》)可見,儒家對生命的有限性是有清楚認識的。《論語·顏淵》中“死生有命”的觀點代表了儒家對待生死問題的典型態度。儒家清醒地認識到了生命本質上的客觀性,即生死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而無法通過宗教等手段進行自我麻痹,而必須以剛健自強的態度面對。
面對人生的有限,儒家并沒有像其他古代道德體系一樣,最終求助于靈魂不滅的彼岸極樂世界,而是選擇了一種尊重、關注人的現實生活的“入世”的價值取向。孔子對鬼神采取一種“存而不論”的態度,優先考慮現實世界的人類生存命題,而“不語怪、力、亂、神”。(《述而》)子路問什么是死、如何事鬼神,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應當“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雍也》)而荀子明確指出“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禮論》)儒家拒絕將對人的終極關懷寄希望于虛幻的彼岸世界,而要求從不可把握的鬼神世界回到人的現實世界中來,積極面對現實生活,從而力爭在有限的現世生活中創造出超越性價值來。
在仁與孝的道德基礎上,儒家體現出了現實層面上的對生命價值敬畏與尊重,例如衛靈公曾問戰于孔子,而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充分體現了儒家對戰爭之于生命的蔑視和損害的厭惡之情。而墨子在看到貴族生活奢華但貧民的生命受到損害時憤怒地說道:“皰有肥肉,廝有肥馬,而民有饑色,野有餓殍。”《論語堯曰》中更說道:“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認為要成為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必須認識到生命價值的寶貴。
(二)儒家的生命價值論
儒家認為生命來源于天。道者天道,也就是天命。天道、天命以及“知天命”是儒家生命觀中重要的范疇,《易大傳》中說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以生為其大德,這說明天不僅具有生命意義,而且具有價值意義。天就是自然界“生生不息”的過程。在這里,生命創造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充分表現了儒家對生命這一天道運行的體現的敬畏之情。
如果說天命的生生不息體現的是尊重生命的“仁”道的形而上的依據,那么人間的父子之愛、兄弟之情則是尊重生命的“孝”道的現實基礎。孟子說“親親,仁也”。(《告子下》)所以為仁要從最基本的親親原則——孝道開始。孔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孝”體現的是儒家對生命的現實存在之延續的尊重,《孝經鄉黨》中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明確地從生命延續必要性的角度申明了對生命價值的尊重。
面對人的生命的有限與脆弱,儒家以積極樂觀的“入世”態度,尋求生命價值實現最大化的途徑。在儒家看來,人的根本屬性在于其道德性,生命的最高價值在于實現仁的道德原則。孟子就把“仁”作為生命價值觀的基本規范和最高準則,孟子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離婁上》)而“仁”作為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不僅成為世俗生活的道德準則,也成為偉大人格的終極追求。
(三)儒家的生命實踐論
儒家哲學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孔子以六藝設教,“立人而弘道”。《大學》開宗明義闡明宗旨:“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這里所指的“大學”,是相對于“小學”(文字訓詁之學)而言,特指以成人成己、治國平天下為目標的實踐性學問;“止于至善”,即將推進社會的完善視為個人道德責任。這套獨特的以實踐價值作為道德修養原則的倫理方法充分證明了儒家傳統教育本質上是人文主義教育,它注重人格培養,以育人為教育的根本目的,強調通過人的社會實踐與歷史使命最終實現生命的最大價值。
儒家也充分認識到客觀條件對人能動性的限制,認為每個人在不同的層次中,可以通過不同的追求實現其人生價值,《孟子·盡心上》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左傳》中則對生命價值的實現提出了三個遞進層次的要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說道:“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具體說,“立德”,就是身以載道,積極履行社會道德規范,達成道德倫理上的生命價值。而“立功”,就是在國家和社會群體的現實事務中做出實際貢獻,形成實質上的生命價值。“立言”,則是通過主體性的探究與思索,將拓展人生境界、發展生命價值的途徑上升到思想的層次,不僅為自己,也為社會整體生命價值的最大化提供路徑。[3]
另外,儒家教育思想還講求實踐中的“中和之道”,要求教育不偏執不功利,達成身與心、知與行的和諧統一,《韓詩外傳》卷五就說道:“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從這個角度上看,生命教育不僅僅是要求從整體性上去理解學生,更重要的是實現對傳統教育思維方式的根本轉換:由少數人成功的競爭式的精英教育思維,發展到倡導和諧共生的生命教育思維。[4]
總的來說,儒家追求以理性現實的“入世”態度,在客觀條件允許的范圍內,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既積極參與社會生活,又踐履倫理道德的終極規范,以實現人的生命價值的最大化。
三、以儒家生命觀指導青少年生命教育
在國內和國際學術界受到普遍認同的一個觀點是:人的生命有人與自身、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三個向度。這三個向度不是平面和靜態的形而上觀念,而是一個互為依托、依次遞進的動態系統,并最終形成一個整體化、系統化的生命價值體系。生命教育應以對象自身為出發原點,逐漸向外拓展到他人、社會、環境,直到對人類整體生命的終極關懷,并最終建立世界倫理的觀念。
而儒家哲學對生命的反思落實于整個儒家哲學,恰好是在身心關系,群己關系,天人關系三個層面展開的,正呼應了當代生命教育三個向度的要求。筆者認為,將儒家生命哲學引入當代青少年生命教育的進程,亦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進行。
(一)修身養性的個體生命教育
儒家生命哲學重視個人身心和諧發展,追求精神價值與物質價值的統一,認為對道德準則的踐履既是人之生命價值的根據,也是生命價值的實現。因此要求在自我修養上注重主觀努力,將外在道德規范內化為自覺的內在需要,以此實現人生價值。
儒家的修身特別強調“自省”。《論語·學而》中有:“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認為自省是對自己學習過程的精神性反思,倘若只學習無反思,則必然使得學習成為無意義的機械化行為,以至于“學而不思則罔”。因此在青少年教育中,除了被動的道德學習外,必須引導其進行超脫于學習的主動性道德思考,這樣既可以培養青少年獨立思維的能力,又能避免單方灌輸式的說教所引起的青少年逆反心理,使其充分體會生命價值觀學習的意義,最終發現生命價值之所在,從而變對生命道德規則的消極遵從為積極履行。
儒家認為,“自省”實現生命價值是精神準備,“克已”是其現實條件,而其最終手段是“力行”。“自省”產生的內心的“仁”,通過“克已”和“力行”的外化,便具象為“忠恕之道”。《論語·雍也》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也就是孔子說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生命教育不僅應引導青少年認識自身生命價值,且應通過“推己及人”的過程,達到對其他個體生命的寬容與尊重。
(二)安身立命的社會生命教育
儒家的人學本質決定了其道德思考不是脫離現實世界的純抽象思辨,而仍將歸結于現實中的人與社會。儒家對人之生命的有限性有著清醒的認識,但并未因此放棄對現世人生價值的追求而寄希望于虛無的彼岸,相反,孔子對生命的價值性和局限性的沖突給出了明確的答案:“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先進》)而《論語·泰伯》篇講:“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可見,這里的“道”便是指對于現實社會的道德責任。要成為“君子”,不僅應注重內心層面上的“修身”,更應主動擔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責任,最終通過“立德、立言、立功”達到“三不朽”的境界,從而以無限的生命價值完成對有限的生命的超越。
青少年時期是人生價值觀選擇的關鍵期,因此,在對青少年的價值教育中,應引導其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虛無主義人生觀,形成“安身立命”的主動意識,以追求真理、回報社會為“正道”,認識到人生的價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獻,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樹立感恩意識和責任意識,從而形成正確的人生價值觀。
(三)天人合一的自然生命教育
自然生命的內涵是生命存在的自然狀態。自然生命教育的核心要義是培養人的生命意識和生命情感,而其路徑則是教育人珍愛生命、尊重生命和享受生命。《孟子·盡心上》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就是從天人感應中體認到基本的人性與人道觀念,再通過對“仁”的實踐重新回歸到日常人際社會關系中。可以說,儒家將基于血族關系的人倫之愛,推及到倫常序列之外的人性之愛,再推及到對自然宇宙一切事物的人道之愛。對于這種由“天人合一”推演出來的樸素認識,杜維明評論道,“這種思想,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大自然和人的那種親子關系”。[5]
儒家的“和生”觀念認為:“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在當代生命教育中,應使教育對象建立生命平等觀,充分認識到人是自然的構成部分,人與自然是共生共存的,人應當根據客觀規律能動地認識和改造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應當培養青少年對自然的敬畏和尊重,養成良好的生態意識和環境習慣;使其通過對自然生命的尊重,進一步習得對一切生命價值的普遍尊重,達到珍視一切生命,內心與自然緊密聯系、和諧相處的“樂生”境界。
個體生命教育,社會生命教育,自然生命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三個層面,這三者是互相影響、依次遞進的整體關系,在青少年生命教育的實踐中,應當將儒家生命倫理觀融入教學實際中,同時緊密聯系現代社會現實,完整地實現個體、社會、自然三個層次的生命教育目標,使青少年得以構建完整、健康的生命價值觀念體系。[6]
——由刖者三逃季羔論儒家的仁與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