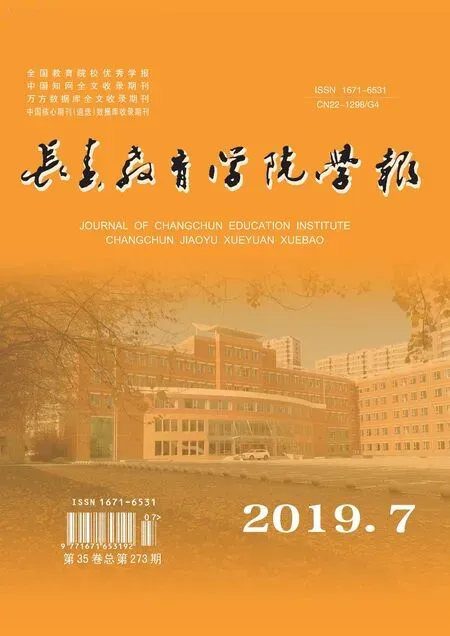中西文論之空白范疇比較探析
周琳莎
空白理論是中西方文論的重要范疇,有著相似的文學意義。盡管空白是文學藝術的普遍現象,但是該詞在中國文論中較少被提及,與空白相匹及的中國提法是“韻味”,其出現總是與意境的刻畫相互伴隨著。因此,中國韻味即為西方的空白。而盡管西方的空白到了近代才被提出,但是中西方都主張空白與實體、不確定性與確定性相結合。同時,在意義和作用方面都是比較相似的,都強調讀者的參與性作用,但是由于其立足的土壤與文論傳統有著巨大的差異,勢必造成中西文論的“空白”在根源、使用范圍有所不同。從范疇上看,中國的“空白”屬于哲學中對“無”的延展,而西方的空白起源于現象學中對“being”的探尋;從使用范圍看,中國的空白可運用于各個領域,而西方的空白理論則主要運用于小說。因此,空白在中西文論中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對中西空白范疇的比較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作品。
一、中西文論空白起源
在中國古代文論中,空白屬于意境的載體,體現作者的情感。文字的有限性導致意境空間大于藝術實境。所以“言外之意,韻外之至”屬于意境范疇,是可以提煉的空白。而這里的空白之所以稱之為空白,是因為它與作品所塑造的“實境”相對,因此,空白突破文字實體,表現出無限的空間與意境。所以,中國的空白是一個模糊又無限的概念,它指向是古代哲學的空間內涵,其本質是宇宙的終極本體——空無。
首先,空白源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是與世界本源有關的無。該宇宙觀建立在中國傳統哲學的基礎上,是儒道所推崇的陰虛、空無的產物。因此,中國文論中的“空白”范疇其實是哲學中“無”在文學藝術領域的體現。《易經》讀本曾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即所謂“形而上。”[1]指道是超越一切事物與現象的抽象觀念,是一種無形的法則與觀念。古代哲學家認為虛無其實是萬物的本原,物質世界是虛無哲學觀的具體產物。在此,“無”的概念也引發文學創作的空白觀念產生,是把對宇宙觀的認識遷徙到藝術創作上來。這說明空白與空無有著相通之處,是藝術創造的本源,一個模糊的無限性概念,展現出一種意境。因此,空白的本質上從屬于哲學空無的范疇。
其次,空白的空無與語言的言說及意義生成有關。空無范疇表明了先人早已經意識到了“無”的存在,從而開啟了中國對空白發展的哲學范疇。尤其以諸子百家為代表,孔子在《論語·陽貨》中曾說:“予欲無言。”[2]認為教育家本應行不言之教。而后孟子提出“充實之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神,圣而不可知之謂神”。[3]因此,孟子認為“美”是充實,“大”應是“充實而有光輝”的實境,只有達到大而化之的神的虛境才是高超的境界。因此,儒家講求實大于虛。但是道家是典型的注重虛大于實的流派。老子在“自然無為”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有無相生”的觀點,“有”與“無”是相互生成的辯證關系,這是與空白的空無有著密切關系的觀點。莊子繼承老子的思想,在《莊子·秋水》中說:“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志者,物之精也。”[4]這里莊子認為語言、意會難以掌握“道”,“道”蘊藏于萬事中。只有把它作為審美對象時,才可以神會其意蘊。這是道家強調“無言無意”的審美境界,強調從“言意之表”到“無言無意”的空白世界之中。
因此,空白的產生與傳統中國語言的意義生成密切相關。文學家善于借用有限的文字營造“不語之事,言外之韻”的情感與“象外之象”的境界,從而凸顯出無限的虛無宇宙本體論所重視的“道”“氣”。
相對于中國空無的哲學范疇,西方哲學家則側重于對being(有)的關注,這也體現在形而上學的研究中。柏拉圖的理念、泰勒斯的水、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赫拉克利特的火等,都是西方哲學家認識世界的一種自我嘗試。西方尋找萬物之有,通過對實體“有”的進一步認識,從而提出“有我”與“我有”的世界。因此,上帝說有光,然后有了光。相對于對being的確定,西方哲學家對無作了否定。比如黑格爾曾說:“在道家以及中國佛教徒看來,絕對的原則,一切事物起源乃是無,可以說,他們否定了世界的存在。”[5]因此,西方在從“有”中尋找意義價值。這也是區別于中國古代將”空白“提升到至高之美的追求。所以,英伽登的”未定點“,伊瑟爾的”空白“理論等都是從”有“出發,尋找實體背后的存在。因此,西方空白理論與現象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現象學產生于西方哲學理性主義以及19世紀以來出現的非理性主義之間的反思。現象學代表人物胡塞爾試圖尋找全新路徑建構理性,其主張“本質直觀”,認為真理就是顯現出來的、被“看”到的東西,是直接給予的自明的東西,其他一切邏輯概念等事物都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并由此得到徹底理解的。因此要“回到事情本身去”直接去“看”。所以,胡塞爾認為要從視覺角度去觀察世界,從而有目的性、指向性地去認知世界的有限性,不確定性。繼承胡塞爾后,英伽登作為空白理念創立的先驅,根據其創作實踐的現象總結出創作規律。英伽登認為文學藝術作品是純粹的意向性對象,認為文本中存在“認識的中心”。它區別于實在的客體,有著充分的確定性方向,本身具有語言現象層、語義單位層、再現客體層及圖式化方面層。通過認識中心展開對文本時間和空間的透視,揭視出這四個層次。因此在英伽登的空白文論中,空白指的是不確定性的點,主要是在于藝術作品的圖片化構成中,各種已經構成的圖片化間的空隙——不確定點。讀者在閱讀中,不斷填充空白,最終徹底消除該空隙。伊瑟爾認為文本由多個圖式組成,必然存在空隙與多個視點。在閱讀過程中,讀者的視點存在于文本之中,讀者是文本透視的主要承擔者。讀者在閱讀文本中只能有限選取文本某一視角,而在讀者的視點之外,空白作為眾多圖式之間未連結的部分存在著。所以,空白是存在于文本與讀者間的相互作用的一種基本成分。只要讀者把文本的視野與內容連接起來,空白便會消失。同時,羅伯格里耶強調空白主要生成于創作主體的透視視角之外。作者眼中的世界是作品的意向性解構,視覺之外存在著大量的空白。這是一種省略、一種缺陷,帶有破碎性與開放性的特征。
總之,西方空白是從“有“出發,通過現象學知識構建空白理論。它是西方文藝作品的一種省略,被直接用于創作與研究。“無“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范疇,“being”是西方哲學的根基。這樣的不同基點導致了中西文論的空白理論的興起歷程是不一樣的。
二、中西空白使用范疇的差異
中國的空白起源于中國的哲學根基,有著深遠的文化底蘊,西方的空白則是近代理論家根據現象學及文學創作的實踐總結出來的,這勢必造成中西的空白使用范疇是不一樣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空白范疇,涉及文學的各個領域且被廣泛運用在實踐中,但是西方的空白范疇主要運用于小說創作中,其涉及領域比較狹隘。這樣的使用范圍區別源于中國古代文論是宇宙觀的哲學根基,因此中國的韻味說隸屬于哲學問題,有著較強的普適性。
而在西方文論中,空白主要是運用于小說的創作過程中,無論是英伽登或是伊瑟爾都主張文學文本的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小說中。在此,小說空白的產生來源于格式塔心理學,比如當健全人面對空白格式塔刺激物時,便會情不自禁生成迫于改變的心理過程。這正如魯道夫·阿恩海姆《視覺思維》中所說:“世界將自己的倒映給大腦,而這些倒映作為原始材料還要被細細審查,重新組織,這是那種被動接受能力的補充,使它能夠以一種積極獨立的創造性能力進行接受。”[6]同時,從文學創作方式上,小說主要是一種敘事藝術,其敘事技巧是“講故事的技巧”或者“講故事的藝術”。在小說中,被敘述的事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敘事技巧是作家與讀者審美需求的滿足。因此,作家往往創造給讀者自由想象的空白,從而使得讀者可以進行美的再創造,真正實現藝術。對于小說來說,空白藝術充分影響了作品的創造成功與否,也是文章意境產生的關鍵。這種藝術是作者創作的方式,也為讀者的想象奠定了基礎。比如巴爾扎克在《守財奴》中,刻畫的神甫把鍍金的十字架送到其唇邊時,處于彌留之際的葛朗臺直接快速把十字架抓在手中。這一簡單的抓的動作,取得震撼性的藝術效果。既斷送了這位老暴發戶的性命,充分體現了守財奴至死不改的貪婪,也給讀者對巴爾扎克的性格留下想象的空間。讀者可以根據空白的空隙進行自發性的想象,增加或者是刪減小說情節,也造成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互動作用。
總而言之,中西方的空白具備復雜的內在差異性,這種差異歸根到底是中西文化的差異。中國講究天人合一,注重對無的探索;西方講求以人為本,注重對being的尋求。這也導致了中國空白的運用范疇遠大于西方的空白理論。同時,空白的研究也表明它能刺激讀者感覺與想象力產生,從而衍生作品詩意的審美過程。總之,中西方的空白理論范疇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通過對中西“空白”的比較研究,有利于推動雙方文論的交流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