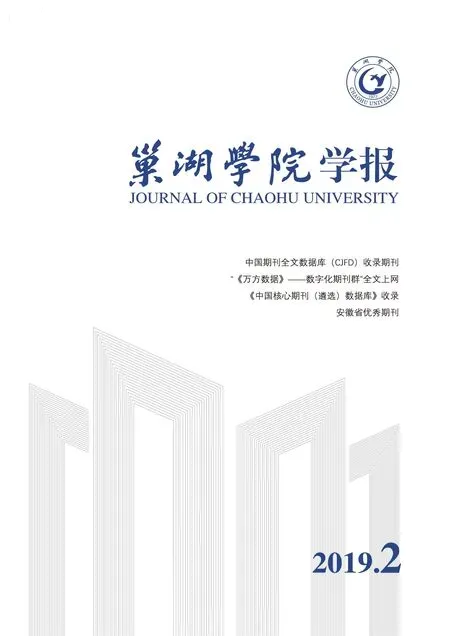“走出去”背景下翻譯理論與實踐研究的再認知
葉小寶 盧 安
(淮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引言
改革開放40年,經歷了兩輪翻譯高潮,第一輪高潮主要是為改革開放服務,翻譯以“引進來”為主;第二輪高潮主要是為“走出去”戰略服務,中譯外逐漸增多,翻譯市場逐步由以外譯中為主發展到以中譯外為主。2000年,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首次提出“走出去”戰略;2013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我國國際化步伐加快。近20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至民間,中國文學、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體制和機制建設日趨完善,渠道和層次呈現多樣化趨勢,明顯標志就是中譯外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
“當前,中國文化國際傳播面臨著一個很大的挑戰:即我們‘做得好,說不好!’或者‘會做不會說,說了人家也聽不懂!’要解決這個難題,翻譯責無旁貸。”[1]放眼世界,由于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深刻影響,翻譯“正身處一個革命性的巨變期”。在《數字化時代的翻譯》(Translation in the Digital Age)中,愛爾蘭著名翻譯研究學者克羅寧認為:“信息時代即是翻譯的時代,這就迫切需要人們要用新的方式來探討和思考翻譯,尤其需要全面考察數字化領域的劇變。”[2]
然而,當前,我們的“翻譯策略與方法、翻譯標準、翻譯觀念等涉及翻譯的根本性問題卻一再引發爭議和質疑,翻譯在中國文學對外譯介與中國文化對外傳播過程中究竟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怎樣的作用,文化界、文學界和翻譯界對此都存有某種程度的疑問及某些有待澄清的認識。”[3]因此,如何擺脫“走出去”背景下面臨的困境,如何迎接翻譯領域的諸多挑戰,如何面向世界言說中國,需要對我國翻譯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兩個方面進行再探討。
二、翻譯理論研究的再思考
翻譯理論研究必定是圍繞著探尋翻譯本質、解釋翻譯現象、揭示翻譯規律而展開。世紀之交,我國翻譯界進入理論反思期,學科的自我反思伴隨著學術焦慮的產生。許鈞2017年就指出,中國翻譯研究主要存在四種焦慮:“理論焦慮、技術焦慮、方法焦慮和價值焦慮。”[4]同年,穆雷作了進一步補充,認為還存在“特色焦慮、話語權焦慮、流派焦慮和創新焦慮”等四種焦慮[4]。“現存的焦慮表明目前我國翻譯學科內部存在不少難以調解的現實矛盾,當前的理論已難以解釋新的翻譯現象、解決新的翻譯問題。在翻譯職業化時代,焦慮的消解有賴于新的觀點、思想與理論的出現,因此立足于本土問題的理論建構也是解決新的翻譯問題、促進翻譯學現代化轉型的現實之需。”[4]
翻譯理論的發展軌跡還可以從其研究范式的嬗變中加以描述。在經歷了語文學研究范式、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范式和解構主義多元研究范式之后,翻譯研究陷入了當下的范式危機,亦即找不到“具有支配地位的翻譯學研究范式”[5]。無疑,在全球化、信息化、技術化、大數據的背景下,已有的翻譯學研究范式滿足不了當下需求,必然出現暫時性危機,這里不妨稱為暫時性失語。一時的失語未必都是壞事,它也可能預示著新的研究范式即將產生。因此,中國譯學研究既面臨著一時“失范”的挑戰,又面臨著重新“建范”的機遇。
(一)不斷追問翻譯本質
任何一個理論的探討必然逃不過對本質的追問和對概念的界定。對“翻譯是什么”的回答,決定了翻譯活動的立足點和最終歸宿。
學者對翻譯本質的論述不一而足:Wyle曾認為翻譯即“逐詞對譯”[6];Nida指出翻譯應該“功能對等”[7];Casagrande提出翻譯“不是在翻譯語言,而是在翻譯文化”[8];Dryden視翻譯為“戴著鐐銬跳舞”[9];Escarpit把翻譯看成“創造性背叛”[10]。 而對于“什么是對譯?”“什么叫對等?”“怎樣在字里行間譯出文化內涵?”“鐐銬是監獄的刑具還是舞臺的道具?”“如何理解技術性的背叛是為了更全面地忠實?”等等,學者作出的思考,都是對翻譯或翻譯過程的本質追問。在種種翻譯觀影響下,在從原文到譯文抵達過程中,譯者塞進了多少被法國翻譯理論家Meziriac所說的私貨[6],或如同周恩來總理所戲稱的翻譯“貪污”了多少[11],都是需要認真檢視的。
我們認為,文學翻譯首先主要是翻譯原作思想,非文學翻譯主要是翻譯原作信息;其次,才是兼顧文化表達和書寫風格。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最主要的是思想輸出,通過思想去影響他人才是文化輸出的最終目的。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曾說,他寧愿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亞。另一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也曾說過:“今天的中國出口的是電視機,而不是思想……,一個只能出口電視機而不是思想觀念的國家,成不了世界大國。”顯而易見,兩位首相所強調的,就是傳播學中的信息滲透或者是跨文化交際中的文化傳播。
在某個特定歷史階段,一旦概念被廣泛接受和采用,一切相關的探討就會以此為母題而展開。例如,自近代以來,嚴復提出的翻譯觀受到廣泛認同,“信、達、雅”便成了指導翻譯實踐的金科玉律。什么是忠實呢?是忠實原文語言結構、言語行為還是原作語用風格,抑或是兼而有之?事實上,不同語言語法規則不同,不同語言使用者的思維習慣亦不同,不同民族文化傳統更是大相徑庭。也就是說,如果竭力對原文和原作者忠實,那么要不要重視讀者感受?忠實原文和服務讀者之間的矛盾如何解決?根據語言結構特點和文化差異進行調適算不算忠實?誠如王克非所言,“不同的語言通過翻譯進行轉換溝通時,就是將一種語言文化帶入另一種語言文化,就會不同程度地發生融合、半融合或變容。”[12]這融合、半融合或變容的本領就是譯者的功夫,且如此術語又面臨著重新界定。
可見,翻譯是復雜的,而“翻譯既是語際轉換,也是文化間的轉換”的說法,是一個十分寬泛的界定。只有對翻譯本質不斷追問,才能拿出具有創新特點的譯品。如果把翻譯看作是“為文化交流服務、為社會和人類服務”,那忠實譯品的主體究竟是“文字轉換的操作者”還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則取決于譯者對翻譯本質的領悟。這一點,從《天演論》的翻譯者嚴復、《巴黎茶花女遺事》的翻譯者林紓、《紅樓夢》的翻譯者大衛·霍克斯和莫言作品的翻譯者葛浩文等人的翻譯觀可見一斑。
退而言之,如果不思辨、不追問,只是簡單地把翻譯當作追名逐利的活兒,那么季羨林所批評的“翻譯危機”則不可避免。當下,不去做本質追問,缺乏耐心,見誰譯誰的“行家”大有人在,這種現象不能不引起譯界警覺!
(二)樹立“譯者中心”的翻譯觀
譯者隱身的原因,有內因也有外因。外因方面,無論從社會評價、經濟效益、學術認定來說,譯者都尚未得到足夠重視。許鈞在《翻譯的危機和批評的缺席》一文中曾提到過這個問題[13]。從社會評價來說,一部翻譯圖書成功了,功勞全歸原作者和出版社;失敗了,罪過全歸譯者。從經濟效益來看,精雕細琢和粗糙濫譯的譯作價格相差無幾。更讓譯者傷心的是,多年來譯作在學術認定上都不算成果。內因主要在于譯者對于翻譯的認識不夠,有的認為只要懂點外語,有雙語詞典和在線翻譯工具,就可以操刀上陣。
譯者隱身,有的是無奈之舉,有的是心甘情愿。對于有精品意識的譯者來說,他們樂于顯身,渴望自己的譯品得到認可。而對于粗枝大葉的譯者來說,他們寧愿隱身,因為隱身就意味著在“作者已死”說辭遮掩下跟著感覺走,譯完之后就可以拿錢一走了之。Venuti就強烈譴責譯者隱形現象。司顯柱也認為“強加在譯者身上的隱形地位無疑是極不道德的,因為它全然漠視了譯者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作用。”[14]
就翻譯主體性而言,翻譯界依然存在模糊認識。如果連翻譯主體性都模棱兩可、爭論不休,則很難保證翻譯不會走樣。我們認為:作者是原文的第一責任人,譯者是譯文的第一責任人。只有確立了譯者的翻譯主體性,只有讓譯者顯身,才會激發譯者強烈的精品意識。
胡庚申2004年曾經提出“譯者中心”翻譯理念[15],但十年間受到種種質疑:如果譯者為中心,文本算什么?如果譯者為中心,譯者自主權過大,導致失控怎么辦?如果譯者為中心,翻譯批評是評判譯者、還是評判譯文?如果譯者為中心,是否意味著“譯者就是一切”?生態翻譯研究中,譯者是否還是中心?等等。事隔十年,胡庚申“被迫”再度發文,對譯者中心的定位、取向、界定等進行反思和再釋,進一步為“譯有所為”夯實理論依據[16]。葛浩文也極力反對譯者隱身,他提出“以‘忠實’為前提、以‘可讀、平易、有市場’為基本訴求、以目的語讀者為中心、凸顯自我的‘再創作’”翻譯觀[17]。好一個“凸顯自我的‘再創作’”,實質上與“譯者中心”翻譯觀并無二致。
在新時期跨文化交流和維護文化多樣性過程中,譯者更應自覺地從中國文化“走出去”國際戰略高度認識翻譯的歷史責任和崇高使命。“譯有所為”就是要求譯者理直氣壯地顯身,用自己的譯德、譯技,將原作最優化地呈現在另一種語言文化之中。譯者是神圣的“擺渡人”,如果不講譯德,不鉆研譯技,胡譯亂譯,安于隱身,是不配做這份天職的。
(三)堅守“為讀者而譯”的翻譯原則
“譯者為誰而譯”是譯作獲得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凡成功譯作,譯者心中必然裝著目的語讀者。葛浩文堅持“以目的語讀者為中心”的翻譯原則,堅持忠實前提下的“可讀、平易、有市場”的翻譯標準,這種翻譯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譯者宏觀層面上歸化、異化等策略的協調,微觀層面上字、詞、句、段、篇話語的運用。
當下譯介出版中,由于策劃、翻譯、校訂、宣傳、銷售等的任務分工、利益瓜分,使得各方面似乎都在為老板(發起方或出版方)服務,對讀者的責任感也萎縮了。美國華裔文化學者Ray Chow曾說:“中國的知識分子經常說老外理解不了中國,我認為這話本身已經有所喻指,說這話的中國學者只是圖省事地將老外搬出來,實際上不是老外理解不了,而是中國的(文化)他表達不了。”[18]在Chow看來,譯者將所謂的不可譯性草率地歸于讀者的理解力,是堂而皇之的責任推卸。其實,怎么翻譯中國文化,就是用目標語讀者聽得懂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才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關鍵所在。
如果一部洋洋灑灑數十萬字的翻譯作品,晦澀拗口得讓讀者難以卒讀,那么這樣的譯品還有什么價值可言。為讀者而譯,就是要深入了解讀者,知其所需、所好。當然,這并不是要犧牲原作、任意篡改原作來取悅讀者。葛浩文的成功翻譯經驗就是,譯者必須站在原作者和譯文潛在讀者之間進行跨文化協調,繼而進行“再創作”。譯作和原作講的是同一個故事,只不過呈現方式不同罷了。不了解目的語讀者,即使是英語國家的漢學家或者翻譯家,也難以勝任翻譯任務。
三、翻譯實踐研究的再探究
進入新世紀,在推進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新時代,翻譯正在發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個時代要求翻譯繼續服務改革開放,服務中國文化“走出去”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服務中國參與全球治理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服務中國國家形象的塑造和中國國際話語體系的建構。毋庸置疑,中國翻譯正迎來千載難逢大變革大發展的黃金時代,一方面翻譯肩負著時代賦予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翻譯也面臨著諸多挑戰。具體而言,涉及翻譯實踐研究的挑戰是:翻譯策略研究欠缺、回溯性翻譯批評的缺席缺位、未能充分認識翻譯產業化、社會化。
(一)多視角研究翻譯策略
國內外翻譯策略研究涉及兩個方面:文化層面和文本層面。文化層面是指從社會、文化、政治等角度研究翻譯策略,把策略細分為歸化、異化、改寫、抵抗、同化、文化移植等;文本層面是指從文本角度研究翻譯策略,把策略分為直譯、意譯、音譯、增譯、減譯、零翻譯、直譯加注、深度翻譯等。也有學者認為這兩個層面分別代表文化學派和語言學派的視角。方夢之認為任何翻譯策略都有三個要素:理論因子、目的指向和技術手段[19]。如果我們用三要素理論來審視當前國內翻譯策略研究,顯然,現有的研究仍然缺乏系統性、科學性和縝密性,對中國文化外譯的闡釋力和可操作性還不具有可復制性。
國內翻譯策略研究呈現兩大趨勢。第一,學者們熱衷西方翻譯策略,對本土翻譯策略沒有深入挖掘。劉宓慶等學者曾呼吁加強本土翻譯策略研究,希望盡快完善本土翻譯策略理論。盡管熊兵曾嘗試將翻譯策略與技巧、方法加以區分[20],但是國內學者多將三者等同視之。總體而言,由于西方翻譯策略理論的不斷引入,2000年后,我國傳統翻譯理論中涉及翻譯策略、技巧或方法的研究處于逐漸被淹沒的趨勢[21]。學者們熱衷于套用國外翻譯理論觀照我國的文化外譯工作,從而忽略了新時期對我國本土翻譯策略進行新的學理探索。第二,應用翻譯策略研究缺乏宏觀、基礎性的理論研究。近年我國應用翻譯策略研究在量上逐漸趕超文學翻譯策略研究[22-23],應用翻譯研究內容上涵蓋了商務、金融、法律、醫學、影視等多個領域,但多是淺談技巧,缺乏宏觀、基礎性的理論研究[24],或是套用西方翻譯理論,“停留在對譯文的評價上,是為了批評而尋找的一種理論根據,并未能提出一種結合實際、操作性比較強、比較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實用英語翻譯理論來”[25],或是研究內容重復、研究視角單一、用例老化陳舊等[26]。一定意義上講,應用翻譯策略研究較之文學翻譯策略研究意義更大,因為翻譯實踐“往往會因一字之差而離題萬里,出現差錯則后患無窮。 ”[27]
“走出去”戰略涉及眾多領域,用戶(讀者)需求多種多樣,翻譯策略研究僅僅依靠語言學知識是不夠的,筆者認為可以從文化層面研究翻譯策略,還可以將翻譯策略研究放在社會學中考量,也可以倚仗“信息技術”擴大翻譯策略研究范疇。
(二)強化回溯性翻譯批評的出席到位
早在上個世紀末,季羨林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國翻譯界面臨的危機,并責難學界的聽之任之,因而造成了“文恬武嬉,天下太平”的局面。本世紀初,商務印書館和譯林出版社兩大權威出版社相關人士相繼發表署名文章,猛烈批評翻譯亂象。商務印書館原編審陳應年認為,翻譯亂象出現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要錢不要質量”[28];譯林出版社原社長章祖德認為,翻譯界的諸多亂象“日益敗壞著翻譯作品本身的聲譽和翻譯界的名譽,助長拜金主義,降低社會的文化品位,成為翻譯圖書市場良性運行的嚴重掣肘,不啻為文學翻譯界乃至整個當代文化的悲哀。”[27]許鈞認為,翻譯危機的主要原因和批評缺席息息相關,雖然翻譯批評不乏理論上的探討,但是理論的探討并不能代替批評的實踐[13]。時至今日,翻譯批評仍未形成氣候。反而,在學界之外,網民們不時吐槽“被翻譯糟蹋的名著”,甚至還會鬧得沸沸揚揚。盡管我們不完全認同網民的觀點,但無論如何,翻譯批評界對翻譯亂象應該有足夠的反應。譯作一出來,翻譯界不敢批評,反倒是“外行”的網民們似乎長著火眼金睛,將譯作中引為笑談的胡譯亂譯之類的“神翻譯”曝光,這是譯界極不正常的現象。
把“蔣介石”(Chiang Kai-shek)翻譯成“常凱申”;把毛澤東詞作《念奴嬌·昆侖》由德文譯成漢語,作者竟成了“詩人昆侖”,諸如此類極其離譜荒謬的錯誤居然出現在學術專著中或者學術網站上,然而,翻譯界對此的反應似乎并不強烈。毫無疑問,這類錯誤不只是專業水平問題,更應該說是工作態度、甚至是職業道德問題,不僅給譯者、譯者單位帶來恥辱,更是給新一代知識分子帶來恥辱。究其原因,還是學界過于浮躁的心態所致。翻譯批評缺席或是批評得不痛不癢,所釋放出的信息使得有些人肆無忌憚地去搶譯、亂譯,直接后果就是外譯中給讀者提供錯誤信息,甚至誤導讀者;中譯外則拉低了中國文化品位,中國文化“走出去”就會落空,中國成為“文化強國”也會成為泡影。由此可見,開展多重回溯性翻譯批評,是“走出去”背景下提高翻譯質量不可或缺的重要法門。
(三)進一步推動翻譯產業化
當今語言服務業包括翻譯與本地化服務、語言技術工具開發、語言教學與培訓、多語信息咨詢等四大業務領域。事實上,“翻譯”走出高等院校和外事部門進入市場,成為語言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也是近年出現的新生事物。我國語言服務業其實是在籌辦舉辦“北京奧運會”期間成長發展起來的,其行業地位是在“2010年中國國際語言服務行業大會”上首次得到官方認可的[29]。如果說“北京奧運會”掀起的是第一波語言服務業的高潮,那么當前“一帶一路”的戰略推進則掀起了第二波高潮。根據中國翻譯協會的調研,2011年,我國翻譯市場上中譯外的工作量已經超過外譯中,達到54%;2014年,中譯外的工作量更是達到60%。隨著翻譯工作量的增加,據估計,我國現在每年的翻譯營業額超過300多億元,語言服務業營業額超過2000億,且每年還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而根據國家工商管理部門的統計,1980年,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語言服務公司只有18家,而到2015年底,這類公司已經達到7萬多家,專業隊伍人數大概有百萬之眾。
翻譯產業的勃興吸引了大量中間人。這里的中間人,是指除了原作者、譯者和讀者(客戶)之外的其他參與譯前、譯中和譯后的發起人、委托人、贊助人、出版商、編輯、審校等,他們雖然不直接參與作(譯)品的創作和使用,卻是活躍在翻譯行業的重要力量,在翻譯項目中對譯文質量要求擁有一定的話語權。與傳統翻譯活動相比,奧運會和“一帶一路”所涉及的翻譯明顯具有“項目化、大型化、翻譯流程復雜化和參與人員多樣化”等特征。因此,翻譯正日益成為一門跨學科的綜合技能。一份譯品以什么樣的方式呈現在讀者(客戶)手里,通常是譯者、作者和中間人多方合作協商的結果,顯然,這也是專業譯員和非專業譯員之間的協商與競爭。實際上,在這場翻譯革命的背景下,最典型的現象是眾包翻譯(crowdsourcing translation)。眾包不同于外包(outsourcing),因為外包的合作對象是經過認證具有資質的專業機構,而眾包的發包對象是網絡平臺上來自各行各業的業余翻譯愛好者。加拿大學者Dolmaya說:“由互聯網用戶志愿進行的線上翻譯行為,已日益成為翻譯研究領域的興趣話題。這些志愿者通常不是職業譯者,但他們相互協作,共同參與完成無任何實質性商業報酬的翻譯項目。”[30]翻譯產業的眾包現象,如同其他產品的眾包,大有崛起之勢,胡安江稱之為“翻譯產業的大眾狂歡場”[31]。這種現象有其積極的一面,卻在質量監管、保密性、剝削用戶勞動等方面飽受質疑、詬病。Baker[32]和英國其他學者曾經探討眾包翻譯的倫理性,而Oloha曾研究過眾包翻譯的社會學意義:“‘眾包’和‘自愿’是許多線上社區和社交網站的特征;與此同時,它也日益成為翻譯活動的特征。”[33]筆者認為,運用跨學科模式和實證研究方法,從社會學視角研究眾包翻譯,對于有效發揮翻譯在當下中國文化“走出去”中的作用,無疑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四、結語
翻譯始終是具有強烈使命感的活動。三百多年前,徐光啟就曾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季羨林更是一語中的,指出:“翻譯是中華文化常青的萬應良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背景下,今天的翻譯和以往的翻譯相比,無論在翻譯數量、翻譯質量、翻譯手段,還是在翻譯內容上都大不相同,“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對翻譯理論和實踐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需要對兩方面研究進行再認知,提高研究的針對性,增強研究的時代性,進一步強化中譯外理論和實踐研究,這樣才能完成時代賦予翻譯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