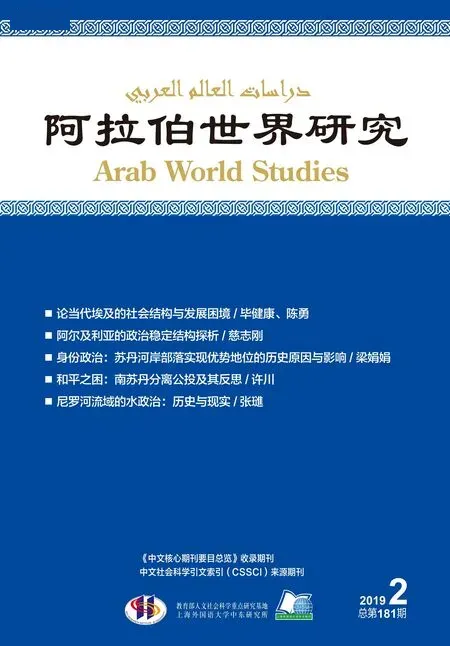阿爾及利亞的政治穩定結構探析?
慈志剛
自“阿拉伯之春”以來,西亞北非地區多個國家政權發生更迭,區域性動蕩重新成為困擾國際社會的難題。這次肇始于突尼斯的政治危機迅速外溢,在區域內產生了連鎖反應,而危機產生的后置效應對各國的政治穩定都具有負面的影響。與其他中東地區國家相比較,阿爾及利亞卻未被卷入這場危機的漩渦,除了小范圍騷亂外,政權仍然維持穩定。因此,有學者提出了“阿拉伯之春例外論”的觀點來討論阿爾及利亞在特殊國際環境下的穩定局面。[注]Boutheina Cheriet, “The Arab Spring Exception: Algeria’s Political Ambiguities and Citizenship Rights,”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2014, Vol. 19, No. 2, pp. 143-156.在中東地區整體處于動蕩狀態的大背景下,對政治穩定的思考是探索其他深層次問題的基礎,故研究阿爾及利亞的“例外”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對阿爾及利亞政治穩定進行結構性解析,對認識阿爾及利亞以及中東國家的政治發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一、 獨立后阿爾及利亞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比較政治學研究的重點轉向了新獨立國家的政治發展問題,西方政客與學者提出以“民主化”的所謂普世主義模式對第三世界的政治系統進行改造,其客觀結果是造成了發展中國家更深層次的政治危機。鑒于民主化模式的失敗,亨廷頓等學者提出政治穩定作為政治發展的核心主題,強調政治變遷的有序性。[注]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版,第23頁21世紀之交的比較政治學在強調政治穩定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政治民主化的內容,從而使政治發展的內涵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因此,當前比較政治學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秩序變遷方案時,更加關注政治穩定的重要意義。然而,在政治學概念中,政治穩定與政局穩定之間在現象層面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但卻存在質的差異。阿爾及利亞獨立后的政治發展歷程中,出現過以政變的方式對政治發展方向進行調整和以武裝斗爭的形式挑戰政府權威的事件。這些事件的出現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對政局的穩定造成了破壞,但從長時段觀察,卻沒有因此而喪失政治的穩定性。獨立后阿爾及利亞政治具有如下特征。
(一) 統治集團內部始終保持穩定
阿爾及利亞是通過民族解放戰爭的方式贏得民族獨立的。在獨立戰爭時期,民族解放陣線承擔著戰爭的領導和組織工作,為了防止出現獨裁專權的情況,民族解放陣線實行集體領導原則,重要決策必須經由集體協商才能通過。隨后迫于斗爭形勢的需要,民族解放陣線的領導權被互不統屬的政治集團所分割。在外交上,1958年成立的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是其在國際舞臺上的最高代表,臨時政府為阿爾及利亞獲得國際社會承認和爭取國際援助開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動。在軍事方面,民族解放軍總參謀部和國內各軍區各行其是。總部位于突尼斯邊境的總參謀部名義上是最高軍事領導機構,在戰時幾乎完全處于臨時政府控制之外,而阿爾及利亞國內的六個軍區最初歸總參謀部統轄,但隨著法軍加強對邊境的封鎖,各軍區領導人逐漸大權在握。因此,有學者認為,獨立戰爭最豐富的遺產就是國家的政治“封建化”[注]David and Marina Ottaway, Algeria: The Politics of a Socialist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 18.。在阿爾及利亞走向獨立后,臨時政府、總參謀部和各軍區領導人開始競爭國家領導權,并形成了特雷姆森集團和提濟烏祖集團[注]特雷姆森集團和提濟烏祖集團:阿爾及利亞獨立初期為爭奪政治權力,1962年7月本·貝拉及其支持者從摩洛哥進入阿爾及利亞西部地區,并將總部設在特雷姆森(Tlemcen)。與此同時,臨時政府總統本·赫達(Ben Khedda)及其支持者也返回阿爾及利亞,將總部設在柏柏爾人聚居區卡比利亞的首府提濟烏祖(Tizi Ouzou),從而形成了以特雷姆森和提濟烏祖為中心的兩大政治集團。兩大政治和軍事對立陣營。最終,本·貝拉在總參謀部的支持下進入阿爾及爾,特雷姆森集團獲得了這場斗爭的勝利。從本·貝拉總統開始,阿爾及利亞的核心統治集團就與軍方形成了特殊的關系,特別是自胡阿里·布邁丁開始,歷任總統都具有軍方背景,即形成了軍方掌握核心政治權力,再由技術專家進行治理的統治模式。軍隊干預政治是保證統治集團核心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當政權遭遇的挑戰觸及軍方底線時,軍隊便會予以強制糾正。
(二) 政治反對派無法對政權構成威脅
在現代政治語境中,政治反對派的存在是社會多元化的表現,這意味著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在社會分化中進行了重新整合,并以政黨等形式予以表達。但在獨立后的阿爾及利亞,政治反對派缺乏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這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社會發展的均質化。殖民主義是阿爾及利亞現代化的發動者,法國殖民者的“文明使命”破壞了傳統的農業社會,地主階層被殖民者取而代之,形成了歐洲移民與阿爾及利亞人對立的二元社會,到1946年,隨著貧困化加劇,農民逐漸成為半無產者。當殖民統治結束時,阿爾及利亞社會主要是由這些無產階級化的農民構成,民族解放陣線是他們的唯一合法代表。
第二,現代化進程緩慢。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了“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則滋生著動亂”的悖論,[注][美]塞繆爾·P. 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版,第31頁。在經濟領域發生的現代化會向社會和政治領域滲透,造成對生活習慣、社會傳統和宗教觀念等方面的沖擊,最終給政治帶來不確定性。阿爾及利亞的現代化在布邁丁時代是以通過“石油美元”向基礎工業注入資金,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為目標,現代化對社會領域的沖擊有限。到20世紀80年代,沙德利總統的經濟改革失敗,被迫開啟了政治改革的大門,到布特弗利卡總統統治時期,經濟發展仍然舉步維艱,改善民生仍為首要難題。因此,現代化帶來的經濟價值對政治價值的重塑在阿爾及利亞進展緩慢。
第三,社會傳統價值復蘇。在經濟價值無法對社會進行整合的背景下,社會傳統價值的作用便凸顯出來,成為政治動員的基礎。阿爾及利亞1989年憲法是該國走向多黨制的開端,憲法規定,任何政黨不得以宗教、語言和地區主義等排他性要素作為成立的基礎。但是實際上,后來對政權造成沖擊的伊斯蘭拯救陣線卻高舉宗教旗幟,而社會主義力量陣線和爭取文化和民主聯盟也以柏柏爾人聚居區為活動基礎,均并未遵守憲法中不得基于排他性成立政黨的規定。
(三) 地區動蕩中的穩定島
外交是國內政治的自然延伸,同時,外交也是確保國內政治穩定的重要手段。獨立后的阿爾及利亞推行第三世界外交,以維護民族獨立和推動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斗爭為目標[注]慈志剛:《淺析阿爾及利亞的第三世界外交》,載《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78頁。,因此,阿爾及利亞也成為全世界革命者心中的革命圣地。在20世紀90年代,阿爾及利亞陷入內戰,軍方接管政治導致政權合法性在國際社會遭到質疑,同時,政府內部存在多元權力中心,造成阿爾及利亞外交官對本國政策的認識和執行也充滿不確定性,[注]Yahia H. Zoubir, “The Resurgence of Alger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9, No. 2, 2004.因此,這一時期阿爾及利亞外交處于收縮和防御態勢,內政和外交無法形成有機的互補。布特弗利卡當選為總統后,阿爾及利亞外交政策開始發生改變,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幾點:第一,阿爾及利亞需要改善政府形象,結束內戰時期外交上的“孤立”局面,獲取更多外國援助;第二,布特弗利卡曾多年擔任外交部長職務,能夠審時度勢地做出改變;第三,部分反政府武裝轉變為恐怖組織,并呈現國際化的趨向。新世紀阿爾及利亞將外交的重點放在地區安全和穩定上,將國內反恐與地區安全統一起來,借助“9.11事件”將本國安全與西方反恐戰略對接,再依靠其強大的軍事存在和豐富的反恐經驗,使其成為地區動蕩中的穩定島,因此,2010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對阿爾及利亞的沖擊遠不如其他阿拉伯國家嚴重。
二、 阿爾及利亞實現政治穩定的核心維度
獨立后的阿爾及利亞完成了從殖民地向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這種轉型期的政治發展本身就充滿了不確定性,因此,獨立后在政權問題上爆發的各種矛盾,由此引發的各種政治事件產生了不同的政治影響,對政治穩定造成了沖擊,但卻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政治穩定的基本支柱。也就是說,政治穩定不是一個孤立的政治現象,它的產生與維系與特定的政治體系相關,政治體系的關鍵要素在政治的動態發展過程中沒發生根本性變化,則政治穩定就具備相應的保障機制。
(一) 政治合法性維度——政治體系的權威性
從獨立后阿爾及利亞政治合法性構建的歷史來看,其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的轉向,通過具有超強魅力的領袖人物為政治穩定提供秩序和規范。
第一階段是本·貝拉時期的“歷史合法性”。所謂“歷史合法性”是指政府的權威來源于革命斗爭的歷史:一方面,本·貝拉通過強調“革命歷史”,樹立領導人的個人權威。作為“特別行動”組織的早期成員,本·貝拉是民族解放斗爭的主要發起人,在民族解放陣線內部享有較高聲譽,在革命中始終保持一塵不染的革命形象,作為僅存的幾位早期領導人之一,特殊的革命歷史賦予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通過官方的革命歷史敘事,賦予其政策以合法性。本·貝拉強調其政策的歷史根源,其自管社會主義的獨特性就在于阿爾及利亞獨特的歷史、語言、宗教和文化。《阿爾及爾憲章》進一步指出,“革命從來不是同過去一下子完全一刀兩斷。人在過去遺留下來的各種條件的影響下進行活動,這些條件又迫切地給人們指出道路。正因為如此,唯有歷史能賦予已經發生的事情以意義。”[注]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文件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39頁。
第二階段是布邁丁時期的“革命合法性”。1965年6月19日,為了糾正本·貝拉偏離軌跡的路線,布邁丁發動軍事政變,便是“為了恢復革命的合法性,為了重新賦予革命原則以全部價值。”[注][阿爾及利亞]布邁丁:《布邁丁言論選編》,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2頁。首先,布邁丁確立了以“烏季達集團”[注]烏季達集團:1965年布邁丁發動政變推翻本·貝拉,革命委員會成為最高權力機構,而革命委員會的核心是曾在革命年代與布邁丁一同駐扎在摩洛哥小鎮烏季達(Oujda)的部分軍官,故被稱為“烏季達集團”。為核心的統治集團。政變后的最高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由發動政變的26名軍官組成,包括總參謀長和各軍區司令等,[注]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07.從而完成了國家機構的重組。其次,完成對民族解放陣線黨的改造。由戰爭年代的老兵填充并重構黨的組織,將戰爭年代與建設年代通過革命精神連接在一起,藉此賦予黨以新的生命。最后,將“革命”作為社會整合的工具。為了彌合民族、宗教和語言等方面出現的分歧,布邁丁希望通過重新解讀“革命”來完成對經濟、政治和社會精神的重塑。
第三階段是合法性的轉型時期。1978年12月,布邁丁突然病逝,導致阿爾及利亞出現政治合法性危機。首先,布邁丁猝然離世,標志著傳統魅力型權威的終結,從而造成短期內的權力真空;其次,隨著獨立后一代的成長,革命已經成為歷史記憶,革命合法性的基礎在時光流轉中遭受侵蝕;最后,民間伊斯蘭運動興起,并成為國家控制之外的政治力量,開始挑戰政府的權威。沙德利總統推行“去布邁丁化”政策,實行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政府在進行自我否定的同時,又試圖建立新的權威基礎。然而,在經濟改革失敗后,政治領域的改革打開了政治危機的魔盒,以伊斯蘭拯救陣線為核心,形成了新的否定政權合法性的“合力”。
第四階段是布特弗利卡時期重建“民族合法性”。1999年布特弗利卡在總統選舉中獲勝,開始了合法性重建的過程。布特弗利卡的第一步是推動民族和解。1999年和2005年分別通過了《民族和解法》和《和平與全國和解憲章》,通過政府主導的和平與和解進程,重新建立政府權威。第二步是重建國際聲譽。2001年在美國紐約和華盛頓遭受恐怖襲擊后,阿爾及利亞及時調整外交政策的方向,成為美國全球反恐的重要伙伴,使阿爾及利亞的國際形象得到改善。第三步是鞏固總統權力。布特弗利卡在第一任期后期開始進行大范圍的人事變動,加強對各級權力機構的控制。2008年11月,阿國民議會以超過四分之三的支持率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取消總統連任限制。隨后布特弗利卡又在2009年和2013年參加總統選舉,并獲得勝利。政治強人主導下的政治秩序仍是政治穩定的重要基礎。
(二) 政治認同維度——民族主義意識形態
阿爾及利亞的現代政治啟蒙是在法國的殖民統治下完成的,其開端就是阿爾及利亞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與強調族群分治的英國殖民模式不同,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強調以理性為基礎的普世價值,以“優越的”西方為模型推進以“同化”為目標的“文明使命”。這種殖民模式為“西方化”的個體開啟了升遷之路,但也因宣揚西方的優越而強化了法國與阿爾及利亞人的整體性對立。在殖民模式下的民族主義啟蒙和對立中,阿爾及利亞的認同意識逐漸出現。同化論者否認“阿爾及利亞民族”的真實性,而伊斯蘭改革主義者則在阿拉伯與伊斯蘭的歷史與傳統中確認了“阿爾及利亞祖國”的文化屬性。[注]慈志剛:《阿爾及利亞自管社會主義起源探析》,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8年第2期,第72頁。在此后的民族解放斗爭中,民族主義成為政治動員的重要旗幟,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獨立以后。
第一,民族主義政治話語的延續。阿爾及利亞是以民族解放斗爭的形式實現民族獨立的,民族主義在這一過程中表現為對殖民統治的反抗,并通過民族的“再生”賦予民族共同體以現實價值。作為大眾政治的產物,民族主義也是大眾政治的制造者。民族獨立確定了阿爾及利亞的自然地理疆界,獨立后的民族主義政治通過大眾動員來確定國家的政治疆界。為了宣告與殖民時代的資本主義和剝削壓迫揮手作別,阿爾及利亞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在官方意識形態中,阿爾及利亞的社會主義是有別于其他國家的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它的獨特性深植于阿爾及利亞獨特的歷史、語言、宗教和文化。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成為民族主義革命的延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轉變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進而上升為國民“忠誠”的依據。到布邁丁時期,他批判了本·貝拉的社會主義,強調社會主義必須以阿拉伯和伊斯蘭傳統作為道德基礎,后來又發動“文化革命”來回歸革命年代的民族主義。到沙德利總統時期,阿政府進行了多元民主改革,造成了國家近十年的動蕩。1999年以后,布特弗利卡重新以民族主義作為宣傳工具,以此來疏導民族情感,并從中獲取政治能量。
第二,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法國對阿爾及利亞除了法律層面的殖民統治以外,還有意識地對殖民地進行文化層面的改造。在殖民體系的話語下,阿爾及利亞社會被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粗暴野蠻、桀驁不馴、世代游牧的外來征服者——阿拉伯人,另一部分則是與歐洲文明相似的、過著世俗的、定居生活的本土居民——柏柏爾人,殖民者通過這種“柏柏爾神話”,為殖民統治建立合法性。殖民主義者通過一種錯誤的邏輯重新構建被壓迫人民的過去,即歪曲它、毀壞它、消滅它。[注][法]弗朗茲·法農:《全世界受苦的人》,萬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頁。與殖民話語下的歷史敘事相對應,民族主義者在1954年的獨立宣言中明確提出為了“阿爾及利亞民族”和“阿爾及利亞祖國”而團結斗爭的必要性。[注]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文件集》,第143-146頁。獨立后的《阿爾及爾憲章》有意識地擺脫殖民主義歷史敘事,將阿爾及利亞的歷史追溯到8世紀的“伊斯蘭征服”時代,反侵略與民族解放是其中的核心主題。布邁丁時代仍然延續反殖民主義話語,國家發起了全面“書寫和重寫歷史計劃 ”,[注]Laurie A. Brand, Official Stories: Politics and National Narratives in Egypt and Alger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42.把阿爾及利亞地理范圍與民族特征形成的歷史追溯到努米底亞時代。[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三局譯:《阿爾及利亞國民憲章》(內部資料),1984年版,第21頁。1979年以后,革命話語在阿爾及利亞的教科書中逐漸消失,隨著柏柏爾人復興運動興起,歷史敘述更加強調團結與統一,比如1992~1993年六年級的歷史教材強調阿爾及利亞人通過共同的語言、宗教、習俗和傳統構成了阿爾及利亞社會。[注]Laurie A. Brand, Official Stories: Politics and National Narratives in Egypt and Algeria, p. 173.總體來看,獨立后阿爾及利亞仍然延續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反復強調民族共同體的延續性。
第三,民族主義外交的推行。民族主義政治延伸到外交領域,對阿爾及利亞的外交實踐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本·貝拉和布邁丁時期,仍然延續革命時代的民族解放話語,在處理對外關系上,以“革命”和“反動”作為國家間交往的價值標準,阿爾及爾也成為那個時代革命者的“圣地”。阿爾及利亞堅定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但主張對主權國家內部事務不加干涉,反對向外輸出革命,阿爾及利亞也因此成為不結盟運動的領導者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倡導者之一。美國學者羅伯特·莫蒂默(Robert A. Mortimer)認為,獨立后阿爾及利亞的外交政策經歷了從革命主義向國家利益的轉變,[注]Robert A. Mortimer, “Algerian Foreign Policy: From Revolution to National Interest,”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2015, Vol. 20, No. 3, pp. 466-482.實際上,冷戰背景下阿爾及利亞的外交政策充滿了實用主義色彩。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失敗,阿爾及利亞在外交上全面收縮,在90年代甚至陷入“孤立”。布特弗利卡執政后,憑借其豐富的外交經驗,采取“安全向西看,經濟向東看”的策略打破了外交困境,與此同時,他還進行了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但獨立自主仍然是國家吸引外資的優先考量要素。2009年通過的新投資法堅持阿方控股政策[注]中國駐阿爾及利亞經商參處:《阿爾及利亞出臺投資新政策保護本國企業》,2009年10月5日,http://d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0901/20090105996226.shtml,登錄時間:2018年5月29日。,該政策雖然因影響外來投資而飽受詬病,但阿爾及利亞始終沒有將其放棄的計劃。
第四,民族主義為導向的政治和解。民族主義通過對內的政治治理和對外的國際交往,確定了民族國家的政治疆界,又通過語言、宗教和歷史的統一,建立對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沙德利時期的政治改革,強調以“去布邁丁化”的多元民主為特征,這與民族主義政權強調統一的原則發生矛盾,伊斯蘭復興運動和柏柏爾人復興運動從政權的高壓下釋放出來,在時機成熟后,發起了對政權的挑戰,試圖擺脫民族主義政治治理模式。1999年7月,阿政府頒布《民族和解法》,該法一方面恢復了國家對民族和解進程的主導地位,重建政府的權威,另一方面也通過大赦的方式試圖重建民族團結。2005年4月,布特弗利卡在其第二總統任期提出了新的民族和解方案——《和平與全國和解憲章》,其核心內容是鞏固和平,鞏固民族和解,增強民族凝聚力等。通過這些實現民族和解,重建民族認同的努力,放下武器的反政府武裝多數通過大赦重新回歸社會。根據半島電視臺統計,截止2006年3月,共有2,629名監獄服刑人員被釋放。[注]George Joffe,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General Amnesty in Algeria,”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3, No. 2, 2008, pp. 213-228.
(三) 政治保障機制——軍政體制的維持
在阿爾及利亞實現獨立后,由于缺乏公認的政治權威,在阿爾及利亞的政治制度化進程中,出現了多個權力中心的競爭,最終以軍人干政的形式完成了政治參與規則的確定。塞繆爾·亨廷頓在討論“軍人干政”時認為,最初的干預可能不具合法性,但是當干預轉變為參與,并承擔起創設新的政治制度的責任,從而使未來的軍人或其他社會勢力的干預成為不可能或不必要時,干預也就能獲得合法性。[注][美]塞繆爾·P. 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199頁。阿爾及利亞軍政體制的建立便是以“軍人干政”的方式開始,以構建新的政治權力關系結束,其本質內容是為民族主義政治發展的不確定性提供強制性的穩定結構。
第一,軍政體制存在的必要性。軍政體制與軍人寡頭政治不同,它強調穩定優先,在此基礎上推進改革。為了確保政治秩序的穩定性和發展的有序性,軍方對政治進行有限干預,因此,有學者認為,中東地區的軍隊不僅是指導現代社會所必須的工業化、制度化和改革的理想工具,還是威權主義實現穩定的關鍵變量。[注]Steven A. Cook, Ruling But Not Governing: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gypt, Algeria, and Turke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首先,阿爾及利亞軍方是現代化變革的倡導者。阿爾及利亞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是從布邁丁發動政變后開始的。其次,軍方支持政治制度化建設。由于軍方缺乏消弭意識形態分歧的有效手段,因此,通過制度化建立超越政治集團和意識形態的法律規范和秩序,達到社會整合的目的。最后,軍方重視合法性建設。軍人干政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但是軍方通過推動現代化和民主化等方面的變革,為國家發展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制度結構,從而為政治的良性運轉開辟了道路。
第二,軍隊政治角色的轉變。阿爾及利亞獨立后分散的政治權力迅速集結為兩大對立的集團——特雷姆森集團和提濟烏祖集團,兩大集團的對立加速了國內政治的碎片化。在總參謀部的支持下,本·貝拉為首的特雷姆森集團獲得勝利,此后,軍隊便成為政治發展進程中的決定性力量。獨立后軍隊參與政治大體經歷五個階段,即本·貝拉時代軍政“聯盟”階段;布邁丁時代的全面參與階段;沙德利時代的軍政分離階段;內戰時期的軍管階段;以及布特弗利卡時代的軍政關系調整階段。1999年擁有軍方背景的布特弗利卡執政后,重新調整總統與軍方的關系,軍隊回歸軍營,并在憲法框架內發揮作用。2003年總參謀長拉馬里將軍宣布,軍隊在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中不會傾向任何候選人。[注]Ulla Holm, “Algeria: President Bouteflika’s Second Term,”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10, No. 1, 2005, p. 32.布特弗利卡完成了軍隊的重新洗牌,軍隊的控制權也轉移到總統手中,唯一不變的是軍隊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
第三,軍政體制的治理模式。阿爾及利亞反殖民統治的暴力特征決定了軍隊在獨立后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軍隊從戰爭時期的革命者轉型為獨立后現代化建設的改革者和政治秩序的捍衛者,軍人與政治的特殊結合形成了軍政體制。獨立初期,為安撫各軍區領導人,政治局對其許以高官厚祿,擴大軍區對政治事務的參與;另一方面,各軍區接受政治局提出的軍隊復原原則,退伍軍人轉變為地方基層干部,在制憲國民議會的196名成員中前軍區領導人便占了三分之一。[注]David and Marina Ottaway, Algeria: The Politics of a Socialist Revolution, p. 72.布邁丁執政后,軍人也從幕后走上前臺,政治上實行高度集權,經濟上開啟以“產業化工業”為特征的現代化,阿爾及利亞軍政體制的基本特征在這一時期最終形成。

(四) 政治調節機制——福利換穩定模式
國民收入的分配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是對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從政治學角度看則是對社會關系的重新調整,它能夠對政治發展進程產生深遠影響,特別是福利性分配對平抑社會不滿,調節社會矛盾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阿爾及利亞獨立初期處于從殖民體系向民族國家過渡的時期,社會經濟的管理與實踐經驗缺失,因此,1963年以后政府才以法令的方式建構替代性的社會經濟體系。到布邁丁執政時期,阿爾及利亞經濟發展模式初步建立,國家掌握更多的經濟資源用于再分配,福利性分配亦始于這一時期。作為一種政治調節手段,福利性分配的主要目標是實現社會穩定,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隨著軍政體制的建立,威權主義政治排斥大眾參與式的政治生活。因此,國家通過提供福利性分配,換取民眾對政治活動的低度參與。其次,阿爾及利亞依據“增長極”理論制定了“產業化工業”戰略,通過工業增長拉動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現代化。根據2010年的數據,阿爾及利亞石油儲量15.4億噸,居世界第15位,天然氣儲量4.58萬億立方米,居世界第7位。[注]《世界知識年鑒》,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頁。因此,炭化氫產業成為工業增長的動力源,但炭化氫產業屬于資本密集型產業,勞動力需求小。受此影響,國家將炭化氫產業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福利性再分配。最后,隨著石油價格上漲,沙德利政府放棄了布邁丁時代的緊縮政策,通過加大社會福利滿足群眾需求,以緩解政府所面臨的政治壓力。
從福利性分配的類型看,可以分為制度性福利和臨時性福利,二者對政治穩定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所謂制度性福利,是國家通過建立某種福利制度對社會資源進行分配,這包括對基本食品實行價格補貼,對公有住房實行低廉租金,為國民提供免費醫療,對全民實行免費教育以及對國家正式職工享受子女補貼等。[注]趙慧杰:《列國志·阿爾及利亞》,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頁。阿爾及利亞國民的稅收始終維持在較低水平。1989年至1990年的政治動蕩期,加上石油價格暴跌,稅收僅占GDP的16.3%,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內戰,2000年稅收占GDP的比例進一步下降到11.5%。[注]Clement M. Henry, “Algeria’s Agonies: Oil Rent Effects in a Bunker State,”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9, 2004, p. 70.2009年政府與工會和雇主舉行了三方會議,決定提高最低保障工資,同時,國家將繼續負擔家庭津貼。這些政策在緩解社會矛盾,調節政府與民眾關系方面長期發揮著作用。為了應對突如其來的政治危機,政府還會增加臨時性的福利。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后,阿爾及利亞的部分城市也出現示威和騷亂,為了應對危機,政府除了部署警力來控制局勢和滿足群眾政治改革呼聲以外,還通過基本食品補給和增加工資等方式平抑民眾不滿。2011年1月,阿爾及利亞糧食局緊急從國際市場采購小麥85萬噸,防止出現糧食短缺,確保百姓基本食品供應。[注]中國駐阿爾及利亞經商參處:《阿緊急進口85萬噸小麥》,2011年1月7日, http://d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101/20110107382373.shtml,登錄時間:2018年6月3日。與此同時,國家向年輕人貸款的條件也變得寬松,以保障失業青年順利就業。
由此可見,“福利換穩定模式”是威權主義政體應對大眾政治參與的調節手段。得天獨厚的油氣資源和炭化氫產業是阿爾及利亞政府的重要政治資本,以石油美元為基礎的福利分配是構建政權或領袖合法性的特殊路徑,通過壟斷福利分配,滿足民眾對物質生活的期望,從而將經濟資源轉變為政治資源。當然,福利分配本身并不能解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但卻能夠遏止突發性的政治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政權的生命力。
三、 當前阿爾及利亞政治穩定面臨的挑戰
2010年以來中東地區迎來了新的政治挑戰,阿拉伯國家的劇變催生了改造中東政治的革命性實踐,當然也對傳統中東國家的政治穩定模式提出了挑戰,它必然會推動中東國家治理體系的深層次轉型,重新思考政治變局與政治穩定的動態關系或許能夠為阿爾及利亞的政治轉型提供新的視角。
(一) 威權主義政治前途未卜
獨立初期,本·貝拉和布邁丁在構建威權主義政治過程中,雖然群眾基礎有所不同,雙方對社會主義的認知和治理模式等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就威權主義的核心構成要素而言,二者并無太大差異。二者的政治權威都是直接繼承于民族解放斗爭,以一黨制政治體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革命歷史的合法性作為威權主義政治的核心要素。政治權威構成要素都具有歷史性,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要素會失去穩定性而走向衰微。沙德利執政時期,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威權主義遭遇巨大挑戰,民族解放斗爭轉變為歷史記憶,一黨制遭遇多元民主的挑戰,自管社會主義經濟也因經營不善而開始向市場化轉型,因此,軍隊強權成為維系政府權威的唯一途徑。現任總統布特弗利卡雖然仍重視革命和民族主義傳統,但與曾主導阿爾及利亞政權的議會、執政黨和軍隊相比,他更希望增強個人權力。[注]Stephen J. King,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46.布特弗利卡一方面將軍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修改憲法,廢除連任限制,為個人連任鋪平道路;另一方面,他又不斷推動政治經濟改革,滿足民眾渴求民主和改善生活的愿望。由此可見,布特弗利卡在其任期內完成了政治權威的重建,他繼承了傳統威權主義的革命話語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堅持軍隊在維系政治權威中的特殊地位,同時,他也順應時代潮流,為新威權主義政治增添了新的要素,這其中布特弗利卡的個人魅力發揮著重要作用。2014年布特弗利卡贏得選舉開啟第四個總統任期。2019年阿爾及利亞將舉行新的總統選舉,從當前情況看,布特弗利卡身體健康狀況堪憂,而不論布特弗利卡以何種方式退出政治舞臺,都會對阿爾及利亞威權主義政治的發展造成巨大影響。
(二) 民族主義政治的衰退
作為意識形態和社會運動的民族主義,它在阿爾及利亞的出現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民族主義可以成為一種革命動員的武器,以民族的視角判斷反殖民運動中的“敵”與“我”。民族主義可以成為一種大眾參與的旗幟,阿爾及利亞人在它的引導下自發走上了自管社會主義的道路。民族主義還可以是一種政治統合的工具,它能夠建構出一個超越地域、血緣和政治觀念的穩定共同體。總之,與其他一些中東國家一樣,民族主義使阿爾及利亞完成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跨越,是推動歷史轉折的重要力量。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民族主義逐漸式微的趨向已不可避免,其式微的根源則在于民族主義本身。一是因為民族主義具有排他性。民族主義通過確定自身疆界的方式建構一個民族共同體,再將民族共同體與主權范圍相重合,建立一個排他性的民族國家。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藝術、文學和語言等問題變成嚴重的政治對立問題,并被用來作為民族斗爭的武器。[注][英]埃里·凱杜里:《民族主義》,張明明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頁。阿爾及利亞獨立初期,將語言、文字和教育作為實現民族主義的工具,否認其他民族的存在。特別是在柏柏爾人問題上,政府否認其存在的合法性,1979年以后,柏柏爾人問題逐漸政治化,這也凸顯了以建構“同質”共同體為目標的民族主義在實現社會整合上的缺陷。二是因為民族主義具有狹隘性。在人類文明交往的特定歷史階段,民族主義通過競爭來劃分邊界和尋求群體認同,對抗式的互動更是成為近代以來民族國家間交往的經常方式。阿爾及利亞經過130多年的殖民統治,使它對民族獨立更為珍視,因此,在國家間交往層面,阿爾及利亞積極參加反帝反殖的不結盟運動,提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等主張。兩極格局解體后,國際關系發生了深刻變革,主權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發生變化,阿爾及利亞的外交身份也從第三世界的領導者向地區核心國家轉變。隨著全球化對民族國家的侵蝕,布特弗利卡時代外交中的民族主義色彩逐漸淡去,這說明在新的歷史時代,民族主義急需完成對自我的超越。
(三) 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推進
政治民主的思想和實踐在阿爾及利亞經歷了一個長期發展和演變的過程。
第一,民族解放斗爭語境下的民主。從民族主義者在奧雷斯山打響反抗殖民統治第一槍,直到1956年蘇馬姆會議通過民族解放陣線綱領,民族主義者都主張建立保衛民主自由委員會,但他們對民主的內涵并未做任何的解釋和說明。獨立前夕的《的黎波里綱領》是民族國家建設的綱領性文件,主張繼武裝斗爭之后,應該進行思想斗爭;繼民族獨立斗爭之后,將進行人民民主革命,[注]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文件集》,第206頁。這里所說的民主在綱領中表述為廢除封建主義制度,建立新的機構和組織來保證人們的解放和自由。
第二,自管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民主。阿爾及利亞在結束了獨立初期的政治混亂后,民族解放陣線通過了《阿爾及爾憲章》,其特點是用階級斗爭話語繪制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藍圖。民主一詞雖然被提及甚少,但卻被賦予了新的內容,即勞動者的普遍意志充分地得到表達。布邁丁時期的民主同樣是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予以闡釋的,所謂民主是要廢除資本主義以前的、舊的、過時的,反動的社會結構,以及它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影響。[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三局譯:《阿爾及利亞國民憲章》(內部資料),第32頁。這一時期的政治民主只是進行大眾動員的口號,缺少制度化的實質內容。
第三,投票箱中的民主實踐。1988年阿爾及利亞修訂了憲法,真正開啟了多元民主改革。受民主化第三波浪潮的影響,阿爾及利亞嘗試用西方自由人權觀念對政治民主進行重新解釋,從初期的民主化實踐來看,投票箱中的選票更多地是表達民眾對生活的不滿,他們對民主政治并無深刻理解。此后,政治民主很快超越了政治實踐的層面,上升為一種政治價值,賦予政權以統治的合法性,這就使民主成為一種被普遍接受的政治游戲規則。從1995年開始,軍方便嘗試通過民主制度重建政權合法性,這次大選標志著阿爾及利亞向民主制度轉變的重要一步。[注]Martin Stone, The Agony of Algeria,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7, p. 121.到布特弗利卡時期,政治民主已經成為政治生活中的常規話語。但是,從當前阿爾及利亞的民主化實踐來看,軍人對政治生活的干預和總統威權主義統治等內在的問題無疑阻礙了民主化向更深層次發展。
(四) 經濟轉型的挑戰
在現代政治中,強大的軍事力量和超凡的領袖魅力都已經不再是政治權威的決定性因素,經濟價值對政治生活重塑的作用體現得越來越明顯。阿爾及利亞獨立初期,民眾通過自發占領被殖民者廢棄的無主產業,開始了自發的自管運動。本·貝拉通過將自管運動納入政府主導的制度化框架,建立了阿爾及利亞的自管社會主義。這種大眾參與式的經濟模式反映在政治生活領域,導致民粹主義政治的發展超出了統治集團的預期。布邁丁掀起了以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為內容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其“產業化工業”增長模式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現代化類型,排斥大眾參與,這也決定了民眾對政治生活的冷漠。20世紀70年代,阿爾及利亞完成了油氣資源的國有化,石油和天然氣在經濟生活中的影響逐漸增強,油氣資源也從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礦產資源和關系國計民生的經濟資源轉變為影響政治穩定的政治資源。布特弗利卡執政后試圖改變“惟石油發展戰略”,但恰逢國際油價走高,炭化氫產業的支柱性地位沒有得到任何改變。2000年,炭化氫部門占全部出口收入的95%和政府財政收入的60%。[注]Meredeth Turshen, “Algerian Oil & Ga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9, 2002, p. 184.到2009年國際油價下降前,阿爾及利亞對油氣資源的依賴程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石油美元仍是政府維持國內政治穩定和調節國際關系的重要經濟資本。2016年阿爾及利亞政府制定了“新經濟增長模式”戰略,試圖實現經濟多元化和戰略轉型,由于傳統經濟模式被賦予了太多的政治意義,因此,新的經濟轉型所產生的效應也會超出經濟層面而外溢到政治領域,二者的矛盾互動為政治穩定增加了無法預知的風險。
(五) 中東安全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并沒有構建出統一的政治規則,相反,地區和國家認同的重建增加了政治發展的多樣性,國際交往的擴大化使國家間的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強,這就為政治穩定提供了一個超國家層面的思考維度。漢斯·摩根索認為,占壓倒優勢的武力、超局部的效忠和對正義的期待這三個條件使國家內部的和平成為可能。[注][美]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徐昕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28頁。從這個角度審視2010年以來的中東變局,突尼斯事件的迅速外溢,并在中東形成多米諾效應,維持和平與穩定的因素在動態的地區局勢沖擊下土崩瓦解,并引發新一輪的政治權力重構。阿爾及利亞與突尼斯毗鄰,在中東發生劇變的背景下,并未發生任何旨在推翻政權的政治活動,僅阿爾及爾等部分城市出現要求政治改革的示威。更為重要的是,阿爾及利亞在整個西亞北非地區的政治安全和穩定在某種程度上對蔓延的政治風暴起到了有效的緩沖,使阿爾及利亞成為危機中的“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阿爾及利亞不具備發生政治變革的內部環境,從而使外部的連鎖效應無法形成有效沖擊。對政治暴力的恐懼、福利換穩定的政策以及相對開放的政治體系確保突尼斯和埃及那樣的大規模抗議沒有發生。[注]Larbi Sadiki and Youcef Bouandel, “The Post Arab Spring Reform: The Maghreb at a Cross Roads,”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25, No.1, 2016, p. 15.另一方面則是阿爾及利亞政府應對危機的策略,即“武力與金錢”的組合模式,實現了政治壓力的軟著陸。毫無疑問,阿拉伯劇變給中東國家政治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這包括政治版圖的碎片化、政治安全的跨國化、恐怖主義的國際化和危機傳播的網絡化等問題,再加上域外大國的推波助瀾,民族國家的政治規則與主權疆界在回應未來的政治挑戰時將更加難以提供有效的解決框架,這也是阿爾及利亞政治穩定需要破解的難題。
綜上所述,阿爾及利亞政治穩定的核心挑戰來自于國家政權內部的政治體系調整、意識形態重構、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轉型的成敗,地區層面政治動蕩的連鎖效應在阿爾及利亞影響有限,而非國家行為體,特別是跨國恐怖組織會對國家安全產生了一定影響,但無法觸動政治穩定的基本結構。因此,如果阿爾及利亞政治穩定的核心維度不發生根本性變化,其政治穩定局面便不會遭遇根本性威脅,但當前阿爾及利亞政治所面臨的挑戰也使得維系政治穩定必須推進政治改革。從中東變局中阿爾及利亞“例外論”的視角觀察,阿爾及利亞的政治穩定源于對20世紀90年代政治危機的反思,經濟危機誘發政治改革,進而導致伊斯蘭主義挑戰世俗政權的劇變模式,使阿爾及利亞經歷了十年的政治調整才走出危機漩渦,而剛剛發生過的阿拉伯劇變從內容來看只不過是信息時代背景下阿爾及利亞政治危機的翻版。阿爾及利亞擺脫危機的模式對亂局過后的中東國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那就是對民主價值的追求讓位于對民生需求的肯定,對政治變革的推動讓位于回歸政治秩序,大眾政治參與讓位于政治權威的構建,最終在實現政治和解的基礎上實現政治轉型。總之,政治穩定的本質便是一個在政治的動態發展中尋找新的政治平衡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