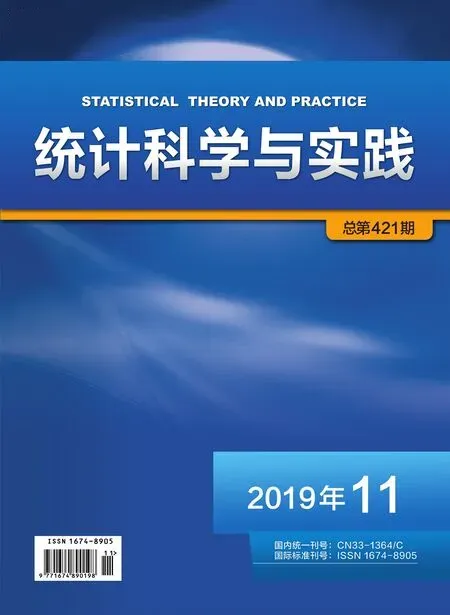工資上漲、勞動力市場規制與制造業企業雇傭結構調整研究
□胡瓊 朱敏
引言
近年來我國人口紅利優勢逐漸減弱,國內企業面臨著勞動成本上漲帶來的挑戰。20 世紀90年代,隨著人口流動政策的放寬,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勞動供給大于需求,勞動力需求方在就業和工資的決定中占據主導地位,政府也放松了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最大限度地創造就業機會(都陽,2014),各類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度較高的制造業企業因此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是,2003年出現的“民工荒”,中國被認為正在跨越“劉易斯拐點”,國內廉價的農村勞動力過度供給已經結束(Zhang et.al,2011;Feng et.al,2017)。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這種變化,推動了勞動工資持續上漲,進而導致國內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上升。
勞動力市場的變化促進了勞動力市場制度的調整。隨著工資水平的上升,勞動者對于回報的預期也逐漸提高,并使得勞動爭議明顯增強,從而對勞動力市場規制的需求也逐漸增加(都陽,2014),當時實行的《勞動法》已經無法滿足勞動力市場的新需求。從而,以“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為立法目的的《勞動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正式開始實施。相比1994年出臺的《勞動法》,新法規加強了勞動者的權益保障,比如增設了應當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法定情形,增設了勞動合同到期終止支付經濟補償金的義務等(董保華,2016)。但實際上也限制了企業用工的靈活性,并進一步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
理論上,勞動工資上漲會刺激企業用資本替代勞動,謀求技術升級,相應地,企業會增加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而在加總層面表現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都陽,2013)。在工資持續上漲的背景下,現階段我國制造業企業是否已經實現了這種轉型升級?本文將從企業雇傭結構變化的角度來回答這一問題。進一步地,《勞動合同法》的出臺雖然能夠保護勞動者權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強勞動者對企業的忠誠度,但同時也增加了企業的勞動成本壓力,限制了企業自由調整雇傭結構的靈活性。那么,《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在工資上漲過程中對企業雇傭結構調整的影響如何?
本文將以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和杭州市薪酬調查匹配數據為樣本,觀察近年來我國制造業企業對工資持續上漲做出的反應,同時以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為研究對象,分析勞動力市場規制在企業應對勞動成本上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本文各部分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簡單介紹本文的數據和描述性分析;第三部分為理論分析和經驗模型;第四部分是主要實證結果;最后是結論。
數據介紹及描述性分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形成的杭州市制造業企業數據和杭州市企業薪酬調查數據。杭州市企業薪酬調查是由政府定期組織實施的以企業中不同職業勞動者工資報酬水平和不同行業企業人工成本狀況為調查內容的抽樣調查,它為我們觀察企業對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反應提供了詳細的基礎數據。同時,該調查包含的勞動合同簽訂信息為我們研究勞動力市場規制對企業雇傭結構調整的影響創造了可能。但是,杭州市企業薪酬調查中企業主要經濟指標類信息十分有限,故而我們將同時借助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提供的相關數據來研究上述問題。
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提供了2013年的企業數據,我們根據企業的組織機構代碼,將經濟普查數據與2013-2015年杭州市企業薪酬調查數據匹配,得到297 家企業。之后,剔除樣本數據缺失和數據明顯異常的樣本,最終得到236 家樣本企業。
本文的目的是要考察在工資上漲、勞動力市場規制進一步增加企業用工成本的背景下,企業是否會通過要素替代來應對勞動成本的上升。前文已經說明,無論是用資本還是技術來替代勞動,最終都將伴隨企業內部雇傭結構調整的發生,也即高低技能勞動力的替換。企業薪酬調查按管理崗位級別、專業技術職務和職業技能等級對每一位調查員工分類,我們據此將員工分為技能勞動力和非技能勞動力,觀察企業內部高低技能員工雇傭數量的相對變化。另外,薪酬調查中對員工簽訂的勞動合同為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還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務為期限的勞動合同進行了區分,以便從勞動合同簽訂的角度來觀察勞動力市場規制是否會限制企業用工結構調整。
觀察樣本企業和員工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簽訂情況。如表1所示,2013-2015年與員工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企業的比例都在50%左右,基本穩定。簽訂率大于10%的企業占比逐年遞增,從2013年的27.12%上升到2015年的33.05%,說明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一市場規制的影響逐漸穩定深入。比較與企業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員工情況,顯而易見,低技能員工占比要遠高于高技能員工,《勞動合同法》的出臺確實起到了保護勞動者尤其是那部分能力相對較弱的勞動者的作用。
理論分析與經驗模型
相對要素價格的變化可能會導致企業進行生產要素的替代。工資上漲后,企業可能會用資本或技術替代勞動,最終會伴隨高技能勞動力對低技能勞動力替代的發生。要觀察勞動成本上漲是否會倒逼企業進行雇傭結構調整,首先需要明確這種替代發生的條件。它不僅受勞動價格的影響,還取決于資本價格、企業現階段的生產技術、計劃產出水平等因素。如果工資一直都保持著高速增長的態勢,那么在長期內勞動成本就可能會對企業構成經營約束,迫使企業用其他要素來替代勞動。相應地,勞動要素本身的投入,或者說技能型勞動力和非技能型勞動力的配比也會發生改變。當然,現實中要素替代能否發生以及何時發生,還要取決于企業使用的生產技術,而這一變量并不容易被直接觀察到,本文將使用企業的利潤水平、所有制特征變量來間接度量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其次,還需要注意勞動力市場規制在其中的作用,下文將對此做進一步討論。

表1 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企業和員工占比(單位:%)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借鑒都陽(2013)使用的勞動力需求方程來估計工資上漲是否會影響企業調整雇傭結構,估計方程如下:表示企業i 在t 時技能型員工數S 和非技能型員工數U 的比值。等式右邊的變量

估計方程(1)時需要注意,由于我們無法觀測到企業計劃的增加值,所以在計算時使用企業當年的實際增加值來替代計劃增加值。但是其中很可能會存在測量誤差,因為企業是提前決定計劃產出水平的,而市場沖擊很可能會導致實際產出與當時的計劃產出不一致,這種不一致就會反映到誤差項中,進而導致內生性問題。為了緩解這一問題,同樣借鑒都陽(2013)的做法,將2013年企業固定資產合計的對數作為工具變量,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
此外,考察勞動成本上漲是否會倒逼企業轉型升級還需要注意勞動力市場規制在其中的作用。一是因為現階段施行的《勞動合同法》在諸多方面都偏向于保障勞動者權益,而增加了企業潛在的勞動成本,如果勞動工資的上升會倒逼企業調整雇傭結構,那么勞動力市場規制的嚴格性增強會進一步加劇這種效應。二是因為《勞動合同法》中的部分條例限制了企業自由調整用工的靈活性,該法律對企業解雇員工做了相當嚴格的限制,企業一旦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就很可能面臨著未來終止勞動合同后需要支付的經濟補償。從而,勞動力市場規制的限制可能會抑制企業進行要素替代。為了觀察勞動力市場規制的作用,我們從總樣本中篩選出有與員工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企業和沒有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企業,分別重新估計(1)式。通過比較篩選出的子樣本企業與總樣本企業的估計結果,來判斷勞動力市場規制是否限制了企業對生產要素的調整。
實證結果
本文使用2013-2015年236 家樣本企業估計工資上漲后企業雇傭結構的變化,以及勞動力市場規制是否會約束企業雇傭結構的調整。估計模型時,我們分別對236家總樣本企業、簽訂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119 家強約束子樣本企業以及沒有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117 家弱約束子樣本企業,使用2SLS 方法①為解決用企業實際增加值替代預計增加值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使用樣本企業2013年固定資產合計的對數值作為工具變量來識別,并對其可能存在的弱工具變量問題和過度識別問題進行檢驗,結果未發現這兩類問題,限于篇幅,檢驗結果不列出。和OLS 方法進行估計,結果如表2、表3 所示。表2 中,全樣本估計結果顯示滯后一期工人工資的回歸系數均為負,說明在樣本觀察期間,工資上漲并沒有促使企業用高技能勞動力替代低技能勞動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制造業企業在勞動成本持續上漲的壓力下,仍然沒有實現用資本或技術對勞動的替代。
表3 為子樣本估計結果,其中強約束子樣本的回歸結果與表2 一致,滯后一期工資變量的回歸結果也為負且2SLS 結果在5%水平上顯著,但是相比于表2 中估計系數的絕對值更大,說明相同幅度的工資上漲,會導致這部分企業技能和非技能勞動力數量之比更大幅度的下降。這一現象可以由勞動力市場規制進行解釋——前面描述性統計部分已經說明與企業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員工多為非技能勞動者,而企業解雇這部分員工的可操作空間很小或者需要承擔很大的解雇成本,形成對低技能勞動者就業的保護,從而工資上漲會進一步導致企業技能工人與非技能工人數量比值的下降。

表2 全樣本回歸結果

表3 子樣本回歸結果
對比強約束樣本和弱約束樣本的回歸結果,在弱約束樣本2SLS 估計結果中,企業滯后一期工人工資對數的回歸結果為負值但不顯著,說明工資上漲對這部分企業調整雇傭結構的作用效果更不明顯,或者說對這部分企業技能勞動者與非技能勞動者相對數量變化的影響不顯著,這一結果從反面證明了勞動力市場規制的存在確實影響到了企業雇傭結構的調整。
結論
勞動工資的持續上漲已經增加了企業的勞動成本,《勞動合同法》的實施進一步增加了企業潛在的用工成本,限制了企業用工的靈活性。本文使用2013年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和2013-2015年杭州市薪酬調查數據,檢驗了工資上漲是否會刺激企業調整雇傭結構,以及以非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為例的勞動力市場規制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全樣本估計結果顯示勞動工資的上升并沒有刺激企業用高技能勞動力替代低技能勞動力;子樣本估計結果中強約束企業高低技能勞動力數量比值下降更大且顯著,弱約束樣本企業高低技能勞動力數量比值也在下降但不顯著。對比可以發現,勞動力市場規制確實會限制企業調整用工結構。如果繼續保持現階段《勞動合同法》下的勞動力市場規制,那么在未來也會因為制度約束而很難實現勞動要素與資本和技術的最佳匹配,實現利潤最大化。所以有必要警惕勞動力市場規制對企業生產要素調整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