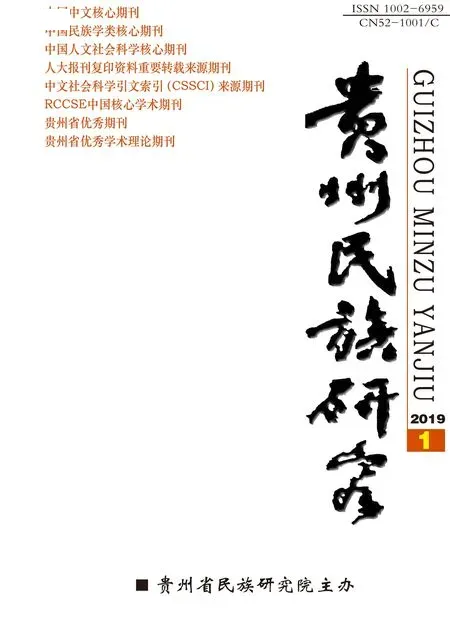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的地域性對接探究
孔 薇
(蘭州大學 藝術學院,甘肅·蘭州 73000)
西北地區作為我國少數民族聚居區之一,有著豐富多彩的民族民間藝術。雖然受地域文化和宗教教義的影響,民族民間藝術的地域性差異顯著,但是縱觀西北地區少數民族民間藝術的文化蘊意和整體發展態勢,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的地域性對接體現得淋漓盡致。一方面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相對單一;另一方面作為我國三大民族聚居區之一,多民族文化融合與區域藝術品格的時代性堆積是西北少數民族群體性民間藝術對西北文化品格的共同塑造。比如:回族花兒藝術在西北地區均有分布,但是河州地區花兒藝術游牧民族氣息較為濃厚,銀川地區花兒藝術的邊塞韻味更是難以比擬。總之,特定的地理環境對民族民間藝術的品格塑造無法衡量,民族民間藝術的地域性對接是民族藝術品格最直接的呈現。
一、典型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概述
(一)基于文化視域下的民族民間藝術范疇
民間藝術作為藝術劃分的類別同宮廷藝術相對立,民間藝術的稱謂同市井藝術相一致,都是對民間社會藝術的總稱。現代意義上的民間藝術是相對學院派藝術而言:是指特定區域的社會群體在社會生活中為自身或者部落生活與生產需求所創造的具有一定審美價值的藝術存在。基于文化視域下民族民間藝術則是指生活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群眾在生產實踐活動中基于一定的文化存在而創造的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無獨有偶的是西北地區受特定地理環境和文化淵源的影響,對民間藝術定位有著相對具體的認知,即民間藝術是特定民間造型藝術。當然,縱觀民族地區民間藝術的普遍存在,民族民間藝術理應包括:民族手工藝品、民族歌舞藝術、民族雕刻剪紙等裝飾性藝術等。總之,少數民族群眾作為民族民間藝術的創作者和傳播者除民間藝術自身的藝術品質外,少數民族群眾普遍能歌善舞的藝術秉性同民族民間藝術的原生態持續發展是一脈相承,或者說民族民間藝術的獨特存在是民族群體藝術創作的結晶。
(二)民族民間藝術的特征
民族民間藝術作為少數民族群眾能歌善舞、多才多藝的民族秉性表現。同民間藝術的維度相比,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多樣性、人文性等特征。所謂民族性是民族民間藝術自我藝術品格的定位,縱觀我國少數民族藝術發展史,各少數民族群眾對本民族民間藝術作品的傳承與創造均有獨特民族藝術韻味而始終無法被復制與臨摹,比如:風雨橋是侗族群眾內心情感的集合,對風雨橋紡織、刺繡等物質形式的藝術延伸和傳遞不單是藝術本身的存在,而是藝術所蘊含的文化魅力與藝術人文表露。同樣西北保安族作為甘肅特有民族,他們的紡織、手工藝藝術始終都以獨特的民族圖騰——保安腰刀為原型,并通過河西走廊獨特的藝術表達手法,使保安族民間藝術成為絲綢之路民族藝術的典范。所謂地域性是民族民間藝術獨特性的地域表現,一方面同一民族在不同生存環境中所延續的民族民間藝術具有明顯的地域差異,比如:甘南藏區藝術同青海藏區歌舞藝術表達手法差異性明顯,甘南安多藏區作為藏傳佛教院所在地濃郁的儒雅同內斂的藝術表達顯得安靜,但是青海果洛地區藏族群眾對歌舞藝術的追求同深邃廣袤的自然環境一致,即注重樂曲的喧囂。在服飾色彩藝術方面果洛地區藏族群眾以黑、藍色為主色調。而安多藏區以自然色彩裝飾居多。另一方面不同民族同一地域藝術表達也有明顯的差異。同在祁連山腳下,裕固族群眾手工藝藝術以格薩爾王故事為主題,而藏族群眾對手工藝藝術的創造以服飾、首飾為主。多樣性是民族民間藝術存在形式的直觀認知,我國少數民族眾多,民族民間藝術的表現形式也多姿多彩,數不勝數。人文性是少數民族民間藝術被逐漸延續的關鍵,一方面民族民間藝術的創作本身是民族情感價值的藝術表達,另一方面民族民間藝術本身寄托人文情感,比如:藏族群眾的石雕——瑪尼石,表達著藏族群眾祈福消災的群體心理[1]。
(三)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概述
按照西北藏族、回族、維吾爾族等人口較多的少數民族藝術創造慣性和東鄉族、撒拉族等人口較少的民族民間藝術的散落來看,民間音樂藝術始終占據著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的主導地位,西北少數民族民間音樂藝術主要包括:以反映少數民族群眾日常生活和生產的回族、東鄉族等少數民族群眾喜聞樂見的“花兒”,以反映宗教文化和宗教禮儀的藏族信徒宗教歌曲及穆斯林群眾禮拜歌曲。此外,藏族群眾對音樂藝術的超自然表達使之成為民族音樂中獨樹一幟的藝術存在,比如:神川熱巴作為藏族特有的音樂舞蹈,在被市場商業化之前通常是以祭祀為主題,換句話說受原始宗教形態和傳統神秘主義的影響西北少數民族音樂藝術的宗教色彩逐漸被淡化,但是在特定音樂表達中依然存在[2]。民族手工藝藝術也是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的有效存在形式之一,藏族群眾特別是安多藏區受佛學教育的影響,注重個體的積德行善,通常利用泥土等脫模制作小型泥造像,俗稱“擦擦”。此外,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藏戲面具作為藏族受工藝也深受其他民族群眾喜愛。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群眾對于地域性民族手工藝藝術的創造愈加專業化,錫伯族除手工弓箭藝術外繪畫藝術也相當精湛,同達斡爾族等兄弟民族所不同的是錫伯族繪畫藝術的主題基本上圍繞西遷為主。當然,東鄉族的傳統手工藝毛紡織及搟制工藝也是西北地區民族手工藝藝術占有獨特地位的藝術存在。此外,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群眾在刺繡、紡織、雕刻等流域都具有鮮明的藝術存在[3]。比如:撒拉族鑿石工藝、互助土族彩繡錢搭子等都以特定藝術存在成為西北民族民間藝術中不可多得的瑰寶。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受宗教文化和民族融合的影響在原生態藝術創造的出發點上基本相似,但是隨著獨立民族的形成西北民族民間藝術的類化也相對模糊,文化主題的對應和民族情感的藝術表達使得西北民族民間藝術成為絲路文化藝術的有機組成部分[4]。
二、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成因透析
(一)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必然性
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的地域性差異始終存在,但具體不顯著。這是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總體形態。縱觀西北民族民間藝術的地域性對接的可能性,一是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的民族融合鮮明,以伊斯蘭教為宗教信仰的東鄉族、保安族等少數民族本身同回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根源為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提供了可能[5]。二是族群忌諱同宗教習俗的藝術表達基本吻合,這是民族民間藝術能夠對接并規避地域性差異的中心。三是民族藝術同民族秉性及民族心理一脈相承,這是民族民間藝術突破地域限制和地域差異,形成統一絲路文化藝術的關鍵。
(二)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可能性
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可能性包括:多民族聚居區民族文化認同的藝術表達、相對穩定的地理單元對藝術土壤的熏陶、區域民族民間文化藝術間的吸納與借鑒、民族群體之間經貿往來中思想情感的對接等方面。這是促使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可能性認知[6]。總之,藝術作為無形的語言、靈魂的燈塔在形成獨立單元文化中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表現
(一)民族民間藝術所承受的地域特點一致
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是民族藝術同民族情感的凝結的結果[7]。民族民間藝術所承受的地域特點的一致性是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基礎。西北地區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區,二元制為主的民族生活習俗成為民族群體彼此文化認同和藝術相同的關鍵。首先,西北少數民族群眾基本上以游牧民族為主,草原文化涵蓋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創作的基本框架之中,特定的地域特色使民族藝術的表達有著相統一的文化基礎。其次,西北地區自然條件惡劣,在長期自然適應過程中統一的藝術表達主題成為民族民間藝術突破地域限制,實現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基礎。比如:藏族群眾在高原生活中為了祈福避難以瑪尼石為原始的藝術表達,除隱性地反映藏區惡劣自然環境的同時祈福心理不言而喻[8]。再者,特定民族民間藝術的發展和民族群眾地域性生存環境的藝術指代,是西北地區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根本,比如:“花兒”作為回族等少數民族音樂藝術在甘青寧地區普遍傳唱,但是河州花兒的民間藝術價值基本上涵蓋了寧夏地區東鄉族花兒藝術的人文表達。當然,隴東張川花兒藝術的內容同關山地域特色向對應,張川花兒多為經商等主題,臨夏花兒則以男女情愛為主。總之,民族民間藝術的地域性整體對接是西北少數民族在藝術創作中共同的心聲[9]。
(二)民族民間藝術基本上以民族生活為主
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的地域性對接關鍵在于民族民間藝術主題表達的一致性,簡而言之,以體現民族生活為主的民族民間藝術將生活藝術化,使得藝術化的生活不僅能夠釋放個體的價值觀,更能融入其他民族生活當中[10]。藝術是沒有地域限制的,以原生態群體生活為藝術的背景,本身是對民族藝術地域性摒棄。比如:青海土族群眾對刺繡藝術的地域性延伸,特別是女性服飾中刺繡花紋的裝飾,被撒拉族、藏族等女性所吸納,但是民族民間藝術的地域性呈現也被放大,土族刺繡一般在衣服的袖子、領周圍,而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藏族女性在刺繡藝術裝飾方面主要集中在紐扣附近。此外,西北地區少數民族音樂藝術基本上圍繞社會生產實踐,接近生活、源于生活的藝術表達和特色民族樂器對民族生活習俗的藝術點綴,除顯著的地域特色外,更多的是民族音樂對群體生活的共鳴。比如:藏族群眾的《砌墻歌》、撒拉族《擠奶歌》等都是對民族勞動行為的認可,基于民族群體社會生活的藝術是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必然選擇。
(三)宗教在民間藝術中的蘊含和隱藏相通
宗教在民間藝術中的蘊含和隱藏相通是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核心[11]。西北地區雖然民族眾多,但是宗教信仰相對簡單,基本上以信仰佛教的藏族、裕固族等和以信仰伊斯蘭教的東鄉族、回族等為主,單一的宗教信仰對民族民間藝術的內部發展與外在認同都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一方面同一宗教信仰對世界認知和自我價值觀的塑造基本相似,折射到民間藝術作品中藝術的形態和主題也大體吻合,比如:花兒作為西北民族音樂的典范,在回族、東鄉族等少數民族中均有傳唱,除花兒內容和地域性差異外,其對伊斯蘭教文化和教義的歌頌完全一致,民族民間藝術的地域性對接就是對民族藝術的內在宗教文化涵養的認可,不同地域同一藝術的文化相同是藝術形態地域性對接的直接反映[12]。另一方面以宗教題材為藝術外衣的民族民間藝術對宗教意蘊的蘊含和隱藏是同一宗教信仰群眾之間傳遞情感的有效途徑之一,統一的精神信仰是藝術思維構建的脊梁,是促使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助推器和永動機。
(四)民族民間藝術的社會期望始終被統一
民族民間藝術的社會期望始終被統一是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的基本[13]。首先,民族民間藝術的發展在承載藝術審美本能的同時孕育著藝術者對社會的期望,西北地區惡劣的自然環境、落后的生產力導致民族藝術現實寫照的藝術表達成為彰顯民族群眾社會期待的關鍵。因此,錫伯族群眾對弓箭工藝的延續不僅是民族工藝的社會需求,而是藝術背后蘊含著創造者的社會期許。其次,民族民間藝術對祈福避禍的社會期待是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本質性的催化,一方面祈福避禍是群體生活的本性,是最簡單的思想表露,另一方面祈福避禍是民族民間藝術在多民族區域能夠共存共榮的動力,毋庸置疑,趨利避害是超越藝術而統一于藝術個體本能。再者,民族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是不同民間藝術基本社會價值的統一,以民族祭祀和民族忌諱為主藝術表達是對民族民間藝術最好的對接回應。或者說,少數民族民間藝術的地域性對接是藝術社會情感價值的接納與融合。此外,地域性民族民間藝術同地域文化對應也是民間藝術地域性對接不可忽略的主旨之一[14]。
總之,西北少數民族民間藝術的地域性對接是民間藝術本能屬性和外在藝術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實現西北民族民間藝術的地域性對接,有助于推動民族民間藝術的文化效應和經濟效能的統一,有助于西北社會整體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