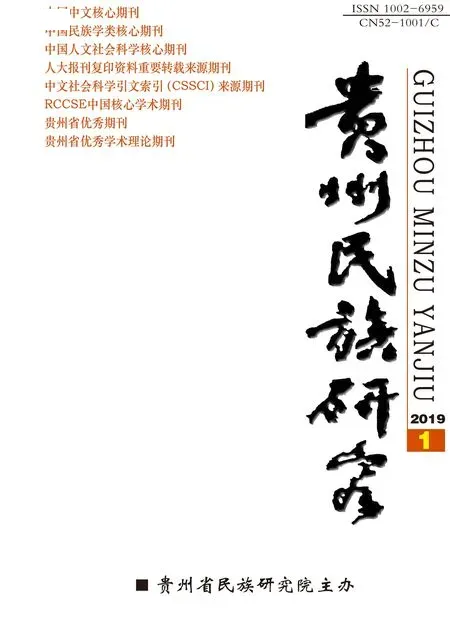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的習慣法透析
劉 輝
(中南大學 網(wǎng)絡學院,湖南·長沙 4100832;安徽警官職業(yè)學院,安徽·合肥 230009)
民族地區(qū)傳統(tǒng)經(jīng)濟治理同社會整體治理混同,使得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習慣法的運用同民族習慣法的社會管理如出一轍,比如,黎族群眾通常依據(jù)古老咒語詛咒偷盜行為,在集市交易中黎族群眾通常將自己農(nóng)產(chǎn)品放置到寨(村)頭,供路人自主選購的“拜貢”制度,就是源于黎族習慣法中宗教教義和鄉(xiāng)約寨規(guī)。換言之,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治理以民族習慣法為依據(jù),在治理中“法制經(jīng)濟”運行機制逐漸占據(jù)主導地位。此外,在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治理中少數(shù)民族群眾逐漸以樸素的市場交易規(guī)則約束著群體經(jīng)濟活動行為,調(diào)解著民族群眾之間的經(jīng)濟糾紛,并在民族習慣法的基礎上形成了完整的經(jīng)濟治理機制,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習慣法的透析成為探究民族地區(qū)傳統(tǒng)經(jīng)濟治理機制的窗口。因此,從民族地區(qū)傳統(tǒng)經(jīng)濟治理方式入手,以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習慣法源頭的運用和體現(xiàn)為依據(jù)透析民族習慣法體現(xiàn),成為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習慣法透析的應有之義。
一、習慣法在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治理中的具體運用
(一)基于非正式制度中自主管理的習慣法
民族習慣法在民族社會運行逐漸演化為潛移默化的,具有震懾力與強制力的非正式制度。在經(jīng)濟治理中民族習慣法的非正式制度影響力最為顯著,特別是以非正式制度中自主管理為主的經(jīng)濟治理成為民族習慣法在經(jīng)濟治理中的集中反映[1]。首先,基于自然界的水、樹木等資源的經(jīng)濟管理中民族群眾通過禁止性、懲戒性的習慣法進行治理。一方面通過宗教教義等民族習慣法使群體對自然資源的索取進行合理規(guī)范,比如,鄂倫春族群眾在樹木等公共資源的管理中,主張禁止砍伐幼苗,對于砍伐幼苗的行為處以納糧懲罰,部分鄂倫春族群眾受原始自然崇拜宗教詛咒觀念的影響,將公共林木砍伐治理同習慣法中的宗教懲戒關聯(lián),使民族公共資源治理逐漸法治化。另一方面,民族群眾在經(jīng)濟治理中規(guī)定了自然萬物的所有權。比如,涼山彝族習慣法以婦孺皆知的鄉(xiāng)約寨規(guī)明確規(guī)定自然萬物所有權歸畢摩所有,換言之,民族習慣法在經(jīng)濟治理中明確規(guī)定“產(chǎn)權”。其次,在民族群眾間的經(jīng)貿(mào)集市中民族群眾以內(nèi)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習慣法作為隱性經(jīng)濟治理的準繩,規(guī)范著民族地區(qū)的經(jīng)貿(mào)活動。比如,西北撒拉族等穆斯林群眾在經(jīng)濟治理方面受到以伊斯蘭教教義為主體的習慣法影響,在買賣交易中崇尚“誠實信賴原則”,堅持童叟無欺,在具體貨物流通中則潛在禁止豬肉等關聯(lián)貨物的流通,且在經(jīng)濟活動成為買賣雙方自主管理的具體反映。再者,以黎族“拜貢”、京族“寄賴”等自主管理的治理模式基本上都以民族習慣法的有機轉(zhuǎn)化為依托。
(二)基于信賴機制的約束性治理
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通常將宗教教義等民族習慣法內(nèi)化到群體意識形態(tài)當中,成為民族群體予以信賴的經(jīng)濟行為準則。換言之,民族習慣法在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主要以基于信賴機制的約束性治理為主。首先,源于民族宗教教義的習慣法以宗教法則約束著民族群體的經(jīng)濟行為,規(guī)范著民族群體的經(jīng)濟活動。時常通過宗教虔誠的踐行至民族群體的商貿(mào)活動當中,一方面民族宗教教義同自然崇拜、自然敬畏相關聯(lián),禁止商貿(mào)活動買賣特定物品,比如,滿族群眾在集市買賣中禁止流通狗肉,并且在長期的生活成為群體具有信賴性、約束性的習慣法治理機制[2]。另一方面,民族群體將宗教教義法則延伸到經(jīng)濟活動中,比如:維吾爾族等穆斯林群眾在經(jīng)濟活動中世代沿襲“誠實信用原則”。其次,民族習慣法在經(jīng)濟治理中通常將經(jīng)濟活動的法制化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習慣法的威懾力成為民族群體之間不斷加強經(jīng)貿(mào)活動的保障,比如,普米族群眾在氏族組織的影響下,氏族群體經(jīng)濟行為的規(guī)范以氏族家規(guī)等習慣法為主,經(jīng)濟活動的規(guī)范通常由族規(guī)調(diào)整,對于缺斤少兩的經(jīng)濟行為一般禁止其參與氏族喪葬活動,重者剝奪祭祀資格。再者,隨著中原王朝對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的管轄,以制定法為淵源的民族習慣法對經(jīng)濟活動治理也顯得尤為重要,比如,以部落首領為土司的民族管轄政策,將民族地區(qū)的經(jīng)濟管理同中央優(yōu)惠政策相結合,經(jīng)濟治理同政治信賴相關聯(lián),以中央王朝律令為主的習慣法對民族經(jīng)濟行為的約束也極為顯著。
(三)基于民族族長元老、的經(jīng)濟治理
民族地區(qū)的村寨族長、元老是民族地區(qū)社會治理的掌舵者,以族長、元老為中心的經(jīng)濟治理是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治理中習慣法運用的民族性濃縮。一方面族長、元老在經(jīng)濟活動中的存在與角色扮演折射著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治理的民族地域性特色。另一方面,以族長、元老為主體的經(jīng)濟治理映射著民族群體別具一格的社會組織體系。就民族地區(qū)習慣法在經(jīng)濟治理中運用而言基于民族族長、元老的經(jīng)濟治理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民族族長、元老是民族經(jīng)濟所有制形式的掌握者。一方面民族地區(qū)普遍存在政教合一的現(xiàn)象,以族長、元老為首的角色掌握民族地區(qū)生產(chǎn)資料、分配形式[3],比如,彝族“畢摩”在原始社會公有制階段掌握著經(jīng)濟成果的分配形式。另一方面,在氏族公有制經(jīng)濟治理中元老占有著絕對的經(jīng)濟主導權,比如,拉祜族村寨受“卡些卡列”制度的影響,在經(jīng)濟治理中“村寨頭人”有著較大的經(jīng)濟話語權。二是以族長、元老為主體的經(jīng)濟糾紛的化解,換言之,族長、元老掌握著經(jīng)濟糾紛的裁量權,比如,毛南族群眾經(jīng)濟糾紛則由專門糾紛化解者“匠講”(類似于元老)處理。三是族長、元老掌握經(jīng)濟治理的制裁權,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治理中元老掌握著絕對的制裁權,既能夠依據(jù)民族習慣法有效地規(guī)范民族經(jīng)濟行為又能較為合理地促進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的發(fā)展。
二、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習慣法的透析
(一)“自然敬畏”下的民族生態(tài)經(jīng)濟雛形
“自然敬畏”下的民族生態(tài)經(jīng)濟雛形是民族習慣法在經(jīng)濟治理中的現(xiàn)代化聚焦,是法制經(jīng)濟與生態(tài)經(jīng)濟的共同體。民族地區(qū)在生態(tài)經(jīng)濟的治理中通常以習慣法的信仰式延伸為主導,注重民族經(jīng)濟治理的制度化調(diào)控。就生態(tài)經(jīng)濟的治理而言,一是針對民族祭祀文化、圖騰文化、宗教文化忌諱下的捕獵等,民族群眾在長期的自然生活中逐漸形成了自然敬畏的發(fā)展理念,比如,藏族群眾忌諱對馬等動物的獵殺,特別是甘南等山區(qū)藏族群眾,忌諱集市買賣誘導下的過度狩獵。二是民族群眾對自然敬畏的民族心理延伸到習慣法的鄉(xiāng)約寨規(guī)中,通過賞罰懲戒的治理機制推動民族生態(tài)經(jīng)濟的發(fā)展。比如,鄂倫春族群眾在砍伐樹木、捕撈魚苗時禁止砍伐、捕撈幼苗,同時以寨規(guī)祖訓的形式鼓勵群眾開展“冬砍一棵、春植一株”的樸素生態(tài)經(jīng)濟[4]。三是鄂溫克族等少數(shù)民族在經(jīng)濟治理中通過習慣法的形式管理群體的砍伐、狩獵行為,禁止春季砍伐樹木,否則由“編戶”按照州律公開處罰。總之,“自然敬畏”下的民族生態(tài)經(jīng)濟雛形是民族習慣法中在生態(tài)領域的凝聚與折射。
(二)“糾紛化解”下的民族經(jīng)貿(mào)治理
“糾紛化解”下的民族經(jīng)貿(mào)管理是習慣法在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具體運用的基本體現(xiàn)。民族經(jīng)貿(mào)管理中的“糾紛化解”是習慣法視域下民族經(jīng)濟治理法制化的基本形態(tài)。就民族群眾經(jīng)貿(mào)糾紛化解的主體性而言,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糾紛的化解有內(nèi)外部之分,以村寨家族為主要形態(tài)的內(nèi)部經(jīng)貿(mào)糾紛化解的治理,一般由族長作為管理者進行經(jīng)貿(mào)糾紛化解。比如,毛南族群眾村寨以同姓群體為主,群眾之間“以物換物”的貿(mào)易糾紛化解基本上由“匠講”處理[5],對于缺斤少兩、質(zhì)次量差的糾紛則由“匠講”責令補足調(diào)換等,對于雙方動手糾紛則由“匠講”請“武相公”執(zhí)行鞭責。以不同民族之間的外部糾紛則由雙方元老、族長共同化解,在糾紛化解中先有彼此根據(jù)本部落族規(guī)詢問彼此的緣由,而后共同處罰,比如,侗族部分村寨在族人同其他民族群體之間的糾紛實行雙罰制,除按照族規(guī)處罰外,有錯者還要接受元老之間調(diào)解后的處罰,個別地區(qū)甚至要給元老一定的補償。從經(jīng)貿(mào)糾紛的嚴重程度而言,有四種糾紛治理機制。一是以元老、族長和專門民事糾紛調(diào)解者為主的化解機制,比如,涼山彝族群體之間的簡單物物交換糾紛一般由“畢摩”管理,而毛南族則由專門糾紛化解者“匠講”處理[6]。二是以元老會為主體的民主決策化解機制。以元老會為主體的經(jīng)貿(mào)糾紛化解在多數(shù)民族群體的發(fā)展歷程中均有體現(xiàn),比如,京族群眾對于柴木買賣之間的糾紛一般由元老會調(diào)解。三是借助行政力量的糾紛化解機制。明清以來民族地區(qū)普遍實行土司制度,以政教合一的土司成為民族地區(qū)最高的行政長官,對于群體間的經(jīng)貿(mào)糾紛則由土司裁決。四是對于復雜糾紛化解的“獸判”機制。民族地區(qū)經(jīng)貿(mào)糾紛的化解一般由民族習慣法化解,但是往往出現(xiàn)難以明顯裁量的糾紛,則由巫師等主持,通過概率性時間斷決糾紛,比如,彝族群眾在糾紛中通常利用“獸判”化解貿(mào)易糾紛。
(三)“懲戒機制”下的貨物流通
“懲戒機制”下的貨物流通是民族習慣法在經(jīng)濟治理中貨物流通領域的基本反映。基于懲戒機制下的貨物流通囊括民族習慣法的諸多方面[7]。一是在民族宗教教義中明確禁止特定貨物流通習慣法攝入,如東鄉(xiāng)族、撒拉族群眾在集市貨物買賣中禁止豬肉類的交易;壯族群眾禁止青蛙的捕殺與買賣。二是民族鄉(xiāng)約寨規(guī)中對特定貨物的流通與買賣的禁止,并且對違規(guī)者進行對應懲戒。如納西族群眾在村寨石碑中明確規(guī)定“禁止買賣尚未成熟的果實”,否則禁止參與宗祠祭祀。
(四)“調(diào)解機制”中的勞動糾紛治理
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治理中習慣法的蘊含成為維護民族經(jīng)濟秩序的壁壘。民族習慣法中以“調(diào)解機制”為樞紐的勞動糾紛治理是民族經(jīng)濟治理的基本體現(xiàn)。就民族地區(qū)社會經(jīng)濟體制而言,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多數(shù)處于原始公社階段,以個體家庭為主的私有制逐漸使得簡單雇傭勞動成為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活動的重要一環(huán)[8]。但是民族地區(qū)勞動關系起初受鄉(xiāng)約文化的影響具有互助的屬性,比如,怒族群眾中土司等通過“瓦刷”的形式開展簡易雇用勞動,佤族群眾則以“珠米“(富人)官覺克”經(jīng)濟剝削為主,在長期的雇用勞動中勞動糾紛成為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不可避免的現(xiàn)狀。“調(diào)解機制”為主要形式的習慣法以調(diào)解的形式進行勞動關系調(diào)整,避免雇主同群眾之間關系的破裂影響族群團結。在勞動關系調(diào)解中少數(shù)民族群眾通過習俗傳說,以倫理道德的準則維持群體內(nèi)部的雇傭關系。比如,壯族群眾通過道德神“布洛陀”的祖祠裁決化解勞動糾紛。京族的一般勞動糾紛則由“翁村”執(zhí)行處罰,村寨之間的勞務糾紛則由“嘎古”中的元老商議解決。
(五)“習慣機制”中的所有制形式
少數(shù)民族群眾久居邊疆、山區(qū),民族群體之間的漢化程度差異顯著。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民族地區(qū)仍然保留著原始公有制、農(nóng)奴制等形式。民族習慣法在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以其獨特的非制度性規(guī)制,規(guī)定了民族經(jīng)濟治理的根本所有制。比如,怒江傈僳族在經(jīng)濟所有制形式方面大體包括個體私有、家族共同所有、家族或村寨公有等形式。隨著農(nóng)產(chǎn)品和手工藝品的個體私有的逐漸擴大,以族群內(nèi)部協(xié)作為主要形式的“伙有共耕制”逐漸成為傈僳族經(jīng)濟治理中所有制形式的基本體現(xiàn)[9]。赫哲族群眾在靈物崇拜和家長制的習慣法靜態(tài)引導下,在經(jīng)濟治理中所有制基本以“氏族制”為主,在狩獵中由“勞德瑪發(fā)”領導,崇尚集體所有制。在漢化程度較高的民族地區(qū),基本上形成了以封建地主階級、奴隸主所有的經(jīng)濟治理體制。比如,阿壩羌族地區(qū)在食鹽的流通治理中無論是土司制還是其他地主階級都以“關鹽店”形式進行所有制管制。
三、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習慣法的源頭
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治理中習慣法是民族社會法意志形態(tài)的體現(xiàn),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治理中習慣法的自然存在以民族群體喜聞樂見的宗教教義、鄉(xiāng)約寨規(guī)等為源頭[10]。換言之,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的習慣法是民族地區(qū)傳統(tǒng)經(jīng)濟習俗、民族宗教教義、民族鄉(xiāng)約寨規(guī)、家規(guī)族訓等傳統(tǒng)民族習慣法的總和。所謂民族傳統(tǒng)經(jīng)濟習俗即民族地區(qū)始終沿襲的經(jīng)濟活動習俗,比如,撒拉族等穆斯林群眾童叟無欺的誠信原則在經(jīng)濟治理中始終作為法律準繩。所謂民族宗教教義是民族習慣法源頭的重要組成,在經(jīng)濟活動中民族群體通常受民族宗教教義的引導。比如,藏族群眾忌諱對馬等動物的獵殺,特別是甘南等山區(qū)藏族群眾,忌諱集市買賣誘導下的過度狩獵。所謂民族鄉(xiāng)約寨規(guī)、家規(guī)族訓等是民族習慣法的特定性體現(xiàn),比如,仡佬族崇尚祖先崇拜,在鄉(xiāng)約寨規(guī)、家規(guī)祖訓中明確規(guī)定:“對于神樹附近區(qū)域進行封山,禁止砍伐、放牧。”使習慣法在經(jīng)濟治理中的功能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總之,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治理中習慣法的源頭無外乎以宗教教義、社會習俗等民族非制度性為規(guī)范。
民族習慣法在經(jīng)濟治理中發(fā)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方面民族習慣法在經(jīng)濟治理中的信仰上升是民族地區(qū)法制經(jīng)濟的建設內(nèi)化與中心,并成為規(guī)范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活動的行為底線和思想準則[11]。另一方面,民族習慣法對經(jīng)濟治理的原則性確立,有效地規(guī)范了民族市場經(jīng)濟活動,特別是自然敬畏機制下民族經(jīng)濟活動的抑制,推動了民族地區(qū)生態(tài)經(jīng)濟的發(fā)展,使民族習慣法治理中經(jīng)濟領域良性機制逐漸確立,成為引導民族經(jīng)濟發(fā)展的牽引力。毋庸置疑,民族經(jīng)濟治理中習慣法逐漸將“法制經(jīng)濟”與“生態(tài)經(jīng)濟”以意識形態(tài)的形式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