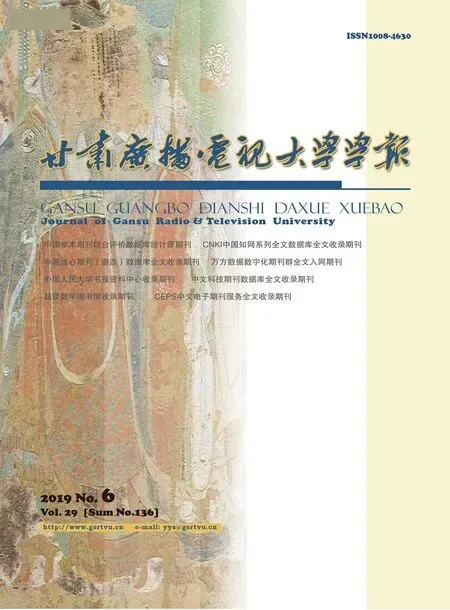論胡適對儒家思想的踐行
張小娟
(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山東濟寧 273100)
胡適不僅是我國白話詩的開創者,文學革命的領導者,在學術上也有不小的貢獻。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在中國古代擁有不可撼動的地位,但到五四之際,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爆發,儒學的地位開始被顛覆。在這場用自由民主思想推翻封建儒家思想的運動中,胡適既是倡導者也是實踐者。他支持“打孔家店”[1]763,反對儒學獨尊。但他并非要打倒儒學,而是以一個真正的儒者身份去改造儒學,給儒學注入時代活力,使其更好地發展。并且,在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動中,他也時刻以儒家的優秀思想勉勵自己,并時刻踐行。
一、文學觀念中蘊含的儒家思想
(一)發展:“歷史的文學觀念論”
胡適于1917年1月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著名的“文學八事”,得到了陳獨秀、錢玄同等人的支持,很快在國內掀起了文學革命。文學革命必然從文學的載體,即語言文字開始。胡適提出“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他認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2],即白話文學。他從歷史發展的眼光出發,指出白話文學才是中國文學的正宗,必須廢除已落伍于時代的文言,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文學要隨時代不斷進步,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種因時而變的思想,早在先秦時期,孔子就已經將之付諸實踐,胡適對儒學的改造便是這一思想的體現。正如胡適在《說儒》中指出的,孔子“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擴大到那‘仁以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國遺民的柔順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進取的新儒”[3]。除了孔子,師從荀子的李斯,也倡導歷史演化的觀念。胡適在《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一書中指出:“李斯的建議中的主要思想是根本反對‘以古非今’‘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我們研究了《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的思想,應該可以明白當時思想界的幾個重要領袖確是相信歷史演化的原則。”[4]他高度肯定李斯等人對“不師今而學古”的反對態度,認為這是值得后人敬仰和學習的。可見,胡適提出“歷史的文學觀念論”的目的,也正類似于當時孔子所做的“振衰而起儒”的大事業,他旨在改造中國舊文學,借著文學革命,構建與時代相統一的中國新文學。
(二)尚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儒家思想是講求“尚用”的,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一書中評論孔門文學時,就明確指出其“尚用”的特征。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指出中國兩千年文學的弊端:“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1]54“‘死文言絕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1]56以歷史的眼光看,文言的時代已成過去,使用文言教學,只會讓教育陷入僵局,日益與現實脫軌。現在所需的教育是能與現實結合,對社會現存問題有指導作用的實用型教育,而要改革教育必然要先從能表達思想的文字開始,要用有生命力的文字——白話,去替代文言,創造出有價值的活文學。胡適這種倡導實用的思想雖然受杜威的實驗主義影響,但很大原因是因為杜威的“實驗主義”與儒家思想之間存在共通點。正如格里德所說:“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上,儒學家的反應和實證主義者的反應又是十分接近的”,“胡適覺得最有意義的也正是實證哲學中那些與他所繼承的儒家基本傾向十分接近的成分。”[5]52在某種程度上,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可以說是儒家“尚用”思想影響下的產物,胡適所要創造的有價值的活文學,就是“尚用”的文學,這樣的文學才能輸入新思想,拯救中國落后的教育現狀,從而為政治建設打開通道。
二、國故整理中顯露的儒學態度
(一)國故整理中高度肯定儒家的自省意識
在自省中求發展是胡適在國故整理過程中一直秉持的態度。胡適認同孔子“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觀點,稱這是“一個圣人的模仿”,并指出“一個民族也和個人一樣,最肯學人的時代就是那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6]117。孟子“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的觀點也影響了他。他認為:“真誠的反省自然發生與真誠的愧恥。”[6]121真誠的反省才能認識到自身的不足,認識到不足才能找到努力的方向,并通過學習借鑒別人的長處彌補自己的不足,在此過程中才能重拾信心。胡適希望在國故整理中反省落后文化的弊端,同時也想找回繼續前行的文化自信。1923年,他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倡導大家整理國故,并對國故和國學做出了界定:“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7]研究過去的歷史文化,我們理清“國粹”和“國渣”。“國粹”能讓我們在面對西方文化的同時堅守民族自信心,不至于走向“民族虛無主義”;“國渣”能讓我們知道自身的不足所在,促使我們吸收和引進新思想,不至于成為“民族中心主義”。胡適在《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中談到文學進化的第三層意義時指出,因為人類“守舊的惰性”[2]75,對于前一個時代留下的無用紀念品,我們沒有及時清除,這些東西如果繼續留存,會變成前行道路上的阻礙。因此胡適整理國故要做的就是清除這些無用的紀念品。只有理清中國的思想文化,充分了解阻礙進步的源頭,才可以逐步做出改變。整理國故是建構新文化的一部分,正如耿云志在《胡適全集》第1卷序言中指出的“為了改造舊文化,創造新文化,既需要引入新觀念、新學理,也需要總結既往的文化遺產”[8]。胡適秉持自省的態度,一心致力于國故的整理,就是要讓大家在反省中認清自身,同時也要帶著信心去建構新文化。
(二)國故整理中充分重視儒家文獻的價值
雖然胡適當時反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儒學,主張“充分世界化”,但他在整理文獻時并沒有摒棄儒家文獻,他放眼于各家思想、各種體裁,“重估價值”。有研究者指出,胡適“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的一系列實踐揭示了“現代中國文藝復興”的一個基礎條件:“人文情感和理性精神的全面復蘇”[9],這個觀點與胡適所倡導的這一運動的內涵也是相契合的。胡適曾指出:“此一重生的產物帶有可疑的西方的外貌。但是,刮掉其表面,你便會發現,它的構成要素本質上是中國的根柢,因大量的風化與腐蝕才會使得重要處更加清楚——由于接觸新世界的科學與民主的文明,使中國的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復活起來。”[10]251而此處胡適所指的人文主義與理性主義,在孔孟思想和程朱理學中皆有涵蓋。他后來也一再坦言:“就全體來說,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中,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我對十二世紀‘新儒學’的開山宗師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11]可見,正是因為他深知儒家思想的價值,在國故整理時才未忽略儒家文獻。
三、自由民主思想中潛在的儒家底蘊
(一)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儒家自由主義
胡適主張的自由主義,即他所倡導的“健全的個人主義”,“第一是充分發展個人的才能”,“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6]7,并不是只顧個人利益的為我主義。在《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一文中,胡適指出:“‘自由’這個詞,并不是外面來的,不是洋貨,是中國古代就有的。”[6]17孔子就是自由主義的先驅。孔子的自由主義思想主要體現在教育方面,胡適高度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指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學,將人看作是平等的”[12]。后來胡適在美留學期間,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廣泛接觸,激活了他心中深埋的儒家自由思想的因子。他認為要從兩個方面去發展人的個性,“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系,負責任。”[1]614并將個人的個性自由與國家命運聯系起來,指出沒有自由獨立人格的社會國家,沒有改良進步的希望。這些思想與儒家思想都有共通之處。
(二)儒家人道和中庸思想下的容忍與自由
胡適一生堅持容忍與自由,這種堅守離不開儒家思想對他的影響。胡適兒時父親便離開了人世,與寡母相依為命,母親身上體現出來的容忍與平和,對他的一生都有重要的影響。他說“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13]在他的婚姻上,這一點體現得最為突出。他雖接受了新學,成為了出國留洋的高材生,但對于母親為他包辦的婚姻,猶豫過后,最終體諒和寬容還是占據了上風。他帶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的頭銜,回家與母親為他選擇的鄉村半文盲女子結了婚,并與其相伴終生。儒家的人道觀念,從母親身上學得的中庸思想,是胡適接受這場包辦婚姻的重要原因。但作為包辦婚姻的受害者,胡適深知這種婚姻觀念為男女雙方帶來的痛苦,故此他倡導婚姻自由。他在《美國的婦人》一文中指出“美國的結婚,總算是自由結婚;而自由結婚的根本觀念就是要夫婦相敬相愛,先有精神上的契合,然后可以有形體上的結婚。”[1]628但他也反對不近人情的離婚,他斥責一些留學生接觸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之后,一回國就馬上離婚,這對未接受西方新學的女方來說是不人道的。這并非是胡適對自己接受包辦婚姻一事的開脫,而是儒家人道和中庸思想在他身上的體現。在政治上,胡適也一直認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說:“因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可說了。至少在現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種互相容忍的精神。”“現代的自由主義,還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6]15可見不論是在政治上還是生活中,儒家的人道和中庸觀念,都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伴隨他一生。
儒學滋養了胡適,他也為儒學的長足發展做出了貢獻。他敢于反省,敢于汲取,有勇氣批判,更有能力建構。無論在他的生活還是工作中,儒家思想都已內化為一種修養外顯于他的行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