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國家而于身無所利”的顧憲成
樊樹志
晚明史上轟動一時的東林書院,創建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禁毀于天啟五年(1625),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卻在當時社會激起巨大的反響。康熙《東林書院志》寫道:“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虛己悚神,執經以聽,東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它的創建者顧憲成因此名揚天下,誹謗之聲也如影隨形,東林書院也被卷入政治斗爭的漩渦。由于政治立場不同,當時人對它的看法大相徑庭,毀譽交加。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趙南星給顧憲成寫神道碑,為之鳴不平,“其于名教是非、社稷安危之計,無不挺身力爭”,招來的卻是罷官;居家講學,“非孔孟之道不談也,善無巨細無不為也,行無隱顯無不兢兢也”,招來的卻是政治誣陷。趙南星感嘆道:“講學者皆欲忠國家于身無所利,倘亦可以無苛呰乎!”

顧憲成(1550-1612)
一、“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
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常州府無錫縣人,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初七生于無錫涇里。年輕時游學于唐荊川、薛方山兩先生之門。萬歷四年應天鄉試第一名中舉,嶄露頭角。他的同鄉兼志同道合者高攀龍為其所寫的行狀,是最有價值的顧憲成傳記,談及他的抱負:“當是時,先生名滿天下,其為文章斟酌古今,獨辟乾坤,學者宗之如山于岳,如川于海。而先生退然謂:此非吾人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于微析窮探,真知力踐,自余皆所不屑矣。”清晰地表明,他的安身立命之處并非文章虛名,而是傳統經學與當時流行的程朱理學,窮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他一出場,就為自己立下極高的標準。
萬歷八年二月,他會試中式第二十名;三月殿試,得中第二甲第二名,賜進士出身,授戶部主事。時年三十一歲。顧憲成與同科進士魏允中、劉廷蘭,并稱榜中三解元,以名世相期許,以道義相琢磨,慷慨激昂議論朝政,對處于權力巔峰的內閣首輔張居正,有所譏刺。張居正頗為忌憚,對主持會試而成為“三解元”座師的申時行說:貴門生有“三元會”,你知道嗎?每日都在評騭時事,居然華袞斧鉞一世。
顧、魏、劉三人確實是在評騭時事,鑒于時事日非,三人相約上書內閣次輔申時行,請他出面匡救。在《上申相公書》中,初涉政壇的新科進士鋒芒畢露。開篇就點明主題:“竊聞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君子非自能在朝也,有君子之領袖為之連茹而進也。今寧無君子之領袖乎?”繼而批評申時行無所作為:“老師(指申時行)之于首揆(指張居正),將一切聽而順之歟?吾懼其為隨抑逆而挽之歟!”字里行間流露出對于現狀的不滿情緒,希望申時行有所作為。三名新科進士雖有別具一格的眼光,卻過于書生意氣,忽視官場的政治規矩。申時行是張居正一手提拔上來的,勢必與張居正保持高度一致,根本不可能出面“匡救”。
申時行豁達大度,并未為難三名小人物。《上申相公書》的過激言詞沒有帶來麻煩,他們的鋒芒依然畢露。萬歷十年,張居正舊病復發,舉國上下惶惶不可終日,達官貴人紛紛齋醮祈禱,高級官僚帶頭,中層官僚仿效,放棄本職工作,沉迷于撰寫祈禱表章,奔忙于廟宇道觀之間,忙得不亦樂乎。再三為之設醮祝厘,手捧香爐,拜讀表章,長跪于烈日之下。顧憲成看不慣這種獻媚諂諛行為,特立獨行,冷眼旁觀。高攀龍《涇陽顧先生行狀》寫道:“江陵(張居正)病,舉朝若狂,為禱于神,先生獨不可。同官危之,代為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同僚出于好意,代他在祈禱表章上署名,顧憲成以為奇恥大辱,快馬加鞭趕去,親手抹去自己的名字,不愿同流合污。
萬歷十一年,顧憲成請假回鄉,研讀《易》和《春秋》。萬歷十四年七月,假滿北上,出任吏部主事,依然特立獨行。他拜謁內閣輔臣王錫爵,兩人有一段絕妙的對話。
王錫爵問:“君家居且久,亦知長安(指北京)近來有一異事乎?”
顧憲成回答:“愿聞之。”
王錫爵說:“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為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為是。”
顧憲成不以為然:“又有一異事。”
王錫爵問:“何?”
顧憲成說:“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為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為是。”
兩人相與大笑而起。
這段對話見于顧與沐《顧端文公年譜》。高攀龍《涇陽顧先生行狀》也記載了這一對話,文字大同小異,“廟堂”寫成“內閣”,“外人”寫成“外論”。一個持“外論”立場,一個持“內閣”立場,政見的歧異顯而易見。
官場猶如江湖,各有各的規矩。顧憲成自視清高,無視政治規矩,使得他很難在官場立足。萬歷十五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主持京官考察工作,把工部尚書何起鳴列入“拾遺”名單,引起內閣輔臣不滿,給事中陳與郊等人,仰承內閣風旨,攻擊辛自修,導致辛自修與何起鳴同時罷官。對于這種不分是非,不辨君子小人的做法,顧憲成慷慨陳詞,批評內閣首輔申時行、次輔許國與王錫爵,“以智角智,以力角力”。《毗陵人品記》一語道破,由于“語侵執政”,顧憲成因“肆言沽名”,降三級調外任—補湖廣桂陽州判官添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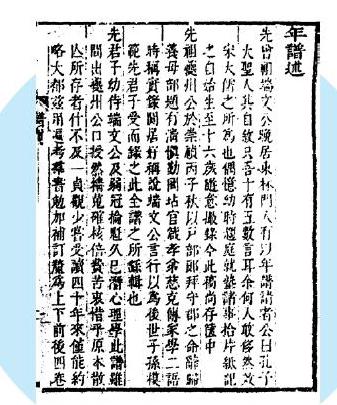
《顧端文公年譜》 〔明〕顧與沐記略
此后,他調任處州府推官、泉州府推官,政績卓異,以“天下推官第一”,于萬歷二十年提拔為吏部主事、吏部員外郎,再度回到權力中心。“三王并封”之議一出,顧憲成與首輔王錫爵的政見分歧發展為正面沖突。以后在考察京官、會推閣臣時,多次與王錫爵意見相左,遭到革職為民的懲處。萬斯同《明史·顧憲成傳》寫道:“(顧)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帝悉不報。”可見顧憲成既得罪了首輔,又違背了帝意,革職為民是不可避免的。
顧憲成的理想是構建清明澄澈的政治局面,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海瑞為楷模。萬歷十四年,海瑞出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本著一貫作風—潔人先潔己,要整肅百官必須先整肅負有監察權的御史,嚴厲約束自己管轄的御史,帶動南京官場風氣大變。陳建、沈國元《皇明從信錄》說:“每下一令,不數語洞中情弊。而都人涂傳巷誦,自大僚至丞郎,無不凜凜奉法。其市物必以價,無敢劇飲為大宴樂,雨花(臺)、牛首(山)、燕(子)磯諸處,官舫游屐頓絕,往時城社豪猾皆屏息莫敢出。”大擺筵席,公款游覽的風氣頓時消失。
南京提學御史房寰,人品卑劣,凌虐士人,貪污賄賂,恣睢狼藉,人稱“倭房公”。他深知海瑞懲貪不遺余力,害怕自己遭到嚴懲,惡人先告狀,詆毀海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圣自賢,損君辱國”。吏部辦事進士顧允成(顧憲成的弟弟)與同僚聯名上疏,抨擊房寰為代表的邪惡勢力,義正詞嚴地說:“臣等自十余歲時即聞海瑞之名,以為當朝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能及者。及稍知學,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大有功于宗廟社稷,垂之千萬年不磨,蓋從萬死一生中樹節于我朝廷者。”至于房寰,早已臭不可聞,浙人每談及者,無不掩鼻,視若臭穢。顧允成等大聲疾呼:“一海瑞不足惜,正人有如海瑞者相繼而指為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寰尚不足畏,邪人有如房寰者相繼而妨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明確無誤地倡導以海瑞這樣的正人君子為榜樣,重建符合儒家倫理的政治局面。顧氏兄弟的理念是一致的。顧憲成主張像海瑞那樣反對“鄉愿”,慨乎言之:“鄉愿之同流合污,從而不倡者也。大家如此,一滾隨去,凡事都不做頭,既以忠信廉潔媚君子,而其同流合污又不為倡而為從,則君子亦寬之而不責矣;既以同流合污媚小人,而忠信廉潔又不為真而為似,則小人亦安之而不忌矣。”
令人不解的是,皇帝在慰留海瑞,切責房寰的同時,以“出位言事”為借口,處分了顧允成等三名進士—“革去冠帶,退回原籍”。如此有失公允的處分,激起正直官員的強烈反彈,對于“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頗有微詞,皇帝固執己見,寸步不讓。
顧憲成、顧允成兄弟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姿態,與政治現狀格格不入,顯得不合時宜,革職為民是遲早的事。“君子之道日消”難以避免,“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的理想,漸行漸遠。
二、“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
萬歷二十二年九月,革職為民的顧憲成回到無錫家鄉,丟掉了烏紗帽,返歸一介書生本色,沉浸于五經四書與濂洛關閩之學,傾心講學著述。讀書人仰慕他的道德學問,紛紛前來求學,于是有“同人堂”的設立。參與講學的有宜興吳達可,武進錢一本與薛敷教,金壇于孔兼等。學生中有的后來成為知名人士,如繆昌期、馬世奇、張大可等。一時盛況空前,論者以為“程朱之門所未有”。簡陋的“同人堂”難以滿足日益增多的求學者,顧憲成有意復興宋儒楊時的東林書院。萬歷三十二年,在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的支持下,以民間集資的形式,先后修建道南祠(祭祀楊時的祠堂)、精舍、依庸堂、麗澤堂,這就是日后聲名遠揚的東林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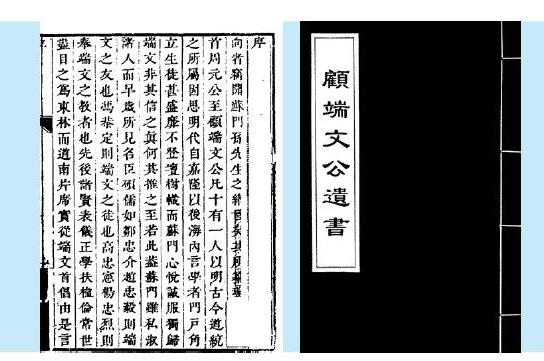
《顧端文公遺書》 〔明〕顧憲成撰
顧憲成在弟弟顧允成及摯友高攀龍、錢一本的輔佐下,把東林書院這個民間學校辦得有聲有色。趙南星寫道:“其學唯就孔孟、宋諸大儒之書闡明之,溫故知新,不離乎區蓋之間。高明者聞而可入,始學者聞之不駭。久之,白當道為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講學其中,東林之名滿天下矣。”
顧憲成引用曾子的話“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作為東林書院的宗旨。他解釋道:“自古未有關門閉戶,獨自做成的圣賢,自古圣賢未有離群絕類孤立無與的學問……群天下之士講習,則天下之善受而為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天下矣。”東林書院的愿景,以繼承孔孟程朱的學脈為己任。高攀龍把東林書院的日常生活概括為六個字:讀書、靜坐、會友,與“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一致的。每個人都下功夫讀書、靜坐,到了互相切磋時,才可以收到以友輔仁的效果。
東林書院的講學活動,稱為講會,每月一次小會(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大會(春季或秋季)。屆時吳越及其他各地士人紛至沓來,蔚為壯觀。東林書院的小會大會,究竟議論什么呢?某些學者以為是“議論朝政,品評人物”,其實不然。顧憲成起草的《東林會約》明確規定:“每會推一人為主,主講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即有所見,須俟兩下講論已畢,更端呈請,不必攙亂。”很顯然,東林書院諸君子聚在一起,并非議論政治,而是在交流研讀四書的心得,由一人主講,然后討論,互相切磋,與今人的想象相去甚遠。
《顧端文公遺書》收錄了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課的講義—《東林商語》,通篇都在探討《論語》《孟子》的要義,向學生講解自己的心得。試舉一例如下:甲辰年(萬歷三十二年)共十則,全是關于《論語》某一章的闡釋。第一則是:“《論語》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顧憲成闡釋與一般經學家截然不同:“細玩此二條,圣人應是重有所感而發。蓋當時人見孔子與群弟子講于杏壇之上,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的,卻囂然自以為伶俐。見孔子汲汲皇皇,忘寢忘食,略無休暇,多嗤其勞苦,至以戮民擬之。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卻飄然自以為撇脫。曾不知迂拙者極是穩當,伶俐者反落險途;勞苦者到底安閑,撇脫者竟何歸著。”為了說明這些高深的道理,他用生動活潑的語言向學生解釋:“人生天地間,日子不是胡亂度的,屋不是胡亂住的,飯不是胡亂吃的,朋友不是胡亂搭的,話不是胡亂說的,事不是胡亂做的。這個心,極靈極妙,不是胡亂丟在一邊的。”
顧憲成為東林書院制訂的院規明確告誡書院同人,不得“評有司長短”“議鄉井曲直”,意思是,不可以在書院中評價政府和官員的好壞,議論家鄉市井的是非。他把社會上流行的作風蔑稱為鄙、僻、賊、浮、妄、怙、悻、滿、莽,要眾人摒棄這九種卑劣習氣。具體說來:“鄙”指的是比昵狎玩;“僻”指的是黨同伐異;“賊”指的是假公濟私;“浮”指的是評有司長短,議鄉井曲直,訴自己不平;“妄”指的是談論曖昧不明、瑣屑不雅、怪誕不經之事;“怙”指的是惡人之言巧為文飾;“悻”指的是對眾人指責,致其難堪;“滿”指的是問答之間意見偶殊,動輒沮抑,使之有懷而不展,有激而不平;“莽”指的是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聽途說,略不反求。
天啟初年主持東林書院工作的吳桂森,繼承顧憲成的既定方針,把上述院規具體化,特別強調兩點。其一是“絕議論以樂時”:“自今談經論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談,有問不答,一味勤修講學,以期不負雍熙,是今日第一時宜也。”其二是“屏俗風以安分”:“夫布衣聚會,既無馬腹之鞭,居肆講求豈堪蠅營之聽!故愿會中一切是非曲直、囂凌垢淬之言,不以聞此席。至于飛書、揭帖、說單、訴辯之類,不以入此門。”
由此可見,以往風行一時的說法—東林書院講習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云云,便有點不著邊際了。
三、“虛和閑止,不關世事”
錢謙益少年時代曾經跟隨父親到東林書院拜訪顧憲成,以后又和其子顧與亭、顧與沐交游。在他心目中,顧憲成的印象竟然如此:“端文(顧憲成)為人,虛和閑止,不關世事,凝塵委衣,危坐終日。”這種印象與人們的臆想截然不同,卻是耳聞目睹所得的真相。吳亮為顧憲成立傳,描述顧憲成在東林書院的生活就是如此:“杜門卻軌,潛心理學”,“與同志闡繹濂洛正脈,其說以性善為本體,小心為工夫。歲有札記,沉潛粹密,與《讀書錄》相表里”。與顧憲成一起在東林書院講學十幾年的高攀龍,對他潛心理學給予高度評價:“自孟子以來得文公(朱熹),千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顧憲成),又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萬歷二十二年)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如鷙,殆幾于無我矣。”高攀龍說顧憲成把全部精力用之于理學,達到無我的境界,是君子退居林下的真實寫照。顧憲成為英年早逝的弟弟顧允成寫傳記,突出的也是這一點:“每歲一大會,每日一小會,弟進而講于堂,持論侃侃,遠必稱孔孟,近必稱周程,有為新奇險怪之說者,輒愀然改容,辭而卻之。”

《明史》(全八冊)〔清〕萬斯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
東林書院的另一位導師錢一本,罷官回鄉后,回歸學者本色,“杜門絕跡,不入公府”,“生平無他玩好,終日兀坐,手不停批”。紀曉嵐為錢一本著作寫提要,說:“東林方盛之時,(錢)一本遂與顧憲成分主講席,然潛心經學,罕談朝政,不甚與天下爭是非,故亦不甚為天下所指目。”這是東林君子的共同心態。
言官一再彈劾前任內閣首輔王錫爵,將趙南星、顧憲成、高攀龍、薛敷教等正人君子斥逐一空,至今海內扼腕。主張起用廢棄諸臣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令當權大佬不能等閑視之。為了應付輿論,朝廷宣布起用顧憲成。
萬歷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顧憲成接到任命:“顧憲成起升南京光祿寺少卿添注。”顯然是執政者敷衍輿論的對策。顧憲成罷官之前先后擔任吏部驗封司、考功司、文選司的郎中,握有人事權;而光祿寺是掌管宮廷膳食的機構,何況又是南京的光祿寺,連宮廷膳食的職掌也沒有,基本是一個“投擲閑散”的虛職。顧憲成征求書院諸同志意見,有的以為“宜行”,有的以為“宜止”。他自己說:“仕宦寧退毋進,吾衰矣,當從其退者。”這一任命畢竟是以皇帝圣旨形式發出的,必須誠懇地向皇帝表明態度,他為此寫了辭呈—《奏為衰病交侵懇恩休致事》:
臣以疏庸,重負任使,頃蒙皇上簡錄,誼當竭蹶而趨。唯是臣年六旬,兩目昏花,兩耳重聽,起居尚須扶掖,何能勉效馳驅?反復思之,與其冒昧而進,孰若審量而退;與其出而顛沛,孰若處而茍全。伏乞敕下該部查臣別無違礙,容令休致,臣愚幸甚。
婉言推辭的理由是“衰病交侵”“兩目昏花”“兩耳重聽”“起居尚須扶掖”,深層的原因則是,他不愿放棄蒸蒸日上的東林書院事業,不愿放棄潛心于理學的追求。在給摯友李三才的信中,他吐露了內心的想法:“東林之社是弟書生腐腸未斷處,幸一二同志不我棄,欣然其事,相與日切月磨其中,年來聲氣之孚漸多應求,庶幾可冀三盆,補緝桑榆,無虛此一生。”
吏部不接受他的推辭,再三催促,并且寬限赴任日期。顧憲成再次上疏,情詞懇乞地寫道:
獨計臣少不自愛,逾壯便衰,行年六十,目昏耳聾,老態盡見,已不足效馳驅鞭策。況今病入膏肓,糾纏無已,奈何尚欲僥幸于萬一也。且夫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亂于不問,以自便其身圖,臣之所大恥也。
這段話值得細細推敲,前半段是對朝廷的陳情,實在是身體有病,難以擔當重任;后半段是為自己辯白,并非不顧國家安危理亂,而自便其身。其實流露的內心獨白,恰恰是“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他給李三才的信吐露自己推辭的原因:“憑軾而觀時局,千難萬難,必大才如丈(指李三才)卓識如丈,方有旋轉之望。如弟僅可于水間林下藏拙耳,出而馳驅世路,必至僨事。”所謂“水間林下藏拙”,就是“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極好的注腳,挑明了自己的真實心態。在《與孫柏潭殿元書》中,他把自己描繪成不問門外是非的隱士:“弟向來筑室枯里中,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寢,其意以詩書為仇,文字為贅,門外黑白事寂置不問。”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把自己說成是桃花源人:“予抱疴涇曲,日坐臥斗室中,酬應都罷,幾如桃花源人,不復聞人間事。”
“幾如桃花源人”,并非顧憲成的矯飾或夸張,而是真實寫照。東林君子都有類似的況味。同在書院講學的高攀龍,給老師趙南星寫信,一再流露入山閉關、不問世事的心境:“龍今年自東林會期外,即入山閉關,以學問宜靜,以衰年宜靜。此時山中人,不一味靜默,非學也矣”,“世局如此,總無開口處,總無著心處,落得做個閑人,自家性命自家受用而已”。入山閉關的閑人,幾如桃花源人,含義并無二致,這與一般人對于顧憲成、高攀龍的印象,似乎相去甚遠,恰恰是真實的另一面。
四、“不肖獨何忍心而默默”
顧憲成自況為桃花源人,是對政治時局極度失望的回應—“門外黑白事寂置不問”。正如高攀龍所說:“世局如此,總無開口處,總無著心處,落得做個閑人。”但是受儒家政治倫理熏陶的士大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情懷,難以割舍,要真正做個桃花源人談何容易!他晚年卷入關于李三才的政治紛爭,便是一個明證,既義不容辭,也迫不得已。
萬歷三十七年,李三才升任南京戶部尚書,又被提名為都察院都御史。此時適逢內閣缺人,有些官員建議,內閣不當專用詞臣,應該參用外僚,意在薦舉李三才。此人既有才干又有聲望,在漕運總督淮揚巡撫任上政績卓著,抨擊礦稅太監貪贓枉法導致民怨沸騰,毫不留情。這樣的輿情,顯然觸犯某些閣部大佬的權益,于是策劃了一場詆毀李三才的運動。
工部郎中邵輔忠率先發難,攻擊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羅列貪、偽、險、橫四大罪狀,說什么“藉道學以為名,依豪賢以立腳,或無端而流涕,或無故而感慨,使天下士靡然從風,乘機躁進者愿依其幕下,感時憂世者誤入其套中”。聳人聽聞地揚言:“一時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勢孤,黨與日甚。”字里行間影射李三才與東林書院的顧憲成“結黨”。浙江道御史徐兆魁與之一唱一和,誹謗李三才“結黨營私”,“年來是非日以混淆,攻訐莫之底止,主盟挑釁,三才乃其戎首”。
清者自清,是非自有公論,李三才連上四本奏疏,主動向皇帝請求辭去官職,杜門謝罪。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兆舒、彭瑞吾,南京給事中金士衡,相繼為李三才辯白。內閣大學士葉向高也向皇帝陳言:李三才已經杜門謝罪,為漕運大政考慮,宜速定去留。皇帝不表態,誹謗者愈發囂張,一些別有用心的言官錢策、劉時俊、劉國縉、喬應甲、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等,接二連三彈劾李三才。正直的言官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學遷等,奮起反駁,為李三才辯護,雙方激烈交鋒。正如萬斯同《明史》所說:“朝端聚訟,迄數月不已。”
身處東林書院的顧憲成目睹這場聚訟,難以抑制心中不平,一反桃花源人的常態,寫了私人信件,寄給內閣首輔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為李三才講幾句公道話,希望兩位實權人物能夠平息持續數月的“朝端聚訟”。信件的主旨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李)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學力行,為古醇儒,當行勘以服諸臣心”;二是“李公在淮揚,能制稅珰(礦稅太監)不敢動,安民弭亂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這其實是很正常的輿情反映,也是人之常情,況且是私人信件,并非公文。孰料被別有用心的官員抓到口實,誣陷顧憲成以下野官員身份,插手朝廷政務,可見東林書院企圖“遙執朝政”。
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為了搞臭顧憲成,搞臭東林書院,無中生有地說:“今日天下大勢盡歸東林矣……東林之勢益張,而結淮脅秦,并結諸得力權要,互相引重,略無忌憚。今顧憲成等身雖不離山林,而飛書走使充斥長安,馳騖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奪之權盡歸其操縱。”
工部主事沈正宗十分仗義執言,顧憲成等僻處鄉間書院,“一味講學,反罵醉生夢死”,“今隱身不忘報國,卻以為罪案矣”,“今一閣部書,便‘遙制國事,彈射不休矣”。
禮部主事丁元薦針對“遙執朝政”的誣陷,據理反駁:一個遠在江南無錫的民辦書院,何以能夠遙控朝廷政治?“夫使東林果操天下權重之勢,則長安諸縉紳何不舍要津而趨山林,而乃操戈秣馬以向攻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僻處山林可以遙執朝政,那么京都袞袞諸公為何不退處山林呢?
顧憲成在寫信之前,已經預料到可能帶來負面影響,為了表達對于李三才人品才干的敬仰,在所不顧。他和友人談及寫信的緣由:李三才由于撥亂反正,“外犯權相,內犯權閹,死生禍福系之呼吸,并不稍顧”,“旁觀者遂群起而求,多吹索抨彈,不遺余力”。對此,他忍無可忍:“漕撫(李三才)嘗簡不肖:‘吾輩只合有事方出來,無事便歸。痛哉斯言,堪令千古英雄流涕,不肖獨何心而忍默默。”出于敬仰,決心打破沉默,仿效老朋友的作風—“當風波洶涌之時,毅然出而挺身擔荷”。預料到有風險,“明知其必不能勝多口,明知狂言一出,必且更滋多口也,夫亦曰聊以盡此一念而已”。因此,他不計較寡不敵眾,不顧慮可能帶來大麻煩,一定要盡自己的心念。
他在《以俟錄》中說,給葉向高、孫丕揚寫信,并無“遙執朝政”之意,純粹是好善、憂世的本性使然:“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憂世癖。二者合并而發,勃不自禁。至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無庸效市賈爭言耳。”他在《自反錄》中再次提及此事,強調寫信給葉、孫二人,一是不敢辜負李三才,二是不敢辜負海內諸君子。對于邵輔忠、徐兆魁之流毫無根據的肆意誣陷,他據理反駁:“百千罪過,臚列滿紙,而實證一切茫如也。”至于宵小之徒攻訐他與李三才“結黨”,他機智地反駁,如果這種邏輯能夠成立,那么他早就是“呂坤黨”“王國用黨”“吳中行、趙用賢黨”“江東之、李植黨”“沈思孝黨”。于是乎感嘆:“其又何所黨哉!如此看來,有黨乎,無黨乎?一憑人謂耳,予何敢擇焉!”真是痛快淋漓,把徐兆魁、邵輔忠之流的讕言駁得體無完膚。
這位謙謙君子顯然低估了宵小之徒的險惡用心,低估了政治斗爭的復雜性,及至事態擴大到不可收拾時,他才意識到給閣部大臣寫信之舉大為不妥,管了不該管的事。為此他悔恨不已—“去歲救李淮撫之書,委是出位”,“懺過而亦悔且恨”。
當他看到李三才遭到四面圍攻,處境岌岌可危,寫信提醒,加意提防,收斂鋒芒:“竊見足下任事太勇,忤時太深,疾惡太嚴,行法太果,分別太明,兼之轄及七省,酬應太煩,延接太泛,而又信心太過,口語太直,禮貌太簡。固知前后左右在在俱有伏戒,亦恐嚬笑令居種種可為罪案,檢點稍融,得不加意乎!”眼見形勢急轉直下,他又去信勸他立即引退:“足下可以去矣,不可以留矣。去也可以速矣,不可以緩矣。”
政治斗爭不以善良愿望為轉移,顧憲成不但救不了李三才,反而使得他自己和東林書院受到牽連。一些政客將李三才與顧憲成一并扣上“東林黨”的帽子,嚴厲聲討。
萬歷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顧憲成在一片誹謗聲中逝世,享年六十三歲。臨死前,他握著兒子顧與沐的手說:“作人只倫理二字。”這句遺言的內涵,或許可以從十幾天前寫給友人的信中,揣測些許端倪。他說:“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于我無所致其毒,久之,或消漸釋,故獨是伸則眾非自詘,同心盛則異類自衰。”君子坦蕩蕩,他以寬容的姿態回應無端的誹謗。
對于他的朋友門生而言,已經臻于無我境界的謙謙君子在誹謗聲中死去,激起的是無限的悲憤和感慨。
東林書院為他舉行公祭儀式,參加的知名人士四十余人,有于孔兼、錢一本、薛敷教、諸壽賢、王士騏、朱國禎、岳元聲、湯兆京、吳亮、孫慎行、于玉立、高攀龍、劉元珍、文震孟、錢謙益、丁元薦、安希范等,都是晚明政界學界響當當的人物。眾人先在東林書院“會哭”,再到他家中拜奠,相向失聲,留連浹日始去。
五、“朋黨之禍中于國”
有正義感的官員激于義憤,向朝廷建言,為顧憲成討回公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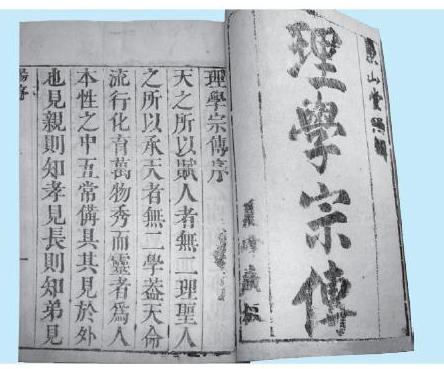
《理學宗傳》 〔清〕孫奇逢撰 自刻本
江西道御史徐縉芳說:“故南京光祿寺少卿顧憲成,忠本天植,學為人師,所著諸書有體有用,斷斷乎名儒君子也,或咎東林觸犯時忌,臣竊以為不然。”
尚寶司丞章嘉楨說:“顧憲成豪杰圣賢者也,當官任事百折不回。而學脈之醇一,操守之精絕,神理之綿密,居處之淡泊,粹然真儒。一腔忠赤,唯思為國家進用賢才,其教澤幾遍海內。”
行人司行人劉宗周說:“東林者先臣顧憲成倡道處也,從之游者不乏氣節耿介之士……一時士大夫景從如云,以故東林最著。唯其清議太明,流湎之士苦于束濕,遂乘淮撫之救,謗議四起。憲成歿,而忌者因指東林為門戶,合朝野而錮之,以為黨人。夫東林果何罪哉?”
萬歷四十四年十月,處境艱難的李三才還不忘為顧憲成與東林書院辯白:自從內閣首輔沈一貫以來,奸黨排斥正人君子,合于己者則留,不合則逐,“今奸黨仇正之言,不過兩端,曰東林,曰淮撫。何以謂之?東林者,乃光祿寺少卿顧憲成講學東南之所也。(顧)憲成忠貞絕世,行義格天,繼往開來,希賢希圣。而從之游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黃正賓、岳元聲、薛敷教等,皆研習性命,檢束身心,亭亭表表,高世之彥也。異哉,此東林也,何負于國家哉?”
盡管正直官員一再呼吁,對于顧憲成與東林書院的誹謗卻日甚一日。到了天啟年間,那些誹謗者紛紛投奔大太監魏忠賢門下,成為閹黨的骨干分子,張四面之羅網,造無底之陷阱,對不同政見者扣上“東林黨”的帽子,予以整肅。朝廷下令取締并拆毀東林書院,關中書院、江右書院、徽州書院受到連累,一并拆毀。高攀龍目睹東林廢墟,憤慨賦詩十首,其中之一曰:
蕞爾東林萬古心,
道南祠畔白云深。
縱令伐盡林間木,
一片平蕪也號林。
名列閹黨“五虎”的倪文煥揚言:東林還未得到清算,東林巨魁尚未全部伏誅,流露騰騰的殺氣。閹黨干將王紹徽編造《東林點將錄》,仿照《水滸傳》梁山一百零八將的名號,炮制黑名單,為首的是: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閹黨的另一名干將盧承欽感到,僅僅鎮壓一百零八人顯然不夠,便仿照北宋末年的“元祐黨籍碑”,炮制了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單—《東林黨人榜》。把已經逝世多年的顧憲成也列入黑名單,排在李三才、葉向高之后,位列第三。盧承欽的惡毒用心,比王紹徽猶有過之。
事已至此,“東林”已然成為莫須有的罪名,大開殺戒,先后有“六君子之獄”“七君子之獄”。以“東林”的罪名,把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以及高攀龍、周起元、周宗建、繆昌期、李應昇、黃尊素、周順昌,迫害致死。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崇禎十一年,復社名士吳應箕與顧杲(顧憲成之孫)相會于無錫,憑吊東林書院廢墟,感慨系之,賦詩一首:
同展道南祠,而傷東林址。
東林何負國,草色已及紀。
不見崔魏時,金碧連云起。
巍巍九千歲,蓬蔂安所倚。
萬古此東林,子無忘所始。
鼎革之后,東林書院終于在廢墟中重建,綿延后世。唐文治撰寫的《重修東林書院碑記》說得好:“書院舊址為顧端文、高忠憲兩公講學之地。方是時名儒碩彥風起云從,研求正學,四方響應。而有明一代之氣節,遂彪炳于寰區。厥后太倉之復社,復東林也;松江之幾社,幾東林也。然則東林之氣節,豈非千古不朽哉!”
萬斯同《明史》回顧這一段歷史,一唱三嘆:“(顧)憲成既沒,攻者猶未止。諸凡救(李)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后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為東林,抨擊無虛日。于是朋黨之禍中于國,歷四十余年,迄明亡而后已。”對晚明黨爭的分析,鞭辟入里,“朋黨之禍中于國”七個字,令人震懾不已。
孫奇逢《理學宗傳》提到一種奇談怪論:“萬歷年之黨局始自涇陽,國運已終,而黨禍猶未盡也。今日嚷東林,明日嚷東林,東林之骨已枯矣,而在朝在野仍嚷東林,豈非作始之人貽謀之不善乎?”孫奇逢反駁道:“乙丙死魏逆諸臣,甲申殉國諸臣,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乎?諸君子之所以為忠臣,而撐柱天地,名揚日月者,在五十年之后,而鼓盪摩厲者,在五十年之前。則涇陽之氣魄精神度越諸子遠矣,豈向俗儒曲學問毀譽定是非者耶!”企圖把朋黨之禍歸罪于東林的謬論,不獨當時流行,今日也有市場,有的人甚至鼓吹“明亡于東林”,這種戲說不是糊涂之極,就是別有用心!讀者諸君只消細細體味萬斯同和孫奇逢的分析,便可辨明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