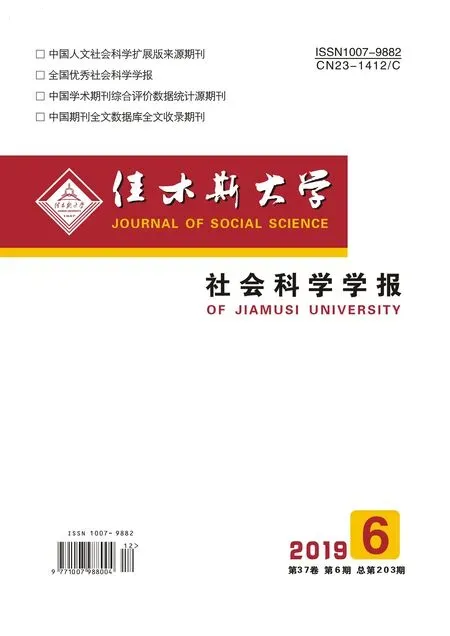齊澤克拯救全球生態危機的實在界動力嘗試
景君學,文小鳳
(蘭州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甘肅 蘭州 730050)
生態問題是世界各國普遍關心的問題。特別是近幾十年來,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不僅影響著全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嚴重威脅到人類社會的永續發展,已經上升成為一種生態危機。“生態危機是指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環境由于人類不合理的開發和利用而導致的生態環境退化和生態系統嚴重失衡的現象,生態破壞主要是因為人類盲目和過度的生產活動。所以,人們普遍認為,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保護環境,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走綠色發展之路就能人為干預生態失衡現象,從而預防生態危機。”對此,斯拉沃熱·齊澤克,一位歐洲著名的“左翼”政治哲學家,他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觀點。他提出“人是自然的傷口”,并且認為生態危機是“實在界”對人類侵犯大自然的應答。他的思想與目前生態學界流行的觀點幾乎是截然相反的,有必要進行深入探究。
一、從拉康出發理解“實在界”
(一)“實在界”是語言分割之前的世界
“實在界”是拉康精神分析學中最為重要的概念之一,拉康認為:“實在秩序描述了生命的那些無法被知曉的領域。當然,在某種意義上,它意味著一切,因為正如我們已經發現的,我們關于世界的全部知識都是以語言為中介。我們從不直接地知道任何一個東西,在這個意義上,實在界是在語言分割之前的世界。”[1]31也就是說,實在界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領域。“拉康眼中的實在界并不是現實生活的客觀世界,它是一種脫離語言符號秩序的‘缺場的在場’。實在界是一種原始的無知和無序,是欲望之源,是一種在人的思維和語言之外又永遠已在此地的‘混沌狀態’。”[2]
(二)“實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之間的關系
拉康提出的“三界”理論中的“三界”,是指實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三界”,我們可以把人類作為一個整體來說,整個人類的進化過程就像是一個嬰兒的成長過程一樣,當人類剛開始進化成為人之后,就像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在意識上,人無法區分自己與自然界,大自然能夠滿足人的基本生物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下,人與動物沒有太大的區別,人們也不是用語言去交流,促使人類去表達生存需求的那個動力就來自于實在界。隨著人類的不斷進化,人開始逐漸有了自我意識,這時人類開始步入想象界。慢慢地,人的自我意識越來越強烈,人開始把自己和他人、他物作出區分,私有制便隨之產生,人們意識到,人所擁有的所有財產都來源于自然界,而且為了獲得更多的私有財產,人往往需要通過與別人的合作才能完成,這時,人不得不加強與其他個體之間的交流來獲取物質生產資料,最初的語言開始形成,這時候人成為主體的自我,處于語言符號的世界即象征界之中。嬰兒期的人類處于實在界,長大后用語言描述的就進入了人類的象征界,而鏡子中看到的自己鏡像就是想象界中的自己。
(三) “實在界”與“象征界”之間存在著無法縫合的“裂隙”
從人類社會產生以來,語言就在人們溝通過程中起著重要的橋梁作用,它是人類最為重要的交際工具。從古至今,人們借助語言保存和傳遞人類文明的成果,人類的所有知識,所有理論都是以語言為中介。如果沒有語言,我們就無法了解關于人類文明的任何知識,那關于世界,我們將什么也不能了解,所以象征界的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語言符號的存在。然而拉康認為,在語言這個意義上,實在界是語言分割之前的世界,無論怎樣的語言都不能完全地將它表達出來,甚至試圖通過語言去表達,本身就是一個缺口。所以,實在界與象征界之間注定存在著無法縫合的“裂隙”。
二、齊澤克激進的生態觀
齊澤克把被破壞、被打亂的大自然進程以及如今的生態危機與“實在界的應答”有機地結合起來,讓“實在界”這一概念通俗化,形成了較為激進的生態觀。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實在界層面的“自然并不存在”
當前存在的全球變暖、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減少、酸雨蔓延、森林銳減、土地荒漠化、大氣污染、水體污染、海洋污染、固體廢物污染等全球十大環境問題,逐漸威脅到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人們總認為是由于人類的實踐活動破壞了大自然的平衡狀態,導致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失調,才出現了這些環境問題。
然而,在齊澤克看來,“自然”是人類抽象出來的一個概念,是人類所處的語言符號世界的功能之一,其實自然并不存在,所以我們也就無需去恢復那個我們原本以為平衡的生態系統。也就是說,我們平時所說的那種自然運作的生態系統其實是不存在的。我們說生態平衡遭到破壞是因為我們在開始就已經默認生態系統本來就是平衡的,即自然界是一個自由運作的、有規律的系統。既然自然是不存在的,那么人們所以為的那個自然運作的、井然有序的、平衡的生態系統也不過是人類的幻象而已。人們一直認為的自然是一個平衡的系統的這種想法也只是人類的一種“回溯性投影”而已。齊澤克指出,我們所要說的保護自然的最大障礙其實就是我們對“自然”這個概念的完美界定,因此,我們必須要走出這種先入為主的思想模式,拋棄對“大自然”的完美印象。
同時,齊澤克認為,人的存在與平衡、穩定的生態系統本來就是互相矛盾的。因為只要人存在于自然界中,人就要向大自然索取,而人向大自然索取的過程就是破壞自然平衡的過程。其實,大自然不平衡是常態,平衡才是偶然事件。人類之所以呼吁“保護環境,綠色發展”,就是因為人總是抱有僥幸心理,認為生態危機還沒有發生,人們想通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來力爭使自然達到那個原始的、穩定的最初狀態。人類總是認為自然界有一個平穩運作的理想狀態,所以,其實人們并未對生態危機產生恐慌之感。既然生態系統有恢復平衡的可能性,那么人類就會存在僥幸心理,總認為人類與生態災難或生態危機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距離。齊澤克認為這種觀點對人類社會發展是不利的,因為人只要存在,生態平衡就是想象界的存在,就不可能實現。
(二)技術:傷害地球,拯救地球?
“似乎是受到馬克思對‘人化自然’定義的啟發,齊澤克提出‘自然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類與其所面臨的各種災難的抗爭而已。”[3]
齊澤克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人們認識生態危機具有重要的作用,要正視生態危機,就必須促進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這樣人類才有可能更加精準地預測危機。在齊澤克看來,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人類提高了認識世界的能力,從空氣質量的下降、酸雨的蔓延到臭氧層破壞等等,科學技術無疑為我們提供了認識這些環境變化的可能性,讓我們透過環境變化這個現象看到了生態環境在逐漸惡化這個本質。他說:“科學技術的發展擾亂了自然的進程,從而使他再也不可能通過自然本身發現一個重建失衡的方法,但訴諸于反科學的新時代也是荒謬的,因為大多數的危害如果沒有科學這一診斷工具是不可能被發現、被察覺的。”[4]392同時,他也認識到,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科學技術對大自然的平衡運作造成危害,但另一方面,恰恰是人們借助科學這一工具才發現了這些危害,否則人們根本無法察覺。所以在齊澤克看來,科學技術對人們認識生態危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生態危機是“實在界”對人類侵犯大自然的應答
齊澤克認為,生態危機是實在界對人類侵犯大自然的應答。他提出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實在界的應答”。其一,他認為實在界與符號世界并不是勢不兩立的,而且實在界彌補著符號世界即象征界通過語言而無法表達出來的那個缺口,實在界支撐、維護著語言符號世界即象征界。其二,另一類“實在界的應答”導致了現實的喪失,人在其中感受到的首先是人的迷失,人被物所奴役,人感受到了不自由,出現了人對自由的逃避。人在現實面前感覺到的是意義的喪失、情感的冷漠、價值的變異,其出現的形式常常在我們意料之外,令我們驚詫萬分。
齊澤克認為,不僅生態危機是實在界對人類侵犯大自然的應答,而且,生態危機已經發生。“我們在現實世界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生態問題,正是由于實在界與象征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與屏障。”[5]一方面,人類總是試圖通過一系列諸如節能減排、回收利用之類的手段來防止生態危機發生,因為在他們眼中,生態危機一定會發生,通過這些措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者減緩生態危機的來臨。總之,普通民眾總是試圖與生態危機保持一定的距離,甚至希望自己與生態危機之間劃清界限。另一方面,“齊澤克重點強調了象征界中‘一小片實在界’對人類的重要性。主體之間要想進行有效的交流,‘實在界的應答’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沒有‘一小片實在界’充當賭注,來確保符號性交流具有一致性,任何符號性交流都是不可能的。”[6]52
在心理上,人類總是不愿意承認生態危機已經發生這個事實,但卻在提及由于人類的開發導致自然失衡時,意識到這是實在界對人類侵犯大自然的回應。齊澤克認為,正是這“一小片偶然的實在界”使人類以為生態危機是人類侵犯大自然的結果。因此,人類一方面試圖通過自身的“環保”行為來阻止生態危機的發生,另一方面認為生態危機是在人類的可控制范圍內,認為生態危機一定不會、也不可能發生。正是這兩個方面的現狀揭示出人類在面對生態問題上的悖論和沖突。
三、齊澤克對生態危機的態度
(一)普通大眾對生態危機所持有的態度
齊澤克認為,在我們所生活的象征界,普通大眾對待生態危機常常有三種不同的反應。第一種是“戀物式的分裂”,即知而不信式。一方面,人們清楚地知道生態危機終有一天會爆發,但總是對生態危機會發生的真實性產生質疑或者抱有僥幸心理。人類總是一邊擔憂著生態危機爆發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另一方面卻抱有生態危機不會發生的僥幸心理,這其實是對生態危機的一種麻木不仁、置之不理的態度。人們只想在生態危機發生之前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不愿意認真對待,因為他們害怕這種極度恐慌的心理會影響到自己的正常生活。
第二種是“神經官能式的轉化”,即知而不甘式。這些人對于生態危機的嚴重性是有深刻的了解和認知的,他們非常擔心生態危機的爆發,由此常常采取一些諸如“節能減排,保護環境和綠色發展”的措施,以試圖減緩或阻止生態危機爆發的速度和進程。然而在齊澤克眼中,這些做法是沒有作用的,因為生態危機已經發生,生態危機并不是還沒有發生或者通過人類的一些行為就能避免的未來事件,而是一種“缺場的在場”,這些做法對于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來說相當于徒勞。
第三種是“精神病式的投射”,即知而甘罰式。這種反應的人將生態危機看成是“實在界”對人類的貪欲開出的罰單。因此,許多人認為,人類必須停止對大自然的瘋狂掠奪,改變以往的錯誤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與大自然之間建立友好的合作關系,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將人類視為大自然這個整體的一部分,與大自然和睦共處、和諧共生。
(二)面對生態危機應該從“逃避”轉為“直視”
在齊澤克的眼中,前面提到的普通大眾對于生態危機的三種反應其實都是人的一種病態心理的表現,人們既賦予實在界一定的意義,又借此來忽略它,人類常常拒絕承認的那個實在界其實恰恰伴隨著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三種反應本質上都是在逃避生態危機。齊澤克認為,針對實在界與符號世界即象征界之間的這道“裂隙”,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并把這種裂隙視為人之所以為人的前提條件。因為人作為人而言,言語是其本質特征的體現。而在拉康那里,實在界恰恰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既然人生活在充滿語言符號的象征界,那這個象征界與實在界之間注定是無法完全互通有無的。所以,無論是第一種“戀物式的分裂”的那種試圖通過極力的否定和懷疑而將生態危機予以擱置,還是像第二種“神經官能式的轉化”那樣試圖通過采取一些措施或手段而尋求心理上的安慰以試圖避免生態危機,或是像第三種的“精神病式的投射”那樣通過限制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來彌補象征界與實在界之間的那個“裂隙”,這些態度和做法都無法使實在界與象征界之間的那個裂口縫合。
介于這個“裂口”無法縫合,對于生態危機,人們只能從以前的“逃避”態度轉向“面對”和“直視”。齊澤克主張人們坦然面對生態危機已經發生的事實,拋棄那種“知而不信、知而不甘和知而甘罰”式的態度,破除“生態危機不會發生”的幻想,從而轉向一種沒有“自然”的生態學。就像前面所提到的,人們要么對目前生態學所揭示出來的生態危機所導致的種種后果感到恐慌,要么逃避與生態危機之實在界的相遇。他認為:“要與環境和睦相處,人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全盤接受這個‘裂隙’、‘裂痕’之類的結構性拱出,然后試著盡可能予以修復。”[7]7
齊澤克認為,人們無法正視生態危機本身是和實在界與象征界之間的這道“裂痕”緊密相關的,但同時,也正是這道“裂痕”阻擋著實在界對人類的報復,使人們維持著正常的生活。我們無法消除這道“裂口”,但我們能夠通過修復這道“裂口”而直視生態危機,這種“直視”是人類的一種“向內的批判”,我們應該意識到,關于自然是“平衡的、穩定的、有序的”等這些美好的幻想其實是虛無縹緲的。生態危機、自然失衡等這些都只是社會歷史進程的一部分,我們所謂的那個平衡的自然不過是人類自身的幻象。人們想方設法地去恢復那種井然有序的生態系統,就是因為人們先入為主地認為自然原本是一個穩定運行的、有秩序的平衡的系統。而這種“平衡的秩序”不過是生態災難造成的“裂痕”。我們應該做的就是直視生態危機,并不將其置于我們所處的符號語言世界中而賦予它任何意義,從而建構一種沒有“自然”這個概念存在的生態學。
(三) 齊澤克提出要警惕生態運動為資本主義所利用
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倡導的生態學、生態美學常常呼吁人們簡約生活、綠色消費等,甚至這些觀念已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齊澤克指出:“環境災難不僅不會破壞資本主義,反而可能會給它提供新的動力,開拓新的投資空間和機會。”[8]我們要警惕資本主義國家借環境災難將要到來的名義為自己國家提供新的發展動力和投資空間。因為資本主義國家長期依賴市場,他們需要不斷地去開拓新的市場來刺激經濟發展。
究其根源,資本主義國家所倡導的這種理念使人們在面對生態危機時持一種中立的觀點,從而無法直面生態危機之實在界,以至于作出一個模棱兩可的選擇。因此,齊澤克認為,因為正是資本主義倡導的這種理念導致了普通大眾在生態問題上的悖論,所以我們面對生態危機的態度必須發生轉變,生態學必須轉向批判資本主義的生態學。生態危機是當代資本主義內部無法調和的矛盾之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生態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人類要想解決生態危機問題,就必須首先消除資本主義特定的生產方式。作為要推翻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無產階級,他們的使命就是要將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制度,從而成為解決生態危機的中流砥柱。
四、對齊澤克激進的生態觀的反思
齊澤克關于生態危機的看法可謂是“離經叛道”,但他的獨特的生態哲學思想所表露出來的理論鋒芒,為我們研究和思考生態環境問題提供了嶄新的視角,但他并沒有提出解決生態危機的具體的措施和方法。此外,他所提出的理論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與缺陷,如忽視了人在生態危機面前的主觀能動性,將精神分析的對象又局限到個體心理的方式,忽視了社會整體的作用等,所以,對于他提出的生態思想,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采取“揚棄”的態度。
(一)齊澤克的思想為生態危機的研究和思考提供了嶄新的視角,但缺乏可操作性
齊澤克認為,在生態危機面前,我們不能模棱兩可,若此若彼,而要保持堅定的態度。資本主義制度給我們直面生態危機本身造成了一定的障礙,因此,齊澤克主張激進的、面向社會主義的生態政治革命。齊澤克可能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他主張將那些“除了鎖鏈沒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和生活在貧民窟的那些“被排除者”作為生態政治革命的主力軍,發起一場生態政治革命來解決生態危機問題。但這種面向社會主義的生態政治革命顯然對于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不適用的,所以實質上他并沒有提出如何解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態危機。況且,我們都無法預料生態政治革命是否會有“后遺癥”,所以他所主張的這種生態政治革命還有待實踐的檢驗,這是他理論上的一個不足。此外,資本主義制度只是造成生態危機發生的原因之一,如果只主張通過生態政治革命來解決生態危機,那顯然是不夠的,而且在組織政治革命的過程中也面臨著重重障礙和難題。
(二)齊澤克認為,積極地適應當前的生態環境也許是相對較為正確的做法
研究表明:人類活動對氣候造成的影響是一個緩慢的、不顯著的過程,大約要在200年以后才會顯現出來,人類無法減緩氣候變暖的速度,現在唯一能做的也許就是保持樂觀積極的心態,適應新的、變化了的生態環境。當前人類所面臨的所有環境問題中,最為嚴峻的是氣候變暖,這個現象目前是眾所周知的,僅僅靠直視它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需要在與自然的“交互作用”中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斷地積累實踐經驗,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并通過不斷創新的理論去指導實踐,以便有可能去應對氣候變暖、生態環境惡化的現狀。面對生態危機,人類不能總是逃避,而要去直視。既然生態危機是不可控的,那我們能做的就是積極地適應生態危機。我們可以將“危”與“機”看成是一對矛盾統一體,“危”與“機”之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有“危”就有“機”,我們應該期待在“危”中發現并創造“機”,從而催生出促進人類向前發展、向前進步的新文明。
(三)齊澤克的生態觀對當前流行的生態學觀點具有一定的沖擊作用
“齊澤克的生態觀對當前生態學中把自然理想化、崇高化、純粹化的傾向具有警示和糾偏作用”[9]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認為,人類是主體,處于支配地位,而自然是客體,只能處于被支配的地位,人類擁有意識就可以主宰其他一切事物,價值評價的尺度必須掌握和始終掌握在人類的手中,任何時候說到“價值”,都是指“對于人的意義”。而生態學所主張的觀點與人類中心主義的核心思想是背道而馳的,生態學、生態美學試圖把自然還原成一個平穩有序運行的統一系統,而將人從“自然”中分離出來,主張人類的實踐活動破壞了自然界的這種運行規律。然而,在齊澤克看來,那個有序運行的自然系統是不存在的,我們必須從對生態危機的“恐懼”與“逃避”轉向“直視”,無論生態危機是可能會發生、必然會發生還是已經發生,我們都要持一種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目前我們所倡導的循環經濟、綠色發展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都主張通過保護生態環境來建立綠色地球,我們將自然崇高化,要求人類敬畏自然,保護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這種思想在目前來講,具有極大的合理性,因為人類想要生存,就需要理性地對待生態危機。而齊澤克的生態觀相對于這種觀點來說,給我們提供了完全嶄新的視角,無疑讓人“耳目一新”,有利于我們從多方面、多角度去思考和解決生態問題。
(四) 齊澤克的觀點給大多數生態學家從“類”“我們”出發去考慮生態問題提供了新的角度
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加速了生態惡化的進程。目前人類面臨的全球性的十大生態環境問題,越來越威脅到人類的生存,隨著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張,人類不得不尋求各種手段和方法來緩解這種緊張的關系,否則人類的生存也難以保證。面對嚴峻的形勢,人類必須認真地對待生態問題,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實現人與自然的共同福祉。然而齊澤克認為,造成大眾在生態問題上悖論的主要原因是資本主義,因此,應該將矛頭指向資本主義,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運行模式和生產機制才是生態問題的真正癥結,所以解決生態問題的源頭在于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齊澤克的這種觀點對于目前我們從“類”出發去思考生態環境問題具有啟發作用,有助于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去研究和解決生態問題。
五、 結語
目前,環境問題越來越嚴峻,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責任也有義務對當前全球所面臨的生態問題作出努力。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致力于建設“美麗中國”,狠抓生態建設,不斷滿足廣大群眾“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美好愿望。總之,不管是目前所流行的生態觀點,還是齊澤克的生態觀點,我們的目的都是通過分析和研究當前所面臨的環境問題,制定出應對環境惡化和生態破壞的對策,通過建設良好的生態環境,讓人民群眾樂享綠水青山,增強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近幾年來,中國越來越重視生態環境問題,中國正在爭取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參與者、引領者和貢獻者,與其他國家一起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中國乃至世界的生態環境向好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