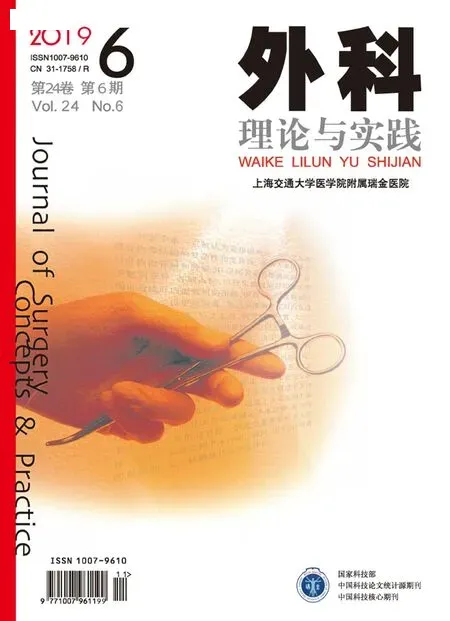乳腺浸潤性導管癌伴導管原位癌的病理特征及預后關系研究
Chih Wan Goh, 吳佳毅, 朱 麗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外科 乳腺疾病診治中心,上海 200025)
乳腺浸潤性導管癌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IDC)伴導管原位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DCIS)是臨床上常見的病理類型。DCIS被普遍認為是IDC的前驅病變,若未經治療,近一半的DCIS將進展成IDC。IDC伴DCIS的臨床病理特征和腫瘤生物學行為可能有別于DCIS和IDC,但IDC中的DCIS成分是否具有預后相關性,目前仍未達成共識。本文闡述了IDC的進展假設模型以及其影響腫瘤生物學的可能因素。此外,基于IDC伴DCIS的臨床生物學特性,對IDC腫瘤內的DCIS組織學分級、占比、分子分型和預后方面進行綜述。
根據2018年全球腫瘤流行病(GLOBOCAN 2018)的統計,乳腺癌是全球女性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惡性腫瘤。2018年女性乳腺癌發病數約占所有惡性腫瘤的1/4[1]。從1990年開始,乳腺X線攝影在臨床篩查工作得到廣泛應用和普及,DCIS檢出率逐年升高。DCIS的檢出率從1970年的5.8/10萬例增加至2004年的32.5/10萬例,隨后維持在平穩水平[2]。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NCHC)數據,2018年美國DCIS的新發病例約 6.4萬例,占所有乳腺癌類型的 19.8%[3]。
大多數學者認為,DCIS是IDC的前驅病變,若未行手術治療,20%~50%的 DCIS 將進展為 IDC[4-7]。 IDC 伴 DCIS 占所有乳腺癌類型的比例,各研究報道差距較大(20%~80%)[8-12]。目前認為,IDC中的DCIS成分不影響乳腺癌的預后和綜合治療決策,浸潤性癌的病理和免疫組織化學特征為主要治療決策因素。然而近年來,病理診斷越來越重視癌前病變的描述,對IDC伴DCIS腫瘤的病理評估應包括DCIS的病理結構(實性、篩狀型或粉刺樣),組織學等級和DCIS占比[13]。不少研究發現,IDC內的DCIS可能有臨床指導意義。
IDC的發病機制
乳腺癌的發病機制復雜,影響腫瘤異質性的因素包括遺傳性基因突變、表觀遺傳病變和微環境改變。乳腺癌是起源于乳腺末梢導管-小葉單位的上皮細胞 (terminal ductallobular unit,TDLU)的浸潤性病變。目前普遍認為乳腺癌存在兩種發病機制模型,分別是新發而成和多階段性生成。乳腺癌新發而成的發病模型認為乳腺癌腫瘤內的異質性是自然選擇形成,而不是通過一系列階段性的細胞前驅演變過程。新發而成的乳腺癌一般只有單純IDC,其腫瘤內不伴DCIS[14]。另外,多階段性生成模型認為乳腺癌是由一系列多階段病變進展而成,從正常細胞至不典型導管上皮增生(atypical ductal hyperplasia,ADH),再發展成DCIS和IDC,其腫瘤內可能伴DCIS[15-16]。不少乳腺導管增生性病變和癌前病變的組織學特征已被定義[17](見圖 1)。
有研究認為,從DCIS發展成IDC的腫瘤是由一系列溫和的腫瘤抑制基因突變累積,而單純IDC腫瘤由更嚴重的抑癌基因缺陷引起。DCIS的復制依賴于上游有絲分裂原,IDC伴DCIS的浸潤性生成機制可能與DCIS前驅病變相關。所以,在DCIS發展至IDC過程中,與DCIS相關的一些預后較好的病理特征將保留在腫瘤克隆細胞內,進而使IDC伴DCIS腫瘤也具有較低的生物學侵襲性[14]。然而,目前在這方面的基礎研究非常有限,兩組之間的驅動機制和基因突變差異需更多的研究驗證。
另外,一些臨床研究發現IDC伴DCIS對比IDC病人可能具有較低的腫瘤侵襲性和較好的預后。Wu等[11]在一項大樣本 (61 745例)乳腺IDC分析中發現,病人IDC病灶中含≥25%DCIS成分時,其乳腺癌特異生存率高于不含DCIS成分病人(98.5%比97.3%,P<0.001)。然而在數據匹配后分析,乳腺癌特異生存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另一方面,Logullo 等[18]發現,在 T1N0M0乳腺癌病人中,IDC 伴 DCIS 比單純IDC病人的局部復發率更低(3.9%比23.1%,P=0.003),總生存率也顯著優于IDC病人(98%比85%,P=0.008)。Lopez等[19]研究接受新輔助治療的病人,發現IDC伴DCIS病人7年無病生存率為87.3%,IDC病人為65.8%;IDC伴DCIS病人7年總生存率為92.7%,IDC病人為71.9%。IDC伴DCIS病人的預后顯著優于IDC病人。
IDC伴DCIS內的DCIS與IDC組織學分級關系
腫瘤組織學分級是評估乳腺癌病人復發風險的重要指標之一。研究發現,同個腫瘤內IDC與DCIS成分的組織學分級具有很高的符合率,因而提出平行通路的進展模式[20]。平行通路的假設是乳腺癌前期病變通過低級別通路發展成低級別DCIS,后者再進一步發展成低級別IDC;同樣,高級別 DCIS通過高級別通路進展成高級別 IDC[21-22]。Roylance等[23]報道,高級別DCIS和高級別浸潤性癌具有8p和18q的缺失及17q的延長;而低級別DCIS和低級別浸潤性癌中也具有相似的16q、8p缺失和1q延長。這個進展模式在基因表達譜分析得到證實,表明腫瘤是根據組織學分級聚類而不是根據疾病的進展分類。
研究發現IDC中的DCIS組織學分級可能是影響乳腺癌病人預后的獨立因素之一。在Holland及Van Nuys的評級系統下,對比IDC伴DCIS腫瘤內的DCIS與IDC的組織學分級,發現兩者具有顯著的相關性,提示IDC腫瘤的侵襲性可根據DCIS成分的組織學分級進行預測。Douglas-Jones等[24]在 IDC伴DCIS的腫瘤內發現,其DCIS成分的組織學分級與IDC的組織學分級和Nottingham預測指數具有密切關系,IDC腫瘤內伴有低級別DCIS的預測指數比高級別DCIS 更低(P=0.001)。 Kim 等[9]認為,IDC 中的 DCIS 組織學分級是影響乳腺癌病人預后的獨立因素之一。IDC伴高級別DCIS的無復發生存率是IDC伴低、中級別DCIS的2.5倍,IDC伴DCIS腫瘤內的DCIS組織學分級可能具有臨床治療的指導價值。
IDC中的DCIS成分百分比
IDC伴DCIS的病理類型可根據腫瘤內的DCIS成分占比分類,其中包括以DCIS為主的IDC和廣泛DCIS成分(extensive intraductal component,EIC)。1981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首次提出以DCIS為主的IDC腫瘤類型,其腫瘤的DCIS成分需至少大于IDC的4倍。大多數研究報道中,EIC的應用更廣泛,其定義為DCIS成分占比>25%,同時DCIS出現在IDC周圍或多灶性分布于正常乳腺組織中[26]。對IDC伴DCIS的DCIS占比進行區分的意義在于更全面地進行腫瘤評估,乳腺浸潤性癌的侵襲性可能與IDC與DCIS成分的比例有密切關系。
在臨床研究方面,EIC是保乳病人局部復發的危險因素之一,這與保乳術后的DCIS殘留密切相關。研究發現EIC比無EIC病人的10年局部復發率更高[27],分別為9.1%和5.2%。另有研究報道,EIC與局部復發相關,但并不是遠處轉移的因素之一[28]。Wong 等[14]在對比 IDC 伴 DCIS 和無 DCIS 的腫瘤匹配研究發現,IDC無DCIS的組織學分級和Ki-67水平比IDC伴DCIS高,可能具有更高的腫瘤侵襲性。Cedolini等[29]發現,病人的無病生存與浸潤性癌內的DCIS成分相關,多因素分析表明伴有<25%DCIS成分的IDC無疾病生存風險是>75%DCIS成分腫瘤的5.6倍(P<0.05)。以上研究表明,EIC主要關注的是乳腺癌病人的腫瘤殘留和復發,然而從腫瘤生物學行為和預后評估來看,EIC病人可能比低DCIS比例病人具有更低的腫瘤侵襲性。
IDC伴有DCIS的分子分型分布
2000年,Perou等[30]通過 8 102個人類基因的互補 DNA(complementary DNA,cDNA)芯片進行基因表達譜分析,發現乳腺癌主要可分為ER陽性型和ER陰性型。2003年,Sorlie等[31]分析456個乳腺癌cDNA芯片表達譜,進一步將乳腺癌分為5個亞型,即luminal A、luminal B、HER2陽性、基底樣和正常乳腺樣。乳腺癌的亞型分類是依據分子水平上的基因表達差異,不同的乳腺癌分子分型在預后和治療反應上存在顯著的特異性。

圖1 乳腺增生性病變的組織學特征(由本院病理科提供)
浸潤性乳腺癌綜合基因表達譜的分子分型也適用于DCIS,且不同的分子分型存在不同的腫瘤進展機制[32-33]。研究發現,TP53和PIK3A的基因拷貝數在DCIS與IDC中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PIK3A基因突變與ER陽性型乳腺癌有密切關系,TP53基因突變與ER陰性型相關[34-35]。此外,DCIS至IDC進展機制在不同的分子分型中具有特定的基因突變或驅動機制,影響腫瘤的生物學行為。在luminal A型DCIS進展至IDC過程中主要發生細胞分化和炎性免疫反應,這些細胞為近2倍體或2倍體核型,具有重復染色體的改變,與 16q缺失和 1q、16p增長有關[33]。 低級別 DCIS主要與luminal A型相關,主要為ER、PR陽性表達,HER2擴增缺失,此類型的乳腺癌病人具有較好的預后[35]。此外,luminal B型具有細胞遷移特征,在復制過程中最主要的丟失基 因為 TP53、PTEN、INPP4B、RB1、MAP3K1 和 MAP2K4[33-37]。HER/ErbB2與細胞周期特征的過表達有關。HER受體家族在細胞膜形成二聚體后,經過PI3K/AKT和Ras/Raf/MEK/MAPK兩條信號轉導途徑被激活。這些信號將傳入細胞核,啟動基因轉錄,導致細胞增殖、浸潤、抗體凋亡并促進血管生成等反應[33-38]。基底樣型DCIS至IDC疾病進展與 B細胞淋巴瘤因子9(B cell lymphoma 9,BCL9)驅動因子密切相關。在IDC伴DCIS的腫瘤中發現,BCL9表達在IDC腫瘤中明顯上調,在敲除BCL9表達后,DCIS細胞的增殖、遷移和浸潤被顯著抑制[39]。高級別 DCIS主要與 luminal B型、HER2擴增型和基底樣型相關。對比低級別DCIS,高級別DCIS具有更多的基因拷貝數改變,發展成IDC的風險更 高[36]。
IDC伴DCIS與IDC的分子分型分布存在差異,IDC伴DCIS往往比IDC具有更多的HER2陽性表達和更低的三陰性比例[11-40]。在分析不同分子分型中IDC伴DCIS與IDC病人的預后,Lee等[41]發現,這兩組病人的乳腺癌特異生存率和總生存率差異并無統計學意義。然而,Dieterich等[8]認為,在luminal型乳腺癌中,IDC伴DCIS病人的局部復發率比IDC病人更低(P=0.012)。 Wong 等[42]發現,在 luminal型伴淋巴結轉移的乳腺癌中,IDC伴DCIS病人比IDC病人的Ki-67更低(P=0.02),具有更低的腫瘤侵襲性。腫瘤生物學和基因組學研究證實DCIS至IDC的進展在各乳腺癌分子類型具有特異性,IDC伴DCIS的分子分型分布于IDC也有差異。除luminal型的研究報道,IDC伴DCIS的各分子分型預后是否存在差異尚不明確。
結 語
隨著分子生物學和基因組學的進展,乳腺癌的診治越來越注重“精準治療”和“個體化治療”,使病人從適度的治療中達到最佳的療效。雖然目前IDC腫瘤中是否伴DCIS并不影響輔助治療決策,然而不少研究報道,單純IDC與IDC伴DCIS的病理學特征、分子分型和預后具有差異。研究乳腺癌生成的機制發現,從DCIS進展的IDC具有更低的腫瘤侵襲性。此外,IDC腫瘤中的DCIS成分比例、組織學分級和分子分型與腫瘤的生物學行為相關,可能具有臨床指導價值。但單純IDC與IDC伴DCIS之間的基因突變、疾病驅動因子和進展機制差異仍需更多的基礎研究和臨床試驗來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