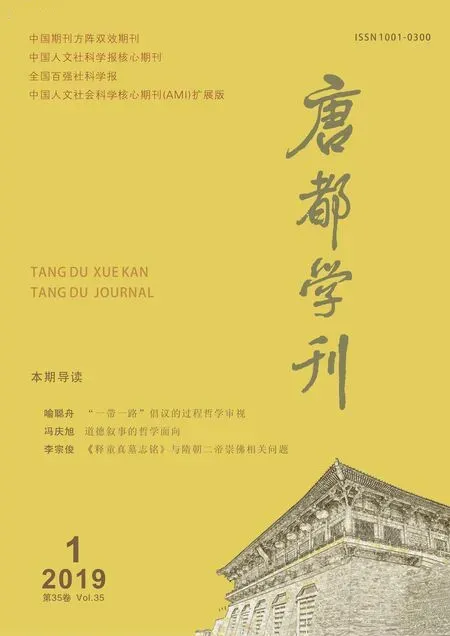淺談民國時期的五四紀念
——以《申報》為中心的考察
龔 琦,付建成
(西北大學 歷史學院,西安 710069)
1919年,北京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五四運動。運動后期,陣地轉移到上海,工商界相繼罷工、罷市。在社會輿論的極大壓力下,北洋政府最終下令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五四運動的爆發,對于當時中國尤其是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青年學生作為獨立群體登上政治舞臺,對當時的政治決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以自由、民主、科學、愛國等為核心的五四精神也得到了廣泛傳播。“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高漲,五四紀念就成了革命動員、教育民眾以及迎合現實之需,得到深入發展”[1],因此自1919年后的每年5月初,學界都會進行相關紀念活動,追憶五四。
報紙是民國時期主要的新聞傳播媒介,當時每年的五四紀念,報紙皆有報道,而《申報》作為民國時期影響力最為廣泛的商業報紙之一,其基本不屬于任何政黨,故能夠較為真實客觀地報道五四紀念活動。本文擬以《申報》為中心,梳理其關于五四紀念的相關報道,探討民國時期五四紀念的方式與特點,借以初步了解五四記憶的傳承與發展。
關于民國時期的五四紀念與五四記憶,目前學界的研究已經呈現出了多角度、跨學科的研究形勢:有學者從政黨政治與五四紀念關系出發,探討了民國時期國共兩黨對五四的相關紀念[注]參見張艷《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五四”紀念》,《史學月刊》,2013年第6期;趙鵬飛《國民黨與五四紀念(1919—1949)》,華中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楊濤《合法性爭奪與民國時期青年節的演變》,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有學者從報紙報道的角度,討論了機關黨報對五四紀念的報道[注]參見張紫萱《國民黨對“五四”話語的“三民主義”改造——以〈中央日報〉1928—1937年的言論為視角》,《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2013年第2期;陳文勝《試析延安時期中共五四運動紀念話語的特點及功能——以〈解放日報〉〈新華日報〉文本為例》,《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還有學者從民族記憶、歷史記憶的角度論述了五四紀念的功能和意義[注]參見凌云嵐《“五四”紀念:被賦予的意義》,《讀書》2017年第10期;孫路瑤《史實與宣傳:中國共產黨人的“五四”記憶與闡釋(1919—1945)》,復旦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周良書《關于“五四”紀念的紀念》,《北京黨史》,2009年第3期;羅志田《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薇娜·舒衡哲《“五四”:民族記憶之鑒》,《五四運動與中國文化建設——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147~176頁。等等。
一、北洋政府時期(1920—1926)
(一)紀念方式與內容
1.純粹意義的紀念
1920年5月4日來臨之際,作為第一個周年,北京學界很早便開始了紀念的籌備工作。5月1日《申報》就根據“秘密據聞”報道了北京學界擬定的紀念活動,即“于五月四日上午開五四運動紀念會、下午在高師開五四紀念運動會。”[2]紀念日當天,北京學界舉辦了盛大的紀念儀式,然“蓋以北京全體學生計、約七萬余、各校皆無此大地址、天安門外雖可以容之、軍警絕不令其在彼開會、無可奈何、不得不在校內開會、共分三處、學生聯合會在北大理科、高等師范在本校、女界聯合會在美以美會……”[3]可見紀念規模之大,人數之多,而其中北京大學的紀念會最為隆重。據報道,北大會場懸掛國旗、五四紀念會旗、黃綾豎幅等物件,紀念會開始之時,首先由開會主席團登場,而后奏樂,再全體起立向國旗三鞠躬;其次向學生宣講五四運動之精神;最后再由各學生代表進行演說與相關報告。值得注意的是,這場紀念會還發放了許多黃白藍三色的紙質小旗,三種顏色分別代表自由、平等、博愛,每面小旗上又都書寫有“五四紀念”四個紅字,代表五四精神永存。紙質小旗的發放配合著講演,使得五四精神得到了極大的宣傳[4]。
除了北京,《申報》還報道了南京、杭州、嘉興等地的紀念儀式。并且在五四當天,《申報》上刊登了黃炎培撰寫的《五四紀念日敬告青年》[5]一文,措辭情深意切、慷慨激昂地宣揚了五四愛國精神,這一做法表明報紙作為新聞傳播的媒介,本身就是紀念儀式的一部分,即通過“刊登宣傳性質的文章”參與其中。而《申報》作為當時影響力最為廣泛的商業報紙之一,就以積極的姿態參與了這一聲勢浩大的學生紀念運動。1921年的五四紀念同樣如此,宣揚了學生的愛國精神以及五四自由民主的精神,茲不贅述。
2.逐漸政治化的紀念
1922年北大的五四紀念,校長蔡元培發表了《五四運動最重要的紀念》一文,《申報》全文照錄。蔡元培表示五四紀念不需要夸張的形式,而需要更多地關注路權、用工權和平民教育權[6]。比起北方學界對民生問題的關注,同時期南方的廣東學界借五四紀念發表演講,其組織了多個演說隊,分赴各個繁華的地方宣傳了五四外交失敗的歷史及賣國賊的罪惡,并重點批判了北洋政府的黑暗和官僚階層的腐敗[7]。這一舉措無疑賦予了五四紀念特殊的含義,并且在1922年5月4日當天,孫中山再次下令出師北伐。正是從這時開始,五四紀念多了政治宣傳的作用。
1923年的五四紀念,恰逢彭允彝事件發生不久[注]彭允彝事件指1923年1月,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彭允彝,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提出重申“羅文干”案件,引起了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不滿,蔡元培認為這嚴重干涉了司法獨立,蹂躪了人權,遂辭職以抗議,引發了北京學界轟轟烈烈的“驅彭挽蔡”運動。,北京學界便對教育總長彭允彝示威,并要求打倒軍閥、否認現政府,擁護人權、維護教育獨立[8]。1924年,上海學生會邀請汪精衛、葉楚傖等人進行演講,二人都贊揚了五年前學生運動的精神,嘆息目前五四精神缺失,希望學生們能夠團結起來,使五四精神長存[9]。而全國學生會則邀請了胡漢民、瞿秋白等人發表演講[10],從演講人員的政治出身來看,都是當時國共兩黨要員,表明隨著國民大革命目標的確立,此時學界的五四紀念已經明確起到了政治導向的作用。
1925年、1926年同樣如此,通過名人(多數為國民黨要員)演講、發行特刊、傳單、示威游行等方式,把本該紀念五四精神的紀念變成了宣傳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政府的紀念。1926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特別通告,要求各級黨部“宜乘此紀念,領導青年學生團結于國民革命旗幟之下”[11]。同年,廣東中山學院的五四紀念還增加了讀國父遺囑、向黨旗敬禮等環節[12]。所有的這些舉措都表明,此時的五四紀念已經政治化、官方化。
(二)紀念特點
縱覽北洋政府時期的五四紀念,特點如下:
其一,該時期以學界紀念為主,政府基本采取不干涉態度。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帝反封建運動,然而對于當時執政的北洋政府而言,則有著重大的影響。為避免紀念五四帶來不必要的動亂,在1920年第一個周年紀念來臨之際,政府命令教育部勸誡學界,同時也命令警察廳在五四期間嚴加防范[13]。但基于五四運動的愛國性質和廣泛的群眾基礎,北洋政府對于學生群體合理合法的紀念只能“不禁止與不干涉”[14],提前做好防范準備。
其二,參與紀念者以學生為主,紀念場所普遍在高校。通過對《申報》1920—1926年報道的梳理,筆者發現北洋政府時期的五四紀念,基本由學界主持,較少有工商界參加。甚至還出現過爭議:在江西九江的五四紀念中,學生要求商界一同紀念并歇業三日的要求遭到商界拒絕,學生本準備抗議,后在政府官員的調解下,變成“姑準(筆者注:指商界)休業一日、以曲全諸君愛國之苦心、還請勿再固執、學生始一一首肯”[15]。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五四運動的主體是學生,由知識青年對政府游行示威,故僅就五四紀念而言,主要是紀念學生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精神。而對于工商界來說,五一勞動節的紀念意義遠甚五四,兩者時間又相隔甚短,因此在五四紀念上,工商界的積極性不如學界。
其三,相比初期,五四紀念后期政治化內容有所加強。最初的五四紀念,紀念內容為宣傳愛國、自由、平等、博愛的五四精神,歌頌青年學生的高尚品德。但是時局在不停地變化,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否認北洋政府,出師北伐。所以從1922年起,《申報》上由廣東學界最先開始,利用五四紀念批判北洋政府的黑暗。隨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開始,從1924年起,北京、上海等地的學界總會在五四紀念期間邀請國共政要進行五四講演[注]1924年前文已提過;據1925年《申報》報道載:學界請了惲代英、邵力子、汪精衛、葉楚傖、吳稚暉等人;據1926年《申報》報道載:學界請了陳布雷、楊賢江、葉楚傖等人。,這樣的宣傳使五四紀念活動政治化,使國民黨“在全國擴大群眾基礎,一致擁護北伐,大多數五四青年參加了中國國民黨,努力國民革命。”[16]7共產黨亦是如此,周良書指出“……但是在具體的紀念中,中共更多的是關注‘五四’的政治意義。這一點上國共兩黨保持步調一致。”[17]由此看出,同為革命政黨的國共兩黨在革命時期都試圖將五四紀念政治化,為自身革命打下基礎。
實時定量PCR測定結果見圖4。結果顯示對照組PCNA、cyclinD1、cyclinE1的轉錄水平明顯強于ONFH 組 (P<0.001)。10 μmol/L GSK126 干預后,ONFH組PCNA、cyclinD1、cyclinE1的轉錄量較未干預前明顯增多(P<0.001),接近于對照組水平(P>0.05)。表明10 μmol/L GSK126能有效地促進激素性骨壞死組MSCs細胞內PCNA、cyclinD1、cyclinE1基因的轉錄。
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7—1949)
(一)紀念方式與內容
1.初期的興盛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國形式上完成基本統一,進入了蔣介石所謂“訓政”時期。同年,在政府主導下,多地舉辦了盛大的五四紀念儀式,筆者以紀念形式最隆重的上海和南京為例,見表1。
通過表1可以看出,此時的五四紀念因為官方主持的緣故,從黨政軍到社會各界皆出席參加;紀念場所也由高校操場變成公立體育場,甚至還增加了飛機表演等耗資頗多的紀念形式。但是紀念內容上卻更加政黨化,并沒有過多地宣傳五四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而是把五四運動與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北洋軍閥、反對共產黨結合在一起,對社會各界尤其是青年學生進行“洗腦”。
1928年4月中下旬,日本出兵山東,北伐戰爭也處在關鍵時期,全國局勢一度緊張,但南京國民政府仍然指示著五四紀念的內容,出臺了《五月革命紀念會籌備進行訊》《市指委會宣傳部 五四紀念宣傳大綱》[18]等各種宣告書,不僅如此,中央黨部還為五四紀念刊發了諸如“以三民主義來統一青年思想!總理是青年一生的模范!撲滅青年的蟊賊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萬歲!三民主義萬歲!”等二十余條五四紀念宣傳口號[19],并在首都南京中大體育館舉辦了黨政軍各機關團體等千余人參加的紀念大會[20]。南京國民政府所有的紀念舉措,其本質只為號召青年相信三民主義,相信國民黨,不要走入共產主義的“歧途”。

表1 1927年上海、南京兩地的紀念五四會議略表
注:表格內容根據《申報》報道歸納總結[注]《今日五四紀念》,《申報》1927年5月4日,第13頁;《五四學生運動紀念大會紀》,《申報》1927年5月5日,第13頁;《南京舉行五四紀念大會》,《申報》1927年5月6日,第4頁;《特別市黨部消息》,《申報》1927年5月7日,第14頁;《南京之五四紀念》,《申報》1927年5月8日,第7頁。
1929年是五四運動的十周年,南京國民政府在首都舉辦了兩場聲勢浩大的官方紀念儀式:一場由黨政各機關及民眾團體共同參與,在第一公園烈士祠舉辦,執委曹立瀛主持并進行報告[21];另一場在政府內部舉辦,主要由文官、參軍兩處全體職員參加,于政府大禮堂舉行,由文書局長楊熙績主持[22]。兩場報告都號召青年投身于革命,打倒以日本為首的帝國主義,勿忘國恥。1930年的五四紀念同樣如此,茲不贅述。
2.由盛轉衰與抗戰時期的短暫復興
1939年是五四運動二十周年,“五四”先后被共產黨,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定為“青年節”。從五四青年節設置以后,抗敵御辱成為五四紀念的主題[24]。雖然抗戰時期,由于外部環境的限制,《申報》上并沒有過多報道五四紀念的紀念儀式,但是卻刊登了許多鼓舞青年抗戰的文章,比如《青年團體發表宣言 紀念青年節 誓發揚五四革命精神有生之日皆報國之年》[25]《五四紀念日 陳誠發表 告革命青年書 應認識時代之使命 以完成抗建之大業》[26]等等,這些文章,多為名人或者各種團體所寫,其通過頗具感染性的語句宣傳了五四精神,號召青年學生堅持抗戰,為國效力。除了對青年學生的鼓舞,抗戰時期的五四紀念還肩負起了對前線戰士慰問的責任。1941年,陪都重慶召開五四紀念大會,百余人參加會議,在系列紀念儀式結束后,蔣介石致敬慰問抗戰前線戰士[27]。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的五四紀念,《申報》記者姚潛修特意拜訪周恩來,詢問其關于五四運動的看法,這也是《申報》首次在五四之際拜訪約談中共領導人[28]。
1942年五四前夕,國民黨突然否認五四為青年節,并命令各省不準紀念[29],故1942年以后直至1945年,《申報》上又幾乎停止了關于五四紀念的報道。
3.徹底政治化的紀念
隨著抗戰的勝利,五四運動紀念復又興盛。1946年,上海舉辦了盛大的五四紀念會,中央常務委員潘公展發表演講,嚴厲批判了共產黨的東北“陰謀”,并宣稱五四既為思想解放之先河,號召部分青年不要被共產主義思想所束縛[30]。不僅如此,5月4日當天,《申報》上發表了長篇社論,寫道:“今天國家抗戰勝利,我們已完遂了當初五四運動的一個政治目標,而在文化方面,建設的工作尤應隨建國大業的展開積極推進。我們要從狹隘的偏見中解放出來,建立適應中國國情的三民主義文化。”[31]同一時期,北平學界也在太和殿舉辦了紀念大會,參加人數竟達四萬余人[32]。
1947年北京大學舉辦了五四紀念周,七天內每天舉行不同晚會,并且舉辦了五四史料展覽會,展出了與五四運動有關的報紙、雜志、文告、私人函件、紀念物等原始史料[33]。這種用遺留實物進行紀念的方式不僅有趣、多元,而且能讓人們最為真實地接近歷史,避免了歷史記憶中的政治博弈。同年,在北大的紀念大會上,何思源、胡適、胡先骕強調了“所有黨派退出學校”“不談政治”[34]等觀點;然而同時期上海的紀念大會,不僅由一批國民黨黨政要員主持[35],中央委員張道藩還通過廣播大力宣揚國民黨的政治民主和共產黨的“陰謀”[36]。
1948年,北大的五四紀念,某學院獻給了校方一個“民主與科學”的旗子,同年,南京中央大學等四十余所單位舉行五四紀念時,則注重宣傳強調了“共匪”的罪惡[37]。
1949年的五四紀念,此時南京已經解放,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張道藩在廣州發表“‘五四’運動的認識”一文,鼓吹五四運動是三民主義文化思潮所發動的,號召青年們為三民主義努力,反對共產主義“新軍閥”[38]。
(二)紀念特點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國完成形式上的統一,但國內政局依舊復雜,情勢變化氣象萬千,這些都深深影響了當時的五四紀念,通過上文敘述,筆者總結如下:
其一,五四紀念由官方主持、社會各界都有參與,其規模、參與人數、紀念形式較之前更加宏大。對于青年學生的組織與動員,早在北洋政府時期,國民黨人就已認識到其重要性,所以自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中央黨部總是積極指導五四紀念。1931年以前,1939至1941年,以及1946年以后的每年五四紀念,在國民黨完全控制的區域內,政府、中央黨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都盡可能地親自主持紀念儀式。因為執政黨對社會記憶的操縱,是培養其政治合法性的關鍵途徑之一[39]。故在國民黨主持下的五四紀念,其紀念內容變成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打倒共產黨,信仰三民主義、擁護國民黨、擁護蔣主席,紀念場所布置變成了“中央搭大臺一座、上供孫總理遺像、黨國兩旗飄揚左右、中掛孫總理遺囑”[40],紀念形式上也增加了向黨旗、總理遺像三鞠躬、恭讀總理遺囑等形式[41]。實際上,這與國民黨政府的總理紀念周的紀念方式頗為接近[注]關于總理紀念周的儀式政治,詳見陳蘊茜《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五四紀念的對象是知識青年,國民黨將其與本黨政治文化聯系在一起,通過成年累月的宣傳灌輸,極大地向青年學生宣揚了其政治合法性,加強了其執政地位的鞏固與穩定。
其二,五四紀念的興衰程度與政黨政治、國內形勢密切相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伊始,五四紀念仍承習北洋時期國民黨紀念的宗旨,并在此基礎上擴大了規模,豐富了紀念內容和形式。1930年7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及《革命紀念日史略及宣傳要點》,把五四紀念排除在國民黨革命紀念日之外,[注]對此,張艷認為這是五四的“缺點”被國民黨發現:學生干政,沒有被三民主義指導,反傳統學習西方。詳見張艷《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五四”紀念》,載于《史學月刊》2013年第6期。所以1931年開始,國民黨五四紀念由盛轉衰。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中日民族危機上升為主要矛盾,動員一切力量抗戰成為戰時主旨,為了盡可能地動員鼓舞青年,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建議下,1939年,國民黨又開始紀念五四。并且,為了與中國共產黨爭奪青年,在中共延安西北青年救國會率先定5月4日為青年節之后,國民黨三青團亦宣布五四為青年節,給予了五四足夠的重視[42],此后,在三青團的帶領下,五四青年節經歷了曇花一現的繁榮。這個時期的五四紀念,相比戰前與戰后,少了對共產黨的抹黑,而更多地去關注對青年學生的鼓舞和對前方戰士的慰問,當然,也鼓勵了青年繼續團結在三民主義旗幟下。也正是在這一年,《申報》記者拜訪了周恩來,顯現出了抗戰時期中共地位的上升。在經歷短暫復興之后,1942年,考慮到五四運動背后并不蘊含國民黨的政治記憶,五四紀念并不能促使青年認同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國民黨內部對青年節的日期產生了極大的爭執。不僅在陪都重慶內部人們各持己見,以汪精衛為首的南京偽政府,也對此有不同意見,最終國民政府規定3月29日為青年節,汪偽政府規定5月5日為青年節,導致五四運動的紀念又落入低谷。抗戰勝利后,五四紀念雖又興盛,但在上海、南京等國民黨控制的核心地帶,五四紀念徹底變成了抹黑、詆毀中國共產黨的紀念,成為國民黨“得心應手”的政治工具。
其三,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五四紀念變成了一種歷史符號。歷史學家柯文指出:“周年紀念可在現實與歷史之間筑起一條情感橋梁,對紀念的人物和事件進行重新塑造,以適應現在的人們和政府不斷變化的看法。”[43]自北洋政府時期開始,根據現實政治的需求,國民黨已有意塑造五四紀念的內容,通過在青年學生中宣傳北洋政府的黑暗,試圖為北伐戰爭與國民革命宣傳造勢。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后,國民黨更是無所不用其極,不僅把五四紀念的儀式變成了總理紀念周的儀式,更通過對紀念內容上的宣傳來維護其統治的合法性。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五四紀念的儀式內容稍有不同,但是其“反對共產黨”的核心思想卻始終如一。通過特定的形式和內容,國民黨統治下的五四紀念,被建構成一個特定的歷史符號,成為改造集體記憶的一種手段。但是其是否成功了呢?歷史早已給出了答案。
三、結語
1919年的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促進了中國革命走向新歷程。而五四運動作為知識青年乃至于人民群眾的集體記憶,是一個凝聚青年學生、動員其情感的政治符號。對五四運動進行紀念,不僅可以緬懷五四愛國精神,更能夠有效動員知識青年參與革命。通過對以《申報》為中心的考察,可以發現北洋政府時期的五四紀念,由于是民間自發組織,故能夠較為純粹地紀念五四精神。國民黨則是有意識地利用五四,其以積極的姿態主持這一紀念,把五四精神與三民主義相結合,賦予了五四紀念的政治含義,意在讓當時國民尤其是青年學生對其政黨文化有共同的認可,從而維護其黨國體制的正統性和合法性。但是其把五四紀念過度符號化,讓五四精神失去了以往的內涵,也引起了學界的反感。
隨著20世紀以來民族主義的發展,國家認同的根源在于共同的歷史記憶。五四記憶作為知識青年乃至全體中國人的集體記憶,承載著一代人共同的榮辱。歷史告訴我們,集體記憶是含有某種精神意義的象征符號,五四紀念旨在保留、傳承五四記憶,從而塑造出對國家、政黨的認同。今天,五四運動早已遠去,中華民族也已然崛起,但是以史為鑒,促進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仍需當代青年砥礪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