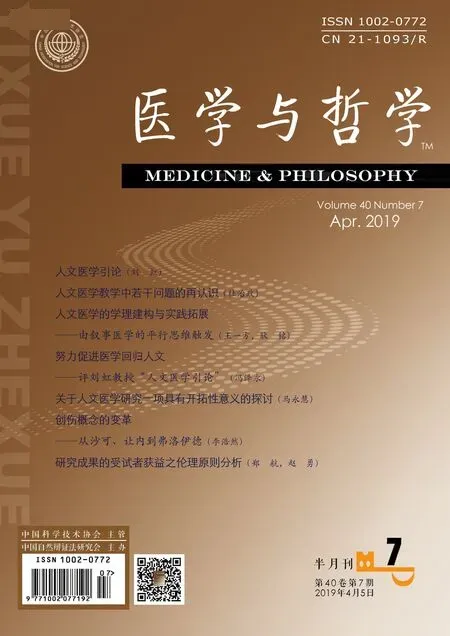人文醫學是完整的精神病學不可缺少的部分
朱承剛
在醫學理論體系中,有一門以醫學人文精神和醫學人文關懷為研究對象的醫學分支,即人文醫學。回顧精神病學的歷史和現狀,作為一名精神科醫生尤其想為人文醫學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價值擊鼓點贊,同時,寄希望人文醫學的不斷發展,呼喚人文醫學更多的研究成果為精神病學所用。
1 人文醫學的缺席:成為“罪人”或“零件”的患者
希波克拉底在2 400多年前就指出“神圣病”(精神病)不是神或鬼魅所致,在疾病是自然過程這一點上,“神圣病”與其他疾病沒有什么不同,“神圣病”患者理應受到醫學和社會的善待。盡管如此,人類社會在其后的兩千年中仍將精神病患者視為“被神所詛咒”的“罪人”。精神病患者或者被監禁在家中,或者被監禁在瘋人院里。中世紀時對精神病人的異常行為施以懲罰并不被視為犯罪,包括流放、監禁、燒炙、勒死、砍頭、活埋等記載屢見不鮮。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指出:瘋人院不是一個醫療機構,而是一個司法機構。一旦被這些司法機構判為“精神病”罪,便再無翻身可能,終身被打上精神病的烙印。
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代《人權宣言》誕生,對人的尊重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時代背景下法國比奈爾(Pinel)醫生提出以人道主義態度對待精神病人,第一次解除其“罪人”的枷鎖,還給“罪人”自由,開始觀察研究患者,開創了從瘋人院到醫院的轉變。
在人文關懷的指引下,從研究疾病的角度出發,德國精神病學家Kraepelin通過仔細觀察患者癥狀的發展變化對精神病進行了分類,奠定了精神病學的基礎。同時代的弗洛伊德更是將精神病患者視為需要尊重的“人”,主張用傾聽和對話的方式開展治療,開創了精神分析學派。人們開始嘗試各種心理治療方法(催眠、心理分析、認知行為療法等)、物理方法(電休克、胰島素休克、額葉切除術等)以及各種藥物治療方法,盡管其中有些方法很危險、殘忍最終很多被證明無效,可是不可否認這些嘗試均不以懲罰而是以治療為目的,這是人類文明的重大進步。
1952 年,氯丙嗪被證明對精神分裂癥有效,由此精神病學史上出現了藥物治療,至今已有上百種精神藥物出現,由此改變了歷史格局,藥物用無可辯駁的療效反證了精神病具有生物學屬性,患者獲得了病人而不是罪人的身份,得以獲得科學的治療及管理。
希波克拉底的醫學人文精神、比奈爾醫學人文關懷的實踐以及殘酷的瘋人院蛻變為體現現代文明的精神病院的歷程體現了人文醫學思想在醫學發展歷史中不斷升溫的大趨勢。但是,當代醫學的發展正面臨著人文醫學溫度下降的窘境。藥物確切的療效使得醫生的醫療重心在“投藥”,視患者如同技術流水線上的零件,忽視對患者的尊重和關愛,人文醫學的價值在醫療實踐中是否真的下降了?筆者認為絕非如此,人文醫學凝聚醫學發展思想史中之精華,對醫學人文精神和醫學人文關懷進行系統化、理論化的研究,這是當代醫學發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趨勢。
作為一名醫生,筆者特別認同“人文醫學是醫學的組成部分,人文醫學是醫生和醫學家看醫學,是探索在醫學中落實人文的問題”這樣的提法。人文醫學彌補基礎醫學、應用醫學和技術醫學之短板,人文醫學的存在,體現著醫學人文本質和溫度。從這個意義而言,如果人文醫學缺席,醫學將不再是人的醫學;病人將還會是“罪人”或者是“機器零件”。
2 人文醫學的引領:踟躕前行的精神病學
人文醫學的引領有助于厘清精神科一系列臨床問題的處置思路。毋庸置疑,精神病學的診斷和治療落后于醫學其他學科的發展。首先,從疾病的診斷而言,精神疾病的病因尚未明了,至今沿襲百年前提出的癥狀學標準。不同的專家對同一患者的診斷有不同意見在精神科是常見現象。美國有研究表明,雙相情感障礙的明確診斷平均需要十年的時間。精神科的醫生常常面對是否需要對前次就診的診斷做出修正的問題,按照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修正診斷往往造成患者的誤解,認為之前的診斷是誤診,醫療陷入沒有必要的糾紛,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尚無良策。
其次,目前精神疾病的分類是基于專家會商的共識,無可避免地受到專家的文化背景和個人觀點的影響,突出的兩個例子:一是在1990年之前,同性戀被認為是一種精神疾病,并有相應的診斷標準,之后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同性戀從疾病目錄中去除,十年之后中華醫學會接受了國際的觀點,在中國的診斷標準中將其剔除,在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中作為一個醫生是機械地根據標準診斷,還是靈活地做出變通?另一個例子是2018年“網絡成癮”被列入精神疾病的診斷,該消息一經公布就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爭議,一個沉迷于上網的少年應該由精神病院進行治療嗎?這樣類似的問題是生物醫學、精神醫學難以解答的,離開了人文醫學的深入思考和系統研究只能是盲人瞎馬。
再者,人文醫學和精神醫學共同研究成果將有助于對患者身份的人文考量,解決如何使更多的患者能在第一時間得到救治的現實問題。精神科的臨床工作中醫生最先遇到的問題往往是患者拒絕治療,要求出院的問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基本上是不認可自己生病了,精神病學專門用“無自知力”來定義這樣的情況,并作為疾病嚴重程度的參考標準之一。由此而派生出“非自愿住院”,也就是老百姓所說的“被精神病”的社會問題。“一個不認為自己有病的人為什么要被送去看病?”患者的家屬也常常左右為難,不治療無法正常生活,治療又恐招致患者的怨恨。《精神衛生法》無奈地使用了“發生或有傷害自身的行為或危險,或者具有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危險”這樣拗口的表述作為強制住院的前提條件。實踐中當精神疾病患者到達傷人或自傷的程度時,往往病癥已相當嚴重,以善為目的的救治該在什么時候介入,目前生物醫學并不能給出答案。人文醫學認為身體既是生理的存在,又是心理的、社會的存在;疾病既是自然的、病理的過程,也是文化的、歷史的過程,從人文醫學的這個角度認識精神病患者身份辨析的影響因素,既有生物醫學、精神醫學的標準,也有社會醫學、醫學心理學、社會文化和醫學人文的考量。
3 精神醫學的呼喚:醫學人文精神與醫學人文關懷
人文醫學以醫學人文精神與醫學人文關懷為研究對象,這恰恰是生物醫學、精神醫學所迫切需要的。
首先,患者的感受是人文醫學的主要研究內容之一,也是每一例患者都會出現的問題,如患者揮之不去的“病恥感”。目前精神科藥物的治療以對癥治療為原則,重點在癥狀控制而無法做到消除病因,尚達不到所謂“根治”。大多數精神疾病患者需要長期穩定服藥,甚至終身服藥,尤其重性精神障礙患者(如精神分裂癥、難治性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長期服藥穩定治療已是精神科治療過程中的共識,多項國內外研究已經證實服藥依從性好壞直接決定患者正常社會功能的恢復情況。但現實中我們往往可以看到很多患者私自減藥、停藥后病情復發,因此常常被反復送入院。其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偏見和歧視仍存在,患者的病恥感強,“生病了才需要吃藥,病好了為什么還需要吃藥?服藥就是精神病人,不服藥就沒有病”。很多患者認為如果自己一直服藥,精神病人的身份就無法擺脫掉,往往希望通過盡快停藥來證明自己已經恢復正常了。另一個原因是精神科藥物尚普遍存在副作用,口干舌燥、乏力、嗜睡、心動過速等,目前的治療手段尚不能讓所有患者完全消除副作用。一線醫生常常面對患者的疑問“為什么要堅持吃會讓自己不舒服的藥?”甚至稱“吃藥讓我覺得頭暈腦脹,我都不是我自己了,我寧愿生病做我自己。”這樣的患者亦屢見不鮮。類似生病吃藥這樣的基本問題尚是精神科的難題之一,精神病學的實踐無法回避“關注患者身體的感受,傾聽患者身體的呼聲”這一命題。依照人文醫學患者感受的理論,精神病患者的感受是其身體個體的、獨特的、無法抹除、無法替代甚至是難以言說的體驗。精神病患者活在他的感受世界中。在生物醫學目前尚無法很好地解決“根治”以及副作用的當下,期待人文醫學在消除社會和患者本人的病恥感上提供更多的研究成果資源,指引解答如何減輕、消除病恥感提高依從性的難題。
其次,治療后患者如何回歸社會是精神醫學的重要問題,更是醫學人文關懷的實施問題。精神科將恢復社會能力作為疾病恢復的重要評價指標,目前尚存在諸多困難。突出存在的問題有三:其一,目前我國精神科治療主流以封閉住院治療為主要治療方式,精神科住院期間患者必須服從醫院的日常生活管理,院內生活相對單調,即便是在大力開展康復治療的沿海發達地區的筆者所在醫院,也尚達不到有充足的人員和設施使得患者在住院治療的同時能很好地完成社會功能的康復。短則4周~6周,長則數月被管理的生活經歷使一部分患者對自身產生“醫源性”自卑感。普通醫院統一的病號服因為有行動的自由對患者尚不構成不適感,可是精神科醫院統一的病號服加上鐵欄桿和嚴格的監管,使很多患者陷入恐懼,多位患者家屬反映“走進住院病房就感覺很壓抑,很像是監獄,正常的人住院一段時間怕是都要瘋了”。如何既保證治療,又能有更舒適的治療環境?歐美發達國家也在建立或是廢止大型醫院的社會政策方面不斷嘗試。如何取長補短,急需要人文醫學的建議。其二,目前隨著我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進步,為照顧管理重癥患者的生活,將重癥患者登記在社會管理系統中的政策正在逐步實施,這項起源于香港對精神病患者傷人事件的防范性法規,在監管患者的基礎上給予患者醫療、生活援助,無疑構筑了精神患者的安全線,可是因為生病而不是犯罪而被登記管理造成了部分患者極大的心理壓力,感覺是社會的“另類人,被監管對象,有害的人,無法管理自己的人”,這樣的身份遭受社區民眾的排斥構成了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的障礙之一。2018年深圳市寶安區在分配公租房時,將17戶租戶的公示信息備注為精神殘疾(17戶精神殘疾家庭中有15戶是自閉癥兒童家庭),未曾想引起了其他社區居民的抗議、強烈拒絕精神病患者的搬入,這一事件無疑是人文的悲哀。其三,出院后的精神疾病患者能否正常婚姻生育,是臨床醫生每每被咨詢的問題。對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政府通過的《遺傳病后裔防治法》是精神科醫生所不能忘記的黑暗一頁。該法律強制規定:“任何患有遺傳疾病的人都將接受外科手術絕育。”其制定的“遺傳病”列表中包括有智力缺陷、精神分裂癥、癲癇、抑郁癥。二戰后該法律遭到全面批判,可是對于治療后的精神疾病患者,婚姻暫且不談,就生育問題而言,很長一段歷史時間里精神科醫生通常都會不建議其生育。目前醫療實踐中基于生物醫學尚不明確遺傳機制的現狀,醫生通常會尊重患者本人及其配偶的意愿,不做干涉,這無疑是人文的進步。
再者,相較其他疾病,精神疾病患者尤其需要“社會支持” (包括親人、朋友、社會的幫助),社會支持是醫學人文關懷的重要表現形式,直接影響患者的預后,是判斷精神疾病轉歸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社會支持對康復有促進、保護作用,惡劣的社會支持誘發疾病的復發。將病患視為“投藥”的對象,視為“零件”的醫生忽視幫助患者獲得社會支持,因而不可能取得最好的療效。如何幫助患者獲得良好的社會支持是精神科醫生的重要工作,完成這一工作可以說是完完全全需要在人文醫學的指引下才有可能取得成果。在實踐中,不同于一般的軀體疾病,精神疾病的病患在發病時往往給周圍的社會關系帶來巨大的壓力甚至是恐懼。精神科常在深夜接收被家屬撥打110送來救治的患者,患者的家屬在送患者入院的時候無不身心俱疲,對精神病院和精神科的治療充滿恐懼的患者家屬并不是個別現象,常說“不要打我兒子,不能給他吃把他變傻的藥啊”。對于復發的患者,家屬帶著悲觀、失望、抑郁情緒的更是比比皆是,“反正是治不好了,出院了也實在是管不了,就讓他長期住在醫院里吧”;在學校或者工作單位發病的患者,社會機構對患者是否還可以恢復學習、工作往往疑慮重重,希望從醫生這里得到評估和保證;處于經濟糾紛中的患者,相關方希望從醫生這里了解患者是否有相應的行為能力。離開患者家屬的安撫教育,患者在治療中得不到支持,在治療后得不到理解;離開患者學習工作環境相關人員的理解,患者康復后生活阻力重重;離開對相關方的溝通告知,患者會遭受不必要的損失。“一個人從學醫那天開始,不僅要學習自然科學和醫學知識,而且要付出相當的時間與精力來學習社會、人文和管理。”若非如此,便不能建立良好的社會支持,因此影響治療的成敗也并非危言聳聽。
精神科臨床工作的共識是基于現有生物醫學的水平上,精神病專科醫生和患者、患者家屬、患者的周邊社會環境的溝通交流不是一個治療中可有可無、錦上添花的工作,而是一個事關治療成敗的不可或缺的工作。“生物醫學求真,人文醫學求善”,醫者研究人文醫學,重在醫學實踐中如何運用人文。精神科醫生最熱切地期盼人文醫學的發展,為以上掛一漏萬的實踐問題給出解答,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