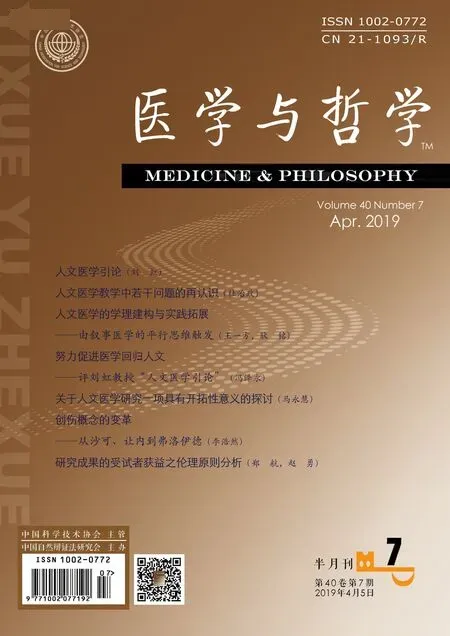努力促進醫學回歸人文
——評劉虹教授“人文醫學引論”
馮澤永
1 回歸人文是醫學的必由之路
劉虹教授的“人文醫學引論”(以下簡稱“引論”)的主要意義,就在于強調醫學回歸人文。“引論”強調人文對醫學的意義,指出:“醫學人文精神是醫學世界的統領”,“醫學價值的體現最終要在醫學人文關懷上才能得以顯現。醫學人文關懷是醫學人文本質可見端、可感態、可觸面;是醫學人文精神走向醫學實踐的介質。”
之所以醫學必須回歸人文,就在于人文是醫學之魂! “人文”一詞最早出現在《易經》。《易經》寫道:“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按照錢穆先生的解釋,人文精神其實就是在“人與人、民族與民族、文化與文化相接相處的”時候必須堅持的以人為本的精神。醫學,正是以人為本,以人的健康為本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門科學。因此,早在兩千多年前,《孟子·梁惠王上》提出“無傷也,是乃仁術”,就把醫學定位于“仁術”。《黃帝內經》強調“天覆地載,萬物備悉,莫貴于人。”唐代名醫孫思邈認為醫者應有“誓愿普救含靈之苦”的信念。晉代楊泉也說:“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西醫在兩千多年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提出:醫術的唯一目的是解除和減輕病人的痛苦,是為病家謀利益。1948 年世界醫學會制定的《日內瓦宣言》,仍然強調,“行醫中一定要保持端莊和良心。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一切的首位”。由此可見,幾千年來中西醫都有著共識:醫學的目的因、動力因、本質和靈魂就是人道,就是人文。
之所以醫學必須回歸人文,還在于醫學必須遵守人的規范。科學,尤其是醫學,它的一切研究、服務及其過程都必須遵守為人服務的規范。它必須把人的地位放得高于一切,它的一切成果必須為人的健康、幸福和發展服務。醫學必須回歸人文的另一個理由,在于醫學實踐不僅僅需要科學方法,也需要人文方法。因為只有兩種方法的結合,才能使我們全面了解具有生物、社會和心理屬性的人,才能與服務對象共情共理。
然而,在過度市場化和利益的驅動下,在功利主義與技術主義的多重沖擊下,當代醫學出現了對人文定位的偏移。這種偏移既表現為醫源性、藥源性疾病增加和過度醫療突出,又表現為醫患關系的疏離、不信任和日趨緊張。正是這種偏移,使醫學回歸人文顯得更加緊迫和重要。
2 值得深入研究和討論的幾個問題
在醫學回歸人文的過程中出現了人文社會學科與醫學的交叉與融合,“引論”對這些交叉融合的學科進行了相應的界定與劃分。文章還指出:“我國人文醫學創建人,著名人文醫學學者杜治政教授指出:人文醫學與醫學人文之間存在的不是名詞之爭,而是存在內容、特征與價值方面的區別之實。厘清人文醫學與醫學人文的關系,闡明人文醫學的本質特征與獨特價值,是人文醫學存在與發展的基礎。”由此出發,“引論”對人文醫學的概念、研究對象、理論基礎、核心內容和研究方法進行了十分有意義的探索,并進一步與醫學人文學科群進行了區分。文章的意義不在于給出了概念、劃定了邊界和指出了方法,因為這些問題還在研究的起步中,還沒有定論。人文醫學是處于嬰兒階段的學科,如果有了定論,它就已經成熟甚至老了。“引論”的意義就在于它提出了值得研究的一些內容。
“引論”對人文醫學與醫學人文的關系作了非常有意義的探索,對二者的歸屬、聯系和區別都作了有深度的研究。但是,把衛生法學、醫學社會學等學科納入醫學人文學科群是否妥當?學科應該如何劃分?這些都還值得探討。事實上,所有學科可以劃分為哲學、數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哲學和數學分別從“質”和“量”的角度對自然、社會和人進行認識和研究,屬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科。自然科學以自然之物為研究對象,認識自然之“事實”,尋求自然規律。社會科學以“人”所組成的社會或組織為研究對象,認識社會之“事實”,尋求社會規律。人文學科是研究人本身的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人”。其基本任務是探討人的本質、建立價值體系和塑造精神家園。醫學兼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特點,但是主要屬于自然科學。在醫學回歸人文和社會化的過程中,社會科學與醫學、人文學科與醫學都出現了雙向交叉融合的傾向。社會科學融入醫學出現了社會醫學、行為醫學之類的學科,落腳點在醫學。醫學充實社會科學則有了醫學社會學、衛生經濟學、醫事法學等學科,落腳點在相應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融入醫學出現了敘事醫學(文學與醫學)、音樂治療學、繪畫治療學、戲曲治療學、修身養生學等學科,落腳點在醫學。醫學充實人文學科則有了醫學哲學、醫學倫理學、醫學文學、醫學美學一類的學科,落腳點在相應的人文學科。因此,“引論”對眾多交叉融合學科群的劃分是值得討論的,人文醫學究竟是一個學科群還是一個獨立的學科也是可以討論的。
研究對象是劃分學科很重要的依據。“引論”說:“人文醫學研究對象的特征是以求善為目標”,那么它與醫學倫理學的區分在什么地方呢?這也是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的地方。
總之,“引論”是一篇有價值的文章,它強調回歸人文、發展人文是醫學的必由之路,并且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的內容。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關注和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