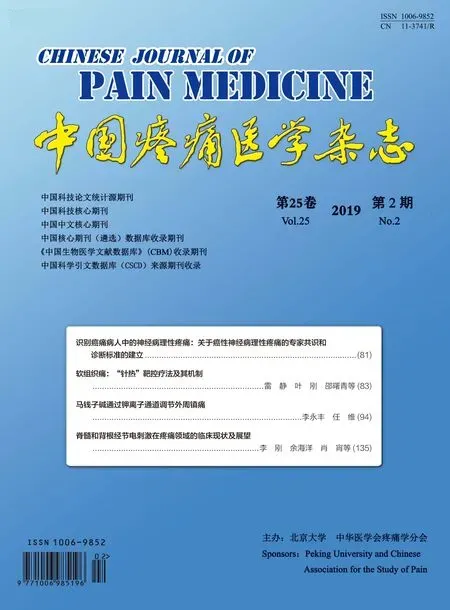HCN通道調控痛覺相關神經元興奮性突觸傳遞的研究進展*
彭斯聰 張達穎 柳 濤
(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1兒科;2 疼痛科,南昌330006)
超極化激活環核苷酸門控陽離子 (hyperpolarization-activated cyclic nucleotide-gated cation, HCN)通道廣泛表達于中樞和周圍神經系統[1],參與調控神經元的興奮性和神經遞質的釋放,在慢性疼痛如機械超敏和觸誘發痛的發生發展中具有關鍵的作用。谷氨酸介導的突觸傳遞的長時程增強(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可導致痛覺回路相關神經元對外周傷害性刺激的反應增強,產生中樞敏化,這是導致慢性疼痛的主要病理學基礎[2]。因此,通過抑制谷氨酸能興奮性突觸傳遞從而緩解中樞敏化,有望成為慢性疼痛治療的新方向[3]。目前研究發現,HCN通道在不同痛覺相關神經元上的亞細胞定位具有異質性,且其調控興奮性突觸傳遞的作用因神經元類型而異,并與多種蛋白質、離子通道或受體等相互協作,部分機制尚未完全闡明。因此,我們就當前國內外研究現狀,首次總結了HCN通道在痛覺相關神經元的亞細胞定位情況,及其對興奮性突觸傳遞的調控作用和機制,旨在為慢性疼痛的基礎研究提供參考。
1.HCN通道的基本特性及其與慢性疼痛的關系
HCN通道于1998年被Santoro和Ludwig等人首先報導[4,5],屬于環孔陽離子通道和環核苷酸門控通道超家族,由6個跨膜結構域(S1-6)組成,其中S4為電壓感受區,S5和S6之間形成陽離子通道孔,此外還有一個位于胞內側羧基端的環核苷酸結合區,可感受胞內環核苷酸濃度的變化,進而調控通道的開放[1]。因此,HCN通道是受電壓和配體雙重調控的。細胞膜超極化以及胞內cAMP、cGMP或cCMP均可激活HCN通道,產生內向Na+-K+混合陽離子電流,即超極化激活陽離子電流 (Hyperpolarization-activated Cation Current, Ih)。根據激活動力學的不同,HCN通道可分為四種同源亞型,分別為HCN1、HCN2、HCN3和HCN4,它們的激活時間依次減慢[1]。在環核苷酸門控方面,HCN通道對cAMP的敏感性較cGMP和cCMP高;HCN2和HCN4對cAMP敏感,而HCN1和HCN3則相對不敏感[1]。
2003年,Chaplan等人運用脊神經結扎(spinal nerve ligation, SNL)模型,首次發現了HCN通道可增加背根神經節(dorsal root ganglia, DRG)細胞的自發放電頻率,產生觸誘發痛,表明HCN通道與病理性疼痛密切相關[6]。隨后,大量國內外研究證實,HCN通道在神經病理性痛、炎性痛和化療藥物誘發的周圍神經病變(chemotherapy-induced peripheral neuropathy, CIPN)中,均扮演著重要角色,通過影響神經元的靜息電位(resting membrane potential,RMP)、自發放電頻率、神經沖動傳導速率、遞質釋放和樹突整合等多種機制調控疼痛的發生和維持(見表1~2)。動物行為學實驗研究發現,HCN通道阻斷劑ZD7288或抑制劑伊伐布雷定、西洛雷定以及利多卡因[7]等藥物,對于神經病理性痛和炎性痛所致的機械痛敏、冷熱覺痛敏、觸誘發痛和自發性疼痛等,均具有明顯的緩解作用[1]。

表1 HCN通道在神經病理性痛中的作用

表2 HCN通道在炎性痛和CIPN中的作用
2.HCN通道在痛覺相關神經元中的分布
疼痛上行傳導通路由DRG、脊髓背角、腦干頭端腹內側髓質(rostral ventromedial medulla, RVM)、腹外側導水管周圍灰質(ventrolateral periaqueductal grey, vlPAG)和藍斑核、丘腦腹后核、杏仁核以及大腦內側前額葉皮質(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和前扣帶回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等部位的神經元和神經纖維組成[8]。此外,海馬、內嗅皮層、小腦、中腦等腦區亦與痛覺調控相關[9~11]。其中,海馬和內嗅皮層可通過增強疼痛相關的焦慮而使痛覺放大[9],小腦的深部核團、蚓部和半球小葉通過與RVM、vlPAG和mPFC等腦區形成直接或間接的神經聯系進而調控疼痛[10],而中腦腹側被蓋區和黑質的多巴胺能神經元可通過D2受體的激活而產生鎮痛作用[11]。HCN通道在上述痛覺相關區域內神經元的興奮性軸突末梢、樹突和胞體均有表達(見表3),這是其調控興奮性突觸傳遞的解剖學基礎[8]。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和免疫金法等實驗證實,HCN通道表達于痛覺相關神經元的軸突末梢,但亞型分布不同。小直徑的DRG神經元,即C類初級感覺神經元,是傳導外周痛覺信號的初級傳入神經元,其軸突末梢主要表達HCN2亞型[12]。痛覺傳導通路的初級中樞——脊髓背角II層,即膠狀質區(substantia gelatinosa, SG),其興奮性軸突末梢表達HCN1、HCN2和HCN4,其中以HCN4為主[13]。此外,在其它痛覺相關神經元,如ACC神經元軸突末梢主要表達HCN2[14],而海馬顆粒細胞[15]和內嗅皮層神經元[16]的軸突末梢主要表達HCN1。然而,目前對于HCN3亞型的研究較少,尚無其在神經元軸突末梢表達的報道。HCN通道在痛覺相關神經元的樹突也有分布,這是其調控樹突整合和突觸可塑性的前提條件。例如,在ACC和丘腦神經元中,HCN1、HCN2和HCN4在樹突均有表達[14]。此外,免疫組織化學染色和電生理實驗證實,HCN通道在上述多種痛覺相關神經元的胞體亦有不同的表達。例如,在DRG神經元中,表達于C類神經元胞體的僅為HCN2[17],而在Aδ類神經元胞體則表達HCN1-3[18],但在SG神經元的胞體,HCN1-4均有表達[13]。以上研究結果表明,HCN通道在不同神經元中的表達水平和亞細胞定位存在差異,提示其調控興奮性突觸傳遞的作用也可能不同。

表3 HCN通道在痛覺相關神經元的亞細胞定位
3.HCN通道對痛覺相關神經元興奮性突觸傳遞的調控作用
現有研究表明,HCN通道對神經元興奮性突觸傳遞的調控作用是雙向的,存在增強和抑制兩種效應。增強效應主要見于SG神經元[3]和vlPAG神經元[19]等,HCN通道激活或表達上調后表現為谷氨酸能興奮性突觸傳遞的增強。例如,在部分坐骨神經結扎(partial sciatic nerve ligation, PSNL)模型和甲醛炎性痛模型的ddY系小鼠中,Ih激活可增加SG神經元的興奮性突觸后電流(excitatory postsynaptic currents, EPSCs),而ZD7288阻斷Ih后可減少EPSCs,且腹腔或鞘內注射ZD7288均產生明顯的鎮痛作用[3]。此外,在SD大鼠的坐骨神經慢性壓迫性損傷(chronic constriction injury, CCI)模型中,vlPAG神經元的HCN1和HCN2表達上調,導致其自發性(spontaneous) EPSCs頻率增加,且該作用可被ZD7288阻斷[19]。相反,減弱效應見于mPFC[20]、丘腦底核[21]、內嗅皮層[16]、中腦黑質多巴胺能神經元[22]、新皮質椎體神經元[14,23]以及杏仁核快速放電中間神經元[24]等部位,阻斷HCN通道后谷氨酸能突觸傳遞是增強的。例如,Cordeiro等運用Long-Evans大鼠的SNL模型,發現在mPFC的 II/III層錐體神經元中,抑制Ih的激活導致微小(miniature) EPSCs的頻率的增加[20]。
在神經環路中,興奮性和抑制性神經元的突觸傳遞活動是相互影響的,共同維系局部的興奮-抑制平衡。因此,HCN通道對神經元興奮性突觸傳遞調控的差異,可能與神經元類型和神經環路的功能不同有關。此外,這種調控效果還可因動物種屬和模型制備方法的不同而異。
4.HCN通道調控興奮性突觸傳遞的分子機制
HCN通道具有電壓感受區和環核苷酸結合區兩個調控位點,膜電位超極化和胞內環核苷酸濃度升高均可激活HCN通道。其中,膜電位變化可影響多種離子通道的電化學驅動力和激活及失活;而環核苷酸通過與其下游的多種信號調節通路偶聯,進而調控神經元的功能。以上特性使HCN通道調控興奮性突觸傳遞的分子機制具有多樣性,根據作用靶點不同可進一步分為突觸前結構(軸突末梢)和突觸后結構(如樹突或神經元胞體)兩大類。
突觸前末梢的調控機制主要有:調控胞內Ca2+或Na+離子濃度[14,25]、膜電位[25]及多種胞內信號通路(如Ca2+/AC1-cAMP-PKA信號通路[14,25]和NOGC1-cGMP信號通路[26,27])。例如,Koga等發現,ACC神經元的LTP與腓總神經結扎的慢性痛行為有關,ZD7288可抑制ACC神經元的LTP,而ACC內注射ZD7288可產生明顯的抗焦慮和鎮痛效果,且此效果依賴腺苷酸環化酶1 (AC1)和蛋白激酶A(PKA)的激活[14]。而Wang等在感覺皮層神經元(II/III層)的研究中發現,抑制胞內的鳥苷酸環化酶(NO-GC1)可降低胞內cGMP水平,進而抑制Ih的激活,最終減少突觸前末梢釋放谷氨酸[27]。
在突觸后結構中,HCN通道調控樹突整合和EPSPs的機制主要有:增強離子型谷氨酸受體(NMDA受體[23]和AMPA受體[23,26])介導的電流、上調胞內Ca2+濃度[23,28]以及激活多種胞內信號通路(如PLC-PKC信號通路[29]、TNFα-TNFR1-p38信號通路[30]和JNK-NO-cGMP信號通路[31])。例如,在多種疼痛模型中觀察到DRG和脊髓背角的p38 MAPK信號通路激活,而致痛因子TNFα可通過激活SG神經元胞內的TNFα-TNFR1-p38 MAPK信號通路抑制Ih,增加SG神經元的sEPSCs從而產生致痛效應[30]。在新皮質錐體神經元中,ZD7288阻斷Ih后可通過改變遠端樹突簇的Ca2+信號,增加頂樹突簇的興奮性傳入,從而顯著增加AMPA和NMDA受體介導的EPSP幅度[23]。
此外,HCN通道在調控興奮性突觸傳遞的過程中,還可與其他蛋白質、離子通道或受體協同作用,參與非痛覺相關的生理功能,例如運動功能、聽覺、認知、學習和記憶等。目前研究發現,可與HCN通道共同調控興奮性突觸傳遞的分子包括細胞骨架蛋白[32]、質子泵[32,33]、K通道[23,34~36]、鈣通道[16,21,37]、α2去甲腎上腺素能受體[29]以及大麻素受體[31]等。例如,在PFC錐體神經元中,阻斷Kir2和Kleak通道后使膜電位去極化,引起Ih去活而增強EPSP[34]。然而,在痛覺調控中是否存在上述機制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以上研究結果表明,HCN通道調控神經元興奮性突觸傳遞的機制因神經元類型而異,且具體的分子機制較為復雜,有待將來進一步研究。
5.現狀和展望
綜上可知,HCN通道在神經元軸突、樹突和胞體均有分布,但表達的亞型不盡相同;其對神經元興奮性突觸傳遞存在雙向調控,而具體作用和機制因神經元類型而異,同時還受到動物種屬、疾病模型制備方法、神經環路的特點以及興奮-抑制平衡等因素的影響。盡管如此,HCN通道抑制劑被認為可有效減少痛覺相關神經元的興奮性突觸傳遞,抑制中樞敏化的形成,從而緩解異常痛覺的產生,因此為慢性疼痛的研究和治療提供了新的思路。
雖然HCN通道目前被認為是治療神經病理性痛和炎性痛的新靶點之一[8],但目前研究仍存在不足之處:①動物和人類作為有機的整體,在慢性疼痛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存在諸多代償機制,而目前在體的動物研究及臨床研究均較少,限制了其應用。②HCN通道的4種亞型的蛋白序列存在高度同源性(80~90%),目前尚無特異性的HCN通道亞型阻斷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關研究的進行[1]。③由于HCN通道在心臟、中樞和外周神經系統分布廣泛且具有異質性,對多種生理功能(例如心臟起搏和心率、神經節律、學習和記憶、視覺、痛覺等)均有重要的調控作用[1],相關藥物的副作用尚未明確,因此,對HCN通道調節劑治療慢性疼痛的研究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