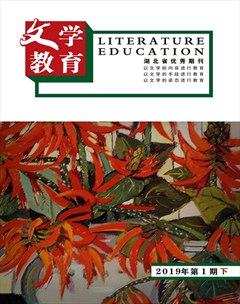《天堂蒜薹之歌》版本研究
孫東洋
內容摘要: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有諸多版本,各個版本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從初刊本到初版本的變化,主要是主旨去政治化,規范標點與完善字詞句,更細膩地描寫環境與人物,強化民間色彩與民間趣味。從初版本到修改本的變化,主要是變更了小說的題目和題記,作者作了一篇自序,對張扣的歌謠詞做了大量修改。從修改本到再改本的變化,主要是作者新作了一篇自序,新增了一個章節并修改了部分章節開頭的歌謠詞,交代了對張扣和高馬的悲劇結局。通過數次的修改,《天堂蒜薹之歌》的文學性得到了提高。
關鍵詞:莫言 《天堂蒜薹之歌》 版本 文學性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創作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對于莫言的長篇小說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學者們從小說的人物形象、敘事、語言、思想乃至翻譯問題等方面進行了很多研究,但卻很少注意它的版本問題。我們應當知道,該書版本眾多,對不同版本的閱讀與研究可能會產生不同的感受,得出不同的結論,因而在進行小說研究時有必要考慮到該書的版本問題。《天堂蒜薹之歌》創作于1987年,迄今至少有五個版本:1988年,最早刊發于《十月》雜志第1期(下稱初刊本);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下稱初版本);1993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修改本(下稱修改本);2005年,南海出版社再次出版(下稱再改本);2009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所謂的“全新本”(下稱全新本)。本文對《天堂蒜薹之歌》的各個版本的比對中,發現前四個版本之間的變動較大,而全新本之于再改本的變動較小,而且集中在對修改本的印刷錯誤和不規范字詞的改正上。故本文詳細陳述從初刊本、初版本、修改本到再改本之間的版本差異,探討莫言的修改原因以及影響,同時窺探莫言文學創作觀念的變化。
一.從初刊本到初版本
初刊本的發表與初版本的發行雖是同一年,但前后兩個版本卻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來說,初版本較之初刊本的改變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主旨上,去政治化;二是形式上,標點和字詞句的規范與修飾;三是描寫上,環境描寫和人物描寫更加細膩;四是立場上,民間色彩和民間趣味的強化。
就主旨的去政治化來說,我們可以從文本的變更與刪減上看到。在初刊本中,題記的署名為“斯大林”,而在初版本中則變為“名人語錄”。在初刊本的第五章中,小說人物高羊和高羊老婆既有對時政時事的議論:“都是氣數,”高羊說,“七六年又是山崩又是地震的,大家嘴里不敢說,心里也都有了數”[1],也對一些政治人物發表議論。但這些與時政相關的議論,在初版本中盡被刪去。由以上兩點,我們可以看到,初版本致力于刪去初刊本中與蒜薹事件不相干的政治人物與事件,以使小說與現實生活中的政治保持距離。
其次,在標點和字詞句的修改上,初版本比初刊本更重視其規范化和修辭性。如初刊本第一章中:警察又用膝蓋頂他的尾骨,催促他向前走,他轉回身,望著警察的臉……[2]在初版本中則為:警察又用膝蓋頂他的尾骨,催促他向前走。他轉回身,望著警察的臉……[3]初刊本版中的逗號在初版本中變為句號,使標點符號的使用更為規范,避免了在一個句號內擠了兩句話的問題。同時,標點的修改也體現出某種修辭性,如初刊本中第三章中四嬸的哭訴“老頭子啊你好狠心,一個人撇下我就走了,你顯神顯靈把我叫了去吧,我的天——”,在初版本中就被刪掉了三個逗號,從而更有力地表現出人物內心噴薄而出的悲痛之情。
另一方面,如初刊本第二章中的“吭吃”[4]變為初版本中的“吭哧”[5],初刊本的敘述話語和人物話語中多處“啦”字變為“了”字,如初刊本中:
四叔用鼻子哼了一聲,四嬸不冷不熱地說:“才吃,你吃啦。”
高馬說吃啦。這時四嬸惡聲惡氣地吩咐金菊點燈。[6]
初版本中則為:
四叔用鼻子哼了一聲,四嬸不冷不熱地說:“才吃,你吃了?”
高馬說吃了。這時四嬸惡聲惡氣地吩咐金菊點燈。[7]
這體現出,在字詞的使用上,作者試圖使其更加規范化,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弱小說的方言化程度的修改意圖。此外,字詞的修改也都關乎小說的修辭作用。如初刊本第一章中有“簌簌噴射的聲音”[8],在初版本中被改為“簌簌的噴射聲”[9],這樣一來,就和后文的“汩汩的流動聲”形成對仗,增添了小說在字句上的美感。
再次,關于環境描寫和人物塑造的更加細膩。初版本相比初刊本新增了許多環境描寫,有自然環境,也有社會環境:初刊版第一章中的一句“天空和大地之間游走著混濁的塵埃”[10]自然環境描寫,在初版本中被擴展為“久旱無雨,天空和大地之間游走著混濁的塵埃,彌漫著腐爛蒜薹的臭氣。一群藍色的烏鴉疲憊地從院子上空掠過,地上閃過灰淡的陰影”[11];初刊版第二章中,在高馬被楊助理關在門外后,作者直接描寫了他在家中的情景,而在初版本中則有一大段高馬從鄉政府大院回家路上的社會環境描寫,其中描繪了馬路邊賣西瓜的老人等。初版本細膩的環境描寫增加了小說的文學性,而適度拉開了小說虛構與真實本事之間的距離。
人物塑造方面,初版本也要比初刊本更為細膩和豐富。初刊本第二章在表現金菊和高馬第一次談話時時,對金菊的心理表現較為簡單,一經高馬說出“你并不情愿”[12],她立馬就“嗚咽”了,而初版本中則增添了金菊內心個人情感與家庭責任之間的矛盾沖突,在高馬說出她“不情愿”與她“嗚咽”之間,有她違背內心意愿說出的話:
金菊用另一只手使勁剝開高馬的手,把那只捏扁了的手抽出來,說:“我情愿。”
“你不情愿,劉勝利四十五歲了,還有氣管炎,連擔水都挑不了,你愿意嫁給個棺材瓤子?”[13]
這一段金菊違背內心意愿說出“我情愿”的描寫,顯露了其內心的個人情感和家庭責任間的矛盾沖突,對人物的心理描寫更為立體。由此,金菊這個人物也就被塑造得更加豐滿與真實。
再次,在立場上,初版本對于小說的民間色彩和民間趣味進行強化。這集中表現在初版本的第十七章。初刊本共十九個章節,而初版本則有二十個章節。其中初版本的第十七章,不管是章節前的一段民間藝人張扣鼓舞群眾抗旱的歌謠詞,還是在澆水空歇期間王老頭給高馬講的一個民間故事,都是初刊本中所沒有的。這一部分的增加,一方面是對初刊本只突出農民賣蒜薹的艱辛,而不涉及種蒜薹勞累的補充;另一方面,出版本中新增的張扣唱的歌謠詞和王老頭講述的民間傳奇故事,都與農民的勞動生活緊密地結合在一處,這在增添了小說的民間文化的趣味性和神秘性的同時,也更加強化了小說的民間立場。
二.從初版本到修改本
從初版本到修改本的修改,大致堅持了初刊本到初版本的修改方向,削弱政治性,增加文學性。其變化有以下幾點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小說題目與題記的變更。題目從初版本的“天堂蒜薹之歌”變為修改本的“憤怒的蒜薹”,一方面鮮明地表達了作者同情農民、憤恨不公的社會制度與貪官污吏的的情感傾向;另一方面與美國現代小說家約翰·斯坦貝克描寫美國三十年代“經濟大危機”時期大量農民破產、流亡的小說《憤怒的葡萄》形成潛在的互文性關系。這都暗示著修改本的情感可能比初版本更加激烈和深廣。題記內容的變更也值得注意。在初版本中,題記為:
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說家總是想關心“人的命運”,卻忘了關心自己的命運。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
——名人語錄[14]
修改版中題記則完全改變:
高密東北鄉
生我養我的地方
盡管你讓我飽受苦難
我還是為你泣血歌唱
——作者題記[15]
我們可以看到,題記的內容完全改變,署名也從“名人語錄”到“作者題記”。初版本的題記,努力闡述“小說家—政治—小說”三者之間的關系;而修改本中的題記則淡化了從小說的政治性,緊緊圍繞著“高密東北鄉”展開,“作者”和其“歌唱”都離不開“東北高密鄉”的鄉土性。
第二,修改本中,作者在修改后做了自序,這是初刊本與初版本中所無的。在自序中,莫言介紹此書創作的一點背景和經過:“我原先不相信一邊寫小說一邊熱淚涌出的事,但寫出這部小說時我鼻子很酸過幾次。因為小說中的人物的遭際能讓我想到我的親人。”也自述了創作意圖,即“寫這樣的小說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小說中描述的現象在現實生活中再也找不到樣板”[16]。莫言的夫子自道更加直接也更加明晰地表達了這部小說與現實的緊密關系,同時也讓讀者看到作家面對社會不公的“良知”。
第三,對瞎子張扣的歌謠詞的修改與增加。較之初版本,修改本對第一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的開頭歌謠詞都有所修改。初版本中,以上三章的開頭張扣所唱的歌謠詞分別為:
尊一聲眾鄉親細聽端詳
小張扣表一表人間天堂
大漢朝劉皇帝開國立縣
敕令俺一縣人種蒜貢皇
——天堂縣瞎子張扣演唱的歌謠[17]
縣長你手大捂不住天
書記你權重重不過山
天堂縣丑事遮不住
人民群眾都有眼
——張扣受審時歌唱斷章[18]
唱的是八七年五月間
天堂縣發了大案件
十路警察齊出動
逮捕了群眾一百零三
要問這案緣和由
先讓俺抽您一支高級煙
抽了香煙俺也不開口
送一張《群眾日報》您自己看
——瞎子張扣對本書作者演唱片段[19]
在修改本中,則分別為:
一聲眾鄉親細聽端詳
張扣俺表一表人間天堂
肥沃的良田二十萬畝
清清的河水嘩嘩流淌
養育過美女俊男千千萬
白汁兒蒜薹天下名揚
——天堂縣瞎子張扣演唱的歌謠[20]
縣長你手大捂不住天
書記你權重重不過山
天堂縣丑事遮不住
人民群眾都有眼……
——張扣唱到這里,一位虎背熊腰的警察忍無可忍地跳起來,罵道:“瞎種,你是‘天堂蒜薹案'的頭號罪犯。老子不信制服不了你!”他跳起來,一腳踢中了張扣的嘴巴。張扣的歌聲戛然而止。一股血水噴出來,幾顆雪白的牙齒落在了審訊室的地板上。張扣摸索著坐起來,警察又是一腳,將他放平在地。他的嘴里依然嗚嚕著,那是一些雖然模糊不清但令警察們膽戰心驚的話。警察抬腳還要踢時,被一位政府官員止住了。一個戴眼鏡的警察蹲在張扣身邊,用透明的膠紙牢牢地封住了他嘴巴……[21]
唱的是八七年五月間
天堂縣發了大案件
十路警察齊出動
逮捕了群眾一百零三
要問這案緣和由
先讓俺抽您一支高級煙
抽了香煙俺也不開口
送一張《群眾日報》您自己看
——瞎子張扣的徒弟對本書作者演唱片段[22]
我們可以看到修改本中的歌謠詞的敘事性明顯增強,去除了小說中心事件相隔太遠的“大漢國劉皇帝開國立縣”等歌詞,增加了張扣被警察毒打的描寫。此外,在修改本的第十六章蒜農大鬧縣政府的情節中,作者也特意加入了張扣的一段具有控訴性、煽動性的歌謠以及聽眾對其歌謠的反應:
……可憐那忠厚老實的方老漢,就這樣一命赴黃泉。一把把蒜薹被血染,一陣陣哭聲驚破了天。天啊天,老天爺你為什么不睜眼,看一看這些橫行霸道的閻羅官……
……聽眾的臉扭曲著,眼睛閃爍著光芒,好像一簇簇火苗在暗夜里燃燒。……
他的喉嚨沙啞了。有人遞給他一塊冰棍,他用干裂的嘴嘬嘬冰棍,清清嗓子,又唱起來。一個衣冠燦燦的青年,舉著一個小錄音機,對著他的嘴巴。[23]
以上修改不僅更多地展現了小說的民間趣味和民間立場,還使瞎子張扣從一個旁觀者、記錄者身份的民間藝人,變成了整個蒜薹事件參與者、組織者,甚至并為此犧牲的英雄人物形象。張扣的歌謠詞、張扣的形象與蒜薹事件的結合變得更加緊密,換句話說,也就是小說的結構變得更為緊密了。
三.從修改本到再改本
相比修改本,再改本也有一些新變化。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修改:一是新的自序;二是再改本中新增了一個章節,即第二十章,由此引起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開頭的歌謠詞的修改;三是在新增的章節中,對張扣和高馬的悲劇結局的書寫。
第一,再改版有作者新作的自序。在自序中,莫言交代了小說的本事,解釋了有關初刊本的題記杜撰了“斯大林語錄”的事。他回顧上世紀八十年代《天堂蒜薹之歌》創作的時代背景:“創作是個性化的勞動,是作家內心痛苦的宣泄,這樣的認識,一時幾乎成為大家的共識”。同時他也指出,書中很多人物都是以他所熟悉的家鄉的父老鄉親為原型的,如“書中那位慘死在鄉鎮小官僚車輪下的四叔,就是以我的四叔為原型的”[24]。
第二,關于章節的增加和歌謠詞的修改。小說由修改本中的二十章,變為再改本中的二十一章,其中再改本中的第二十章的內容是修改本所無的。因為再改本章節內容的變動,致使第二十章和二十一章的歌謠詞也有相應的修改。修改本中的第二十章的歌謠詞,上文已有過討論,現將再改本中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歌謠詞列出如下:
唱的是八七年五月間
天堂縣發了大案件
十路警察齊出動
逮捕了百姓九十三
死的死,判的判
老百姓何日見青天
——張扣在縣政府西側斜街演唱[25]
蒜薹事件眾口傳
誰是誰非真難辨
俺師傅多言招禍殃
這樣的錯誤俺不再犯
讓俺抽您一支高級煙
送一張《群眾日報》您自己看
——瞎子張扣的徒弟對本書作者演唱片段[26]
相比修改本從瞎子張扣唱歌謠詞沒有交代地直接過度到張扣的徒弟唱,再改本中的歌謠詞中多了徒弟對師父“遭禍殃”的結局的明確交代與引以為戒。實際上,這也與再改本已在第二十章明確交代過張扣的壯烈犧牲相映照。
第三,對張扣和高馬的悲劇結局的書寫。這兩個人物的結局,在再改本以前沒有過交代,直到再改本中才有相關書寫。關于張扣,再改本沿著修改本的思路繼續深化張扣的英雄形象,在第二十章中描繪了他遭到迫害之前的堅持正義的剛強表現,以及他被暗害身亡的悲慘場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張扣歌唱時和他被暗害之后,他都得到了許多人的擁護、幫助與同情。其中不僅有老人、年輕人和女老板,甚至一群小偷、乞丐、下三濫們都對張扣的死表現出莫大的悲哀。民間與官方的對立,在再改本中無疑顯得更大了。
主人公高馬的結局,也是在再改本中才得到明確交代。在再改版的第二十章,小說先描寫了審判后高馬在獄中的表現,又敘述了他得知曹家要與金菊結陰親的消息后,試圖逃獄而被槍殺的悲慘結局。這樣的結局在完成悲劇人物塑造的同時,無疑也增添了小說的浪漫色彩和悲劇氛圍。
綜上,《天堂蒜薹之歌》這部小說從初刊本到初版本、從初版本到修改本,再從修改本到再改本的修改過程中,作者堅持提高小說文學性的原則,去政治化,雕琢字句,完善結構,著力塑造鮮明的人物形象,增添小說的民間文化、民間趣味和浪漫色彩。從文學性的角度來看,我們無疑可以說莫言對這部小說的修改是成功的。
參考文獻
[1][2][4][6][8][10][12]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十月》,1988年第1期,第156—157、137、146、146、137、136、144頁。
[3][5][7][9][11][13][14][17][18][19]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4、32、30、3、1、26、名人語錄、1、272、287頁。
[15][16][20][21][22][23]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作者題記、序、第1、251、265、217頁。
[24][25][26]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序、第256、269頁。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